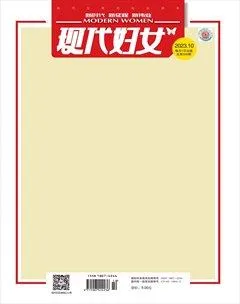不為“社恐”遮望眼,獨樂眾樂俱歡顏

那天朋友圈里小米說自己“社恐”,我“啊”了一聲。女友小米在重慶有一家叫“米牧”的服裝品牌店,設計、裁剪、制作、銷售一條龍,重慶女友經常在她那個小小的縫紉店里,搞一些讀書、觀影之類的活動。小米像一朵羞答答的太陽花,不動聲色地忙這忙那,笑意寫在臉上。
如果連小米都是“社恐”,那我也算吧。那一刻突然想起最近閨蜜兩次請我去看他們系統投拍的雜技劇,那次還說看完劇要跟主創人員一起吃飯,還有一位河南老鄉,而兩次我都一口拒絕了。
我是不是“社恐”?也許是。因為我越來越喜歡一個人待著,或者獨自玩耍。只要放下工作,眼里所見、耳邊所聽都可以是我的玩物。這些年尤其不喜歡大聚會,即使朋友間的小聚,如果沒有共同感興趣的話題,也懶得參加。
年輕時特別愛湊熱鬧,很羨慕那些在任何場合都能呼風喚雨、左右逢源的人,如今他們有個名字叫“社牛”。但是隨著年齡的增加以及自我閱歷的深入,已不再葉公好龍。“明確的愛,直接的厭惡,真誠的喜歡,站在太陽下的坦蕩,大聲無愧地稱贊自己。”黃永玉老先生的這句話,是我目前的心態與狀態。
反思那些年:“社交”是萬金油,“人脈”是行走的名片
記得那年老公的大哥生病住院,我們去探望,肝癌晚期的他拖著瘦弱的身體,指著我正上大學的兒子說:“你不愛說話不行,男人要在社會上闖蕩,要會社交……”我心里“呵呵”。大哥正是每天跟那幫江湖兄弟胡吃海喝,酗酒把身體搞垮了。記得有一年春節我們回老家,只有剛到家時匆匆一見,后面幾天他都在應酬。
我有個女友,兒子有海外留學背景,在北京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孩子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在出租屋里刷劇、玩游戲,很少交朋友和社交。女友就總說兒子不陽光、不正常,懷疑有抑郁癥。有一次她帶著兒子來我們家,我一看,在她嘴里有抑郁傾向的兒子,高大帥氣陽光,談吐也很好。我說:“這哪里有病啊?簡直太健康了。”女友對我的判斷深表懷疑,她說:“你是外行,要讓劉大夫看看。”劉大夫是我先生,精神科醫生。那天,女友說再給兒子兩年時間,如果還是這樣頹廢,就回老家去。
其實,女友的問題也是我們很多家長的問題。認為孩子如果不善交際,就在社會上邁不開步。這和我們這一代所經歷的“人情社會”有關。彼時,熟人是一種資源,沒有人脈則寸步難行,不會社交等于無能。
可是,如今早已進入智能化、云社交的時代。實話說,有段時間我也說過兒子“溝通”有問題,他則義正詞嚴反駁我道:“我沒問題。”后來我發現他在網上給人講課,頭頭是道,找工作也是一路順暢,這才想到:也許是自己落伍了。
我步入社會時,正值改革開放的20世紀80年代末,那時“社交”是萬金油、“人脈”是行走的名片。所以我年輕時一度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最大弱項是不會搞關系。而反思那些年,正是因為自己不會搞關系,所以大部分時間都致力于自己喜歡的事情。而隨著日漸成熟,驀然回首才發現:“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顯然,如今社交已不是孩子們的必修課,升級版本的“社交”是——反求諸己。打鐵還需自身硬,做更好的自己,“執于一而萬事畢”。
一面是“社恐”泛濫,一面是“搭子社交”流行
今年春節假期,我們一家3口去南京,老公的大學同學在朋友圈發現他的行蹤,非要請吃飯,我兒子堅決不去。其實,我打心眼里也不想去,但是礙于情面還是去了。坐在豪華餐桌前,望著將近20來個陌生面孔,我就后悔了。
我倒是很為孩子們高興,他們在“做自己”這件事上更清醒也更勇敢。我總覺得年輕人“社恐”與我們那些年cYbnrN4mmGla8d06nc14GA==過度強調社交與人脈的作用有關。
華東政法大學杜素娟教授認為,被泛化的“社恐”,其實是年輕人的一種防御與抵抗。大部分人可能只是內向、不合群,就把自己歸類為“社恐”。如今“社恐”被泛化使用了,它的外延被無限擴大了。就像“躺平”是對“卷”的防御“,社恐”可能是對“過度社交”的抵抗。當“社交無力”和“社交疲憊”成為通病,年輕人最終外顯為“社恐”的模樣。

其實據我觀察,兒子的社交圈少而精。有中學、大學、研究生的同學圈子,有踢球球友的圈子,有同事圈子,好像沒有刻意去迎合某些圈子,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樣子。
也許說“圈子”都落伍了,最流行的說法是“搭子”。比如“飯搭子”“旅游搭子”“考研搭子”“游戲搭子”“運動搭子”“攝影搭子”等,“搭子社交”在年輕群體中日漸流行。這種效率高、成本低的新型社交關系,主打“垂直領域”與“精準陪伴”,更在乎三觀以及興趣的契合度。如果說,消滅孤獨是關于社交的最初愿景,那么找到同類、共同追夢則是當下年輕人的社交高級形式。
其實,每個人性格不同,對于社交的需求、處理方式也不盡相同。那種“社交人脈”獨行天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愿我們所有的人,不畏浮云遮望眼,無論“獨樂樂”還是“眾樂樂”,俱歡顏。
(摘自《中國婦女報》)(責任編輯 史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