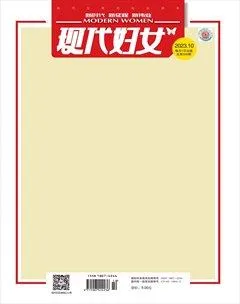純潔的惦念
那天,我照例沒(méi)有午休,作為廠長(zhǎng)秘書(shū)的我獨(dú)自在辦公室值守。那臺(tái)落地式電風(fēng)扇有氣無(wú)力地左右擺動(dòng),吹著并不能解暑的熱風(fēng)。
我將頭仰靠在椅背上閉目養(yǎng)神。恍惚間,有人敲了兩下實(shí)際敞開(kāi)著的屋門(mén)。“你好!”一位女孩笑盈盈地站在門(mén)口,“借用一下電話(huà)……”“請(qǐng)進(jìn)!”我忙不迭地答應(yīng)并詢(xún)問(wèn)著,“是哪個(gè)車(chē)間的?”廠里將近千人,而女工居多,我不可能都認(rèn)識(shí),因此以為是某車(chē)間的女工。“呵?不是……我是南邊高中的學(xué)生。”“噢!我還以為是同事呢,原來(lái)是校友……”由工廠南行1里多遠(yuǎn)的那所高中曾是我3年前畢業(yè)的母校。“你也是從我們學(xué)校畢業(yè)的?”女孩略帶驚詫地睜大眼睛。此時(shí),我才打量了一下她:淡黃色連衣裙,苗條挺拔的身材,淺白色涼鞋配黑色網(wǎng)襪,烏黑的頭發(fā)梳成一條過(guò)肩的馬尾,白皙透著紅潤(rùn)的臉龐上掛著清純的笑容,是個(gè)潔凈雅致的女孩。我的目光一掃而過(guò),因?yàn)樗枷胧冀K比較守舊,從未有長(zhǎng)時(shí)間盯著某個(gè)女生看的習(xí)慣。盡管此時(shí)我僅24歲,正值朝氣飛揚(yáng)、飄逸粲然的年華。
通過(guò)她給家里打電話(huà)以及與我的幾句攀談,得知她家在離此10多里的喑牛淀,因交通不便而住校;同時(shí)確認(rèn)是低我三屆的高中校友。不敢問(wèn)她的姓名,當(dāng)時(shí)我是那么鈍拙而靦腆。“你在這兒工作真好!”從她誠(chéng)懇的語(yǔ)氣中聽(tīng)不到假意恭維。“有啥好的?還是要好好上學(xué),考上大學(xué),才有更好的前途。”我認(rèn)真地回應(yīng)著。臨走時(shí),她笑著向我道謝:“在學(xué)校教導(dǎo)處打電話(huà)太拘束,還是來(lái)這里打更隨便,還認(rèn)識(shí)了你這位校友。”送她到廠門(mén)口,她閃著澄澈的眸子向我揮手:“校友再見(jiàn)!”我站立在原地,伸展了一下臂膀。在這悶熱的暑氣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絲少有的舒爽。
第二次見(jiàn)面,是當(dāng)年初冬的一個(gè)傍晚。我們騎自行車(chē)走同一條馬路。“校友好!”她從后面趕上來(lái)喊我。她穿著長(zhǎng)長(zhǎng)的風(fēng)衣并圍著厚厚的圍巾,但那獨(dú)特的嗓音和明亮的笑眸讓我馬上確認(rèn)。“咋不在學(xué)校住著,要回家呀?”“對(duì)!正好是回家周。”她笑著回答。“學(xué)習(xí)更緊張了吧?趁著回家好好歇歇吧……”除了講學(xué)習(xí),我扯不出更合適的話(huà)題。“還有半年就高考了,大伙都在熬,我基本沒(méi)戲。考不上,就去找你這位校友,幫我找份工作。”她一副很認(rèn)真的態(tài)度。“上大學(xué)才是正路。”我重復(fù)著第一次見(jiàn)面的觀點(diǎn)。她沒(méi)有吭聲,只是對(duì)著我笑。“語(yǔ)文老師說(shuō)你挺有文采。你的作文還給我們讀過(guò)。你也算是咱校出來(lái)的名人……”“你咋知道我的名字?”“和老師打聽(tīng)的呀!”她爽朗地笑出聲來(lái)。看來(lái)我在明處她在暗啊!冬日的夜色降臨很快,但我看到她的笑顏是那么燦爛。臨到分開(kāi)的十字路口,她對(duì)我大聲喊:“校友再見(jiàn)!”呼嘯的北風(fēng)中,我感到一股難得的暖意。

先后兩次見(jiàn)面,發(fā)生在我們年輕的1992年。
次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了她的來(lái)信,大意如下:感謝學(xué)兄對(duì)我學(xué)習(xí)的鼓勵(lì)。但如果高考失利,一定請(qǐng)幫忙,找份可以由高中生來(lái)干的工作。落款沒(méi)有名字,只有“校友”兩個(gè)字。信封和信紙上的字跡都那么清新雋秀,令我這個(gè)寫(xiě)字的人喜歡。我也想過(guò)回信,但除了知道她家在范圍不小的喑牛淀,其他信息未知,只有望信興嘆,等待她某一天突然出現(xiàn)。
盡管一別30年,盡管往事渺如煙,兩次見(jiàn)面的片段偶爾仍會(huì)在眼前浮現(xiàn)。其實(shí),也并非奢望與她再次見(jiàn)面,只有發(fā)自心底純真圣潔的良愿:唯愿叫不上名字的她笑顏依舊、幸福平安!
(摘自《海外文摘·文學(xué)版》)(責(zé)任編輯 辛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