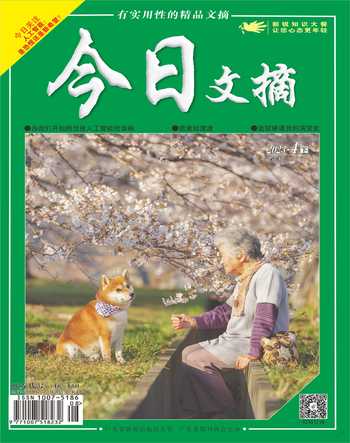住在這座城,每天都要出國1萬次

剛走出家門,一腳就踏到另一個國家,是怎樣的體驗?歐洲巴勒小鎮的居民最有發言權。這塊土地的面積還沒有廣州天河區大,卻分屬于不同兩國,而且不是簡單地一分為二,而是一大塊中包含了零零散散的33塊碎片。其中26塊屬于比利時,叫做巴勒-黑托克;另外7塊是飛地中的飛地,屬于荷蘭,叫巴勒-拿騷。因此,巴勒鎮的地上畫滿了國境線,經常走上幾步就能出國,還能左腳踩荷蘭、右腳踏比利時地反復橫跳。這個小鎮,于是成了歐洲著名的“飛地小鎮”。
所謂飛地,就是指屬于某個行政區管轄但不與其主體接壤的地方。比如,阿拉斯加就是美國最著名的飛地。而巴勒小鎮上的荷比領土,或是零散分布,或是互相嵌套,形成了“飛地套娃”的獨特景象。
大量的飛地雖然給兩國政府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難,但巴勒鎮特有的情況也讓這里的居民擁有了獨一無二的生活方式。
由于比利時和荷蘭的法律不盡相同,個別巴勒鎮的居民便打起了法律的“擦邊球”,他們運用得天獨厚的優勢隨時跨越國界進入另一個國家,雖然這些跨界行為無非是從一棟樓進入另一棟樓、從這條大街走到另一條大街。
比如荷蘭的乳畜業發達,乳酪價格低廉。比利時制定了較高的關稅以保護本國的乳業,這條法律規定卻讓巴勒鎮的荷蘭人與比利時人看到了“商機”。荷蘭人把乳酪攤位擺到距離邊境長度不足10米的地方,比利時人“不經意”地跨過邊境購買乳酪。
對于鎮上居民的國籍,比利時和荷蘭采取了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居民的家門口朝向哪個國家的領土,那么他的國籍就屬于哪國。如果有居民的家門口正好朝向他不想加入的那個國家,只需要在他想加入的那國一側再開一扇門就行了。
據說,有不少人用類似方法選擇賦稅更低的國家作為居住地,以此降低家庭的財政壓力。
為了加強人員管控,降低走私犯罪的發生率,每戶居民的門前都必須插上本國國旗以表明身份。這里的國境線不是由高墻和鐵絲網組成,有的只是地面上標注的邊境線,一邊寫著字母“NL”代表荷蘭,一邊寫著字母“B”代表比利時。
在看不到國境線的地方,可以參考建筑物門牌,它們使用的是各自國旗的顏色。不少當地居民也會在陽臺或房頂懸掛國旗,以表明身份。
20世紀90年代,比利時和荷蘭放棄了交換領土的想法,尊重鎮上兩國居民的意見,根據原始地契明確鎮上每一寸領土的具體歸屬。由于使用原始地契作為確認領土歸屬的依據,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由于歷史變遷,原有地契上的建筑早已改變,同一座建筑很有可能橫跨兩國。有的住戶廚房在荷蘭,衛生間在比利時;有的住戶床頭在比利時,床尾在荷蘭。
居民朱利安·李曼斯的家在巴勒鎮的邊境線上,他說:“房子的90%是荷蘭的;10%,也就是廁所,是比利時的。”但由于房屋的大門在比利時這邊,所以他成了比利時居民,即使他在荷蘭出生和長大。
甚至有的電影院也是兩國各占一半,這樣的安排也給居民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好處。由于兩國審查方式不同,總會有一些電影在本國無法過審或是推遲上映,但巴勒鎮的居民卻可以在不越境的情況下通過掛在幾米開外對方國境內的銀幕,看到本國看不到的電影。
當然凡事有利必有弊,復雜的邊界也給生活在這里的居民造成了一些困擾。橫跨兩國的建筑里如果有工廠,那么工廠必須要根據每名工人站立的工位實行所在國的勞動法。
如果你身在比利時巴勒,打算寄信到街對面的荷蘭巴勒,那么這封信可不會是過個馬路那么簡單。它將被送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再轉到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經層層轉寄,最后才能回到相距不到50米的街對面。
為了方便管理,荷蘭與比利時的政府在同一座建筑內辦公,國境線剛好從建筑中間穿過;兩國警察也共用一棟警局,只不過分別出警解決自己國家轄區內的案件。
如今的巴勒鎮上,比利時和荷蘭的居民生活井然有序,荷蘭方面為城市提供燃氣和自來水,比利時方面負責城市中心的電力供應,兩國輪流為居民提供垃圾運輸等市政服務。
隨著歐盟一體化不斷加深,同屬歐盟的比利時與荷蘭也逐步淡化了國籍觀念,這一點在巴勒鎮體現得尤為明顯,小鎮的居民也認識到了自身的獨特性,并借此發展出了特色旅游業。
分屬兩個國家的居民打破了國界的藩籬,和諧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雖然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情,但巴勒鎮的實踐經驗為世界上一些戰火紛飛的地區提供了借鑒,你死我活并非唯一的選項,和諧共處也將成為可行的模式。
(沈陽煦薦自《新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