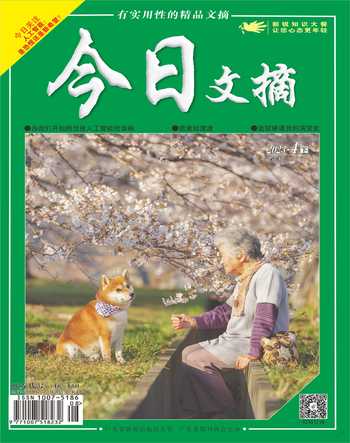春兒
有一次,我路過(guò)一條寂靜的小街,在拐彎處碰到一家不大的百貨店正搞熱賣促銷活動(dòng),便不由得停住了腳步。然而,讓我止步留戀的并非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商品,而是一句話:女士們、先生們,進(jìn)來(lái)看一看、瞧一瞧,走過(guò)路過(guò),不要錯(cuò)過(guò)……是的,走過(guò)路過(guò)不要錯(cuò)過(guò)。可更多的時(shí)候,我走過(guò)路過(guò)卻還是錯(cuò)過(guò)。
剛從技校畢業(yè)那年,我去一個(gè)離家十幾里地的沙場(chǎng)挖河沙,來(lái)回要經(jīng)過(guò)一家餐館,開(kāi)餐館的是父女倆。有時(shí),我也進(jìn)去歇歇腳,要點(diǎn)面條、米粉充饑。時(shí)間長(zhǎng)了,我才知道餐館里的女孩叫春兒,比自己大三歲。
我干的是體力活,食量大得驚人,春兒常常會(huì)背著父親多給出我一份,卻堅(jiān)持只收一份的錢。雖然她算不上美麗,但是有一種很清純的溫柔,看我的時(shí)候,眼睛里似乎有一種異樣的東西在游動(dòng),這讓我的心迷亂而不平靜。
秋天過(guò)了一半,天忽然冷下來(lái),我晚上回家的時(shí)候感到絲絲寒意,于是決定去餐館喝杯米酒暖暖身子。幫我酒杯斟滿酒后,春兒進(jìn)屋里意外地拿出一雙布鞋,紅著臉沖我說(shuō):“穿上它吧!專門給你做的。”
長(zhǎng)這么大,從來(lái)沒(méi)有異性朋友如此關(guān)心、體貼過(guò)自己,我心頭一熱,順從地穿上了暖和舒適的布棉鞋。也是從那天起,我對(duì)春兒產(chǎn)生了一種說(shuō)不清道不明的感覺(jué),或者,這就叫“愛(ài)情”的前兆吧!
日子一天天流逝,我對(duì)春兒的“感覺(jué)”依然停留在“前兆”里,總覺(jué)得一個(gè)挖沙工是不該奢望享有愛(ài)情的,雖然知道春兒的心意,但卻始終沒(méi)有勇氣向她表白。直到一天,春兒說(shuō)她要與別人結(jié)婚了我才大吃一驚。
那天,接送新娘的禮儀車在喧鬧的鑼鼓聲中開(kāi)動(dòng),車輪穿過(guò)小街,也碾碎了我的心。
次年冬天,沙場(chǎng)放假了,我閑來(lái)無(wú)事,便自告奮勇地跟隨老板駕駛一艘破舊的敞篷小船去河對(duì)岸打魚(yú)。小船行駛到河中央,我隱隱約約看見(jiàn)遠(yuǎn)處的水草里躺了一個(gè)穿著紅色衣服的女人,形態(tài)居然跟春兒幾分相似,等船近了些,我急忙脫掉衣服要跳下去救人,說(shuō)時(shí)遲那時(shí)快,老板一把攔住我,問(wèn)我是不是中邪了,那根本不是人,而是條紅鯉魚(yú)。我愣了一下,驚出一身冷汗。老板一網(wǎng)撒下去,把那條被水草纏住動(dòng)彈不得的大紅鯉魚(yú)撈了上來(lái),足足十幾斤。
不久,一個(gè)壞消息傳來(lái),身懷六甲的春兒在河邊洗衣服時(shí),一不小心滑進(jìn)河里去了,等救援的鄉(xiāng)親趕來(lái),她人已飄到河中央的水草堆里,變成了冰涼的尸體。
那段時(shí)間,我常常去餐館喝悶酒。有次喝醉了,我邊用頭撞桌子,邊對(duì)春兒爹說(shuō),“大叔,我和老板去河對(duì)岸打魚(yú),早看見(jiàn)了春兒的魂了,當(dāng)時(shí)就應(yīng)該來(lái)告訴你!”
春兒爹老淚縱橫,說(shuō),這怎么能怨你,這是她的命呢!
后來(lái),我仍然時(shí)常想念春兒,她的身影時(shí)常走進(jìn)我的夢(mèng)里,始終如一地溫暖著我堅(jiān)硬的心。
(周睿聰薦自《遼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