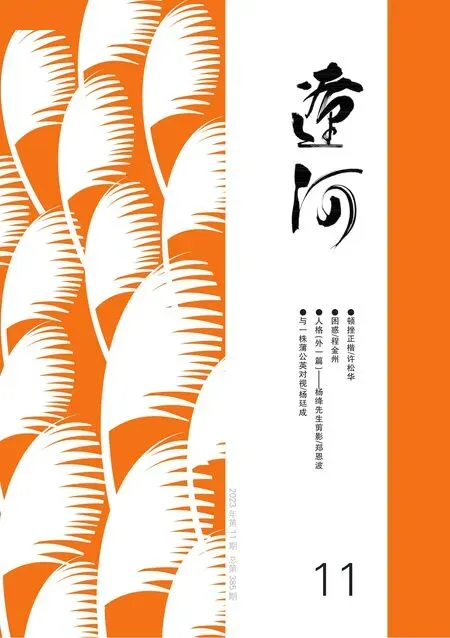收音機情結
馬建華
或許,每個人都有自己鐘愛一生的物品。 比如,某種牌子的手表、某種牌子的鋼筆、某種牌子的相機等。
而我鐘愛收音機。
我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接觸到收音機的。
當時,我大約五六歲,住在重慶市南岸區。 街上幾乎每家都安裝了有線廣播小喇叭。 大街上的特定地點還安裝了高音大喇叭。 區廣播站每天分早、中、晚三個時間段定時播放節目。 每次播放節目的時間大約是一兩個小時。
那時,人們主要是通過收聽廣播節目了解外界的信息和國家大事。
父母聽廣播時,有時候,我也坐在旁邊聽。
雖然我年齡小, 很多節目聽不懂,但是通過收聽廣播我學會了一些歌曲,比如《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是公社小社員》《讓我們蕩起雙槳》等。
我有個高中同學的長輩是馬來西亞華僑。 這個長輩在經濟方面給了他家不少幫助,他家的生活條件比其他同學家好。
我們得知他家買了收音機時,幾個同學好奇地一起去他家里看。 收音機用綢緞蓋著,如同珍寶。 他不讓我們觸碰收音機。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收音機,真想用手摸一下。
我家有收音機是在1976 年。 那時,我父親在工廠里當領導,他們單位剛開始生產收音機,收音機是“山城”牌的。因為生產技術不先進, 生產數量少,工廠為了照顧本系統職工,給本系統職工發了購買收音機的優惠券。
高中畢業后, 我回老家當了知青。休假回家探親時,我看見父親買了一臺收音機。 這臺收音機一尺多長,半尺寬,聲音響亮。 我天天擺弄收音機。 假期結束時,我想把收音機帶到鄉下,父親不同意。父親說:“你的兩個弟弟也想聽。”母親說:“讓建華帶走吧。 他喜歡學習,一個人在農村孤單……”
收音機在城里是稀罕物品,在鄉下更成了寶貝。 自從我有了收音機,經常有小孩圍著我。 他們露出驚奇的目光,有個小孩用手摸著,天真地問:“里面有人嗎? ”
有一天,隔壁劉叔家的小孩牛兒不小心碰翻了板凳,收音機從板凳上摔在地上,沒有了聲音。 我急忙撿起收音機,可收音機的塑料殼摔破了,喇叭掉了出來。 劉叔急忙跑過來向我說對不起,不停地訓斥牛兒。 我說:“壞就壞了,沒事的,他又不是故意的。 ”劉叔第二天送給我兩只雞,說是賠償被弄壞的收音機的損失。
我去趕集時,找人把收音機的喇叭線焊接上。 收音機又響了。 收音機的殼沒辦法修復,我用細電線把收音機捆綁上,雖然外觀有點兒難看,但是還能正常收聽節目。
我經常拎著收音機,邊走邊收聽節目,周圍人都投來羨慕的目光。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雖有些傻氣,可在當時覺得挺好。 村民有人家娶媳婦請我去作客時,還叮囑說:“一定把收音機帶來哦。 ”
②加強示范區建設。借鑒歐盟經驗,對一些重大技術難題,如降雨——徑流分析、臨界預警指標的確定方法、預警信息發布等,宜選擇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特征的小流域,建立山洪災害防治小流域示范區,開展專項研究,并作為一項長期任務持續開展下去。通過不斷探索,提出上述重大技術難題的解決方案,完善后向全國推廣。
大約在一年后,有一次,我和幾個知青去幾十里外的東溫泉洗露天澡。 當我洗完澡時,發現裝收音機的布口袋不見了。 我找了好一陣子也沒找到。 知青謝志遠忽然說:“水里有你的衣服! ”
我一看是裝收音機的布口袋,不知道什么時候掉水里了。 我急忙跳進水里去撈。 收音機被水泡后,報廢了。
結束知青生活,返城后,我在皮革機械廠當工人。
那時, 我每個月的工資是二十塊錢。 我留五塊零花錢,剩下的交給母親。我省吃儉用,湊足了十幾塊錢,買了一臺比先前那臺小一點兒的 “海燕牌”二手收音機。 幾年后,我漲了幾次工資,我就又買了臺“東方紅”牌二手收音機。
有一段日子,我每天定時收聽錢鋼創作的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連播。 我聽得津津有味,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對文學創作萌生了興趣。
我結婚時,舊收音機不能正常收聽節目了,就花了一百多塊錢買了一臺新收音機。 新收音機的聲音效果好,收聽節目時的感覺也好很多。
我不是為了面子, 而是為了學習。當時,我通過收聽中央廣播電臺播的課程,取得了本科文憑。 單位在我取得大學本科文憑后, 給我加了一級工資,還把我從工人轉成了干部。
改革開放后, 我離開了原單位,到另一家單位做起了采購和銷售工作。 我經常出差,那時主要是乘坐汽車和輪船出行,路程短的需要幾個小時,路程長的需要好幾天。 為防止影響到其他乘客,我又買了一臺帶耳機的收音機。 這種收音機體積小,方便攜帶。 我每次到外地出差,都把這臺收音機放在包里。
隨著時代發展, 人們生活水平提高,電視機涌入到尋常百姓家。 電視機搶占了收音機的位置,人們不再那么需要收音機了。
但是,我聽收音機的習慣依然沒有改變。 無論在陽臺上曬太陽,還是在小區里散步,或是外出游玩,我都帶著收音機。
收音機能把零碎的時間充分利用到學習和了解外界信息上。
歲月悠悠, 路漫漫, 人生能有幾多情? 我鐘情于收音機,我從收音機里的節目中獲取了知識、 愉悅……我感覺聽收音機讓生活變得非常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