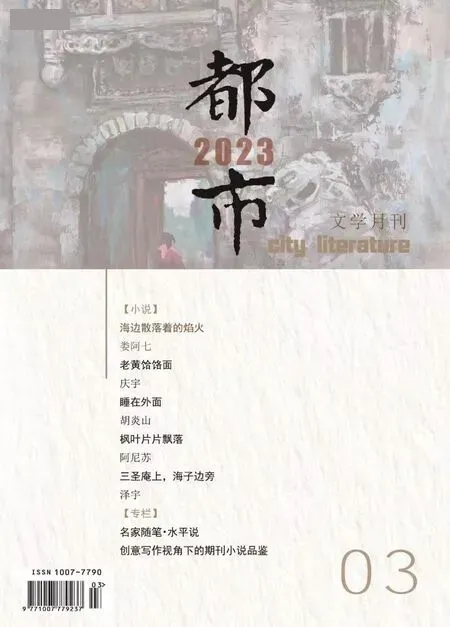卷首語
婁阿七的短篇小說《海邊散落著的焰火》,用一種“無痛”的方式寫出當下婚姻之痛。“我”和維西選定離婚日期、安排“離婚旅行”,這看似戲謔的“儀式”,并未落入現代人的俗套。維西在旅行目的地對“儀式”的拆散,暗藏了一種巨大的心理擺動——不是對婚姻狀態的最后“陪伴”,而是曲終人散前的刻意放逐。維西隱身而去,將“我”與她之間的“裂隙”豁然敞開,消除了禁忌的“我”貌似信馬由韁,實則直抵荒涼。在“我”“器官意圖”的活躍以及輕車熟路的“輕浮”之下,是幾多無奈的迷茫。“我”與維西之間彼此“自在”的距離,預示著不期再相遇、別后兩茫茫,同在一個海邊,忽已遠至生死之遙。“金”“木”相拒以及母鯨的氣味、原始的鯨叫,這些意象點綴著婚姻的行將就木。但煙花散落的“真相”,并不遮沒它曾經璀璨的綻放。盡興的灑脫,也是盡興的憂傷。
阿尼蘇的中篇小說《楓葉片片飄落》,纏纏繞繞、起起伏伏的講述中,總有猜不透的東西牽著人走。沒錯——那是“我”的一面之詞,但如此辛苦地裝出善良無辜的口吻,終究是一場掩飾不住的徒勞。秋天的楓林多么美啊,可以寄托妹妹天賦異稟的才情和品貌,亦在見證“我”軀殼內妒火之狂飆。一個市井之家應有的平靜、一段逃過無情之劫千里相會的愛情,最終都無法逾越“我”心里深藏的黑洞。“我”是否還能厚顏無恥地說——“我”是以痛心疾首的方式“愛”著妹妹的?
澤宇的短篇小說《三圣痷上,海子邊旁》,流蕩著楊柳風吹不散的煙火氣,沉淀著老太原簡單實用的哲理。“二姐”的媽憑著“外地人嫁到太原來,死都要留在城里”的執著,熬過了日子的破敗和張皇,而“二姐”的故事也終將如母所愿:找個本地戶口有房有車的男人成家。但“我”的世界里還有“二姐”的另一種氣場,她從那個僵硬的故事里破繭成蝶,活成了一種韻味,一度殞落的靈魂也在琴聲中復活,同時復活的還有三圣庵、海子邊的故去時光。這個“太原故事”在“聽琴”處達至圓潤,火候剛好。
慶宇的短篇小說《老黃饸饹面》,講老黃的“凌亂”,卻溫情脈脈。做了大半生饸饹面,沒得商量就轉入了面館被淘汰的命運,回不過味兒的老黃,對全家人的“不聞不問”憤憤不平。小小面館也有傳奇,寫著老黃為之驕傲的成就。這個家現在的模樣,不就印證了面館歲月的哺育之功嗎?哪怕育出的仍舊是平凡的生活。
胡炎山的短篇小說《睡在外面》,跳出庸常講述奇枝怪葉。“睡在外面”,不是睡在外間、不是另有居所,而是睡雞窩、睡草垛、睡牛欄、睡豬圈……對于小樺而言,這無關乎流離失所,而是秘密的收獲。是夢入星空、獨向天地,是對鄉村世界自我蒙蔽的完美繞過。睡在外面的小樺心里長出了遠大,天大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