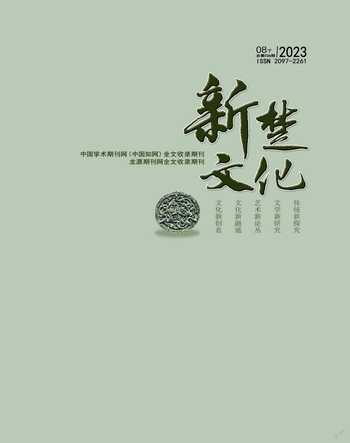試析文化研究的價值與局限
【摘要】21世紀(jì),文化研究在被介紹、傳播、熱捧、質(zhì)疑的過程中不斷進(jìn)軍更多領(lǐng)域,為文學(xué)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但與此同時,其本身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引起學(xué)界關(guān)注。于是,探析文化研究的價值與局限,從而探求擺脫困境的出路就非常有意義。從事魯迅研究的學(xué)者薛林榮出版的《魯迅的飯局》由于借鑒文化研究、外部研究等理論方法,自出版之后廣受熱議。從對此書的評價入手來試析文化研究的價值與局限,以此探求擺脫困境的出路,這不失為很好的切入口。
【關(guān)鍵詞】文化研究;《魯迅的飯局》;薛林榮
【中圖分類號】I206.7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3)24-0022-04
早在20世紀(jì)50年代,英國的利維斯提出了文化研究這個概念,在學(xué)界引起軒然大波。60年代初,英國的伯明翰學(xué)派設(shè)立文化研究中心,弘揚大眾文化,從此之后,文化研究正式成了一個準(zhǔn)學(xué)科和跨學(xué)科的理論。90年代,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春風(fēng)吹到中國,帶來了我國文學(xué)研究的新潮轉(zhuǎn)向,也就是“文學(xué)不斷走向泛化,走向邊緣化、大眾化、世俗化,文學(xué)研究也再次由內(nèi)向外突圍轉(zhuǎn)向,即由審美批評走向文化研究”[1]。文化研究這個概念的含義十分豐富,學(xué)界對文化研究有著幾種理解,大體概括為跨學(xué)科;打破文本,置于社會歷史文化視野下;文學(xué)觀念上使文學(xué)重返社會。文化研究的到來,對于文學(xué)研究既是機遇,又是挑戰(zhàn),文化研究突破了內(nèi)部研究方法的局限,打破了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的冰層,為文學(xué)研究帶來了新研究方法,擴大了文學(xué)研究的疆域,把全新的研究成果再納入文學(xué)研究,但另一面卻隱藏著將文學(xué)研究墜入泛文化、消費主義的陷阱的危險。
薛林榮作為研究魯迅的學(xué)者,也深感魯迅研究的路子越來越狹窄,大多數(shù)是小圈子的學(xué)術(shù)交流,精英化的學(xué)術(shù)切磋和普羅大眾的關(guān)系越來越疏離,于是薛林榮在恰逢魯迅140周年誕辰之際,將自己過去20多年的文稿匯集成了“魯迅微觀”系列,其中最受大眾歡迎的則是《魯迅的飯局》。該書擷取大量史料,選取角度新穎,從魯迅的重要飯局切入,該書容納魯迅自1912年來到北京至1936年在上海去世的24年期間參加主持的大大小小飯局,以此窺探魯迅整個生活概況、脾氣性格等。薛林榮將文化研究和文學(xué)研究、內(nèi)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巧妙融合,從魯迅日記入手?jǐn)X取史料,從普羅大眾都熟悉的平常飯局切入,將魯迅圣人光環(huán)褪去,將之置于日常視角,為讀者還原人間煙火中的魯迅。并且薛林榮通過飯局,將民國市井、文人群觀、文史事件等復(fù)雜龐博的信息親切地向普羅大眾娓娓道來,打造了民國文人生活現(xiàn)場,這些都是其作品廣獲好評的原因。但同時也有一些非議,如詬病該作品史料單一、論證無依據(jù)、隨意揣測、認(rèn)為有消費魯迅之嫌。由上述鋪陳,《魯迅的飯局》是研究文化研究的價值與局限的一個極佳切入口,接下來本文將通過評價《魯迅的飯局》史料研究的優(yōu)劣,試析文化研究的價值與局限,希望探求出照亮文化研究的出路。
一、文化研究的價值
文化研究的到來為干涸的文學(xué)研究帶來新鮮血液,如甘霖一般滋潤,如洪流一般開闊,如野草一般狂放,從某方面來說,它的進(jìn)軍對于學(xué)界是一大喜事,現(xiàn)將文化研究的價值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跨越學(xué)科邊界、促進(jìn)共同發(fā)展
文化研究的突出性質(zhì)在于跨學(xué)科性,文化研究引進(jìn)眾多學(xué)科的理論成果,和政治學(xué)、歷史學(xué)、社會學(xué),甚至大眾文化、傳媒文化、飲食文化等聯(lián)結(jié)起來,打碎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的冰層,為文學(xué)研究帶來多樣的研究方法,拓寬文學(xué)研究的疆域。如若將學(xué)科之間的邊界處理得好,分辨出哪些能跨,哪些不能跨,將會促進(jìn)文學(xué)與文化的共同發(fā)展,否則會陷入文學(xué)、文化都沒保住的窘境。
關(guān)于《魯迅的飯局》,作者獨出機杼,從魯迅1912年至1936年期間組織和參加的大小飯局入手,通過魯迅日記中與何人、于何地、食何餐的記述,聯(lián)合其他相關(guān)史料,成功繪制了民國時期北京和上海包羅萬象的美食地圖,讓讀者了解了百年前中國的飲食文化,包括魯迅日記中記載下來的,北京老字號65家,上海75家。作者還科普了其中飯店的經(jīng)營狀況、服務(wù)態(tài)度、主打菜樣等細(xì)節(jié)問題,甚至記述了軟炸肝尖、叫花雞的制作過程,雖然魯迅在日記中很少評價菜品的味道,但如若提及,一定讓人印象深刻,例如魯迅愛吃的同和居的炸蝦球、稻香村的沙琪瑪?shù)取S卯?dāng)代的話講,作品可另起別稱為“魯迅的大眾點評”,美食文化在文學(xué)的加持下成功“出圈”,甚至大家去北京上海旅游可以根據(jù)魯迅的美食地圖走一走,這將會成為一條標(biāo)新立異的旅游路線,《魯迅的飯局》促進(jìn)了美食文化、旅游文化的發(fā)展。飲食文化喜聞樂見,這也許是此書在作者“魯迅微觀”系列中最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二)拓寬研究視野、呈現(xiàn)全新景觀
文化研究的到來,讓學(xué)者將視野看向文學(xué)之外的廣闊社會歷史中,將社會歷史也一起成為研究的大文本,不再局限于文學(xué)作品和文學(xué)現(xiàn)象的小文本,而將之放在外部的社會歷史中,從而呈現(xiàn)出前期過分強調(diào)“審美”所遮蔽的問題,提供了更多描述歷史的聲音。這種方法來源于沃倫、韋勒克提出的外部研究理論,即研究文學(xué)與時代、社會和歷史等外部世界的關(guān)系。以《魯迅的飯局》為例,文化研究為讀者們還原了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呈現(xiàn)出全新的文學(xué)景觀。
其一,勾勒出不一樣的魯迅。讀罷此書,使讀者對魯迅的印象不再只是劍拔弩張、以筆為矛的戰(zhàn)士魯迅,還是一個抱怨“枯坐終日,極無聊賴”的小公務(wù)員,一個把壁虎當(dāng)寵物的護(hù)寵達(dá)人,一個嗜好零食、停不住嘴的吃貨、頑童,一個計較客人吃他點心的小機靈鬼。
其二,講述了魯迅的“朋友圈”。薛林榮巧妙地通過飯局,不僅呈現(xiàn)了民國美食地圖,還展現(xiàn)了魯迅與民國作家的相交、相知、相離,讓讀者從文人交往中讀出了文人風(fēng)骨、仁者道義、鏗鏘大局。例如分歧疏離后仍在學(xué)術(shù)上惺惺相惜的與錢玄同之交、愛與憎交織的與劉半農(nóng)之交、死后同鄰的與日本內(nèi)山的深切之交。
其三,科普了有趣的“冷知識”。作者通過飯局輻射到許多文學(xué)事件,以此把文學(xué)史中的重大文學(xué)事件放置在真實的民國生活現(xiàn)場中,讓讀者加深對文學(xué)事件的理解。例如達(dá)夫賞飯造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名詩誕生、橋香夜飯助力“奴隸社”建立等。
薛林榮巧妙地借鑒了文化研究的相關(guān)方法,尤其是韋勒克的外部研究方法,做到以魯迅為原點,通過飯局切入,外擴到參加飯局的文學(xué)大家和飯局中發(fā)生的文學(xué)事件,從而營造出讓人垂涎三尺的民國生活現(xiàn)場,甚至可以說,魯迅生命中的二三事以星火之態(tài)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最偉大的時刻,從而側(cè)面展現(xiàn)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三十年波瀾壯闊的面貌,使讀者不禁慨嘆萬分,文學(xué)革命的燎原,這一桌桌飯局可能也在發(fā)揮著細(xì)小的作用。
(三)反哺文本研究、助力深層解讀
文化研究和文學(xué)研究相輔相成、互文共生。文化研究由文學(xué)研究發(fā)展而來,后又將研究成果融入文學(xué)研究,在擁擠的文學(xué)研究中尋找縫隙,在縫隙里尋覓增長點,從而助力文學(xué)研究。如若兩者關(guān)系處理不好,很容易使文學(xué)成為文化的注腳,羅崗提出的“讀出文本”和“讀入文本”可以說是解決這一問題可貴的嘗試。“‘讀出文本是指對文學(xué)文本的解釋不能封閉在文本內(nèi)部,而必須把它放置到一個更開闊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予以理解;但僅有這步是不夠的,所謂‘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不是一個先定的解釋框架,而是一種需要在文本中加以檢驗的話語實踐,這樣就必須把‘社會歷史文化的因素‘讀人文學(xué)文本,仔細(xì)地觀察它們在文本中留下了怎樣的痕跡,以及文本對它們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和它們發(fā)揮了何種的作用。”[2]薛林榮的《魯迅的飯局》就將“讀出文本”和“讀入文本”運用得恰到好處,這一優(yōu)點也豐厚了此書的文學(xué)價值。例如作者在某一章將飯局與作品文本對話,將作品中S城與紹興城聯(lián)系,將《在酒樓上》的小聚視作魯迅“紹酒越雞”之飯的現(xiàn)場版,薛林榮細(xì)讀文中點餐的對話、菜品的描寫,發(fā)現(xiàn)魯迅不知不覺將鄉(xiāng)愁寄予在了文字上;再比如作者從傳叔祖母治饌餞行,探討傳叔祖母與魯迅作品中“衍太太”的關(guān)系和魯迅對故鄉(xiāng)的感情和筆下的故鄉(xiāng)寫作。這樣的例子很多,在將“讀出文本”和“讀入文本”融合的方面,薛林榮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的。
總之,文化研究的價值,不僅在于開拓視野,拓寬研究邊徑,更在于從中塑造全新的文學(xué)景觀,尋找創(chuàng)新的研究點,最終反哺文本研究,尋找研究縫隙,探求多重含義,促進(jìn)文學(xué)研究新發(fā)展。
二、文化研究的局限
自全球化浪潮將文化研究席卷到中國,理論熱、文化熱讓中國應(yīng)接不暇,正如浪潮必將卷起粗礫細(xì)沙,中國處于文化研究浪潮的頂尖也定將受其侵?jǐn)_,對于西方引進(jìn)的文化研究,難免會出現(xiàn)跨學(xué)科邊界沒處理好的問題,沒有很好地和中國實際相結(jié)合的問題,從而進(jìn)入消費主義的陷阱,淪為閃耀但淺顯的碎片,而處于高潮頂端的人們極易享受文化研究帶來的福澤,而很難敏銳觀察到其局限,更難談對其困境進(jìn)行反思,筆者嘗試將文化研究的局限和薛林榮的《魯迅的飯局》結(jié)合起來談,也許這樣,文化研究的局限會談起來更加形象,并且薛林榮此書的研究方法可能會對擺脫文化研究此時的困境有一些幫助。
(一)進(jìn)入消費主義陷阱
自60年代初,英國伯明翰學(xué)派對文化研究賦予了新的特點,此學(xué)派認(rèn)為文學(xué)應(yīng)拒絕高低文化二分論,將文化定義概括為廣義,提倡大眾文化,這也標(biāo)志了文化研究在學(xué)界確立了主導(dǎo)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受伯明翰學(xué)派提出的與大眾文化相關(guān)的文化研究影響,消費文化思想蔚然成風(fēng),文學(xué)從精英群體拓寬到了大眾邊緣群體,但消費主義愈演愈烈,導(dǎo)致了大眾文化提供的文化商品質(zhì)量參差不齊,以至于學(xué)界開始憂慮大眾文化消費經(jīng)典、消解崇高等問題。不出所料,《魯迅的飯局》此書一出,果然遭到了一些批判:魯迅被他的極簡日記狠狠消費了!這些批判是站不住腳的,該書雖是從飯局入手,但并沒有為了博人眼球,而戲謔歷史,解構(gòu)文學(xué),制造魯迅的花邊新聞。每一論證都是論從史出,并且并非僅僅單從魯迅日記,還旁征博引了目前學(xué)界可拿到的所有相關(guān)史料進(jìn)行論證,而且薛林榮并沒有單一地偏信史料和他人論證,而是立場客觀,經(jīng)常尋找多個史料印證某一觀點。例如作者并沒有為吸引眼球,將魯迅日記中的“邀以妓略來坐,與以一元”[3]大做文章,而是挖掘青蓮閣歷史、旁引史料、分點分析,最后得出事實確實存在,但這只是借著酒勁的“打茶圍”之舉。
之所以有一些讀者認(rèn)為作者涉及史料單一,有消費魯迅的嫌疑,可能跟作者給作品的定位和敘述風(fēng)格有很大關(guān)系。薛林榮深感魯迅研究逐漸成為精英圈子里的自娛自樂,并在采訪中說過寫此書的初衷是“我希望把他與普通百姓息息相關(guān)的聯(lián)系寫出來”(他指魯迅)。[4]此處可以看出作者對此書的定位就不是一本精英化的學(xué)術(shù)著作,而是想打造成大眾普及書目,希望它是本有趣、大眾愛看的書。作者對此書的定位也影響了創(chuàng)作風(fēng)格,此書雖采史嚴(yán)謹(jǐn),論證有據(jù),但筆調(diào)親切疏松,仿佛一個魯迅的朋友把魯迅的故事講給讀者聽,并且此書為使閱讀順暢,引用的部分文字沒有在文中注明,而在書末單獨列出,這樣的對書的定位和漫談的敘述風(fēng)格可能會讓沒有細(xì)讀的讀者有了誤解和評價的偏差。但薛林榮有些對于史料的鋪陳總結(jié)確實乏善可陳,例如部分旁逸斜出的內(nèi)容、反復(fù)重復(fù)的史料、大篇幅鋪陳通識性的內(nèi)容有湊字之嫌,像“80后、90后、公務(wù)員”這些當(dāng)代用語有討喜之嫌。
(二)淪為閃耀但淺顯的碎片
由于文化研究發(fā)展勢頭正猛,大批文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躍躍欲試,又由于“文化”這個概念的模糊性,一切文化都被歸于其中,最后大多作品成了“四不像”“巨無霸”,但卻因研究方法新奇或貼近社會現(xiàn)實則狠狠地蹭了文化研究的熱度,這種現(xiàn)象將導(dǎo)致悲慘的學(xué)術(shù)泡沫。此外,我國文化研究的方法有單一化的傾向,巴克提出“在認(rèn)識論層面,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三:民族志、文本方法和接受研究”[5],而國內(nèi)研究者大都集中在了自己得心應(yīng)手的文本方法,并且所涉獵的文本多是學(xué)界廣泛流傳的史料,容易形成史料雜亂、文本整體碎片化、意義零散化的現(xiàn)象。也就是說,這對學(xué)界學(xué)者敲起警鐘:文本方法需要打磨,并借鑒西方的民族志方法,更應(yīng)親身走進(jìn)現(xiàn)實生活和文化群體,讓所得結(jié)論的依據(jù)更加經(jīng)得起推敲,以防成為“美麗”的學(xué)術(shù)泡沫。
回到這本書,薛林榮考證功夫可謂嫻熟,從魯迅日記中將魯迅的飯局中何時、何人、何地的信息梳理出來,再順藤摸瓜,拿相關(guān)人士的回憶性史料、其他研究者的著作作為補充,致力于還原魯迅一筆帶過的飯局細(xì)節(jié),并刺探文學(xué)史爭論、傳播史略。可想而知,這樣的工作量沒有海量的史料梳理是做不到的。值得欣喜的是,薛林榮并沒有停留于史料整理,還實地考察得到了一些珍貴影印,例如魯迅致姚克請柬等,讓讀者剛一翻卷,看到赴約請柬的一瞬間,就有了自己踏入民國生活現(xiàn)場的身臨其境之感。但筆者也不得不承認(rèn),此書極個別史料之后的見解有些淺顯,高高拿起,輕輕放下,使文章有飄浮之感,這可能和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就有了關(guān)系。
三、結(jié)語
關(guān)于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如何在其中找到平衡一直是困擾學(xué)界的一個問題。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出現(xiàn)的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內(nèi)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超越,將西方引進(jìn)的概念取其精華,因地制宜,做到本土化,并且應(yīng)該時刻注意和反思的是,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關(guān)系應(yīng)杜絕對其二元對立地看待,將關(guān)系割裂很容易導(dǎo)致泛文化現(xiàn)象或庸俗社會學(xué)的極端。
文化研究像一把雙刃劍,它的開放性、跨學(xué)科性質(zhì)既開拓了研究路徑,又助力文學(xué)研究的發(fā)展,但也不得不承認(rèn),文化研究壓榨了文學(xué)原本的主體地位,使文學(xué)走向邊緣化。那么在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時代,研究者的出路在哪里呢?以文學(xué)為落腳展開文化研究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嘗試,因為文化性是文學(xué)的基本屬性,所以文化也必須根植于文學(xué),從而將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重回文學(xué)中回顧,這是否會照亮文學(xué)之路呢?筆者認(rèn)為雖然薛林榮的《魯迅的飯局》也有受文化研究局限性產(chǎn)生的小毛病,但也不得不承認(rèn)它為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分歧的解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薛林榮在文化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復(fù)雜關(guān)系中找到了平衡的訣竅,選取“飯局”為切入口,讓高雅文學(xué)與口腹之歡相得益彰、讓普羅大眾和精英學(xué)者同享書籍盛宴。
參考文獻(xiàn):
[1]吳秀明.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料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6.
[2]羅崗.讀出文本和讀入文本——對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和“文化研究”關(guān)系的思考[J].文學(xué)評論,2002(02):85-86.
[3]魯迅.魯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299.
[4]孫行之.魯迅的朋友圈與飯局:一部飯桌上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N].第一財經(jīng)日報,2021-07-02(A11).
[5]Chris Barker.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M].Sage Publications,2000:26-27.
作者簡介:
劉曉涵(1999-),女,漢族,吉林延吉人,沈陽師范大學(xué)碩士,研究方向: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