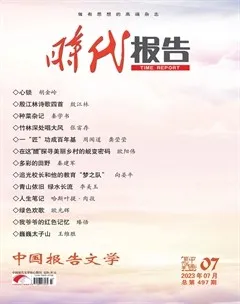蒙馬河的述說

沃野莽原麥浪黃,穗豐粒滿待收倉,烏云密布霧茫茫……又逢收麥季,盡管是陰暗潮濕的天氣,蒙洼大地依然機聲隆隆,站在蒙馬河的岸邊,一望無際的麥穗正等待顆粒歸倉。
芒種打場,忙亂的打場場景漸行漸遠。收麥搶種依然還是那么緊張。這里的莊稼人農忙時就怕雨水天氣,那是個蛤蟆尿泡尿都能淹的地方。當地有個順口溜:十七、十八雨尋頭,二十四、五滿河流。每年進入五月就到了雨水季。 蒙馬河暗流涌動,一場大雨都會洶涌澎湃,溝滿河平。
在我12歲那年,陰歷五月十三那天,莊臺上的人都在麥場里扒垛攤麥子,開始曬麥,打場。風平浪靜,火辣辣的太陽直曬著,天熱得讓人心里發慌。東場的駝背大爹不緊不慢地趕著牛,拉著石磙一茬套一茬地碾壓著攤了滿滿一場的麥子。嘴里不停地罵著幾個兒子:“干會兒活就溜得沒個影了,一個個偷奸耍滑,離了我,等著睡樹底下接鳥糞吃。”大爹家孩子多,罵小孩像唱歌,都成了習慣。臨近中午,天上突然出現了云。我和三姐還在東大地用大耙子摟麥子,天陰沉了下來,我們就趕緊把麥子捆好放在架車子上往回趕,剛走到場對岸的路上,就聽到大爹才過門的二兒媳帶著哭腔喊:“大,別打了,雨要來了,人家都在搶著收場呢。”大爹仰臉看天,沒言語,繼續趕著牛不緊不慢地往前走。他家有七八個干活的勞力,也有停住氣的資本。俺家三個姐姐,勞力弱,干啥都緊著活做。老遠就看見俺家的麥剁堆起來了。正午時分,突然一聲悶雷,撕開了厚厚的烏云,冷不丁的雨點冰冷地砸在人們的臉上,場里一瞬間像熱鍋上的螞蟻,一個個慌不擇路,吆喝聲、喊叫聲,亂作一團。我們拉著車子剛過場角的小石條橋。瓢潑大雨就劈頭蓋臉地砸下來。平地起水,架子車拉著拉著就漂起來了。這時人們一個個的都被淋成了落湯雞,麻木地站在水里看著自家的麥子被沖走。
風雨過后,60多歲的胖二娘從臺子上深一腳淺一腳地蹚水走到自家的場頭,看到打出來的麥粒都被沖進水溝里,雙手拍著胯,一屁股坐在水窩里哭喊著說:“老天爺呀,你這是要滅俺一家人吶,這一家人還咋活呀!……”大嫂、二嫂在一旁陪著落淚。二哥心煩氣躁,粗聲粗氣地吼了聲:“哭啥哭,餓不死。”那一年,家家都吃著生芽子的麥面。手搟面下到鍋里碎得就像豆雜面,沒了黏性。蒸出來的饃是烏黑的,像死面疙瘩,一點兒也不暄。吃到嘴里黏牙。那一年俺家接濟了二娘幾袋麥子,親戚鄰居遇到困難都會有個幫襯。
15歲我能獨立掌車把了,我和父親到魚塘邊拉麥,這是一家人起早割掉的一畝六分地的麥子,我負責用叉子把小麥都挑到車子上,父親在車子上“踩車”。車子裝到一定高度,就用兩道繩交叉著把麥子勒緊。車子裝滿后,我用肩膀扛著車把,雙手拽著繩使勁地往下拉,父親在車子上弓著腰,鉚足了勁往上提。我和父親用盡全力提拉繩子的時候,繩子從后面竟然斷掉了。父親從2米多高的車子上摔下來,躺在地上的父親當時昏厥了過去。我丟下車子,驚恐地抱著父親,顫抖的聲音不停地喊:“大、大……”直到他慢慢地清醒了過來。
后來母親問我:“從那次你爹摔了一跤之后,是不是對你好多了?”我問為啥,母親說:“通過那件事,你爹覺得你還是很知道心疼他的,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看著你抱著他流著淚喊叫著,心里特別幸福,你讓他感覺到了你是個孝順的兒子。”我說:“那不是理所當然的嘛。”娘說:“你平時和你爹一樣,沒個笑臉,寡言少語的。不善交流,一家人也會覺得很冷漠,有時意見不合還頂撞兩句,更沒了父子間的那份親情。”沒想到一次意外讓父親對我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1991年家鄉發大水,我是一名軍人,受到部隊領導的親切慰問,還特意批準我回家探親搶險,我滿懷感恩的心情,坐火車從北京趕到阜陽,轉坐船回蒙洼,當地政府已經通知到各家各戶,王家壩閘隨時準備開閘泄洪。四里湖行洪區已經是波濤洶涌、水滿為患。蒙洼蓄洪區也是內澇成災,人們都在蹚水把場里打好的麥子搬運回家。我也迅速地換下軍裝,投入到運糧隊伍中去。
麥場離莊臺一公里,路都已沉入水中。莊臺上老少齊上陣,扛的扛、背的背,在水里排成長龍,深一腳淺一腳地循著路走。在麥場與莊臺之間,有座橋叫新橋,是橫跨在蒙馬河上的一座生產橋。橋的兩邊有高30厘米、寬60厘米的平面護欄。人們不管從哪里來,都喜歡坐在兩邊高處的水泥平面,歇歇腳,聊聊天。搬運糧食的人,體力好的一口氣就能把上百斤的口袋扛回家,體力弱的背著半包糧食還要氣喘吁吁地在橋上歇一會。四哥家剛過門的新媳婦背著小半包糧食戰戰兢兢地跟著隊伍往前走,一個趔趄連人帶麥子滑進深水中。旁邊幾個人扔掉糧食把四嫂拽了上來,大家哄笑她,崗區來的漂亮新娘子,這次成了落湯雞。四嫂驚魂未定,顧不上別人打趣,丟下麥子,被人攙扶著回去了。
經過一天的忙碌,人們把最下層,已被水淹沒的麥子撈出來裝到袋子里,扛回家都已經是筋疲力盡。隨著上游王家壩放閘的槍聲響起。洪水從蒙馬河長驅而入,涌向蒙洼大地,半天的時間蒙洼地區一片汪洋。這時地里還未收完的糧食、蔬菜,房屋,農業種植、水產養殖全部沉沒在水中。我想,怒吼的蒙馬河和蒙洼人該是多么傷悲。
如今蒙河拓浚工程和臨淮崗工程的完工,讓淮河流域越來越暢通,科學治水已初見成效。曾經的蒙洼三年兩頭澇,五年一大淹的水災場面將一去不復返。蒙馬河將會長期安逸平靜,默默地滋養著蒙洼人。
責任編輯/石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