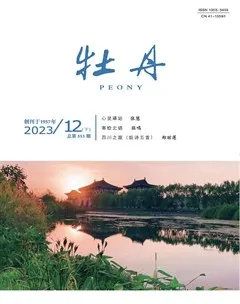《文心雕龍·物色篇》中的感物方式
《文心雕龍·物色篇》(以下簡稱《物色》篇)是《文心雕龍》全書中表現自然景物在詩詞歌賦中起關鍵作用的論說篇章,全篇以自然風物及其詩賦表達貫穿始終,將“物色”與詩人內在情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劉勰的論說首先以四時流轉對物與心的影響起調,從時間角度對景物引發的情感觸動進行了形象的表現,結合宇宙運轉與內心世界,開拓了一個內外兼容的寬廣空間。緊接著指出“詩人感物”的種種方式,援引《詩經》《楚辭》、漢賦佐證,并對當時盛行的“文貴形似”風氣作出評價,提點“后進”。最后以贊語作結,回到物與時序對主體感物抒情的作用。其中“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幾句集中體現了劉勰對感物方式的觀點,揭示了詩人在感受自然景物時生理、心理層面的交互作用。
劉勰在《物色》篇中的論述聯系過去、當下、未來,統一了物、情、辭,其評論的境界十分開闊,而理解《物色》篇中的感物模式,須從對“物色”的理解入手,而后深入到對感物概念及其方式的探究。本文在掌握《物色》篇的基本內容與結構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古典文學中有關材料,對《文心雕龍》中“物色”概念以及感物方式作出美學闡釋。
一、“物”與“色”
在《物色》篇中,“物色”二字時而并提,時而分論。其中,“物”作為獨字出現次數最多,共有9處;“色”作為單字出現僅有一次;“物色”則在文中出現4次,并且基本出現在開篇和尾部。并提時,“物色”指代的是詩文中被描寫的對象,即自然景物;分論時《物色》篇以說“物”字為主,對于“色”只有在描寫外物顏色時有所提及。
作為被人描摹的對象,自然景物在進入文人視野之前是客觀對象,是與人相對的自然景物;進入詩人視野之后,外物就會被染上主觀的色彩。物的主客之分雖然不是《物色》篇議論的重點,卻是中國文論中現實存在的問題。劉勰稱“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即說明物是詩人內心世界得以生成的根源,也是情志得以陶冶的基礎。這里的物不是平面的、單調的、個體的,而是有廣度、深度和延伸性的物質概念。“歲有其物,物有其容”,容,盛也,意為盛受、容納。從山林皋壤到玄駒丹鳥,生物的不同種類、大小都被納入“物”的概念中。中國古代對“大”“小”的理解通常能夠從數量、體積轉移到道德、精神境界。例如,《詩經》中“碩人俁俁”“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有美一人,碩大且卷”等,“大”常與美聯系在一起,既是對抒情對象的感性描述,也帶有道德意義。《莊子·逍遙游》從鯤鵬、斥鷃之別到“小大之辯”,表現了人生視野、理想、境界的差異,在精神層面賦予“小”和“大”內涵。《物色》篇的“物”如果只按進入詩人審美體驗的客觀對象來理解,顯然不符合《物色》篇范圍如此廣闊的描述和深刻的意蘊。“物”還具有變幻無常、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如“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物色》篇從四季、氣象方面刻畫自然風物,物在時間與空間尺度的附加作用下有了延伸的變化感,成為蘊含宇宙能量,富有生命感的“物”。這樣的“物”才能感召詩人,使人心搖曳。
《物色》篇還對物的呈現做出論斷,即“物貌難盡”“物有恒姿”。前者描述的是物的多樣性、無窮性,后者描述的則是物的永恒性、穩定性。二者看似矛盾,實際上可以相融。劉勰以辯證統一的觀點看待物,從宏觀的視角看到了物的多樣性,譬如山有高低陡峭之貌,樹有高矮疏密之貌。隨著季節的流轉,物貌也會變化,在詩詞中才有了“于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群積矣”。而“物有恒姿”是將物放在了特定的環境中,這里物與思對舉,可見這是在一個相對固定的時空尺度下的論斷,具體來說就是詩人進行構思創作時所見之物,在創作期間是不變的,即使變化了也保持著同一性。例如,唐代詩人崔護《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桃樹實際上與從前有一定差別,但樹的位置、走勢等是恒定的,帶給詩人的思緒也是無限的。總而言之,《物色》篇的“物”是一個范疇,它區別于人本身和人的活動,也區別于詩人主動創作出的、呈現在詩詞歌賦中的文字的物,而是具有多維度、多面相的自然之物。
“物色”中的“色”一說借用佛教中“色”的含義,指與本體相對應的現象界,即“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色”。劉勰少時入定林寺,與僧祐居處十余年,博通經論,其文學思想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響。然而《物色》篇中用“色”字只有一處,原文為“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立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顯然“色”這一概念的直接來源是顏色。“五色”早在商周時期就有記載,《尚書·虞書·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老子》:“五色令人目盲。”陳鼓應注:“五色:指青、赤、黃、白、黑。”三國時期漢文佛經中,對“五色”也有較多記載。經統計,后漢三國時期的漢文佛經中共有55個五色用例,其中有52個表顏色義。在有些經典和語境中,五色是一個以確數之名,表示豐富、眾多顏色的詞語。“五色”這一概念明顯是對顏色的描述,到唐代才逐漸演變為現象界。
以“色”代指自然風物的表象既反映了文人寫作中對顏色的重視,也解釋了“物色”意義生成的過程。顏色的描述強調了感官中的視覺要素。《物色》篇中唯有“沉吟視聽之區”和“屬采附聲”二句提及感官,而其中的視覺與聽覺卻都是捕獲事物的關鍵感官。視覺可以捕獲物的顏色、形態、體積,聽覺可以捕獲聲音,二者對物的包圍基本上可以把物的特征感受清楚,詩詞歌賦所表現的也是這些表征,并且是鮮明的表征。范文瀾注“物色”曰“蓋物色猶言聲色”,其實可以與視聽相連,表達的仍是物的表征。以“色”代指現象并不準確,現象比表征更具體,細節更豐富,卻也更雜亂無章。呈現在文本中的“色”是經過凝練、抽象的,譬如“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未盡桃花、楊柳所呈現的形象,而是以“灼灼”“依依”抓住主要特征進行表現,這種抽象與凝練便是“色”字所表達的內涵。“色”一字在《物色》篇能夠推廣至表征,是與“物”字結合意義擴大的結果,其本質仍然是人對物的捕獲,作為審美體驗可以納入感物的環節。
“物色”涵蓋了具體的自然風物及其內蘊和表征,在《物色》篇中,劉勰將“物色”作為感物作文的基礎和動力,實際上對文人的體悟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
二、感物
詩人若想有所闡發,必然要有所憑依。詩人詩興所發,心之動搖都由“物色”引起,亦即“感物”。關于“感物”的理論,可以追溯至《禮記》,《禮記·樂記》開篇即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至魏晉南北朝,感物理論在文論中得以延續。陸機《文賦》:“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鐘嶸《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曰:“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多次提及與感物相關的理論,如《明詩》篇:“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詮賦》篇:“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他將感物的過程揭示出來,形成《物色》篇的主體。這一部分的論述主要集中在“是以詩人感物”到“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這一段的論述是循序漸進的,從《詩經》時期的“以少總多”到漢賦時期的“詭事瑰聲,模山范水”,劉勰提出了不同的表達方式,反映了相同感物方式隨著時間發展在文辭方面發生的變化。
人感物的必備條件是心神與感官,前者與萬物共振,后者接收物之表象。前文論及,物包羅萬象,能夠帶給人多重感官體驗和內心感受。詩人在此環境中“聯類不窮”“流連”“宛轉”“徘徊”,這些內心世界的活動與外界互聯互通,相互聯結,類似于“通感”,旨在形成回環的渾然境界。紀昀評:“隨物宛轉,與心徘徊八字,極盡流連之趣,會此,方無死句。”在這個渾然的感物體系中,詩人看似失去了主體性,與由自然引導的“迷狂”狀態相類,但實際上詩人并沒有失去主導性,仍然能自主地捕捉事物。如果是前者,那么就是情志被物色蒙蔽的狀況。雖然物是詩人內心和筆下草木世界生成的根源,但其不能站在比心神、情志更高的地位上。屬于內在活動的神思、情志和屬于外在的物是兩個不同的體系,《文心雕龍》無二者互相來源之說。《物色》篇強調的是二者的協同變化,情以物遷,而物色又與心徘徊,是一個符合自然規律的圓滿交互過程。在此過程的基礎上,詩人借文辭抒發情志,文辭便成為反映這種感物方式的載體。
這種聯通交互的感物方式在文辭上的體現經歷了一系列變化。《詩經》時期,是“一言窮理”“兩字窮形”“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楚辭時期,是“物貌難盡,重沓舒狀”;漢賦時期,則是“模山范水,字必魚貫”。詩賦的字數越來越多,描述也越來越詳細,以盡顯技藝、新意。到了“近代”便演變成了“文貴形似”,劉勰的評價是“窺情風景之上,鉆貌草木之中”。這種文辭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感物方式的變化,從“情以物遷”“隨物宛轉”到“窺情風景之上”,自然的交互在胸中激蕩,文辭變為借自然風物表達情感,感物中融入詩人的目的和主動思考。前者所代表的平衡被打破,后者看似是“物”這一端更加重要,實際上是“人”的作用越來越突顯。在作為表達工具的語匯豐富發展的同時,人的感官表達也得到了發展。把握事物的表征越全面就表示人的感官表達越健全,在感物方式上的體現即所調動的感官越來越多。《詩經》時期只能在詩中展現一方面,而在南北朝的詩歌中能展現更多層面的組合。《詩經》“以少總多,情貌無遺”建立在人們對事物有共同的體驗上,所以典型特征能引發人們的聯想,從而讓讀者覺得情貌盡顯而意味無窮。“近代”詩賦則能“瞻言而見貌,印(疑作即)字而知時”,通過文字直接在腦海中形成形象和感知,“感物”通過文字轉化為“物感”。這一時期的感物方式是“體物為妙,功在密附”,具體的物的形貌代替了“不窮”的“萬象”之物的地位。“且《詩》《騷》所標,并據要害”——詩騷成為后世文人面對的一座大山,人們很難超越其精妙簡練,因此只能在文辭方面進行繁復的變化。然而這種重“色”而輕“物”的做法雖然反映了人在感知層面的進步和意志的作用,卻使物的表現簡單化。劉勰在《物色》篇推崇的是詩經“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批評了當時文壇“模山范水,字必魚貫”“青黃屢出,繁而不珍”的現狀,是對詩經“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的
回歸。
三、結語
《物色》篇贊語寫道:“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一句寫物,一句寫人,生動地展現了感物過程中的兩個主體。除此之外,還展現了人感物的普遍過程:感官接受物的表象,進入內心并產生情感的變化,生出創作的興致。不管是物與人的自然交互,還是人對物的全面把握,作為感物方式并無明顯的高下之分。在創作中依靠正確、合適的方式把握事物,表達情志,才能匯通物與情與辭,創作出理想的作品。
(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