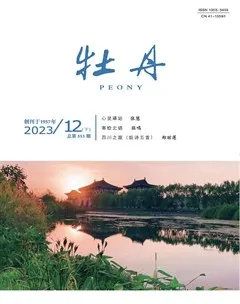李娟非虛構散文的真實性與詩性
自非虛構寫作登上當代文壇,真實性一直是非虛構作品中的應有之義,但作為文學作品,非虛構作品理應滿足受眾的審美期待。在國內非虛構寫作一味追求真實性的情況下,作家李娟的非虛構散文將真實性與詩性完美融合,為國內文壇的非虛構寫作增添了一抹清新的色彩。其真實性表現為作家的“在場”和冷靜客觀的敘事態度,其詩性表現為清新質樸的語言風格和藝術手法的運用。
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設了“非虛構”專欄,倡導當代作家深入民間,探索多元的時代內涵,自此,大眾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非虛構寫作這一文學熱點上。國內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非虛構作品,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李娟的《羊道》系列散文等。這些作品的出現不僅激發了其他作家的創作熱情,也引起了讀者對當下社會現狀和問題的關注。
李娟的非虛構散文與其他非虛構作品有所不同,她將目光投向偏僻荒涼的西部地區。她創作的非虛構散文主要書寫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百姓的現實生活和邊疆地區的別樣風光。以個人的親身經歷為基礎,李娟在作品中真實地展現了當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模樣,引發了人們對游牧民族前景和命運的關注與思考。在真實性的基礎上,李娟的創作方式具備詩性的特點,既展現了邊疆地區的原始風光,又使讀者獲得了豐富的審美體驗,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性和欣賞性。
一、真實性
李娟的非虛構散文忠實地記錄了她在牧區的見聞,并以客觀的視角展示了事件的真相,沒有對事件進行任何夸大或扭曲。同時,她還巧妙地運用了藝術手法,以一種令人滿意的方式講述了故事的真相。這種創作方式既保持了內容的真實性,又呈現了令人滿意的藝術效果。與傳統散文相比,非虛構散文更加符合散文的定義,因為它堅持基于個人經歷的真實性,并反對夸大和扭曲事件,以展現作者親身體驗的重要性。
(一)作家“在場”
自非虛構寫作登上中國當代文壇以來,就與“在場”“介入”這兩個概念緊緊聯系在一起。“在場”是具有重大影響的一個哲學概念,意為熟悉、了解所面對的事物,對事物有直接性經驗,呈現事物的本真面目和規律,無遮蔽。文學意義上的“在場”就是主張創作主體貼近現實生活,以主動的姿態親身體驗某一群體或個體的生活境遇。“介入”一詞由法國著名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提出,旨在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薩特認為,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一種介入社會、參與社會生活的行動,是對社會現象和問題的關注與呈現。
《人民文學》雜志的非虛構寫作計劃名為“人民大地·行動者”,其目的在于激勵作家通過實際行動,深入社會生活,對某一社會現象和事件進行實地考察與體驗。實踐性的寫作方式能夠提供更加真實、深入的社會觀察角度和情景描繪,使作品更具有可信度。通過深入社會,作者能夠親身體驗并了解社會現象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從而以更加全面和準確的方式呈現給讀者。在“非虛構”專欄的一系列作品中,作者運用田野調查等人類社會學方法,以“在場”的方式參與整個故事現場,力求最大限 度還原事實的真相。
2008年,李娟的母親在阿勒泰的烏倫古河南岸承包了一塊向日葵地,李娟與家人投身于向日葵地的耕作勞動。然而,這塊土地歷經了黃羊的啃食和破壞、三次重新種植、連續的干旱與蟲害困擾,最終才有了豐收。離開后,李娟一直對那片土地念念不忘,于是將自己在向日葵地的生活經歷記錄了下來,名為《遙遠的向日葵地》。《冬牧場》是李娟的第一部長篇非虛構散文作品。2010年冬季,李娟與相熟的一戶牧民家庭深入新疆阿勒泰地區南部的冬季牧場和沙漠地區,親身體驗了長達三個多月的牧民生活。李娟生動記錄了牧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同時展現了阿勒泰地區的牧民在冬季轉場時獨特的生存景觀。李娟以真實參與者的身份,運用紀實手法,直面現實存在的社會和民生問題。作家“在場”使她的作品展現出一種現場感,因為她不僅是一名講述者,更是牧民生活和事件的參與者。作者以“在場者”的身份敘述生活瑣事,其創作依據草原上牛羊的習性和四季變化,順應自然規律,展現出獨特的價值期望和追求。
(二)冷靜客觀的敘事態度
在大部分非虛構作品中,作者參與了整個故事,并且親身體驗了故事中所描繪的生活,因此,作者大多以第一人稱為敘事視角。比如梁鴻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梁莊人,在描述梁莊所發生的變化,講述梁莊人的故事時,會以“我”的聲音發表自己的思考和見解。李娟在作品中也是以“第一人稱”來敘事,但是她始終站在外來者的角度給讀者呈現游牧民族原汁原味的生活圖景,對于牧民的傳統的生活習慣、觀念習俗,李娟從不加以評判,她只負責將自己的親眼所見轉述給讀者。比如在《羊道》系列中,李娟寫“我”幫一個流鼻血的小男孩止血時,大家覺得“我”小題大做;胡力牙疼服用的卻是治胃病的藥;居麻不管頭疼還是腳疼都吃阿司匹林等。李娟保持一貫溫和的態度來敘述,讀者能夠透過她的眼,看到一個完整的、不加修飾的西部角落,從而產生對它的感受和思考。
二、詩性
詩性一詞具有多重含義。狹義上的詩性指的是詩歌的特質,廣義上的詩性則指與邏輯性相對的藝術性和審美性。在維柯的《新科學》中,他提出了詩性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概念,特指原始人類在思維方式、生命意識和藝術精神等方面的特征。從這個角度來看,詩性通過藝術性和審美性的方式來表達、傳遞了人類在思維方式、生命意識和藝術精神等方面的特征。
一部成功的非虛構作品不僅僅是對現實的簡單模仿,而是作家通過對現實素材的解構和重構,以洞察力透視事物的本質,從基于事實的認知中提煉出藝術的“真實”。在這個過程中,作家的主觀意圖和藝術化處理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李娟文字的動人之處在于她恰到好處地融合了非虛構素材和虛構想象,增強了非虛構文本的文學性和審美性。李娟作品中的“詩性”特征主要體現在她清新質樸的語言和藝術手法的運用兩方面。
(一)清新質樸的語言風格
當前,國內非虛構作品的主題集中于探討社會現實困境等,這些作品的語言風格通常是沉重的、直擊現實痛點的。然而,李娟的散文作品描繪了新疆的風土人情,她常常從內心的感受出發,以詩性的方式表達。她的語言風格清新質樸,給讀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
著名作家曹文軒曾談及詩性的品質和特征,他將詩性視為流動的、水性的。就像水一樣的詩性,在語言文字上表現為去除浮華和做作的辭藻,干凈、簡潔,敘述流暢自如且充滿韻味。從這個意義上看,李娟的非虛構散文作品完美地符合了詩性的特征。
首先,李娟的作品運用了大量簡潔易懂的語言。在描繪哈薩克牧民的生活時,作者穿插了少量哈薩克族名詞,并用漢語對其進行解釋,語言親切質樸。李娟還習慣于用最簡單易懂的文字描繪邊疆地區的地貌和風景,為尚未涉足邊疆地區的讀者提供了原汁原味的游覽視角。此外,在人物塑造方面,她常常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對話來展現當地居民之間的互動,與哈薩克人用“生硬”的漢語交流的對話場景,李娟也一字不落還原,沒有摻雜過多修飾和雕琢。這種語言表達方式揭開了大眾甚少關注的邊地人民生活的神秘面紗,也更加真實地展現了作者在阿勒泰地區的生活,使人感到新奇而又
真切。
其次,由于少時在阿勒泰地區的成長經歷,李娟對這片土地傾注了自己的感情。李娟的文字表達充滿著感性色彩,帶有詩意,獨具個人風格,作品里的萬物在她的筆下都變得可為人感知。李娟的文字世界展現了動、植物的生態及人類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呈現出一種和諧自然、有序而和諧的狀態。李娟在描繪曠野、森林、云、風、山和水等自然景觀方面具有獨特的才能,同時也善于描寫貓、狗、牛羊等牲畜以及各種花鳥蟲魚。在李娟的作品中,山川自然與世俗生活相互交織,相輔相成。盡管她所描繪的是遙遠而陌生的邊境地區的生活,但卻充滿了人間煙火氣,這歸功于她敏銳的筆觸和內心深處的柔情。
(二)藝術手法的運用
非虛構作品歸根到底是文學作品,需要體現出文本的文學性。在李娟的作品中,除了忠實記錄客觀事實,李娟還將個人所感和體會通過藝術手法來表達,對非虛構素材進行了巧妙的藝術加工。這種處理方式不僅增強了作品的文學性和審美性,還使得非虛構真實與藝術真實相結合,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例如,在《阿勒泰的角落》中,李娟回憶在喀吾圖地區開裁縫鋪的時光,通過對布料的描述,深入探討了當地的禮儀風俗、傳統理念和審美價值觀。實際上,李娟以布料為突破口,以獨特的視角揭示了這個地區獨特的文化特點。她在文中寫道:“我們接收的布料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布,散發著和送布來的主婦身上一樣的味道。我們用尺子給她量體,觸著她肉身的溫暖,觸著她呼吸的起伏,不由深陷一些永恒事物的永恒之處。”作者在描繪布料和喀吾圖主婦之間的聯系時,運用了虛實相互融合的藝術手法。這種融合不僅涉及布料的實際用途,還觸及更深層次的主題,如美、時間和人生等永恒命題。通過合理地結合虛構想象和非虛構素材,作品呈現出了藝術真實。在喀吾圖,布料不只是生活用品,還有社交和禮儀屬性,是人們出門拜訪和參加宴會時必不可少的禮品。因此,布匹在這里進一步成為維系家庭倫理的精神象征。以布料為媒介,作者將觀察的焦點從當地人對待布料的態度擴展到他們的精神層面,感受到了當地人古老而深沉的生命氣息。
又如《九篇雪》里描述的牧民小孩努爾楠,李娟運用了大量的比喻手法,形容他的聲音嬌脆、清晰,像是在一面鏡子上揮灑的“一把又一把的寶石——海藍、碧璽、石榴石、水晶、瑪瑙、貓眼……叮叮當當,晶瑩悅目……”。李娟把努爾楠的聲音比喻成美麗的寶石,其實也就是將這個人物比作閃閃發光的寶石。李娟看到的是自由、恣意的努爾楠,因此,她沒有花費大量筆墨寫努爾楠物質短缺的生活,而是更加關注他快樂又純粹的內心世界。努爾楠內心的明朗和快樂,反映了哈薩克民族堅韌的人生觀,是孩子們日后獨立面對游牧生活的肥沃滋養。李娟運用藝術手法描繪出了缺乏物質資源但內心豐盈的牧民小孩的童年,不僅將努爾楠這個人物從貧乏的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增添了人文魅力和溫度,而且為讀者提供了多樣的視角來觀察牧民的
生活。
在李娟的非虛構散文作品中,我們看到了真實性和詩性的融合。她不僅以獨具性靈的文字呈現了真實的邊地牧區生活面貌,還運用多種藝術手段描繪出了那片土地上的靈魂,形成了具有個人鮮明特色的創作風格。李娟的創作打破了傳統的非虛構敘事格局,以詩性的方式來書寫沉重的話題,既滿足了社會對文學真實的渴求,也滿足了讀者的審美期待。這一非虛構寫作范例拓展了非虛構寫作的創作路徑,豐富了非虛構寫作的創作經驗,促進了非虛構文學的發展。
(長江大學)
作者簡介:熊瓊宇(2000—),女,湖北咸寧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