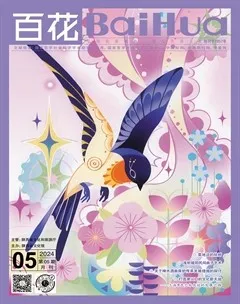陜北聲樂教育的開拓者





孟宗伋,陜西綏德人,出生于1939年10月22日,畢業于西安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陜北民歌研究會榆林市副會長、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客座教授、著名聲樂教育家,曾任榆林市歌舞團團長、榆林市民間藝術團業務團長、榆林市藝術學校校長等。孟宗伋在聲樂教學的道路上,美聲唱法與民族唱法教學結合的問題上,尤其在陜北民歌的聲樂教學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績,為省內外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聲樂演員,為全國藝術院校輸送了大量的藝術人才。他創作了大量的聲樂作品和舞蹈音樂,其中舞蹈音樂《情深宜長》獲省首屆音舞調演二等獎、“喜洋洋”三等獎、“春情”三等獎,歌曲《送大哥》獲省新民歌改編優秀獎。孟宗伋多次受到地區表彰和獎勵,被授予市“優秀園丁獎”和省“優秀輔導員獎”。2007年在“中國陜北民歌經典”中,被選為對陜北民歌有杰出貢獻的人物之一。
初識孟宗伋老師是在2017年,雒勝軍引薦我拜訪了孟老師,由于都是陜西省綏德縣人,見面分外親切,后面在音樂學院舉辦的活動中也見過幾次,但一直未有深入交流。2022年12月,我有幸來到孟宗伋位于曲江的家中對其進行專訪,走進孟老師家,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精致的小花園,屋里裝修古色古香,83歲的孟老師為人和藹,思維清晰,精神飽滿。
訪談者與孟宗伋老師在其家中合影(2022年12月13日)
訪談時間:2022年12月13日
訪談地點:陜西省西安市鴻基·紫韻小區(孟宗伋家中)
采訪者:吳婷
被采訪者:孟宗伋
(以下吳婷簡稱“吳”,孟宗伋簡稱“孟”)
一、學藝經歷
吳:孟老師,請您談一下您的成長經歷,您從何時開始接觸陜北民歌?
孟:1939年,我出生在綏德縣砭上,子州林附近。我父親是中醫醫生,我們姊妹7個,我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兩個哥哥一個姐姐,所以每個人都要靠自己闖,我姐姐四幾年就到延安去了,家里邊在當時也是思想比較開放。我在榆林工作了一輩子,我父親都沒上來過一回。我還常逗我父親說:“人家都來看娃娃呢,你怎么不來?”我父親說他放心著呢。
我父親是從山西來到綏德的,由于他從小跟我爺爺學的中醫,后面就被分配到了縣醫院的中醫科,搞了一輩子中醫,我父親也想讓我學醫,但我愛好文藝。
吳:您從小一直在綏德上學,是嗎?小學是在哪個學校?
孟:小學在綏德一小,初中是在綏德一中,到高中時期我就到了西安音樂學院附中了。
吳:您的成長背景是什么樣的?您對文藝愛好大概是從幾歲開始?
孟:這個時間就早了,大概從我四五歲就開始了,抗大演出隊排練的時候,像我這么大的孩子就都趴在旁邊看,我姐比我大七八歲,也跟著一起看,看完回家后,我姐就讓我學個二寡婦,我當時就在炕上給我姐學二寡婦表演。
可能那個時間就是萌芽,到了小學后我也喜歡唱歌、扭秧歌,反正只要學校有文藝活動,我就是打頭的。老師上音樂課教唱一首歌,我課余時間一定會唱上個幾十遍,知道我愛好文藝,只要有表演機會,我的老師一定會推選我去參加,后面我自己都學會了看簡譜,當時我的班主任安老師對我特別好,我非常感激他。那時候,延安歌舞團、陜西歌舞劇院經常到綏德演出,我們平時有很多機會看各種演出,每次綏德只要有晚會了大家都愛看,其實再也沒什么看上的,不像現在能看的多。再一個就是中央歌舞團、總政文工團來綏德采風,他們只要來采風,我就跟著他們去學舞蹈,我跳過東北的秧歌《逛街樓》,兩個人的舞蹈,拿手絹跳,還跳過朝鮮舞,當時在綏德還跳得挺好的。
吳:您去上西安音樂學院是一個什么樣的契機?
孟:當時西安音樂學院附中來招生,在社會上張貼公告,自己想報名就可以報名。本來招了兩個,但另一個男孩當兵走了,就沒有招他。我記得去考試的時候,我就唱了首歌,唱的《高樓萬丈平地起》,朱培元老師和許芝蘭老師聽完后,當場就說把我定了,最后我就上了音樂學院附中的聲樂系。
在孟宗伋老師家中對其進行專訪(2022年12月13日)
吳:您當時考上以后就直接去了?家里人也都同意是嗎?
孟:我家里人都很支持,我當時愛好文藝,也特別想去,我當時高中也考上了,但就一心想去西安音樂學院。我跟喬建中老師是附中同學,當時他在榆林考的,我在綏德考的。考進去以后,我們的專業課是分頭上,他學二胡,我學聲樂,但文化課都是在一起上。
吳:附中畢業后您就直接上大學了嗎?當時大學是考的嗎?
孟:基本就不考,直接就上了,我高中上了3年,然后大學上了4年。
吳:那您上大學除了聲樂,還學什么?
孟:還學鋼琴,再就是文化課,中心還在聲樂上,但我當時鋼琴也很不錯,每次班里要上臺表演都是讓我表演,我的老師是潘麗浩。
吳:您畢業的時候多少歲?
孟:畢業的時候我23歲。
吳:您當時上音樂學院附中,有沒有說給家里減輕負擔什么這種想法,還是純粹就是喜歡?
孟:沒有那個想法,因為我們家里條件還可以。喬建中老師當時是因為他家孩子多,家里負擔太重了。1958年我考入西安音樂學院,師從朱培元老師和許芝蘭老師,當年她們來綏德招生,就把我招到西安音樂學院了。進入音樂學院后,我就跟李欣老師學習,我感覺李欣老師是我所遇到的老師里最好的老師,不僅在聲樂,而且在做人等方面,對我都有很深遠的影響,所以我畢業后,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會堅持走下去。
吳:您在音樂學院主要學習的是美聲還是民族?
孟:李老師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她教的是美聲,但是她是用美聲給我打的底子,唱歌還是以唱陜北民歌為主的。聲樂方面很多基礎的東西,比如氣息、喉頭的穩定等,都是按李老師的方法來,但唱歌還是教我唱陜北民歌。她覺得我多唱陜北民歌,將來畢業回到地方上有用。真正唱民歌還是在讀西安音樂學院時,雖然之前我就喜歡唱,但比較系統地學民歌還是跟李欣老師。李欣老師教的味道就不一樣,雖然說是陜北民歌,但味道跟我們以前唱的還是不一樣。
吳:李欣老師在發聲等演唱方法上是要求你們按照她的方法來嗎?
孟:李欣老師不這樣要求我,她覺得我唱得只要舒服,就是對的,她主要教唱歌的氣息,口腔要打開,喉頭要打開,這都是共通的。關鍵就是氣息,她對這方面要求得比較多。口腔要打開,至于唱的時候,好比說拐幾個彎,三個還是四個彎的,這些她都不干涉,由我們自己喜好,唱得舒服是第一原則。
吳:您當時在音樂學院上學的時候,上專業課也是一周上一節是吧?
孟:兩節課。有時候老師有空了,就跟我說:“孟宗伋快坐下,再給你上節課。”當時關系處得特別好。我從附中開始,就一直跟她學。
我非常感激能遇到這樣一個好老師。我們那個時候一個星期就要去臺上表演一回,就是班級或者系里的匯報,每次上臺前,李欣老師都會為我們整理頭發,看看我們扣子扣好沒,頭發整齊不整齊,拿我們就當自己的孩子一樣。
二、放棄省樂團回到榆林
吳:那您當時畢業有機會留在西安嗎?為什么要回榆林?
孟:我畢業就回到了榆林,先差點被分到省樂團去,我們一個班20人,僅有3人被留在西安工作,同學們都很羨慕,但我當時很不甘心,覺得自己學了這么幾年,最終就拿個合唱夾子唱一輩子,我自己心里覺得不舒服,當時就放棄了,想再去別的地方碰一碰。我是綏德人,沒有去過榆林城里,從小就聽說榆林特別好,而且榆林又靠近內蒙古,民歌素材比較多,所以我就想回榆林。那個時候西藏文工團想讓我去呢,覺得我能跳能唱,比較適合,結果人事局說沒有那邊的指標,當時是必須要有指標的,沒有指標就去不了。當時我在班里面還學得可以,就又問我要去哪兒,說我還可以去東方基建廠或者黃河基建廠,我說我不想去,就決定回陜北了,后面他們把分到榆林的那個人給調到靖邊去了,把我調到榆林了。
吳:您是哪一年回到榆林去的?
孟:1962年我就分到榆林去了,我當時背著被子,提著柳編的書箱子,當時一到榆林,我就覺得榆林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我當時檔案已經到榆林了,先去的民政局匯報。民政局的工作人員給我提供了榆林師范、劇團、秦腔團、榆林中學、榆林工會等單位讓我選擇,我最后選擇了榆林工會。我當時覺得工會接觸的基層比較多,開始上班后,也是苦惱了一段時間。那幾年,我一直就給各個單位輔導秧歌,每年過春節都鬧秧歌,我輔導過的每次都是第一名,所以當時鬧秧歌就有點名氣了。
農業學大寨時,我們縣上的領導就問我,你是音樂學院畢業的,你給我們寫上一首農業學大寨的歌,我就同意了,我寫的《榆林農業學大寨戰歌》一度在榆林傳唱度很高。后來,縣上領導又問我能不能組織一個農業學大寨的宣傳隊,從各單位抽有文藝特長的人,成立這樣一個宣傳隊(借鑒內蒙古烏蘭牧騎宣傳隊,他們一個旗一個旗去牧民家里演出),我又同意了,因為我在中學時期就經常搞這個。我當時在榆林各個單位抽了十八九個有文藝特長的人,有吹的、拉的、彈的、唱的,排練了二十天左右就下鄉去演出了。有次我們主任看到后也表揚了我們。我當時是這樣的,每到一個村子演出,下午就先去了解村里的好人好事、發生的變化,臨時編寫成歌,晚上演出時就在晚會上表演。所以當時這個宣傳隊走哪兒都受到大家的歡迎和好評。我們領導看了幾次演出后,提出想讓我壯大宣傳隊,于是就招進來十個人,把演出隊伍壯大了。
吳:當時你們排的都有些什么節目?
孟:有舞蹈、說唱、小戲等,當時編排節目以我為主,本來音樂學院里也沒有學這些,到工作后逼著人,都得去嘗試。
吳:下鄉演出中有什么難忘的經歷嗎?
孟:通過這些演出,我意識到,藝術還是要下鄉。我們有次到魏家峁下鄉,有個紅石橋公社,那時候整個公社都沒有電,我們下午就把爛棉花放到柴油里,捆住,然后悶到柴油里三四個小時,到晚上把這點燃吊到舞臺上,就相當于燈了。老鄉們都坐在地上,我記得天氣特別冷,演員們冷得都說要不別演了,但我看著臺下,這么冷的天,沒有一個人有要走的意思,坐得齊齊的,我當時就覺得這些人太需要文化生活了,我就說不行,再困難也要演。這場演出給我的印象很深,我深刻地意識到,廣大的農民需要文化生活。
1971年,宣傳隊改建成榆林縣文工團,由我出任團長,縣文工團先后排練了《劉三姐》《江姐》《蘭花花》《三十里鋪》《牧童與小姐》等歌劇和民族歌舞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其中民族歌舞劇《蘭花花》在不到兩年時間里,共演出100多場,演出場次這么多,在榆林還是頭一次,這也成就了一段榆林劇團演出史上的佳話。
這之后排演的節目也逐漸多了,當時下鄉還沒有汽車,連個手扶拖拉機都沒有,都是自己背著鋪蓋,拿著樂器。我當時還拉手風琴呢,也是自己背著手風琴。我們把榆林24個公社一個一個都跑遍了,村村都走遍了。那個時期演完反響很好,縣上開大會也表揚了我們,覺得我們能夠深入生活,能夠把當地這些好人好事表演出來。有一次我們到三岔灣演出,有個勞動模范沒來看戲,我當時就覺得真可惜,我就把手風琴拉上,再找了幾個唱歌的,去他家里面,給他唱了一唱,感動得他熱淚盈眶。我在這些年的下鄉演出中,深深感到了農村需要文化,群眾需要文化。有的地方連路都沒有,我們從榆林城扛著紅旗出發,步行90里,到小壕兔等地演出,點著煤油燈照明,一鍋洋芋糊糊就是飯。
吳:那所有的演出您都參與是嗎?
孟:都參與,雖然我是團長,但是演出都要參加的。
吳:那您還記得當時都有些什么節目嗎?
孟:那可太多了,《蘭花花》《趕牲靈》《三十里鋪》等陜北民歌,還有創作的《紅旗新歌》等,很多演完就沒再演了,又重新編。當時團里有個搞文字的,他寫詞,我譜曲,譜好之后就給演員們教。我譜曲時會運用一些民歌的素材。在1976年,縣上決定再次擴充文工團,又招了一批人,招了三十個人,都是十來歲的小孩,這三十個孩子一下就把文工團給充實起來了。
吳:那您招這些演員的標準是什么?
孟:有唱歌的,有跳舞的,但沒有院校畢業的。我記得當時有個演員叫章鴻燕,她爸是湖南的,娶了一個靖邊的妻子,家里有四五個孩子,當時來找到我說,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能不能把他大丫頭招進來。我當時就聽了一下,發現這丫頭說話咬舌,說大寨是“dà dài”,說紅旗是“dōng dī”,但是音樂感覺挺好,聲音條件也不錯。我不死心,把這娃帶到西安找白秉權聽了一下,她一聽就說這能唱得了歌。我只能自己慢慢教,給她一個字一個字地矯正,最后慢慢矯正過來了。后來蘭州軍區文工團來招人,要一個唱民歌的,當時文工團有個老師聽到章鴻燕唱了《秋收》,他聽完就去給單位匯報了。當時我們給章鴻燕唱歌錄了盒式磁帶。后面她就去蘭州軍區文工團了,剛去四五天,她就參加了全軍的比賽,得了獎。現在章鴻燕在北京呢。
吳:您在團里主要教什么?
孟:我在團里主要教聲樂,每天早上我拉著手風琴,帶著大家訓練聲樂,訓練完聲樂,就開始練功。練功請的是延安歌舞團的老師。那個時候縣上很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就聯系了陜西省歌舞團,帶學生去歌舞團學習了半年多,學完后回來立馬就不一樣了。
1981年,我們團參加省上第一屆音樂舞蹈調演,當時我們請了國家一級編劇、海政歌舞團團長霍向東,跟我一起排了一臺具有濃郁陜北地方特色的民間歌舞晚會。女生小合唱唱了《九連環》,舞蹈比較多,有陜北踢場子等,當時在演完后一下把觀眾給鎮住了。當時我房間隔壁住的是文化部的領導,看得文化部的領導們激動得一晚上睡不著,他們說都好多年沒看過這么具有民間風格的歌舞晚會節目了。因為當時流行的是鄧麗君等人唱的流行歌曲,民族民間的東西相對少一些,所以大家都對我們那臺晚會評價很高。1982年,文化部就把我們調到北京,給文化部和各個演出團體進行展演。
吳:是把您個人還是整個藝術團?
孟:把我們整個團調過去了,差不多在北京待了半個多月,給北京的其他文藝團體演出,讓大家都能意識到我們走的這條“民間”道路是正確的。在北京,我們的演出受到了很高的評價。
1982年7月,從北京回來后,榆林就正式成立了榆林民間藝術團,我是業務團長,把王向榮、六六旦等很有名的民間藝術家也都調進來了。那年我們去西歐演出了一次,反響也特別好。
吳:當時團里面招進來的演員都是有編制的嗎?
孟:是的,都是帶有編制的。
吳:那您工作后都跟誰學習過民歌?
孟:唱民歌的有上海音樂學院的王品素,我跟她學了一段時間。當時上海音樂學院有兩個老師來榆林采風,我給幫了一些忙,臨走時她們問我有什么要求,我說我想跟王品素老師學習學習,后面就幫我聯系了王品素老師。跟王品素老師學習,最大的收獲就是因人而異,不是一種方法,在每個人身上都能套,應該根據每個學生的不同情況,老師再決定怎么教。我剛開始跟王老師上課時,都是王老師講我聽,上了一段時間課以后,王老師讓我先說,我就把我的想法講出來,她再告訴我一些技術性的問題,如氣息一定要放下、別把氣撐那么大等。我們經常會探討,當時我和王品素老師關系處得非常好。
吳:當時跟王品素老師學了多久?
孟:學習了差不多半年。后來我們成立了民間藝術團,我們團請來了中央歌舞團的張樹楠,他是組織第一批陜北民歌合唱隊的人,當時在我們團里待了有差不多半年。這個合唱隊在綏德縣清水溝訓練了兩年,后來到了延安、北京,最終在北京解散了。
吳:當時是您把張樹楠老師請過來的?
孟:是我請過來的,從北京請過來的,當時我去北京,結識了張樹楠,我一說我是陜北的,他就很感興趣,主動提出想來。我當時有個想法,想著把張樹楠請過來后,能再組織一個陜北民歌的小型合唱隊。他在我們團總共待了三個月,臨走時,我去送他,他眼含熱淚,跟我說:“孟老師,你就這樣教學生,這條路是對的,我希望不久的將來能看到你的民歌合唱團。”我能感受到他對陜北民歌的熱愛。我們倆在學術上也是相見恨晚,聊得非常投緣,有時候聊到大半夜都不睡覺。后面他回北京后,我還去北京看望了他,現在他已經去世了。
吳:除了這兩位老師,您還接觸過別的老師嗎?
孟:我還跟金鐵霖交流過,他在教學方法上,也強調要有個性,但是金鐵霖的共性更多一些,他的共性和其他老師的共性還不一樣。我為什么能夠和金鐵霖交流,是因為我有個學生叫劉鴻飛,他從十一二歲開始跟我學,后面唱得一直不錯,我就把他送到海政歌舞團去了。他到了海政歌舞團后,歌舞團的領導又把他推薦給了金鐵霖,金鐵霖見了劉鴻飛后很感興趣,他就問誰給你教的,唱得一點問題都沒有,就這樣唱下去。后面金鐵霖又把他推薦給了空政歌舞團。有一次我去北京,在劉鴻飛的引見下,我見到了金鐵霖,他為人很熱情,對我的評價很高,說我“沒有把學生教壞一點”。我給他講了很多陜北民歌相關的東西,他告訴我,別的都挺好,這些歌的風格把握,就得靠我自己去琢磨,教得沒有問題,這從劉鴻飛身上就能看得出來,我給他基礎都打得很好。后面劉鴻飛學完回來后,空政歌舞團想留他,但榆林這邊怎么也不放人。
三、既是嚴師又是慈父
吳:那后面您就一直在榆林市民間藝術團?
孟:后面榆林地區辦了榆林市藝術學校,領導說我辦文工團這么多年有經驗了,讓我去辦這個學校,后面我就去當了校長,就在鎮北臺下面的窯洞,我在這兒又待了十年。到了這兒我培養了王曉怡和秦靖紅,秦靖紅參加了全國青歌賽,獲得了三等獎;王曉怡現在可以說是陜北民歌唱得最好的一個,她還主演了《歲月韶華》。我雖然是校長,但我也上課,我從來不給孩子們誤課,即便我有時候要去開會,給孩子們上不了課,回來后我也一定要給孩子們補上。我對這些孩子都非常好,跟自己的孩子一樣,到后來這些孩子也都叫我“孟爹爹”。我對這些孩子的原則就是,在學習上我一點也不放松,生活上寬容,調皮也可以,但是不能太違規。
吳:這個學校是什么性質的學校?
孟:這個學校的性質是中專,屬于陜西省藝術學校分校,這也是在我接手后。學校最開始是“背糧學藝”的,就是學生背著糧食來,老師給上課,但是畢業不分配,也就辦了一期。這批學生畢業后,也無法就業,那個時候我剛到學校,帶著學生們組織了一臺晚會,領導們看了后覺得學生們表現得很好,就把這些孩子分到榆林市的秦腔團,現在這些學生成了榆林市秦腔團的主干力量了。
吳:從您這兒開始,榆林市藝術學校就都包分配了嗎?
孟:從我開始,就開始包分配了。我就跑到省文化廳的藝術處,我就想問看能不能辦個省藝校的分校,后面通過陜西省藝術學校校長劉榮和省文化廳,辦了三個省藝校的分校,榆林一個,咸陽一個,安康一個,榆林市藝術學校是辦得最好的一個。榆林市藝術學校畢業的這些學舞蹈的孩子后面都到了榆林民間藝術團了。現在榆林藝術團里面跳得好的、能教學生的都是原來榆林市藝術學校畢業的,唱歌的現在挑頭的是王曉怡。
吳:那當時成立陜西省藝術學校的分校,直接就把學生都轉過來了?
孟:對的,學生直接就都轉過來了,畢業之后就都開始分配了。其實從第一屆學生開始,也是我給聯系的就業,就是我剛說的把他們分到秦腔團了。
吳:那您在榆林市藝術學校待到退休?
孟:是的,我在榆林市藝術學校一直干到60歲退休。
吳:您退休以后主要還在從事教學工作是嗎?
孟:退休以后主要還是教學,主要教聲樂,鋼琴也教。
吳:我知道第一批的陜北民歌十大民歌手有好多都是您培養出來的,您這么多年培養的這些學生里,具有代表性的都有誰?
孟:章鴻燕,咱們前面說過;再就是王艷霞,她現在在鄭州;雒敏,現在在廣州;尚平,現在在福州。再有榆林學院的楊婷、王蓓等人,都是我的學生,他們現在都主要從事陜北民歌的教學和表演工作。再下來就是王曉怡、秦靖紅、雒勝軍、雒潔等,反正唱陜北民歌的基本都跟我學過。
吳:除了學生還有其他人慕名來找您學習的嗎?
孟:雒翠蓮就是最早慕名來找我學的,她當時是在歌廳里唱歌,來找我上課,我看她聲音條件挺好,就開始教她了。
吳:您是只要對陜北民歌感興趣的都給教,還是您對學生還會有一定的要求?
孟:我主要是看學生熱愛不熱愛民歌,再看聲音條件、音樂感覺這些。
吳:您是怎么給學生上課的?
孟:首先要練聲的,就是美聲的練聲方法,基礎好的學生,就按正常的練,如果學生練不了復雜的,就讓他練兩個音的,比如“15”。練完音符就要唱短句,比如“13531”,就要把字套進去,像《茉莉花》《趕牲靈》這些都可以,練習短句就能練習到咬字。我還會給自己的學生講如何理解歌曲,從而將感情融入歌曲,避免把歌曲唱得沒內在、沒感情,吸引人的歌曲要唱得有感情。
吳:您的學生都識簡譜?
孟:大部分都識簡譜,五線譜少一些。
吳:您認為練聲最重要的是什么?
孟:腔體要靈活,能夠自主調節,這個能夠掌握好就可以了。比如吳碧霞,人什么都能唱,民歌也能唱,美聲也能唱,戲劇也能唱,她唱河北梆子唱得挺好的,這就是她的腔體會調節。喉頭的穩定性也是很關鍵的,不管唱什么,喉頭不穩定是唱不了的,喉頭穩定了,其他慢慢也就自然而然都好了,這跟蓋房子打地基一樣,如果地基沒有打好,房子肯定蓋得不穩當。
吳:那您在這么多年的陜北民歌教學中,有什么心得?
孟:老師一定要愛護自己的學生,就當成自己的孩子那樣,這也是我從李欣老師那里學到的。教學生的時候一定要有耐心,不要唱不對就批評他,越是這樣學生越唱不來,要一點點給他講透,這樣學生容易接受,學得會快一點,他和你之間沒有隔閡了,也敢放開唱了。
四、陜北民歌創作要像柳青那樣扎根基層
吳:您工作這么多年,還有什么別的感觸?
孟:回顧我這一生的工作,我認為做我這個專業的,不能浮到上面來,就是不能老在大地方,一定要去基層,到了基層后,雖然生活上苦一點,但學到的東西就會多一些。我記得安塞文工團請我去給他們輔導一段時間聲樂,希望我能排一個三人的小合唱,他們要拿這個合唱去參加比賽。剛開始我也很困擾,農民連譜子也不認識,后面我結合當地特色選了一首《小桃紅》,在《小桃紅》的基礎上,改編了一個無伴奏的三人小合唱,配了和聲。恰好我有個助手是延安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幫助我給他們三個訓練,因為他們不識譜,我都是一句句給教的。最后這首《小桃紅》參加全國第一屆群星獎比賽,獲得了全國群星獎,陜西省就這一個群星獎。
吳:這大概是哪一年的時候?
孟:這大概是八幾年吧,就在全國第一屆群星獎的時候。
吳:您是怎么評價這首民歌的?
孟:我覺得這首歌就是旋律很簡單,但加上和聲后,旋律就更豐滿了。后面吉天把這首民歌改成男聲版了。
吳:吉天跟你也學過是不?
孟:吉天學的時間不長。
吳:您還改編過別的民歌嗎?
孟:還改編過《黃河船夫曲》,是一個四部合唱。當時榆林臨時組建了一個業余合唱隊,要去參加比賽,請我出個節目,我那時手頭上有個《黃河船夫曲》的初稿,后來就定了這首。
這個合唱隊是由榆林師范學院聲樂系學生和機關干部組成的,訓練了一個月就去參加比賽了。當時參加比賽的總共有25個合唱團,有5個特等獎,我們的節目獲得了特等獎里的第一。參加完這個比賽后,我對陜北民歌又有一些感悟,陜北民歌應該像侗族大歌一樣,加點和聲進來,就會把陜北民歌突出得更好。
吳:您在陜北民歌方面的創作主要是把一些陜北民歌改編成合唱嗎?
孟:主要就是改編,我還改編過賀藝和白秉權的《圪梁梁上的二妹妹》,也在全省比賽得了第一名。因為陜北民歌就是這邊山上唱,那邊山上聽呢,是有回聲的。所以獨唱效果可能并沒有合唱效果好,我改編的時候加入和聲,好像就在黃土地里、山里邊,山山洼洼的回聲,會顯得陜北民歌更空曠些,更宏偉一些、厚實一些,更能體現陜北人宏厚、粗獷的性格。
吳:您覺得改編得比較好的就是《小桃紅》《黃河船夫曲》《圪梁梁上的二妹妹》嗎?
孟:主要就這三個能拿出手的,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民歌改編不要脫離陜北音樂這一素材,且要有生活經歷,要到民間底層去,去體驗、了解大眾的想法,像柳青那樣扎根基層,了解基層的需求,這樣才能夠創作出新的佳作來。陜北民歌能在全國甚至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有它的獨到之處,不管怎么改編或改寫,都應在這個元素里去改、去寫。
吳:那您自己想成立民歌合唱隊這個事情,最后成立了沒有?
孟:沒成立,沒有指標,再加上后來我到了藝校,主要都是教學的工作了,也就沒有再組建合唱隊了。假如我一直在藝術團,那我應該就成立了。所以我就覺著咱們西安音樂學院里面應該成立一個陜北民歌合唱隊,學校不是招進來了一批批陜北民歌專業的學生,還有聲樂系的學生,我覺得成立一個陜北民歌合唱隊還是很有條件的。
五、用新的概念去演唱陜北民歌
吳:在陜北民歌教學方面,您是大家公認的泰斗級的人物,我了解到很多民歌手,他們提得最多的就是您跟白老師,基本上都是跟你們學的。我碩士畢業論文寫的就是黃土地藝術團,所以當時跟雒勝軍、雒翠蓮他們都做過訪談。當時我就了解到雒勝軍以前在藝校學習時,他學的是山西梆子,但是他自己愛好民歌,就開始跟著您學習唱民歌。下面請您談談您對陜北民歌現狀的看法。
孟:我覺得現在唱陜北民歌的人多了,但是唱得出類拔萃的卻不多,真正能夠唱得很好的,別說全國了,就是全陜西都能唱得很有名的都不多。為什么呢?我認為就是亂唱,適合他的歌他也唱,不適合他的歌他也唱。再就是,現在都是民歌手,沒有經過老師的指導,大部分都唱得不順,厚度上卡得太多了。我認為應該在各個縣里成立短期的培訓班,起碼先把聲音給擺順,擺順以后,再對聲音的高或低進行調整,自己慢慢摸索。
吳:那您覺得當下陜北民歌的生態如何?
孟:現在環境變了,年輕人的喜好也變了。現在農村年輕人少,大多是老人,這種情況難以激發歌手對陜北民歌的熱愛。
你像綏德現在的秧歌,每天晚上都在扭呢,其實如果能夠把這些人組織起來,扭完秧歌以后再唱唱歌,把這些都加進去后,可能陜北民歌會扎根更深一些。動員他們多唱唱陜北民歌,這樣慢慢地可能就能有新的東西。
吳:現在我觀察到有很多陜北民歌手,是真的喜歡陜北民歌,但是也有很多民歌手,就是為了成名或者為了演出賺錢,可能就會唱那么幾首民歌。針對當下陜北民歌手的現狀,請談談您的看法。
孟:我覺得這個很不好,很不利于陜北民歌的發展。從現實出發,弄線上培訓班,這也很困難,我就覺得針對扭秧歌的人,大家扭一扭,唱一唱,這可能是一個方向。再就是政府部門也應當選拔一些比較好的苗子,對這些好苗子進行培訓,不能都讓農民去唱。
吳:傳統音樂在當下的生存狀態的確都挺難的,陜北民歌其實還算是生態比較好的,各方的扶持力度都比較大。
孟:所以我建議各縣文化館,扭秧歌的人,不能光扭秧歌,扭完秧歌一定要唱歌呢,或者邊扭邊唱也可以,今天唱這個歌,明天唱那個歌,慢慢地大家會唱的就多了。
吳:這個想法挺好,但現在的年輕人對陜北民歌的了解和關注度都很低,您有什么好的建議?
孟:這個是事實,我覺得還是可以進一步提高年輕人對陜北民歌的關注度的。
吳:請您具體談談。
孟:如果能編定陜北民歌的教材,把最簡單的陜北民歌印一個冊子,發到各個學校,上音樂課的時候,老師就可以給學生教這些,學生也會從小對陜北民歌有一個基礎認知。
吳:對于陜北民歌未來的傳承和發展,您還有別的想法或者建議嗎?
孟:現在時代變了,像我們小時候唱的跟你們現在唱的都不一樣了。有些重點人才,應該重點培養,培養出一批演唱陜北民歌的尖子,大家都跟著這些尖子的腳步繼續發展。再就是看你們這些理論研究者能有什么想法。
吳:其實挺難的,我們的有些建議和想法其實都淺薄的,只是站在個人立場上的一些觀點。因為我也做了一些考察,傳統音樂的發展牽扯的東西太多了,不是說我們想怎么樣就能怎么樣的。
孟:我覺得可以的,比如說定期到哪個縣里邊去,由政府出面組織人去教一教,教上兩個月或三個月,但這個不是一次結束就完了,需要長期進行。
從陜北民歌發展歷程看,1942年以前,陜北民歌在民間流傳得比較多。1942年后,好多文藝工作者來到陜北基層生活,搜集了很多陜北文藝素材,出現了許多優秀的陜北民歌。新中國成立以后,《蘭花花》在世界舞臺上得到金獎,新時期以來《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等一批優秀作品,將陜北民歌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在這之后,能讓人們眼前一亮的新歌曲似乎沒有了,而陜北民歌如何出新,得做很多研究。如何反映現實生活,如何反映生活變化等,這些都要用新的概念去演唱陜北民歌。目前雖然有一些歌曲,但和久唱不衰的《南泥灣》《我的祖國》相比差得太遠,很難流傳下去。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唱陜北民歌,這是一個好兆頭。
吳:其他您還有什么想說的嗎?
孟宗伋與學生畢業音樂會合影
孟:我學西安音樂學院辦的陜北民歌班有些松散,其實開辦陜北民歌班是個好事,但是太倉促了。
就應該有專門的人去編寫適合陜北民歌班學生的教材,文化課、即興伴奏課、視唱練耳課程等,都需要教材。
這樣再開始招生,孩子們進來學習有方向、有信心。可以針對陜北民歌班的學生開一些音樂鑒賞課,讓他們欣賞各個地方的傳統民歌,至少可以擴充他們的知識面。除此之外,學校也要組織演出實踐活動,提供實踐交流的機會。
六、總 結
孟宗伋是榆林綏德人,父親是中醫,所以也想讓他學醫,可孟宗伋卻偏偏熱愛唱歌跳舞。老師上音樂課教唱一首歌,他課余時間一定會唱上個幾十遍,在自己的摸索中他竟學會了簡譜。當時總政文工團、中央歌舞團、陜西歌舞劇院不時有人到綏德來采風,在班主任安老師的推薦下,孟宗伋有了可以跟專業人士接觸學習的機會,這對于長年生活在小縣城的孟宗伋來說,打開了他認識音樂的一扇窗,并有機會接觸學習東北二人轉、朝鮮舞等。
中學畢業后,孟宗伋考入西安音樂學院,師從李欣老師,主修聲樂,輔修鋼琴。李欣老師在演唱方面對孟宗伋細心教導,在生活上也無微不至地關心。李欣老師的教導不僅從聲樂方面,而且從做人等方面,都對孟宗伋產生了深遠影響。
1962年畢業后,孟宗伋回到榆林,先被分配到當時的榆林工會,從事行政工作,那段日子讓孟宗伋苦悶不已。農業學大寨時,他譜寫的《榆林農業學大寨戰歌》廣為傳唱。孟宗伋是當時榆林少有的聲樂學院派,掌握系統而科學的音樂知識。孟宗伋為農業學大寨宣傳隊的成立做出了重大貢獻,當時新招的演員都由他培訓,但學員們都沒有接受過正規訓練,教學條件也十分有限,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孟宗伋邊教邊學邊摸索。
1971年,宣傳隊改建成榆林縣文工團,由孟宗伋任團長。有了宣傳隊雄厚的聲樂基礎,在孟老師的帶領下,縣文工團先后排練了《劉三姐》《江姐》《蘭花花》《三十里鋪》《牧童與小姐》等歌劇和民族歌舞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烈關注。其中民族歌舞劇《蘭花花》在不到兩年時間里,演出100多場,成了榆林劇團演出史上的一段佳話。
為了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孟老師主動帶著文工團的演員去基層演出,一年有多半時間都在基層。
1981年,陜西省文化廳組織了“文革”后首場歌舞音樂調演,縣文工團作為榆林地區唯一的歌舞團赴西安參加演出。孟宗伋邀請霍向東老師編排了一臺具有濃郁陜北地方特色的民間歌舞晚會,這臺晚會艷驚四座,第一次讓世人知曉榆林還有這樣一支高水平的演出隊伍。
1982年,文化部專調文工團赴京進行示范表演,王向榮、六六旦等一批陜北民歌演員也隨團演出。
1982年7月,榆林民間藝術團正式成立,孟宗伋任團長,主抓業務,在發掘整理、繼承研究和發展陜北民間藝術方面取得了優異成績,培養了一大批具有極高藝術造詣的演員,這批演員也在后來成為榆林文藝界的中堅力量。
1989年,孟宗伋又被組織安排到當時條件艱苦、教學力量相對薄弱的榆林市藝術學校任校長,繼續從事聲樂教育工作。在這里他培養出了榆林民間藝術團和秦腔團的一批主要演員。
孟宗伋當初在學校學的是美聲,他以美聲唱法里的科學方法為基礎,融合陜北民歌特色,形成了獨特的陜北民歌教學方法,培養出了許多優秀陜北民歌手。
目前,陜北民歌在進一步向前發展上還存在不少問題,其傳承和創新就面臨著許多困難。孟宗伋提出了三點想法:首先,每天傍晚在廣場扭秧歌的人,都是出于興趣自發組織的,文化館可以讓這些人在扭完秧歌后學唱陜北民歌;其次,政府部門應當選拔一些比較好的苗子,對這些好苗子進行培訓;最后,音樂協會等部門可以選一些耳熟能詳的陜北民歌,印成一個冊子,發到各個學校,老師們就可以在上音樂課時給學生教陜北民歌。
孟宗伋老師作為陜北這塊黃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民歌代表,始終如一奮戰在聲樂教學的第一線,廣學博覽,刻苦鉆研。他在中國美聲唱法與民族唱法教學結合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條獨創的、適合自己的、別具一格的新路子,在聲樂教育方面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如今,孟宗伋的學生遍及北京、廣東、海南、河南、甘肅、四川、福建等地,為陜西乃至全國培養了許許多多優秀的聲樂人才,他們在各種聲樂比賽中屢屢獲得大獎。
(西安音樂學院)
參考文獻
[1] 霍向貴.陜北民歌大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
[2] 《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陜西卷[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0.
[3] 喬建中.土地與歌[M].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