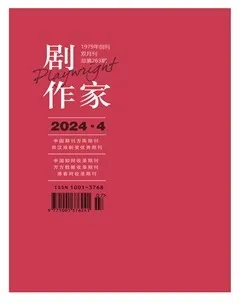純愛與真諦
摘 要:本文從對文學母題的傳承、戲曲文學性的追求,以及思想格調與表演特色的角度,對國內首部小劇場錫劇《紅豆》進行剖析。結論是,其對于文學性、思想性的突出表現,以及對情感與文化的思考,尤其是對于真摯情感的寫意化表達,是《紅豆》的藝術實踐獲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同時,這也對地方戲小劇場作品的藝術實踐具有開拓性和啟發性的意義。
關鍵詞:《紅豆》;文學性;小劇場戲曲
錫劇《紅豆》是國內首部小劇場錫劇作品,由無錫市錫劇院出品,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院長羅周任文學指導,江蘇省戲劇文學創作院創作部副主任俞思含編劇,中國評劇院國家一級導演安鳳英導演,無錫市錫劇院國家一級演員王子瑜、蔡瑜主演。該劇以昭明太子蕭統和女尼慧如之間的情感為主線,著力彰顯“小而不小、小中見大”的小劇場劇目創作藝術追求。劇目入選江蘇省藝術基金資助項目、江蘇省小劇場精品劇目、江蘇省小劇場演出季優秀劇目巡演、當代小劇場戲曲藝術節、中國小劇場戲曲展演,并在紫金文化藝術節小劇場單元展演中獲優秀劇目獎、最佳編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表演獎、最佳舞美設計獎,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劇場精品之作。
《紅豆》自問世以來,便受到諸多關注,尤其是受到了年輕觀眾的歡迎,在錫劇小劇場,以及地方戲小劇場的藝術實踐方面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探究其成功的原因,還要從文學與戲曲、情感與文化的關系中尋找答案。
一、山水有清音——基于文學母題的題材選擇
在中國文學史上,昭明太子蕭統以其過人的才情、文壇的號召力,以及《昭明文選》的編纂而擁有一席之地。《梁書》謂其“美姿貌,善舉止”,風姿出眾加之英年早逝,使得其本身便具有傳奇性、神秘性及若隱若現的悲劇性。這樣的人物自然是愛情故事所鐘愛的男主角。至于與其以紅豆為信物的女主角,以及這段過往的來龍去脈,則并不見于正史記載。編劇俞思含在創作談中提到,其將女主角設置為女尼慧如,創作靈感主要來源于《紅豆生南國——一個城市曾有的古典愛情故事》一書。該書圍繞昭明太子與慧如、范蠡與西施、梁鴻與孟廣、梁山伯與祝英臺這四對眷侶的愛情故事與無錫的聯系,編訂相關內容的散文,或抒情、或考證地再現出這些傳說在無錫當地人生活及中國文化中的巨大影響力。需要指出的是,后三個故事皆有戲曲作品演繹。《紅豆》的主創團隊選擇了相對冷門,但同樣重要的“紅豆”故事,可謂別具慧眼。并以其他三個故事在本劇中作為相思子開花的背景所在。全劇剛剛拉開帷幕時,歡喜石便言道:“掐指一算,千年間你不過綻放三次。第一次,范蠡西施,泛舟太湖;第二次,孟光梁鴻,歸隱梁溪;第三次,梁祝化蝶,善卷洞中。卻不知,要待到哪般情、哪般愛、哪般的相思情債,才能牽引你再度花開。”范蠡西施,是犧牲之后的久別重逢;梁鴻孟光,是亂世之中的相濡以沫;梁祝化蝶,是生生世世的生死相依。三者為本劇故事的展開提供了豐富的文學母題,并奠定了纏綿篤深的情感基調。
劇中的蕭統與慧如,一為太子,一為女尼,二人在宗教與世俗雙重標準中擁有著身份上的鴻溝及這道鴻溝帶來的禁忌感。這無形中增加了故事的張力。同時,宗教境界與世俗情感的交纏,也讓這一故事的生發有了風月之外、團圓之上的可能性。加之貫串全劇的“紅豆”意象,愈發顯露出愛而不得的悲劇性與破碎感。劇作中,顧山上的千年相思子是兩人情感的見證。紅豆樹的第四次開花,是慧如即將離別蕭統之際,面對蕭統的挽留,慧如言道:“今日相見,愈是歡喜;來日相別,愈添感傷。既知因果,何必執著。”這種透徹與隱忍,相比其他三個愛情故事的曲折、親密與悲壯,是清淡而趨于宗教意味的。相思的形態本不只一種,有一種,便是想要觸碰,卻最終縮回的手。為了無法相伴的所愛之人,強忍自己心中洶涌的情感,某種程度上是比恣意地釋放情感更加困難的事。
《紅豆》便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拉開帷幕。用錫劇對這個故事進行詮釋,恰如歷史上的昭明太子于湖上所吟左思《招隱詩》:“山水有清音。”錫劇藝術素來擁有“太湖一枝梅”的美譽,其“水八仙”般靈動清亮的聲音,是太湖的氤氳水汽與江南的人文情懷所孕育的。古紅豆樹,至今仍然矗立在無錫顧山,默默接受著往來者的情感寄托與美好祝愿。《紅豆》是誕生于太湖和顧山的作品,是錫劇與孕育其誕生的地方文化的結晶,亦是“山”高“水”長的地緣。從這個角度來說,《紅豆》對于錫劇的意義不僅僅是一部小劇場作品,也是焐熱歷史題材、以舞臺藝術呈現地方文化的努力。更為重要的是,它通過唯美的藝術形式,對幽微人心進行了一次深入的探究。
二、南朝風度——戲曲文學性的復歸
歷史上,蕭統所編選的《文選》一書中,有“古詩”十九首,頗為膾炙人口。清人陳祚明曾于《采菽堂古詩選》中評“古詩十九首”曰:“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蕭統與慧如便是這般“有情而不能言”。在“蠟鵝厭禱”事件發生之前,兩人不能言說的感情恰如紅豆——同樣出現在本劇中的蕭統之父梁武帝蕭衍曾有詩:“南有相思木,含情復同心。”以心印心,脈脈含情,并以此心此情觀己觀物,可謂是對男女主角情誼的真實寫照:他們之間的感情早已超越了男女之間的戀慕,從知己間的惺惺相惜,朝著藝術化的方向發展。在相思之外開創了另一重境界,又或者說,對相思進行了新的詮釋與補充。
除了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主線之外,還有昭明太子蕭統與其父蕭衍之間的父子線。綰合兩條線索的,則是慧如為了彌合父子嫌隙而做出的生命選擇。可以說,慧如不僅是《紅豆》的第一主角,也是本劇所塑造出的極具個人特點的角色。不同于以往文學傳統之中“思凡”的小尼師的情癡形象,她實實在在是一位修行人。除了對于蕭統不動聲色的深情,她對這個世界乃至自我,都有著一份冷靜而慈悲的觀照。面對蕭衍的心疾,其從佛教“六根”的角度予以觀照:“觀之眼,惶惶巡視眸光驚。觀之耳,肅肅而立聽微聲。觀之鼻,滴滴汗珠落沾凝。觀之舌,澀澀苦味自環縈。觀之身,搖搖虛飄兀奔行。觀之意,惴惴難安不息停。此六識,朝朝夕夕相纏繞,皆只因,心癥困囿未曾清。”蕭衍坐立難安、滿心猜忌的窘態,被清水明鏡般的慧如映射出來。無需任何臧否,便與蕭統的光風霽月形成鮮明對比。對于自身心底的情愫,她亦不是不知。蕭統是她平靜心海中唯一的波瀾。月圓之夜,她思慕戀人,一念心起,“暫擱經卷佛前放”,下山而去。縱然有過猶豫與抽離,她卻毫無小兒女的嬌羞之態,而是月入云端、水涌暗流般的清明。更為可貴的是,慧如不僅堅持自己對蕭統的愛慕,篤信蕭統對蕭衍的忠誠,也相信普遍存在于天地之間的“滴水恩、天倫親、相思意、知交音”。在她心中,虔誠、懇切、熱忱,是如同白蓮般高潔、如星月般璀璨的品質。正如康德所言:令他思之愈頻,念之愈密,愈覺驚嘆敬畏的,是頭頂上的繁星與內心的道德律令。在慧如心中,其修行正是令人性去除染污,開顯清凈。“縱然是風雨如晦、群山傾塌、海河流盡,也仍有不變之人、不改之心、不消之情”,為了這種信念,她選擇以自身為供養。慧如“枯泉重流,白浪自溢”的弘誓,不僅是在佐證蕭統的清白,化解父子的矛盾,更是彰顯人性的光輝與對這抹光輝的堅信。
同樣是消失在水中,蕭統最終自沉江心,并非普遍意義上的殉情,而更像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追隨。他追隨著自己對情感最初、最深也是最終的感知,慧如便是這種感知的具象化。相比于慧如,蕭統的感情更“癡”。劇中,其新選《高唐賦》《神女賦》《洛神賦》三篇情賦,皆是描摹朦朧飄忽、捉摸不定的形象與情愫。在那個為文不避駢儷、不厭雕琢,文學高度自覺的時代,《昭明文選》的編纂確定了一代文學之典范。蕭統對于“情”的感知,亦從個人之相思延展到對世情普遍性的描摹。《紅豆》所塑造的蕭統,亦有別于才子佳人題材戲劇中習見的風流小生形象——郎情妾意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權力地位更不是他的追求。對于文學的癡迷與熱愛,推己及人的敏銳情感,與心儀之人的靈魂共振,才是構成他生活的要素,亦是他與父親紓解心結的關鍵所在。劇中的蕭衍,已是一代梁帝。但當他白衣舞劍,追憶自己與“竟陵八友”的悠游歲月,其意氣風發,足以令云水般如如不同的慧如恍惚。彼時的他,與蕭統一樣,為了文章——這一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不飲不食不眠不休。他亦解得相思的滋味,亦是愿將那些細膩情感選編入卷帙的人。對文學與相思的熟稔,恰如慧如手中可以啟迪六識的檀香,能夠喚起對初心的體悟與回歸。
修文、參佛、相思,這是《紅豆》所展現出的南朝風度與文學傳統。值得一提的是,全劇從歡喜石的自白與訴說開始,由紅豆樹貫穿,就連以詼諧為本色的歡喜石,也有對相思的思考,足以見得慧如與蕭統的“至情”可以感動木石。并且這感動還足以引發另一種遐思:歡喜石在全劇結束時喃喃自語:“來世啊,我可不再做塊石頭,我也要當個人,去看看這相思是啥顏色?去嘗嘗這相思是啥味道?”這充滿向往的低語,讓受眾不禁想:這歡喜石是不是《紅樓夢》中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那塊羨慕人間煙火的補天遺石呢?這是屬于江南的浪漫與聯想,是文學世界的回響與互文,也是劇作留給熱愛文學的觀眾的彩蛋。
三、繪事后素——《紅豆》的情懷與情韻
“無情何以修文,無愛焉能參佛”是《紅豆》的主旨。這一題旨的文學化與舞臺化,都是存在一定難度的。宗教徒對于世人的悲憫,編纂者對于文學的熱愛,以及兩者之間欲說還休的細微情愫,都決定了本劇與大開大闔、汪洋恣肆的表達方式相異趣。本劇則以“淡極始知花更艷”的筆調,書寫了對于相思的多重思考,展現出獨特的情懷與情韻。演員們以自己的風采,讓人物從案頭上靈動地走來,將綿綿相思之意訴與觀眾聽。
蔡瑜所扮演的慧如,以其端莊典雅的形象與蘊藉深情的唱念,塑造出有別于以往戲曲中女尼、坤道的形象。下山、相約、面圣、沉水,皆是她的自主選擇。做出這些選擇的動因,不是世俗情欲,而是對內心理念的堅守。借用佛教中的說法,慧如的行為邏輯,并非被“業力”牽引,而是受“愿力”鼓舞。為了情,她自愿背負信仰意義上的罪業;為了所愛之人,她甘愿在淺淺一面之后即刻抽身而去;為了對世間普遍情感的真摯與神佛相證的篤定信仰,她自愿付出此世肉身消弭的代價。在清凈與至情之間,有勇氣承受內心的撕扯;亦可在堅持自己的選擇時,面對洶涌水流熙怡微笑。慧如這個角色,用她特有的力量感宣告“大女主”作品從來不只一種實現方式。
男主演王子瑜則在表現“父子線”時采用了一人分飾兩角的表演方法,運用不同行當的身段與唱念,來營造兩個角色之間的反差感。這也是本劇中最能體現小劇場作品“實驗性”的所在。尤其是蕭衍回憶往昔歲月時,脫去象征皇權的袍服,回歸白衣,但仍然戴著髯口。此刻的蕭衍、往昔的蕭衍與不戴髯口、至誠率真的蕭統,雖為一人扮演,卻是歷歷分明。此處的藝術處理賦予髯口新的功能,即在劃分角色行當之外,另有展現同一角色的年齡變化的作用:歲月讓風采風流的少年,變成了工于心計的帝王,執筆之手最終執刀弒君,縱然再穿上白衣,胸前長髯卻如同樹木的年輪一般,宣告著時光與少年心性的一去不返。
除了一生一旦兩位主角之外,本劇的角色還有一木一石。歡喜石以丑角應工,為劇作平添了詼諧與跳脫,且具有敘述者的身份功能。相思子則除了開場時的自我介紹之外,再無曲白。她以冷峻的目光,見證著這段不俗的感情。舞臺上千絲萬縷的紅線,展示著男女主之間的情感糾葛。相思子則是紅線的司掌者,那剪不斷理還亂的紅線,在她的掌中交纏、變幻,勾勒出蕭統與慧如的宿命感。兩人情濃之時,她則用水袖表現紅豆樹開出白色花朵的場景,用靜默的純潔歌詠這段別有根芽的深情厚誼。極盡精簡的舞臺與演員陣容,卻構成了冷熱相諧的舞臺畫面。
《紅豆》作為第一部小劇場錫劇,其并不以小劇場本身所具有的“實驗性”“先鋒性”為主要追求目標,而是發揮戲曲在傳情寫意方面的優勢,以“情”與“韻”為藝術特色,將留白之美發揮到極致。
中古之后,“紅豆”意象頻繁出現于文學作品之中。王維以盛唐人的自信,宣告“此物最相思”。敘事文學奇珍《紅樓夢》中,寶玉擊箸而歌,吟唱著“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點點斑斑的相思子,正是相思本身的樣子:鮮紅、熱烈、富于顆粒感。錫劇《紅豆》,則以紅豆樹所開花朵的潔白、心心相印的默契,以及汩汩的白水,刷新了人們對相思的認知。它正是以這樣一種玲瓏剔透的表達訴說著真情的可貴。在講求“搞事業”“水泥封心”成為普遍風氣的當下,似乎輕言“純愛”與“信仰”都是奢侈而不理性的。然而真情從來不應該因為稀缺而受到質疑,追求真情并為之付出也不應該因為難得而遭受詬病。或許這就是《紅豆》的意義所在:它讓我們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人際關系與瑣碎生活里,仍然可以相信,這個世界上仍然存在隱忍而克制的愛,也仍然存在愿為這份愛舉身赴清池的力量。這份愛與力量,亦足以消融血液中的冰凌。
《紅豆》是一臺素雅而清冷的戲,但它真誠的內核是如此灼熱,熨燙著每一顆鈍感而麻木的心。
責任編輯 姜藝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