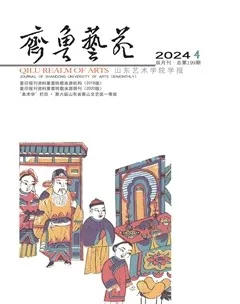“山的那一邊”:20世紀20年代國產電影的現代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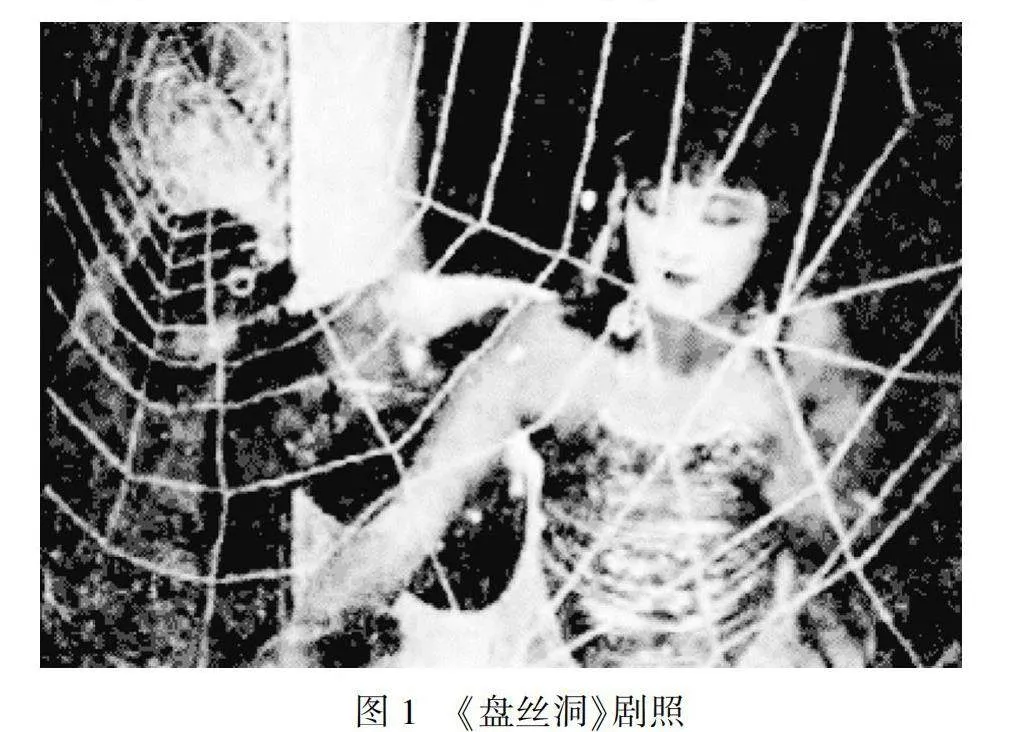
摘 要:從“可見性”的話語被納入社會建構的體系中開始,電影在形塑國人的自我認知、主體意識和現代想象方面,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20世紀20年代是國產電影漸趨興起的初始階段,來自不同背景的創作者紛紛借助電影媒介呈現社會轉型時期的現實狀況和異域景觀,啟發國人的現代意識。在中國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中,電影人通過視覺修辭和批判言說,以不同的敘事策略和話語形式,于改編、身體和空間三個層面,引導國人通過視覺手段營造主體意識和現代想象,實現了影像對社會的再建構及對現代的想象與啟蒙。
關鍵詞:20世紀20年代;視覺性;想象;現代性
中圖分類號:J9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236(2024)04-0078-09
19世紀中后期,中國進入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轉型時代(1895—1925)”[1](P2),“轉變”與“不穩定”幾乎作為普遍特征表現于后發國家現代文化演進的過程之中。早在16世紀甚至更早,人們就已經普遍認為現代是以視覺為中心的。而對于中國而言,“大部分新的文化形式和視覺話語都是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被引介到中國的”[2](P14)。彼時,人類經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視覺革命,視覺圖像在捕捉現實的基礎上,進行“想象”的再加工,并作為一種啟蒙手段,引導國人“觀想”外部世界。
視覺圖像早期便已通過雕塑、繪畫等藝術手段來影響人們對世界的感知,但攝影技術的誕生,卻足以成為打亂我們視覺體系的裝置,常常被看作視覺現代性的象征。而電影以對現實世界的“再現”和映射,“挪用現實的表象而作為語言的可能性,也成為了現代性表象最重要的載體”[3]。其作為一門科學技術,同步于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成為當時國人看向“遠方(外部世界)”、感知現代的重要媒介。這種感知并非僅由觀看內容決定,而是隱含在觀看過程中,即觀眾基于銀幕“幻象”引發的未知想象力,帶領其“駐足”于特殊的位置,注視從未踏足過的領域,以電影為媒介連通世界。因此,“將對電影的理解從物質實體轉向一種與電影觀看相關的媒介實踐過程”[4],便可以發現,電影作為再現物質現實及以想象為目的的媒介,開拓了人們的想象空間,給國人提供了打開眼界,了解“山的那一邊”是什么的途徑。
想象具有“把人的意識中不在場的意義于心靈中在場的能力”[5](P161),想象力一直作為審美認知和審美實踐的重要來源,作用于文學藝術的創作與接受過程。在現實與想象的合力下,科技與想象并存的電影,推動中國向現代發展,并使觀眾把對現代性的想象和體驗,置于對電影媒介的感知和體驗過程中。因此,考察早期國產電影的現代想象,不僅不能忽略作品的意義視角和時代的發展維度,同樣也不能將“觀察者的歷史簡化為技術和機械實踐的變遷史”[6](P15)。我們試圖將電影史研究納入到視覺文化的研究中,以求探究早期國產電影身后的視覺機制、想象空間和文化意義。由此可以提出如下問題:20世紀20年代的國產電影,通過哪些方面的視覺內容,建構了國人的現代想象?這些視覺內容如何引導國人在本土想象異域世界,從而轉變為具有現代意識的現代觀眾?這構成了本文對早期中國電影史展開研究的核心話語邏輯。
一、改編想象:文圖對話與想象力重構
電影的誕生(1895)與清末民初中國思想的轉型運動,在時間上歷史性地契合在一起,電影作為新興的現代產品,與當時的中國開始打開國門嘗試接受現代思想的舉動放在一起,便順其自然地成為了20世紀初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重要見證。根據《游戲報》的一段記載,可以看到當時的中國觀眾對電影初入中國時的認識:“近有美國電光影戲,制同影燈,而奇巧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座客既集停燈開演……觀者方目給不暇,一瞬而滅……觀畢,因嘆曰: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如蜃樓海市,與過影何以異……千百狀而紛呈,何殊乎鑄鼎之象?乍隱乍現,人生真夢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觀。”[7]對于觀眾而言,電影同時作為科學技術和文化形態訴諸于觀眾的視覺,接受并想象遙遠的現代世界。
湯姆·甘寧(Thomas Gunning)認為1905年以前的電影沒有被敘事沖動所主導,當時絕大部分都是以“可見性”(visibility)為中心,以視覺奇觀為主導的“吸引力”電影。直到大衛·格里菲斯(D.W.Griffith)作為電影話語轉型的典型代表,將電影作為一個符號與敘述故事和自我表達聯系在一起后,電影手段才從顯現“吸引力”轉變為戲劇敘述的元素。[8]電影在中國誕生以后,并未直接步入以敘事電影為主導的創作,直到張石川和鄭正秋于1913年導演的《難夫難妻》上映一段時間之后,即從20世紀20年代《閻瑞生》《海誓》的出現為肇始,才逐漸轉向故事片創作主導。20世紀20年代,成為了國人自制電影集中創作的第一個階段,這一時期約有650余部電影上映。
雖說敘事電影的流行使電影手段從顯現“吸引力”轉變為戲劇敘述的元素,但這種戲劇并非中國的傳統戲曲或早期沒有正式劇本的文明戲。如果沒有電影劇本,中國電影就很難擺脫其在“電影藝術”上的邊緣地位,也就無從建構自己獨特的藝術特色。因此,在中國20世紀20年代上映的電影作品中,有一部分便是直接來源于對中西方文學的改編,并且導演們選擇改編的文學作品,大都體現出一種“先進性”與現代性。
琳達·哈琴(Linda Hutcheon)將文學改編看作“一種帶有變化的重復”[9],利用媒介對源文本進行一定程度的改變,在改變過程中經由現實與想象創造出新的故事世界。而如果從受眾對故事世界體驗的角度來考察文學改編,那么20世紀20年代由文學改編而成的電影作品主要有兩種模式:訴諸想象(敘述模式)與訴諸認知(展示模式)。[10]在觀眾的接受過程中,想象是自愿的,也是被動的,但想象力的產生是一個在形式直觀中“目擊象存”的過程。改編經典作品歷來被視為電影制作人的不竭源泉,事實也證明,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行業對中西方文學作品的改編,不僅緩解了當時電影劇本短缺的問題,更使得中國電影迅速走上了“藝術”道路。
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人對改編自“名小說”電影影響力的認同,可以從當時的報紙文章中窺見一斑。《國產電影取材名小說之先聲》中寫到:“歐美電影。名著者類皆摭拾名家說部。如《賊史》《羅賓漢》《歌場魅影》等。胥署名重一時之著作……斯不特林琴南之文學。益為名重。而原著者迪根斯之思想。亦能灌輸我讀者矣。故攝制家以名小說為電影之劇本。其名貴是可想見。毋怪電影既成。映諸銀幕。自欲空巷有觀矣。”[11]從對改編自“名小說”之電影的“名貴”“空巷”等描述中,都能看出早期影人對此類作品的信任。
改編想象是20世紀20年代國產電影的一大創作策略,在從文字到圖像的轉換中,也完成了文學想象到視覺想象的轉變,觀眾能夠更為直觀地通過電影這種現代形式以及電影作品中蘊含的源文本精神和理念,初步形成對現代的想象認知。管海峰導演自述其在外國環球雜志上看到有人將電影稱為世界三大產業之一,并且其又有戲劇藝術的基礎,便想拍一部電影。而談到為何會拍《紅粉骷髏》(1921)時,管海峰自述:“尤其在中國,當時除有滑稽無聲短片以外,還沒有長故事片,因此我就想嘗試拍攝一部長片。劇情的選擇十分重要,我從中外偵探小說中挑選出一部比較精彩的故事‘保險黨十姊妹’,就決定以此為藍本加以改寫。”[12]
影片以十姊妹組成的保險黨誘騙青年人,獲取保險賠款為故事主線,直至最終案件被破獲收尾。對于《紅粉骷髏》這部作品,彼時報紙廣告如此描述:“真馬上臺,全體西裝,全堂西樂,偵探好戲。”[13]影片集脫胎于現代小說的偵探故事、教育警示的主題內核、仿照美國電影的布景方法、象征現代的西裝和汽車、當時流行的“中國式”武打風格以及貼近社會現實的滑稽愛情于一體,最大程度地調和了傳統舊戲、新劇向現代電影過渡而產生的矛盾,謹慎地接受著陌生的現代化表征。觀眾一方面經由對西式布景方法、西裝和汽車的觀看,實現對外部世界的想象,并與外部世界產生聯系;另一方面跟隨影片的故事內容,從思想上接受和延伸對現代的想象。
小說和電影作為不同的媒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是對媒介間性的研究,不應只集中于不同媒介在其特殊性基礎上的相互碰撞,同時也要考慮時代背景、文化區隔及媒介差異。早期電影的形式特征,并不等同于對戲劇的原始模仿,由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創作實踐,也并非只是簡單的用圖像代替文字的行為。
20世紀20年代改編自小說的電影,之所以能夠在觀眾與影片的表現形式及內容之間建立想象關系,尤其是對“現代”的想象,不僅是因為其依賴于電影改編小說形象后的“陌生化”效果和電影在時空上的影像效果,即觀眾在視覺上的現實印象,而且還依賴于電影富有包容力的“公共視野(public horizon)”[14]以及小說中所體現的現代性話語被符號化轉譯的結果。在這一視野和作為符號與鏡像的轉譯中,“富于解放性的沖動與現代性的癥候同時被反映、拒斥或否認,或被改變或得以協商,新的大眾公共也讓自己和社會看到自己的形象”[15]。在作為公共場域的電影中,觀眾憑借觀看和想象在視覺無意識中體認其身份的改變。
朱瘦菊導演的鴛鴦蝴蝶派電影《風雨之夜》(1925)的故事原型是英國作家亨利·萊特·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93年的小說《碧翠斯》(Beatrice),林紓將其譯為《紅礁畫槳錄》,朱瘦菊又在此基礎上,改編為電影《風雨之夜》,這部典型的轉譯自西方小說的電影作品,見證了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嘗試和努力,同時也暗含著對接納“現代性”的矛盾心理。原版小說《碧翠斯》創作于英國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期,著重表現了時代主潮對現代秩序的建構,以及試圖消除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帶來的社會混亂的某種實驗,小說內容以悲劇結尾,意在探討現代社會制度下人們對“女性”和“婚姻”認知態度的轉變。而被改編的《風雨之夜》,則是以大團圓式的結局,展現了一個“浪子回頭”的故事,同時也通過電影創作表達,回應了當時中國各界對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憂思和矛盾情緒。雖然《風雨之夜》對原版小說中的結局和人物都做出了較大改動,但影片內容和思想均可看出其深受西方現代小說符號化轉譯后影響的痕跡。《國文周報》也于1925年評論此片“使觀眾覺有西洋浪漫色彩至快感”[16],而改編和譯介的行為,本身也是“現代話語與中國文化傳統的競爭與協商,是回應西方現代性的一種方式”[17]。
李澤源導演,侯曜編劇的“新派”電影代表作之一《一串珍珠》(1925),改編自莫泊桑創作于1884年的短篇小說《項鏈》。《一串珍珠》不但體現了電影在技術上的精進,同時亦呈現了西方現代文化逐步與中國傳統相結合的趨向。《一串珍珠》中,侯曜保留了原小說的基礎人物關系,建立重新語境化的中國敘事特征,在傳統基礎上書寫并建構了其對現代的想象。影片主旨是“攻擊虛榮,總結懺悔”[18],但從法國到上海,從假項鏈到真珍珠,從字幕中文言文、白話文與英文同時出現的改編細節,都可以看出創作者對現代的想象和訴求以及對傳統與現代的調和嘗試。文章《評〈一串珍珠〉》中記載道:“全片的字幕比較從前來的進步,因為他們已經顧到字幕的本質美了。‘君知否君知否,一串珍珠萬斛愁,婦女若被虛榮誤,夫婿為她作馬牛’”[19],并評論道短短幾句話就能抵得上白話文一大篇的劇旨說明。但具體到作品內部,白話文在影片的字幕中頻繁出現,英文同樣也是。“新文化來自于構成現代性文化語境的共識,這種共識表露出自1840 年以來中國屢次受挫后對自身在世界地位的重新認識和訴求于現代化的愿望。”[20]因此,這種改編以及文化轉譯所體現出的不穩定性和流動性,正是電影人和觀眾對“新文化”和“現代性”未知想象的心理表征。
20世紀20年代的國產電影,大量使用文學改編,除了劇本短缺和藝術探索的有意為之,19世紀40至50年代“小說的圖像主義”轉向,更在視覺基礎上,為之后讀者、觀眾接受電影做了鋪墊。雖說早期由小說改編的電影,傾向于強調互文性,忽略了觀眾的感官體驗。但實際上,我們都一再面對“視覺感受作為現代主導感官這一普遍存在的事實”[21](P77),攝影圖像的誕生和普及,也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小說內容展現及讀者體驗小說的方式。更為顯在的是,早在“19世紀40年代晚期,小說已經開始提供特定種類的視覺描述”[22](P515),這些小說通過提供視覺信息,讓讀者有了“讀”的行為視覺化的感知,將小說媒介和“觀看”行為聯合起來。如此,觀看什么以及如何觀看等“視覺性”思想,早在電影誕生之前,便已經成為了語言表達的重要推手,它意圖讓接受者獲得某種視覺特殊性。
另外,20世紀20年代“新文化運動”初興。此時,文學作品的“新化”帶有強烈的西方色彩,由此改編自中外文學作品的電影,也隨之有同樣的傾向,再加上電影本身作為西方現代技術和文化傳入中國代表的特殊定位,使得現代小說和電影同時以圖像化、視覺化的手段,賦予國人諸多現代想象。小說作為傳統媒介,其內容信息的圖像化轉向,縮短了觀眾對電影這種新興技術的接受距離,也滿足了觀眾源自小說的視覺期待,而電影創作也在視覺表達上靠近語言。二者呈雙向哺育的態勢,同時通過視覺和文字在空間和認知上的雙重經驗,給予觀眾現代圖景的對照和對現代生活的想象與“體驗”。
二、身體想象:身份危機與肉體烏托邦
電影作為較早出現在中國且具有公共性質的現代產品,率先將“外部”世界的景象,通過電影媒介動態化的形式,呈現于國人眼前,建構國人的現代想象。不過相較于文學而言,“身體”的登場,在早期中國電影銀幕上,呈現出一種更為矛盾性的現象存在。
一方面,電影將視覺的真實性,建立在身體的質感和運動之上,通過其不可避免的物質性、空間性和時間性基礎,營造“真實”幻象,從而想象“外部”世界。然而,至少在《莊子試妻》(1914)出現之前,中國早期電影的身體實踐觀念,都是將女性身體排除在外的,原因恰恰是電影所具備的公共屬性。也就是說,在中國最初的實踐過程中,公共性的電影生產,試圖將女性的身體“私人”化,阻止其進入公共空間。另一方面,早期電影又與“現代身體”密切相關,這種“現代身體”,尤指女性及其身體在公共場域中的公開展演,無論是以畫報、照片還是電影的形式,都被視為人們試探和表征“現代性”的一種方式。例如《棄婦》(1924)中的芷芳和月鳳、《玉梨魂》(1924)中的梨娘、《風雨之夜》中的城市女性——莊氏等形象的逐漸誕生。因此,雖然性別化差異是傳統中國的典型顯現,但女性的“身體符號”,通過電影媒介,從“私人”空間邁向公共空間的實踐,不僅代表著人們對“現代”的想象和嘗試,而且使得女性的性別屬性,在現代社會建構和文化建構過程中,也具有了獨特的身份意義。
有基于此,在早期中國電影的銀幕實踐中,“身體”存在矛盾性的原因何在?電影人回應這種矛盾性的策略,便部分解釋了20世紀20年代起,女性形象在中國電影銀幕上的頻繁變革實踐的特殊地位。縱觀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電影始終呈現著“分擔國家命運同時又滯后于中國思想史與文化史”[23]的微妙特征。從“身體”的視角來看前一個特征,實際上早在18世紀,“身體便進入了‘知識控制’與權力干預的領域”[24](P26),被政治寓意所包圍。“身體”作為國家民族的隱喻,同時以對象和手段兩個面向,作用于社會發展。在“對象”層面上,民族國家身體與個人身體互為因果,奠定了國族認同的基礎。在“手段”層面上,個人身體的銀幕實踐,又在比較被動的情形下,承擔著分擔國家命運的責任。
“不同時期的激烈斷裂,并不總是伴隨著內容上的完全改變,更可能是某些現存因素的重組。”[25](P200)20世紀20年代的文化改革,打破了傳統中國既有的社會結構和話語形態,對西方現代文化秩序的熱情,表明了對傳統的反抗,其中對性的壓制性話語的反抗和性別觀念的改變,便是表現之一。在這之前,女性在電影這樣的公共場域中幾乎“不可見”,她們的日常生活狀態與公共影響力也被有意忽略。以《閆瑞生》(1921)為發端,在此后的中國電影作品中,女性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影片《閆瑞生》便設置了一個通過真實妓女扮演妓女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女性通過電影進入公共領域,給男性帶來了一定的身份危機,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并非僅是女性主動要求改變現狀的結果,還取決于彼時民族國家在動蕩的轉型中對女性身體的需求。也就是說,社會文明發展的動力,既來自于身體的主動需要,也來自于對承載“欲望”的身體的征用。因此,觀眾將電影中的女性身體作為圖像以及承載圖像的媒介,在視覺上把對“現代”的想象嫁接到對“身體”的想象上。從而,探索女性便是想象現代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不僅能夠滿足觀眾的視覺愉悅,還能使其通過女性身體想象現代。當然,女性的登場看似跨越了傳統,確立了女性在社會中的現代結構,也滿足了觀眾的娛樂需求和對現代的想象,在政治性與娛樂性中共存,但實際上,其大多數都被作為滿足民族國家需求的激進表達和召喚即將出場的男性而存在。因此,雖不可否認女性及其身體在該階段所體現出的先進性和現代性,但同時要承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引發了女性的身份認同危機,具體體現為一種斷裂性,即本質上的錯位感與時代上的疏離感。
以《盤絲洞》(1927)為例,影片取材自名著《西游記》“盤絲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和“情因舊恨生災毒,心主遭魔幸破光”兩回[26],故事設定為一群蜘蛛精偽裝成“美女”誘騙唐僧,準備吃唐僧肉的情節。《申報》對此片的描述為:“(美)仙女戲浴,(奇)真鷹竊衣,(趣)強迫成親,(神)杯中悟空,(驚)刀劍齊飛,(險)火燒魔窟。”[27]同時,導演但杜宇在角色的服裝設計上也很有想法,“每一套服裝,恒在百金之上,如蜘蛛精所穿之衣,遍體鑲鉆,光耀燦爛,其價更屬倍蓗”[28],其又賦予電影版本中的蜘蛛精角色以“情”的特質。“仙女戲浴”、情欲和情感元素的設定,不僅豐富了蜘蛛精在電影中的“少女”形象,還凸顯了其“人”的特質(如圖1[29])。
女性身體以裸露的肌膚和曼妙的姿態,在公共媒介中的表演,最大程度地挑戰了傳統和男性。在影片中,這些女性不僅在視覺上體現為美麗和誘惑,其在身體和武術方面,也不亞于男性。影片以商業性和藝術性并存的視覺奇觀以及凸顯女性社會主體意識的方式與現代精神相契合,為觀眾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想象空間。通過《盤絲洞》,將觀眾對蜘蛛精“私人化”的個體想象,轉變為一種公開的視覺想象,借助現代語境,公開表達對欲望的直視和對美的追求。電影文本內的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了更為具象化的現代特征指稱,其中女性主體也通過身體呈現,完成了自我意識的表達。但影片的結局,也恰恰說明了早期中國電影在試圖接受“現代”時的謹慎心理以及對現代性的“批評”。影片結尾,蜘蛛精被孫悟空燒回原形時,“只為了情欲一念,卒至自焚終身”[30]的字幕緩緩出現。這種策略雖然調和了現代視覺奇觀與傳統社會規范之間的矛盾,但也凸顯了女性在表達主體意識時所遭遇的復雜身份危機。女性身體成為平衡20世紀20年代社會轉型帶來的不確定性的工具,但由于它是通過視覺機制來發揮作用的,因此又以給觀眾提供奇觀想象的方式,來調節不穩定性。
如果說《盤絲洞》只是在外部視覺上充滿現代性想象,而對女性意識的凸顯,在本質上依舊傾向于傳統的話,那么《紅俠》(1929)在內在表達上則更為“激進”。在《紅俠》中,男性主體始終處于核心話語結構之外,金志滿是傳統男性的代表,同時也是欲望的化身。八位只穿肚兜和短褲的女性,散布在金志滿所處的空間中,通過女性身體的暴露,在視覺上強化了他的“傳統性”,以吸引力奇觀構建觀眾對女性的想象,也是對現代的想象。而文仲哲作為一個文弱書生,更無法進入社會結構的中心發揮作用。兩位男性主體在俠女蕓姑面前均處于“示弱”狀態。而影片中蕓姑復仇并成功的敘事語言,表明了女性在當時社會結構中的登場和勝利,但蕓姑身上所體現出的獨立女性意識之確立,是以“俠女身體的去欲望化”[31](去性化)為代價的,女主角成為了反映社會問題的主體。換言之,蕓姑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是因為其主動消解了自身欲望,以此方式與傳統社會“求和”,并以一種溫和的成功,迎合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通過女性身體指涉,現代不僅是文化改革語境中女性主動爭取的結果,同時也是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的必要需求。女性主體通過在電影這樣的公共領域中的表演,將女性的歷史和欲望公開置于社會結構中,賦予女性“新穎的”、獨立的現代身份,并以此在視覺和意識上建構了觀眾對現代的想象。當然,就像《盤絲洞》或《俠女》展示的那般,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無論是女性身體的公開表演,還是女性主體意識的凸顯,其中都涉及了復雜的社會因素。女性凸顯了其主體意識和現代身份,從這個角度來看,進步意義顯著,但不僅局限于此,其同時還充當著民族國家轉型時緩解困境和矛盾的工具以及對男性主體的“轉性化”再現。
與其說20世紀20年代女性身體在公共領域的表演所凸顯的女性意義的確立是一個視覺過程,毋寧說是對文化與現代想象的符號化代指。承載女性身體的圖像,并非僅因其“可見性”而被確立含義,還因“觀看者賦予了它象征意義與一種精神的‘框架’”[32](P466)而顯現存在價值。事實上,視覺奇觀是對可能提供的東西的想象,而非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因此,女性身體在電影銀幕上的實踐,歸根結底是一種意向性活動,它由身體對象主體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對話構成,并通過電影媒介來實現,表征為女性身體的公開展演。換言之,女性身體及其銀幕表演是建構觀眾現代想象的一種方式,也是中國向現代轉型的重要表征,但是這種在變革時期由多種因素所塑造的現代女性,在視覺呈現和意義確立上,都帶有一定的不穩定性和想象性。
三、異域想象:空間實踐與都市“形象”建構
電影、女性、都市與現代“多面一體”,“婦女是都市現代性的寓言和轉喻 (metonymies)”[33],都市卻以空間為載體,更為“具身化”地容納了眾多國人對現代的想象和“體驗”。都市以一個開放、時髦的姿態,進入傳統的中國社會,其自身蘊含的特性與“現代”不謀而合,上海以及為數不多的通商口岸,便是當時中國最接近都市的空間。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都市是人想象的產物,其映射的是開放與現代。在眾多想象異域空間的途徑中,電影提供了最為直觀的通道,觀眾通過電影,完成了對都市和現代的想象性建構。
20世紀20年代的國產電影和都市之間,并非簡單的主客體關系,而是一種共生關系。電影和都市相互呈現,又相互指涉。一方面,電影和都市都作為訴諸于“可見性”的視覺對象,以表征現代的用途,分別被嵌入都市景觀空間和電影影像空間,打造了基于圖像的、想象中的現代都市。另一方面,二者又同時作為地理意義上實在的電影空間和都市空間相互交織,引導觀眾在“幻象”中進行空間實踐,“具身化”地體驗現代都市,通過視覺內容經驗化地想象現代世界,基于都市的空間形態,建構現代社會。
想象作為一種“體驗”現實的方式,與電影合力,共同將意識和記憶賦予都市空間,同時又把現代都市的外部形態納入視覺意識,讓早期的國人觀眾在視覺無意識中跟隨電影生產的都市空間想象現代世界,感知現代秩序。這種想象雖然是基于“看”的行為延伸的,但這并非只是觀眾在一個特定空間中看到另一個空間,從而想象該空間的簡單過程,而是瓦爾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所謂的“身體與圖像空間”的交互。都市空間內嵌于圖像空間中,成為現實與影像化現實的合體。因此,空間(電影中的都市空間、實體的都市空間、電影院)不僅作為內容和中介,同時在媒介基礎上,也作為“媒介行為”在觀眾想象現代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媒介行為強調的不僅僅是媒介的連接作用,而且“聚焦于媒介的實踐,關注媒介所涉及的動態的中介實踐和過程以及對人和社會產生的不同面向的影響”[34]。換言之,無論將空間作為視覺對象,還是文化對象,來想象異域世界,其都是一個基于空間實踐的整體過程。在觀看過程中,觀眾通過電影媒介,短暫地實現了主體置換。在現代化的影院空間中,其“游走”于影像化的都市空間,通過空間中的都市象征物和都市意識想象現代,形塑了實際生活空間之外的現代社會空間。
與電影作為一種展示視覺奇觀、體驗公共文化的媒介一樣,早期的電影院作為典型的現代城市建筑,首先也是一種空間媒介,即一種通過特定的公共空間(茶館、咖啡館、廣場、戲院、專業電影院),強化觀眾視覺感知并產生社會性交往的途徑。“空間媒介再現著世界,它亦生成、敞開著世界。”[35]尤其現代的專業電影院,既作為地理上的觀影空間,又作為媒介空間和文化空間,建立了其與現代文化之間的關聯,將電影和都市這種外來文化,放置于有一定秩序的空間之內,并將其“轉譯”為觀眾可感知的視覺形態和觀念意識,引導觀眾接收銀幕上的視覺信息,通過觀眾在影院中的社會身體的能動性,獲取對現代的集體經驗。
茶館和戲園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都市文化的一個典型空間。1908年,上海虹口大戲院的建立,標志著獨立觀影意識的初步形成。之后的十余年里“傳統的茶樓/戲園開始讓位于擁有‘鏡框式舞臺’和座位編號的現代戲院”[36](P125)。20世紀20年代,專業影院已經大量建立在諸如上海這樣的都市當中。從茶館、戲園到專業影院的過渡,不同觀影空間的形態演變,是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一種表征,電影和影院作為都市空間的重要構成部分,生產著現代知識和現代文明,現代文化經由影院空間儀式化,共享給國人觀眾,引導國人與都市接軌,與現代文明接軌。
另一種形態的空間實踐,即觀眾通過電影中的都市符號和都市空間傳遞的都市意識來想象現代。似乎是出于特殊時期對嘗試新事物的迫切,都市中的各種空間和物質實體(咖啡廳、街道、舞廳、火車、汽車、西裝、飛機等),紛紛進入20世紀20年代的國產電影作品中,“都市”自然而然成為現代性實踐的主要視覺內容。這些視覺內容,對當時的中國觀眾而言,是充滿吸引力與具身感的。由此,觀眾得以跟隨鏡頭,進入不同都市空間,面對形態各異的都市物品,“體驗”都市文化,在流動的空間中感知現代。而電影中所呈現的表征現代的視覺內容,不僅僅是一種通過視覺可見性引導觀眾想象現代的單向過程,而是一個相互影響、互相建構的過程,觀眾也會能動性地釋放對這種視覺內容的反應。即“電影屏幕所通向的,不是‘對象’的世界(自然),而是‘準對象’的世界(后自然),那個世界能反過來觸動觀者所處的空間(社會)”[37]。在這一時期的電影創作實踐中,人們運用特定的敘事策略、電影技巧和象征性道具,結合個人對“現代”的認知與反思,來喚起觀眾對現代先在的集體想象,進入現代記憶。
早期的電影創作者在“吸引力”電影的票房潛力中,早已意識到異域想象的號召力和價值。但是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人對“現代”的認知、想象和表達,卻更多是在一種社會批判話語中進行的,具體到電影中,便是將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對立起來,以對前者的謹慎展示和批判,來表達對現代的認知和想象。這不僅是由于當時大眾對“現代”的碎片化和不確定性的認知造成的,也是電影人的一種創作策略。在當時混亂的現實中,電影人通過電影作品提供的視覺愉悅和敘事秩序,將傳統與現代聯系起來,建立歷史與想象的鏈接;將人和現代空間聯結在一起,塑造二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從而使得觀眾參與到現代歷史發展的進程中。
以《風雨之夜》為例,小說家余家駒帶著妻女回鄉下養病,其妻莊氏嫌鄉村無聊,便獨自返城,經歷一系列事件之后,又幡然醒悟。隨著余家駒和莊氏二人進入到鄉村空間,其“現代性”的象征也隨之消失,一種特殊的“身份”在鄉村失效,而莊氏因不適應返回都市的舉動,便隱含了創作者對都市精神危險一面的敏銳察覺。影片借助對莊氏追求物質的批判,表達了對“現代”的態度。在空間形態上,伴隨莊氏的是別墅、敞篷汽車及俱樂部等物質性空間。影片對這種追求物質性的批判,反映的便是對都市以及都市“現代精神”的認知。電影人以主觀的真實性話語和對不同人物的細節設計為基礎,以犧牲其他文化為代價,來證明自身文化的合理性,側面也反映出電影人在面對“現代性”時的矛盾。
除像《航空大俠》(1928)等作品呈現的街道、西裝、汽車、咖啡廳、飛機等富有指向性的建筑,作為現代性的象征,被頻繁納入電影文本之外,舞廳也以一種現代化公共空間的形態進入電影,進入到當時的上海。電影人們也紛紛借助異域空間,延伸觀眾對異域文化的想象,當迥異于中國傳統城市空間的舞廳進入中國后,“都市中的現代人有意無意間用區別于傳統的表達方式重新正視都市文化景觀”[38],而當舞廳被納入電影銀幕大量傳播時,這種對都市空間的區別審視,不僅體現在都市的現代人身上,也體現在銀幕前想象現代的觀眾身上。陸潔編導的《透明的上海》(1926),第一次將舞廳置入電影,與女性一同反映都市空間的現代性和曖昧性。與傳統的茶樓不同,影片中現代舞廳的“身份”,并非是受當時社會歡迎的空間,反而是一種“不正常”的象征,因為此類都市空間,是青年人墮落于浮華與虛榮的罪惡之地。
總的來說,20世紀20年代國產電影對異域景觀的主動呈現,是觀眾想象現代的有效途徑。這種既具備商業價值,又具備文化價值的影片,通過影院空間對都市空間和都市意識的描摹,強化了觀眾的文化想象。它將都市作為一套意象化的符號系統,訴諸于觀眾視覺體系,引起觀眾對現代都市的想象和“解讀”。從空間作為媒介的角度來看,將都市空間置于電影銀幕,不僅是一個使其“可見”與“被看”的過程,同時也是將其“置于某種‘生成’ 和‘展開’ 的實踐之中”[39]的過程。觀眾在影院空間中感知都市空間,通過與空間的互動,建構對現代的想象和現代化的社會意識;再加上電影人普遍采用批判性話語表述現代的敘事策略,便使觀眾對于現代的想象,從“景觀”空間,轉向了“文化”空間。
結語
早期國人對現代的感受和認知,是一個想象性建構過程。畫報、幻燈片、攝影等訴諸于視覺的媒介技術,在電影出現之前,便揭示了“視覺現代性”對國人接受現代的重要作用。但早期電影不僅作為技術媒介訴諸于人們的視覺可見性,而且還是一種蘊含著復雜話語體系和現代觀念的現代媒介,體現了國人在接受現代啟蒙時的謹慎與矛盾,呈現了有關現代的視覺想象,建構了國人的現代意識和主體身份。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在經歷社會轉型,“經由現代政治啟蒙和國家意識所引發的現代民族自覺”[40],使得中國人逐漸從傳統走向現代。在這一走向現代的過程中,國產電影成為當時建構現代想象的視覺話語,并引導國人轉變為具有現代意識的現代觀眾。
首先,這一時期有大量電影改編自中外文學作品,其在視覺和意識層面,拉近了觀眾與電影的距離,并通過文字與圖像的對話與轉譯,以具備“公共視野”的電影為媒介,在想象力的基礎上,建構了觀眾對現代的初步想象。第二,電影對女性身體的展現,不僅是因為女性主體意識在現代公共空間中的覺醒,還是出自民族國家轉型時期對女性身體的需要,這不僅強化了觀眾“看”的欲望,即對視覺的依賴和對現代的感知,同時也為女性帶來了身份危機。第三,都市作為現代的重要組成部分,被納入電影,以不同的空間形態和都市意識,構成一套符號化的現代系統,經由影院空間和視覺空間,引發觀眾的空間實踐,在現代空間中想象與感知現代。
與早期小說、漫畫和畫報等形式啟蒙國人想象現代、建構現代觀眾的方式同步,20世紀20年代的電影,借助公共性與現代性,使自身成為啟蒙大眾的文化產品和建構國人視覺想象的載體。在視覺可見性的基礎上,其通過改編、身體和空間三個面向的操作,得到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同時也建構和實現了國人的現代想象與民族觀念。
參考文獻:
[1]張灝.思想與時代[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2]彭麗君.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M].張春田,黃芷敏,張歷君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3]于昌民.電影研究的未來:在現代性的歷史與電影哲學的主體之間[J].電影藝術,2020,(5).
[4]沈薈,錢佳湧.看電影:實踐范式下的媒介理解及其想象力[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9(1).
[5]趙毅衡.哲學符號學:意義世界的形成[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
[6][美]喬納森·克拉里.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M].蔡佩君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7]佚名.觀美國影戲記[J].游戲報,1897,(1).
[8]Thomas Gunning.The Cinema of Attraction: Early Film, Its Spectator and the Avant-Garde[J].Wide Angle, 1986,8(3).
[9]田王晉健.沉浸在另一個世界——琳達·哈琴改編理論研究[J].當代文壇,2015,(5).
[10]曾巍.基于受眾體驗的文學改編模式及媒介技術反思[J].文藝理論研究,2023,43(4).
[11]毅華.國產電影取材名小說之先聲[J].良友畫報,1926,(1).
[12]管海峯,管錫鵬.我拍攝“紅粉骷髏”的經過[J].中國電影,1957,(5).
[13]佚名.《紅粉骷髏》廣告[N].新申報,1916-11-21(4).
[14][15][33]米蓮姆·布拉圖·漢森,包衛紅.墮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視野:試論作為白話現代主義的上海無聲電影[J].當代電影,2004,(1).
[16]李鎮.進退維谷 悲喜交集——1925年“鴛鴦蝴蝶派”電影《風雨之夜》的歷史與解讀[J].當代電影,2018,(11).
[17]秦喜清.現代性、傳統審美與類型混搭——以朱瘦菊的《風雨之夜》為例談中國電影的融合之道[J].電影新作,2018,(6).
[18]鐵盟.談談《一串珍珠》 [J].良友畫報,1926,(1).
[19]心冷.評《一串珍珠》 [J].國聞周報,1926,3(4).
[20]虞吉,馬麗琳.論早期中國電影傳奇敘事的審美選擇——基于《一串珍珠》的史論評析[J].藝術百家,2015,31(5).
[21][22][32] [英]馬丁·杰等,唐宏峰主編.現代性的視覺政體:視覺現代性讀本[M].汪瑞等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
[23]戴錦華,孫柏,楊燁瑩,安爽.“文化革命”、“女性”的發明和中國電影——戴錦華談“五四與電影”[J].電影藝術,2019,(3).
[24]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
[25]Fredric R.Jameson.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M]// Jone Belton.Movies and Mass Culture.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6]孫紹誼,董舒,石川.魔幻、“凡派亞”文化與類型/性別之爭:《盤絲洞》與中國“喧囂的20世紀20年代”[J].文藝研究,2021,(6).
[27]佚名.《盤絲洞》廣告[N].申報,1927-01-28(版次不詳).
[28]王培雷.《盤絲洞》文本改編的表演視角[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3,(6).
[29]別有“洞”天——1927年神怪片《盤絲洞》的歷史及解讀[J].當代電影,2014,(6).
[30]徐紅.論《盤絲洞》的重映與早期電影的商業現代性[J].當代電影,2014,(6).
[31]周舒燕.超越性的俠女身體——重讀電影《紅俠》中的女性形象與敘事策略[J].當代電影,2017,(9).
[34][35][39]楊家明,景宜.媒介行為:認識“空間媒介”的“第三重進路”[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3,30(8).
[36]張真.銀幕艷史:都市文化與上海電影:1896—1937[M].沙丹,趙曉蘭,高丹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
[37]吳冠軍.從“后理論”到“后自然”——通向一種新的電影本體論[J].文藝研究,2020,(8).
[38]王婷.都市空間與現代性——從早期中國電影與舞廳的曖昧交織談起[J].文化藝術研究,2020,13(2).
[40]李培.主體呈現與醒世覺述:清末民初報刊漫畫的視覺現代性[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27(6).
(責任編輯:葉 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