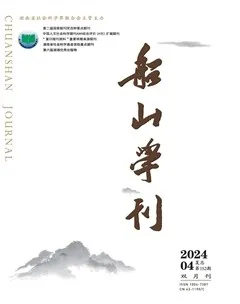時與勢:晚清關中陽明學之歷史境遇
摘" 要:晚清由于國是日非,德衰業敗,程朱理學在官方的支持下雖然有短暫的復興,但其地位并不牢固,對程朱理學的質疑與批評屢見諸士人筆端。在野的士人試圖在程朱的義理之學與陽明心學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以期維護理學的道統與學統。晚清關中陽明心學一系以柏景偉與劉古愚為代表,二人在西方列強入侵,關中本地天災人禍不絕的現實情況下,從理學內部摒棄門戶之見,主張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融合。同時,劉古愚從西方現代科學技術對世界發展大勢的影響出發,繼承關學經世致用思想,接受西方新學,并將其應用于對現實社會的改造之中。與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相呼應,劉古愚建立新學堂并實行有別于舊式書院的教學新模式,造就人才甚多,推動了關中近代化進程。由于近代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與傳統告別,以理學為根基的關學歷經千年,也走向終結,取而代之的是關中文化的新樣態。
關鍵詞:晚清" 關中" 關學" 陽明學" 劉古愚" 柏景偉
作者常新, 西安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西安" 710049)。
中國傳統學問不似西方哲學偏重概念與邏輯之分析,而總是與人的生存境遇相關切,自先秦諸子百家至晚清救亡圖存種種理論都與生民和國運相關涉,由此也形成中國文人常常以深切之歷史感去看待學術問題的傳統。就史學而言,流傳不息的經典文獻絕不是斷爛朝報式的資料拼湊,而是注重微言大義。同樣,深刻的哲學作品必須默認深厚的歷史知識背景。5-10縱觀中國文化史,幾次大的思想突破,皆與“道術將為天下裂”的社會動蕩背景相關,西周末年至東周“禮壞樂崩”引發的先秦諸子百家爭鳴,魏晉南北朝“越名教而任自然”引發的玄學思潮,宋初佛道二教日炙背景下出現的理學,晚清在文史哲諸多領域都將晚清界定在1840—1911年,這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還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形成時期。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巨變,王國維曾言這一巨變:“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參見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外二種)》(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0頁。以來列強環伺下形成的“中學”與“西學”之爭及社會轉型皆然,末者即是現代社會學家、哲學家和史學家所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盡管有人將中國近代思潮比附西方“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但余英時認為這種比附是“牽強的比附”,只能在中國史研究上造成混亂與歪曲,“中國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但他也認為19世紀晚期以后,中國傳統在內外力量交攻之下,很快進入一個解體的過程。參見余英時著:《總序》,《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第6—7頁。。這一時期關中社會文化面臨轉型:經濟由傳統向近代轉型,思想由關學傳統向近代文化形態轉型。本文采取思想史與哲學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偏于一隅的關中為考察對象,檢討晚清陽明學復興的歷史境遇,以示此時理學內部文化保守主義試圖通過理學理論的轉化,尋求救亡圖存路徑的趨向。
一、晚清關中的“時”與“事”
關中地區是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為周秦漢唐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中國文化歷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亂”后,關中作為國家中心的地位逐漸喪失,清初的黃宗羲在其《明夷待訪錄》中概括了這一歷史過程:“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為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辟,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煙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20-21晚清關中雖偏于一隅,但經濟有一定發展,形成了涇陽、三原、鳳翔等商貿大縣,這些縣域經濟在道光初年比較活躍 如道光年間涇陽“縣城內百貨云集,商賈絡繹,借涇水以熟皮張,故皮行甲于他邑。每于二、三月起至八、九月止,皮工齊聚其間者不下萬人”。參見盧坤撰:《秦疆治略》,道光刻本。,甚至在財政狀況較好的情況下擔負較重的賦稅以支持軍事用度和戰爭賠款 如咸豐年間湖北巡撫嚴樹森說:“陜西為財賦之邦,西、同、鳳三府又為菁華薈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陜省協餉聊以支持,即京餉巨款亦多取盈于此。”參見楊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魯、吳廷錫纂:《民國續修陜西通志稿》(五),《中國地方志集成·省志輯·陜西》第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195頁。,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與東部省份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
在學術思想方面,整個清代,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的地位一直未曾改變,盡管在乾隆期間漢學曾風光一時,但漢學家身份的民間性特征非常明顯,沒有官方的全力支持,漢學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由于漢學的訓詁考據與晚清所面臨的社會危機關聯性不大,漢學在乾嘉之世興盛一時之后便逐漸衰息,漢學與宋學之間的攻訐以二者的調和與兼采而告終。理學內部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間的學術爭論得以延續。晚清的經學也迫于形勢發生了轉變,出現了今文經學的興盛,這一轉變的出現是基于晚清學者對乾嘉學派考據學的反思,晚清學者要突破乾嘉學派的瑣碎考據,強調經學的經世致用。但關中經學沒有走向考據一途,而是回歸到先秦的經學傳統 陳俊民認為李二曲提出的“儒學即理學”同顧炎武提出的“理學,經學也”兩相輝映,二人都主張用“儒學”“經學”代替“理學”,向原始儒學還原。(參見陳俊民:《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頁)賀瑞麟的弟子孫迺琨恪守清麓學派家法,將包括經學在內異于程朱的思想視為異端,“凡漢學家、詞章家,管商之權謀功利,異端之虛無寂滅,與夫近代之陽儒陰釋,一概廓清而掃除之”。(參見孫迺琨:《復廖燮堂書》,《靈泉文集》卷四,民國二十九年(1940)濟南善成合記印務局印版,第51頁),這一傳統在以劉古愚為代表的晚清關中士人身上有明顯的體現 劉古愚(1843—1903)名光蕡,字煥唐,古愚為其號,陜西咸陽馬莊鎮天閣村人。劉古愚通經致用,被譽為渭北經學領袖,著有《孝經本義》《詩大旨》《書微意》《大學古義》《論語時習錄》《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說》《管子小匡篇節評》《荀子議兵篇節評》等。參見劉光蕡著,武占江點校:《劉光蕡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前言》第2頁、《點校說明》第2頁。。晚清關中王學所論與社會危機相關,這為包括陽明心學在內的理學復興提供了契機,尤其是漢學對理學空疏無用的批評及時人對科舉的批判,為陽明學被重新認識提供了空間。在李二曲與劉古愚之間,關中還有不少心學傳人,如陜西安康祝塏和鄜州羅焜,二者皆服膺二曲之學,是王學在關中承上啟下的人物 祝塏之學“大抵本于王文成”(參見賀瑞麟著,王長坤、劉峰點校整理:《賀瑞麟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8頁)。羅焜“日潛心于馮少墟、李二曲諸書”(參見王美鳳:《關學史文獻輯校》,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514頁)。。
關中陽明學復興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因素,那就是陽明學在日本的盛行,影響了在日中國留學生,他們將陽明學在日本的情況介紹回國內,促進了國內陽明學的復興。如宋恕在《戊戌日記摘要》中記有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十二日“訪晤立庵、陽州,又識牧放浪、河本默堂。始見《禪宗報》及《陽明學報》”940。此時西方意志主義哲學思想逐漸傳入,與陽明學突出自我、強調心力相應和,因此五四以前唯意志論在近代啟蒙者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鴉片戰爭前后的龔自珍及戊戌變法前后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身上都可見其端倪。239他們皆對陽明心學持肯定態度,尤其是康有為稱“言心學者必能任事,陽明輩是也。大儒能用兵者,惟陽明一人而已”248。梁啟超認為“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茍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余年,斯學銷沉,而其支流超渡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為用也”46。梁啟超“稱頌王學”的歷史意義在于試圖通過傳統資源來會通中西,這一思路影響到現代新儒家,后者開創出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性如何接軌的嚴肅議題。18晚清關中陽明學者李寅、柏景偉、劉古愚關注維新運動,尤其是劉古愚與康有為、梁啟超互通聲氣 劉古愚與康有為未曾謀面,但他是康有為改良思想的熱情支持者,他把康有為思想介紹到關中,把自己的學生送到北京和上海結識杰出變法人士。百日維新失敗后劉古愚受到牽連而被捕,由于陜甘總督的介入才得釋放。參見王昌偉著,劉晨譯:《中國歷史上的關中士人:907—1911》,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53—154頁。,并創辦維新團體“復邠學會”,宣傳救國維新思想,開關中維新運動之先聲。后“復邠學會”又成立農會,成為上海農會的分支機構,積極開展維新救亡運動,這一時期他們皆將陽明心學視為挽救危局的思想源泉 《清儒學案》說劉古愚“究心漢、宋儒者之說,尤取陽明本諸良知者,歸于經世,務通經致用,灌輸新學、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為學,亦以此為教”。參見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古愚學案》,《清儒學案》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7365頁。。由于以劉古愚為代表的心學派推動,關中在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促進了近代西北地區的社會轉型。當然陽明學在晚清的復興無法挽救宋明理學的整體頹勢,在晚明以來東傳的西學與中國傳統學術所形成的張力下,晚清政府迫于形勢在“中體西用”的主旨下發起了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但這根本無法解除各種社會危機。就此而言,晚清陽明心學的興起可以視為儒家文化在中國歷史上作為主導性文化的“回光返照”。
二、晚清關中陽明學復興的機緣
晚清陽明學的復興一方面基于國是日非所引發的士人對程朱理學的質疑,另一方面同官方的默許態度有關。在官方的士紳階層,有不少人公開宣揚陽明心學,如道光時期的湯金釗(曾任吏、戶、禮、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汪廷珍(曾任禮部尚書、太子太保銜、協辦大學士),同治年間的李棠階(曾任戶、工、禮部尚書,軍機大臣,加太子太保銜)為學不立門戶,不爭異同,對心學頗為贊同。湯金釗《敦艮齋遺書序》中言“孔、孟、《詩》《書》言性言天以氣不以理辨,后儒分理氣為二之非,謂主敬之說,或誤會而操持太嚴反失靜之本體”。“后儒分理氣為二”,即程朱理學分理氣為二。(參見徐潤第:《敦艮齋遺書》,《四庫未收書輯刊》4輯2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44—245頁)汪廷珍在重修陸象山文集序中言“考陸者必參朱,考朱者不廢陸”,主張融合朱子學與金溪(陸九淵)學。(參見陸九淵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46頁)李棠階在《勸士條約》中言“自朱子《近思錄》而后,莫過于孫夏峰之《理學宗傳》,其書以宋明十一子為正宗,并及漢唐以來諸儒”,“看陳白沙先生書亦可,白沙為粵賢冠冕,果能于其遺書虛心領會,必有得力”。《理學宗傳》“宋明十一子”分別為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涵蓋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主要人物。(參見李棠階:《勸士條約》,《李文清公遺書》卷五,光緒八年(1882)河北道署刻本)道光初年,官方將明末清初的心學家劉宗周、孫奇逢、湯斌等人從祀文廟。同治十一年(1872)、光緒五年(1879)官方兩度重修毀于戰亂的貴州龍崗書院(內祀王陽明)。在民間,陽明學也呈燎原之勢。如晚清啟蒙思想家宋恕對陽明、梨洲“素所宗仰”553。與宋恕同稱為“浙東三杰”的陳黻宸(另一人為陳虬)“治性理宗陸九淵、王守仁”。1229維新派的康有為“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61。梁啟超稱贊陽明心學“高尚純美,優入圣域”140,在為萬木草堂與時務學堂制定的《萬木草堂小學學記》與《湖南時務學堂學約》中,他通過對陽明心學的改造,提倡民權,鼓吹變法。陽明心學成為革命與變法的思想源泉與依據。
晚清關學發展延續了清初以來大勢:朱子學與陽明學并行不悖,朱子學力辟陽明學,陽明學融攝朱子學,如道光年間關中程朱理學的堅守者賀瑞麟強調理學內部門戶時指出“學以孔孟為門戶者也,程朱是孔孟門戶,陸王非孔孟門戶”69。清初關中陽明學者李二曲始終認為朱子與陽明“均大有功于世教人心,不可以輕低昂者也”36,這是關中陽明學者學術取向的傳統。晚清關中陽明學的發展同全國保持大致相同走向,出現了明確鼓吹陽明心學者,如道光年間關中學者李元春言道“邇陸王學熾,其與程朱幾成孔孟、楊墨之相爭”333,其中又以劉古愚為典型。對劉古愚學術取向有直接影響的為黃彭年、李寅、柏景偉三人,其中黃彭年、柏景偉是與賀瑞麟同輩的學者。黃彭年原籍湖南醴陵,生于道光四年(1824),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嘗掌教關中書院,在關中書院時著力栽培劉古愚。李寅與柏景偉為關中學者,二人是陽明心學的繼承者。李寅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長劉古愚三歲,家境富裕,少時“研究經史,泛濫百家”,“論學以心得為主,不欺為用,破除門戶之見,其大端近象山、陽明,而不改程、朱規模”。75-76柏景偉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長劉古愚十二歲。劉古愚與李寅、柏景偉“訂昆弟交”280,屬同輩學者。柏景偉與賀瑞麟“聲氣相應”95,賀瑞麟稱其“生平重事功,勤博覽,其論學以不分門戶為主,似乎程、朱、陸、王皆可一視”126。劉古愚在其為柏景偉所撰寫的墓志銘中更是明確指出柏景偉“講學宗陽明良知之說”,“不流于空虛泛濫”。95劉古愚心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深受李寅與柏景偉的影響,李寅將陽明著作借與劉古愚,并指導劉古愚讀書“不博覽無以盡變,不反觀無以自成”,劉古愚自稱“蕡稍稍知學自此始”。75
在中國歷史上,關中地區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西周的禮樂文明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開儒家思想風氣之先。張載以“勇于造道”的精神與勇氣提出“性與天道為一”的理學主題,將北宋理學推向高峰。王徵是晚明最早會通儒耶的士人,通過接觸利瑪竇等人東傳的“天學”,引進與研究西方工程學,達到了極高水平,其與鄧玉函完成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機械工程學”著作。239楊屾作為康熙、乾隆時期的關中農學家,為應對西方“上帝創世”“天國來臨”諸宗教信仰挑戰而著《修齊直指》,此書成為王徵之后清代關中會通中西的經典參見陳俊民:《張載關學的歷史重構》,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140頁;呂妙芬:《楊屾〈知本提綱〉研究——十八世紀儒學與外來宗教融合之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12年第40期,第83—127頁。。晚清劉古愚面對危如累卵的時局,“務通經致用,灌輸新學、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為學,亦以此為教”3,著《修齊直指評》。關中學術這一傳統對晚清關中士人影響頗深,成為他們超越自身學術局限的不竭動力。
晚清的關中地區雖沒有直接遭受西方列強的侵擾,但各種社會危機不亞于京師。第二次鴉片戰爭及中日甲午戰爭雖然在空間上沒有殃及關中,但戰后的賠款給關中地區的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咸豐十年(1860)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規定賠款英法軍費各800萬兩白銀,在各省中陜西與山西負擔最重,各為30萬兩。《辛丑條約》規定4.5億白銀分兩期支付,第二年賠款總額為2315.9萬兩,陜西負擔竟達60萬兩之多。參見劉俊鳳:《民國關中社會生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頁。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國“扶王”陳得才率部入陜,在關中以南的商州燃起戰火。西捻軍首領張宗禹率軍進入關中,在關中和清軍展開激戰。同一時期回民起義席卷整個西北,關中地區社會生產力遭到空前破壞,這在時人諸多的文獻記載中都有相關的記錄。在文化領域,乾隆以來盛行于東南的漢學在關中遭到抵觸,晚清關中理學代表人物李元春、賀瑞麟對漢學提出批評。賀瑞麟視漢學為明代心學的余緒,認為漢學對宋學的批評“生心害政,風俗波靡而禍卒中于國家”。參見賀瑞麟著,王長坤、劉峰點校整理:《薛仁齋先生年譜序》,《賀瑞麟集》,第37頁。此時關中理學由于自身缺乏活力也逐漸式微,如文化發達的三原出現“儼然儒者,口不道詩書。聞人言圣賢學若相戒不敢近見,繩規士群訾笑之,或曰理學先生,蓋鄙夷之也”202的現象,這亦即王汎森所探討的“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問題王汎森所言“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主要系指地方上的思想、文化、精神、心靈、信仰等層次的內容之空虛與茫然、不安定,或混亂。參見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84—285頁。。社會經濟的凋敝與文化的沉悶需要新的文化樣態出現。
考察晚清關中陽明學還有一個維度,那就是清初以來經世致用之學的興起。明清易代,引發了明遺民對時局與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對經世致用之學的探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噩夢》與《黃書》、顧炎武的《日知錄》分別考察了傳統政治秩序的改變、歷代風俗與郡縣制度的利害得失等方面,旨在尋求一條挽救社會危機的道路。166同黃宗羲、顧炎武并稱“海內三大儒”關于明清之際“海內三大儒”歷來有兩種說法:其一系指孫奇逢、黃宗羲、李二曲,如全祖望之《二曲先生窆石文》中言“當時是,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為三大儒”(參見全祖望撰,黃云眉選注: 《二曲先生窆石文》,《鮚埼亭文集選注》,濟南: 齊魯書社,1982 年,第 123頁);其二系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如章炳麟在《重刊船山遺書序》中言“明末三大儒,曰顧寧人、黃太沖、王而農,皆以遺獻自樹其學”(參見王夫之:《船山全書》第16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441頁)。后者是當前學術界流行的說法。的關中李二曲以“悔過自新”與“明體適用”之學提供了系統的經世致用的方法。李二曲所務經世之學重點不在具體知識層面,而是著眼于世道人心的改變。李二曲早年著有《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十三經注疏糾繆》《二十一史糾繆》《易說象數蠡測》等書,后來自認為這些著述無當身心,或焚燒,或不以示人。晚年李二曲更深切地認識到“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致治無由,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于明學術,以提醒天下之人心” 651 ,此即李二曲的“明體”之學。李二曲的“適用”之學 “重實行,不重見聞”136,認為“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于世” 512。李二曲的“適用”之學爾后為其弟子王心敬與楊屾所發揚, 學界對楊屾是否出于二曲之門有爭議,楊屾同邑后學張元際(1851—1931)所撰《楊雙山先生事略》言其“少出盩厔大儒李二曲之門,二曲許為命世才”(劉光蕡著,武占江點校:《劉光蕡集》,第709頁),但林樂昌通過考證否定了這一說法(參見林樂昌:《論楊屾的儒學體系及關學史地位》,《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6期,第75—82頁)。直接影響了晚清的劉古愚與柏景偉。
三、關學融攝陽明心學的新面向
關中雖處西北內陸,但同樣受到晚清西方列強入侵所導致的危機影響。這一時期關學對陽明心學的融攝帶有鮮明的憂時救世之時代印記,這一點在康有為為劉古愚《煙霞草堂文集》所撰寫的序言中可窺一斑。康有為謂劉古愚學行“以良知不昧為基,以利用前民為施,篤行而廣知,學古而審時,至誠而集虛,劬躬而焦思,憂中國之危,懼大教之凌夷而思救之”7。以劉古愚為代表的關學學者對陽明心學的汲取與消化不似其前輩以心性問題為鵠的,而是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對現實問題之探討。“每治一學,輒欲施之實用”10,“為關輔力挽衰頹”536,同時通過“學古而審時”,對傳統文化進行符合時代的轉化。這一轉化與賀瑞麟、牛兆濂堅守朱子學,試圖以傳統禮教來挽救人心、拯救世運的策略不同。柏景偉與劉古愚通過提倡新學、創辦實業,使關學融入了現代的學術旨趣。
關于柏景偉的學術思想取向,從劉古愚為其撰寫的《同知銜升用知縣柏子俊先生墓志銘》及署名為柏景偉的《〈關學編〉前序》可窺其一斑。 這篇《序》是柏景偉晚年歸老灃籍村病中與劉古愚商討《關學編》定稿時的口授資料,由劉古愚手書,從此《序》中可看出二人學術宗旨的相同性問題。在《〈關學編〉前序》中柏景偉回顧了自周公以來的學術發展歷程,指出在宋代道學創立之初尚無門戶之見,南宋朱子之學與象山之學“始合終離”。明代關學在南大吉傳播陽明心學之前,皆以朱子學為尚,其后關學內部出現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差異。馮從吾“統程、朱、陸、王而一之”,為“集關學之大成者”。41據此看出柏景偉與劉古愚認同馮從吾綜合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學術取向,并在續寫《關學編》時遵從了馮從吾的撰寫理路。 在續寫《關學編》方面,賀瑞麟與柏景偉、劉古愚存在差異。作為晚清關中程朱理學的代表,賀瑞麟續寫《關學編》所增七人,皆為程朱理學的信奉者。在《重刻關學編后序》中劉古愚言柏景偉“論學力除門戶之見,而統之以忠孝”42。在這篇《序》中劉古愚還談到王徵被補入《關學編》的緣由,認為盡管王徵講事天之學,與程朱理學有相違背之處,但王徵在明亡后絕食殉國,已盡君臣之義;進而得出西學與儒家倫理綱常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二者是可以統一的。劉古愚這一觀念預示在西學大舉進入中國時,儒家思想如何通過調和與西學的關系,來保持自身的獨立性,這一觀念也體現出柏景偉與劉古愚學術思想開放性的一面。
柏景偉作為晚清陽明學者,其學并非完全承襲陽明,而是受劉宗周思想之影響更為深刻。劉古愚所撰《同知銜升用知縣柏子俊先生墓志銘》言柏景偉“講學宗陽明良知之說,而充之以學問,博通經史,熟習本朝掌故,期于坐言起行。其學外似陳同甫、王伯厚,而實以劉念臺慎獨實踐為歸”95。陳同甫即陳亮,王伯厚即王應麟,前者是南宋與葉適同講王霸義利的功利主義者,后者為宋末元初博學多才、涉獵經史百家的大學問家。劉宗周是晚明浙中王學的集大成者,其學以慎獨為宗。劉宗周對慎獨的理解有別于先儒,他將“獨”與“意”本體化,提出“圣學之要,只在慎獨。獨者,靜之神、動之機也”361,“意者,心之所存,非所發也”,“至靜者莫如意”。390其意批評王門后學脫略工夫的空疏學術之風氣,強調通過內心修養而達到致良知的境界。柏景偉為學雖宗陽明良知之學,但具有明顯的破除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藩籬的學術取向,且在晚清國是日非的境況下強調通過教育與講學培養經世致用之人才。
同此性命,同此身心,同此倫常,同此家國天下,道未嘗異,學何可異也?……
故“理一分殊”之旨,與“主靜”“立人極”“體認天理”之說,學者不以為異,而其所持究未嘗同也。然則“主敬窮理”與“先立乎大”“致良知”之說,得其所以同,亦何害其為異也。535
朱子學與二程之學在本體與工夫的論述方面存在差異,在理學內部未曾引起爭議,同樣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皆為圣學后傳,應該求同存異,不應以門墻之見而相互駁難。柏景偉與劉古愚主講味經書院及其他書院之時,“以經史、道學、政事、天文、輿地、掌故、算法、時務諸學教諸生,分別肄習,關中士風為之一變”533。這一教學內容與傳統書院教學內容大為不同,呈現出教育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一面,這也是根據時局所作出的一種理性的選擇。這種教育模式的目的在于“一空標榜拘墟之習,而務以圣賢道德、豪杰功名相與糾繩,相與淬勵,為關輔力挽衰頹”536。在時局動蕩不安、危機四伏之時,柏景偉非常關注經世致用之學,試圖通過學術與具體社會實踐,改變社會的危局,改變關中的頹勢。這種學術的取向也使關學漸漸遠離宋明理學天命心性等范疇,而代之以現代自然科學的新內容,關學也因此逐漸消融于現代學術而走向終結。
劉古愚對陽明心學的融攝基于理學內部程朱理學對陽明心學的批評態度。劉古愚融合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與門人論學的兩篇書信中,其一為《與門人王伯明論朱陸同異書》,其二為《與門人王含初論致良知書》。關于儒學內部的門戶之爭,劉古愚認為并非學術思想自身具有本質性差異,而是儒學內部人為造成。即使程朱理學一系,自周敦頤、二程至朱子,其學術也并非完全相承,而是存在“宗旨不同”“氣象不同”的實際,學術殊途同歸,“茍專心向道,皆能同于圣人”。劉古愚甚至提出“九流皆吾道之支,而耶教則與吾并域而居”,耶、佛也可成為儒學的“方外之友”。122這是晚明儒、佛、道三教合一理論的延續,也是清初理學內部清算的主要方面。
劉古愚在《與門人王含初論致良知書》中提出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應該互救其失,而不應相互駁難與攻訐。劉古愚梳理了明代自陳獻章提出“靜中養出端倪”至王陽明提出致良知明代心學精致化的過程,并追溯陳獻章“靜坐”工夫與二程“靜坐”工夫在源頭上的一致性,皆有功于圣門。劉古愚認為學術門戶之爭,起于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的末流背其師說,進而形成相互指責之勢,學術的辯論“即染市井斗口惡習”,嚴重破壞了儒學思想的一致性。劉古愚痛感于此,“于人辨程朱、陸王者全不置詞,不欲爭閑口舌也”。124
劉古愚為學“導源姚江,會通洛、閩,以誠明立體,以仁恕應物,直指本源,切于實用”278,其對陽明心學的融攝還體現在《大學古義》與《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說》之中。在《大學古義》中劉古愚闡發了古本《大學》之義,對“明德”“格物致知”的理解與陽明相合,而與朱子相左。他不同意朱子將《大學》首句“親民”解為“新民”,對朱子《大學》補傳部分及訓“物有本末”為“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導致一物二分提出委婉批評。他認為朱子對“致知在格物”的闡釋會導致“《大學》全篇皆是‘格物’之傳”的弊端。361劉古愚視“明德”為道之本,“至善”為學道之詣,“明德”是性善,“明明德”是復性之學。347他在《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說》中闡明了心、性、理、氣之關系,統攝和調和張載太虛即氣、朱子性即理、陽明心即理之意明顯,其曰:
理、氣、性,天之道也;民、物、親,人之道也;身、心、性,己之學也。性、理不作圈,心不書界,性無聲臭,理無盡藏,性即理也。心載而運之,心亦即理也。……氣分陰陽,以虛而運也。氣之所至,即流為形,而理為之主,有物有則也。天之生人也,理載氣行,而聚為形;人之合天也,形修氣充而會其理。463
劉古愚將本體之理、氣、性一并打通,將身、心、性視為為己之學,對《大學》“親民”作出了人道主義的新解,將其與“物”相接,稱“圣賢立學之意,凡以為民也!學者有志于學,須立地有民胞物與之量方可言學”348。這一理解同劉古愚所處時代民族面臨諸多危機,民生維艱的現實相關。性、理、心三位一體,動靜相宜,生發與規定萬物。劉古愚對性、理、心的這種理解同其所持反對理學內部程朱與陸王之爭的理念相關,是對朱子學與陽明心學所作的一種綜合。
劉古愚對良知的解釋不似陽明明白簡潔,而是通過陳獻章“靜坐養出端倪”引出,認為“端倪”即為“良知”。“良知”之“良”為“道之大原,不為氣質物欲所蔽錮”,良知之“知”,“其體清明精粹”。123劉古愚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同陽明大致相似,“‘致’是推極其明,‘格’是方正其德,‘致知’是具眾理,‘格物’是應萬事也。萬物皆吾性所固有”。350另外劉古愚具有將心、性下降為形而下的傾向,他將“良知”本體視為世俗所謂的“良心”,視“致良知”的工夫為“作事不昧良心”。他認為講學“宜粗淺不宜精深”,不再以“辨明正學”為目的,“不必與禪家爭性理,當與耶氏爭事功;且不必與耶氏爭事功,當使中國之農、工、商、賈,不識字之人,皆自命孔子之徒,為孔子之學”。124其“致良知”之意超越陽明心性本體層面,與晚清以來“實學”思潮相結合。他試圖通過講學,以簡易直接的心學喚醒民眾意識,奮發圖強,這是關學與陽明學融會的一個新面向。這一現象的出現同晚清以來理學頹勢難挽,國是日非,西學逐漸大行其道的現實直接相關。
劉古愚工夫論與陽明工夫論具有相合之處,但也存在分歧。二人的相同之處體現在對“誠意”的重視上,都將其視為“格物”的工夫。陽明視“誠意”為“致良知”,認為“《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44劉古愚同樣認為“《大學》明王道,以誠意為本”356,“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國必先治,家必先齊,身必先修,心必先正,意必先誠,格物也”352。劉古愚與陽明“誠意”的相異之處體現在對“意”之界定上。劉古愚對“意”的理解同朱子與陽明均異,認為朱子訓“意”為“心之所發”不妥。陽明晚年對“意”又有更為精確的界定:“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1316陽明對“意”的理解比較靈活,籠統地說主要指“意識”或“意念”45,存在善惡之分。劉古愚對劉宗周訓“意”為“心之主”甚為贊同,認為“意”即“性善”,350是一個具有本體性質的概念,“明德在心為意,意為吾心靜而存主之神,有極象焉”356,“知”是明,“意”是明德,因此“意”是至善的。
王陽明“四句教”首句涉及“心”,他在《大學古本序》中將 “心”定義為“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271,“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1070。劉古愚對“意”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心”,這也是劉古愚與陽明思想相異之處。劉古愚雖言“心亦即理”,但又將心視為“性”與“意”的承載者。463就此而言,他將“心”下降為形而下者,“然心載明德,非心即明德也”357,“性以心為舍,究不得謂心即性”355。“心”與“身”“涉于應事接物”362,同屬“物”的范疇,而“‘物’是明德所被之物,即身、心、家、國、天下也”351。劉古愚將“心”降為形而下者同其利用心學簡易工夫直接相關。他認為“今日儒生講學宜近而切求兵、農、工、商之務,不宜遠而高語天人性命之精”160,通過弱化心性之學,強調經世致用,以應對時局的變化。
在知行次第方面,劉古愚同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有異,強調“知先行后”。劉古愚從《大學》“明德”“親民”“至善”出發,提出“大學之始,必先知之,然后再加細密工夫。‘明明德’必至如圣人,方為至善,而學始可止;‘新民’必至如王者,方為至善,而治始可止”348。從本體與工夫二者言,先有對“至善”的知曉,而后方可行“止于至善”的工夫。身、心、家、國、天下是“物”,是包括自身修養在內的社會實踐對象;誠、正、修、齊、治、平是“事”,循其先后之序,是社會實踐的方法與目標。天下之事物如綱在目,一絲不亂。在“物”之中,“修身為本”,是“格物”之要,是“知”;在“事”之中,“誠意”為本,是“行”,352“知”先于“行”357。劉古愚心性之學的這種變化正如錢穆所言“晚明儒則把注意力轉向外面,替代以前之所謂內心深處;又轉向事事物物具體的變化上,替代那事物變化之最先根源與最后本體”359,是理學發展大勢所趨。
關于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劉古愚予以支持,認為:
“無善無惡”者,不可以善惡名也,如初生之孩提,可謂之善乎?可謂之惡乎?如人一念未生,可謂之善乎?可謂之惡乎?而人之材則未有不能為善、不能為惡者。……今日為學不必求深,但即日用之間,時求無愧,他皆可不問矣。19-20
劉古愚對“無善無惡心之體”的理解接近陽明,認為“無善無惡”是“意”未動之前“心”的一種本然的、沒有規定性的狀態。但劉古愚又強調面臨時局的動蕩與不安,為學應該以解決日用常行的實際問題為指歸,而不應限于諸如心性本體的超驗問題,學術應該服務于現實問題的解決。
劉古愚對陽明心學的繼承與修正有深刻的社會背景,一方面是封建制度的解體與國是日非的現實,另一方面是理學的式微與西學東漸。他必須尋求一種新的學理與實踐,以應對時局的變換。劉古愚和劉宗周對“意”的界定意味著對陽明心學的修正及對王學末流的批判,其“知先行后”之旨是應對巨大社會變革的策略與選擇。劉古愚在《學記臆解》中借用王夫之語表達了這一意旨,認為“教學以親師、講藝為務本”,面對天主教傳播,“中國幾無敢言宋、明理義之學者”,“吾國乃日疲弱不振,耶教遂盡收吾教之說以為己有,而以教于吾國,以收吾民”。“故今日之教民,當注意在化民成俗”,“使人人自出其本心,自精其生業,則兵練于伍,農勸于野,工精于室,商智于市”。344-345如果說陽明提出“致良知”是應對理學內部程朱理學“支離”的危機,那么劉古愚對陽明心學的修正則主要是應對“西學”東漸及王學末流引發的諸多社會危機,是晚清的“事功之學”。
關于晚清柏景偉與劉古愚融合程朱與陸王之學還有一個被學者忽視的問題,即二人與賀瑞麟的關系問題。賀瑞麟與柏景偉年齡相仿,而長劉古愚近20歲,因此賀瑞麟屬于劉古愚的前輩學者。柏景偉與二人皆互相視為同調,柏景偉續寫《關學編》未竟,托付賀瑞麟完成編寫任務,在病榻口述,讓劉古愚手筆《重刻關學編前序》。賀瑞麟為《關學編》寫的《序言》對柏景偉的學術取向稱贊有加,但對柏景偉融合程朱與陸王的做法卻頗有微詞。劉古愚肯定賀瑞麟與柏景偉為晚清關中學術典型,并為柏景偉撰寫了墓志銘。賀瑞麟對程朱理學視為異端的思想排斥不遺余力,翻檢《賀瑞麟集》,未見賀瑞麟提及劉古愚。《清麓年譜》記載同治十一年(1872),涇陽味經書院創建者許振祎(時任陜西學政)邀請賀瑞麟主講味經書院,賀瑞麟以味經書院章程“不滿人意”為由婉拒,1106而味經書院章程正是由劉古愚主持完成的。據此可以看出賀瑞麟與劉古愚之間的微妙關系,這一情況也成為我們了解晚清關中內部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之爭的蛛絲馬跡。
四、關中王學的經世思想與具體實踐
“知行合一”是陽明學最富思想特色的一個命題,梁啟超對其評價甚高,稱其為“最有名而且最有價值的一個口號”2。“知行合一”成為晚清有志之士尋求民族救亡之道的思想資源,在這一思想下儒家的經世致用之學被賦予新的內涵,志士仁人試圖通過對西方文化的吸收改變時局的頹勢。在1897年梁啟超為湖南時務學堂擬定的《湖南時務學堂學約》中,立志、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等方面皆有王陽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意味,其總目標在于培養經世致用之才,服務于救亡圖存,尤其是使陽明“知行合一”思想成為革命的主要精神動力。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905年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演說時說道:“五十年前,維新諸豪杰沉醉于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萬人于水火中之大功。”278盡管孫中山先生在此將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作為日本維新運動的精神動力,但其目的主要是喚醒中國民眾 。“我們中國此時,人家的好處人人皆知道,我們可以擇而用之”280,學習國外先進經驗,踐行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
柏景偉強調知行合一,“博通經史,熟習本朝掌故,期于坐言起行”95,未弱冠之時就留心兵事、天文、輿地之學,“大類橫渠”125。面對晚清亂局,柏景偉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早在鴉片戰爭期間就認識到這是中國遭遇嚴重危機的開始。在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期間就意識到培養新式人才迫在眉睫。光緒十一年(1885),柏景偉同劉古愚、胡子周(三原巨富,劉古愚摯友,求友齋資金贊助者)三人在味經書院內部創建“求友齋”。求友齋同其他書院的最大區別在于其講授內容不涉科舉時文,而是含經、史、政、道四項,同時附天文、地理、算法、掌故各學。為教學之需,求友齋兼有刻書、校勘等課程,將教學與實踐相統一,刊刻了許多圖書,其中包括前文曾談到的楊屾的《豳風廣義》。求友齋為關中造就了許多新式人才,陜西布政使陶模組織測繪陜西地圖,求友齋的學生承擔了主要的測繪任務,這是其他書院學生所不具備的、具有現代性的新技術,顯示出柏景偉和劉古愚等人所具有的超前意識。柏景偉為平息關中頻仍的戰亂,曾入左宗棠、劉典(時任陜西巡撫)幕府,“籌筑堡寨以衛民居,設里局以減徭役,提耗羨以足軍食”93,頗有建樹。
劉古愚之學“導源姚江,會通洛、閩,而其用歸于阜民富國”281。在《復邠學舍學規》中,他提出以“致良知”與“修良能”來協調知行問題,認為“講讀經史,務為實行”,259他自己“終身以農桑、工藝為事”281。劉古愚在給友人的數封信件及序言中都談及中國貧弱的原因,“吏、兵、農、工、商,窳敗不能治事”639,即缺乏真正的經世之才。劉古愚認為學習實用的西方科學是挽救危亡的有效手段,因此“能大興物質,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以強中國”,“以新書、新藝、新器大舉農工,以救一方民,以移惠中國”。7劉古愚在主持味經書院、崇實書院期間大興西學。他本人學習了梅文鼎的《歷算全書》、朱世杰的《四元玉鑒》、偉烈亞力和李善蘭合譯的《代微積拾級》、丁取忠的《白芙堂算學叢書》等數學知識,在求友齋刊刻了《梅氏籌算》《平三角舉要》《九章翼》等數學著作。李二曲高足楊屾的《豳風廣義》《蠶桑備要》及《修齊直指》也在求友齋刊刻,劉古愚為《豳風廣義》作了注解闡說。
光緒二十三年(1897),在近味經書院之處官方又建崇實書院,以提倡新學與自然科學。在學使趙惟熙上皇帝的奏折中有崇實書院教學內容的記錄,書院分為四齋,教學內容會通中西,涵蓋了中國經典、西方教務風俗人情、中外古今時局政治并刑律公法條約、外國水陸兵法、地輿、農學、礦務,兼習外國文字、物理及化學相關知識,其最終目的是“以培濟世經邦之略”。4007-4008
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后,劉古愚就認識到西方列強之所以在中國橫行,主要是依靠他們的堅船利炮。在執教味經書院之時,劉古愚曾給書院學生命題“論西洋機器之利,中國今日必不能拒,當效法之”,以啟發學生,并撰《泰西機器必行于中國說》以說明中國采用西方機器生產的必要性31。在主持崇實書院期間,為解決書院經費問題,劉古愚籌劃興辦機器織布局。這一舉措背后有其深刻的思考:西方列強經濟入侵,嚴重破壞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掠奪了大量財富,造成百姓生活困苦。在《創辦機器織布說略》中,劉古愚詳細說明了這一舉措的重要性。243在后續的具體實踐中劉古愚動用各種資源進行籌款、考察,但最終由于各種原因,機器織布局未能成功創辦,但這次嘗試為陜西興辦實業培養了后備人才。此后不久,劉古愚與學生開辦了用機器軋棉籽的工廠,邁出了陜西民用工業采用近代機器的第一步。劉古愚在味經書院、崇實書院培養了許多人才,一直追隨劉古愚的有陳濤、李岳瑞(李寅之子)、張秉樞、張元勛、胡均、張鵬一、張季鸞等人。這些人都受過中學與西學的熏陶,在陜西傳播新學與新知識,成為推動關中近代化歷程的關鍵人物。
余" 論
理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在晚清趨于終結,這也是理學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階段。從宏觀層面考察,理學的終結同近代中國社會危機所導致的整個社會轉型直接相關。章太炎在清末所作《清儒》一文中用寥寥數語評價清代理學,認為“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155。梁啟超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言道“清代理學家,陸王學派還有人物,程朱學派絕無人物”58。二人所采用的參照系為宋明理學,此等結論盡管稍顯苛刻,但大致無誤,說明了清代以來理學漸漸走向衰落的事實。關學自清初李二曲提出“悔過自新”與“體用全學”,到民國牛兆濂所言“孔子決不會錯,朱子亦決不會錯。學者但當篤信,而不必致疑,死守而不可躲閃也”354的發展史,大致同章太炎與梁啟超的結論相符。這一時期的關學主要沿著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軌轍發展,并未超邁宋明理學前賢。這一時期西方東傳的天主教教義與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對關學產生了一定的沖擊。至清末,迫于時局,以劉古愚為代表的關中士人沖破理學的藩籬,大膽接受西方近代科學知識與政治思想,開啟了關中近代化進程。這一歷史進程也促使陽明心學在關中逐漸式微,直至作為主導性觀念形態退出歷史舞臺。我們可以將劉古愚“中體時用”概念的提出作為這一事件的分水嶺,他淡化了“心學之說”,將“心性之說”導向了自然科學劉古愚在時務齋刊刻的《桂學問答》跋語中提出“道以中為體,以時為用”,“中”即包括陽明良知學在內的心性之學,“時”即時代性。劉古愚的“中體時用”概念突破了洋務運動提出的“中體西用”概念,將西方先進文化與科學技術作為構建中國新文化的有效組成部分。參見張鵬一編:《劉古愚年譜》,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第130頁。。尤其是劉古愚的弟子張元勛比乃師走得更遠,他揚棄了賀瑞麟和劉古愚以“心性本體”為道的思想,在《原道》中對“道”的功用重視超過了對道的本體重視《原道》中有相關問題的問答:“問:言道不言體,體不易知歟,抑故秘不示人歟?”“答:體不能言,可言者不名體。”“問:體何故不能言?”“答:無聲無臭。”“問:不能言,能見歟?”“答:不能。”“問:不能言,不能見,不能聞,胡知為道?”“答:以用知之耳。”張元勛主張的“用之體”的具體內容,也是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知識。參見張元勛:《原道》,民國八年(1919)尊經堂校印本。。這與關學傳統大為不同,預示著關學作為主導性意識形態在關中的終結。吳宓可視為劉古愚再傳弟子,在《空軒詩話》中言及促進關中近代轉型的關鍵人物,茲錄原文于下:
咸陽劉古愚太夫子(光蕡),為關中近世大儒。其學在李二曲、顏習齋之間,雄深篤健,能以至誠感人。近數十年中,吾陜知名之士,無不出其門下。吾生父芷敬公(建寅)、嗣父仲旗公(建常)及陳伯瀾姑丈(諱濤,三原)、王幼農姨丈(名典章,三原)、李孟符世丈(諱岳瑞,咸陽)、邢瑞生世丈(諱廷莢,醴泉)、張扶萬世丈(名鵬一,富平)等,皆相從受業。張季鸞君(熾章,榆林)亦晚歲之門弟子。宓兒時曾獲拜謁,今不復能省記。惟今茲刊印詩文,追溯師承淵源,則于古愚太夫子不敢不首致其誠敬。184
這段文字所列舉的人物大多是近代陜西各個領域之名流。王典章家族為關中巨室,他本人歷官四川、廣州,皆有政聲,后來承擔了劉古愚著述的刊刻任務。李岳瑞為劉古愚至交李寅之子,同劉古愚情同父子,甲午戰爭后參加了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與宋伯魯創建“關西學會”,鼓吹維新。張鵬一著有《太史公年譜》《魚豢魏略補遺》《唐代日人來往長安考》《唐金石考》《唐金石拓片集》《呂刻唐長安城考》《在山堂日記》等。陳濤追隨劉古愚時間最長,是劉古愚創辦實業的得力助手,劉古愚創辦實業的外聯工作主要由其負責,深得劉古愚的信任與倚重。陳濤也積極參加維新活動,辛亥革命后在政府財政部擔任職位,但由于派系斗爭,未能施展抱負。張季鸞是近代中國報業的拓荒者,他和國民黨元老、大書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學家李儀祉并稱為“陜西三杰”。張季鸞去世后,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唁電稱其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大公報》對國共兩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張季鸞與兩黨都保持良好關系。在特定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將張季鸞逝世視為緩和國共關系的一次契機。張季鸞逝世第三天,《大公報》刊登了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的聯名唁電:“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參見《大公報》,1941年9月8日。。吳宓本人則是同湯用彤、陳寅恪齊名的“哈佛三杰”之一,創辦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的《學衡》雜志。上述諸人皆未走上以性理為宗的理學之途,而是適應時代要求,匯入民國新學人的洪流中,與關學漸行漸遠。
考察關學終結的另一個點是1905年在中國實行了千余年的科舉制被廢除,新式學堂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關學失去了發展的土壤。宋代關中地處宋與金、宋與西夏戰爭的前沿,書院不甚發達。張載通過講學,成就了藍田三呂、蘇昞等理學家。元代關中書院逐漸興盛。明代關中的關中書院、三原的宏道書院成為培養科舉人才的主要基地,明代關學學者大都有在這兩個書院授業與講學的經歷。從兩個書院的科舉題名中可以看出造就人才甚多,其中不乏關學中堅。科舉制度廢除后,這兩個書院完全走上新式教育之軌道,尤其是由劉古愚及其弟子主持的三原宏道書院一時成為陜西教學水平最高的學校和陜西思想文化的中心45,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培養近代意義上的經世致用之才。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新式學堂的出現,使關學失去了作為一種學術思想與生活態度的存在土壤,關學所討論的天道性命也不再是學術與思想討論的主導性問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融合關學與西方新思想的新文化形態。關學中的躬行禮教不再主導民眾的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后來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新的生活方式,關學隨之終結還有一點需要說明,作為一種學術形態的儒學在當代的研究,應讓學術回歸學術,讓儒學在與其他文化的對話中發展和更新自己。參見湯一介:《總序》,載汪學群《中國儒學史》(清代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總序》第7頁。作為關中理學的關學也應該如此。關學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終結并非意味著其作為觀念形態與哲學形態的終結,它作為一種思想和觀念形態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在許多方面仍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
【 參 考 文 獻 】
劉述先.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博根: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宋恕.宋恕集.胡珠生,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
楊國榮.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康有為.康有為全集:第2集.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黃克武.梁啟超與儒家傳統:以清末王學為中心之考察.歷史教學,2004(3).
陳黻宸.陳黻宸集.陳德溥,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賀瑞麟.賀瑞麟集.王長坤,劉峰,點校整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李颙.二曲集.陳俊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
李元春.李元春集.王海成,點校整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劉光蕡.劉光蕡集.武占江,點校整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馮從吾.關學編(附續編).陳俊民,徐興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宋伯胤.明涇陽王徵先生年譜(增訂本).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焦云龍,賀瑞麟.三原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王美鳳.關學史文獻輯校.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劉宗周.劉宗周全集:第2冊.吳光,主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7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梁啟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2版.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張靜廬,等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58.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牛兆濂.牛兆濂集.王美鳳,高華夏,牛銳,點校整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吳宓.吳宓詩話.吳學昭,整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武占江.劉光蕡評傳.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編校:祝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