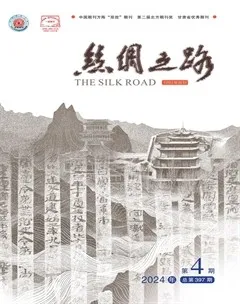文明互鑒視域下簡牘學研究的新進展
[摘要] 2024年9月,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敦煌召開。本次會議共有來自國內外20多個高校、科研院所的8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提交文章70余篇。參會學者圍繞懸泉漢簡及相關戰國、秦漢、魏晉簡牘,就簡牘文化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簡牘文本與簡牘制度、戰國秦漢政治史與法制史、秦漢社會經濟史、簡牘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五個方面展開了熱烈探討和交流,推動了簡牘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
[關鍵詞] 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簡牘學; 懸泉置; 絲綢之路
[中圖分類號] K892.29" " [文獻標志碼] A" " [文章編號] 1005-3115(2024)04-0082-07
簡牘是紙張普及之前中國古人使用的竹、木材質書寫載體,承載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歷史記憶。近代以來,甘肅出土了7萬余枚簡牘,內容豐富,價值極高。同時,甘肅簡牘作為絲綢之路文化遺產,是華夏文明繁榮昌盛和對外交往“美美與共”的見證。對其內涵予以揭示,尤其是對其文物價值的挖掘闡釋對于“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具有長遠戰略意義。如何更好保護、研究、利用甘肅豐富的簡牘資源,是簡牘學界迫切需要關注的問題。西北師范大學作為國內外簡牘學研究的重要陣地之一,在簡牘研究方面學術積淀深厚。2021年5月,西北師范大學成立簡牘研究院,為學校簡牘學科發展搭建了一個良好的科研平臺。同年12月,西北師范大學簡牘學科被甘肅省政府列為甘肅省屬高校國家一流學科突破工程重點建設的“4+1”學科中唯一的冷門絕學學科。為加快推進簡牘學一流學科建設,2023年7月,由西北師范大學牽頭,舉辦了首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學界名宿相聚甘肅敦煌,共同探討簡牘學及相關研究領域的發展和未來。
2024年9月4-7日,由由中國秦漢史研究會、西北師范大學、敦煌市人民政府主辦,西北師范大學簡牘研究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田澍工作室、甘肅簡牘博物館、中西書局、敦煌市文物局承辦,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敦煌市文物保護中心(敦煌市博物館)、甘肅絲路郵驛(懸泉置)文化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協辦的第二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甘肅敦煌召開。西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賈寧,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東北師范大學教授王彥輝,甘肅省文物局二級巡視員白堅,酒泉市委常委、敦煌市委書記王彥群,韓國木簡學會會長、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秉駿,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朱建軍出席開幕式并致辭,開幕式由西北師范大學簡牘研究院院長田澍教授主持。來自韓國首爾大學及澳門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華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湖南大學、華東師范大學、鄭州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西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河北師范大學、浙江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青島大學、西北師范大學等20多個國內外高校、科研院所的80余位專家參會。本次研討會共收到參會論文70余篇,涉及懸泉漢簡等戰國秦漢魏晉簡牘、絲綢之路文明、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古文字、先秦秦漢史等領域,均是簡牘學及相關領域的前沿之作,對推動簡牘學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簡牘文化資源的保護與利用
自20世紀初,國外探險者在中國西北地區先后發現數批漢晉簡牘以來,簡牘研究日趨繁盛,時至今日簡牘學已成為無可爭議的國際顯學。與此同時,兼具文獻與文物屬性的簡牘,如何做好保護和利用,應是其研究過程中的首要課題之一。為此,本次會議期間數位專家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論見。張德芳《懸泉漢簡與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從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等五個方面強調了懸泉漢簡的重要價值,通過分析懸泉漢簡的內容,可以進一步理解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何雙全《懸泉置遺址的保護與利用》從懸泉置遺址的復原展示、活化展演等角度提出了懸泉置的保護和利用建議,為懸泉置遺址的保護和利用提出了更為清晰的路徑。柳肅、梁麗《懸泉置遺址的復原和保護利用研究》通過對懸泉置遺址進行的考古學和建筑史學的對比研究,提出了懸泉置遺址的復原和保護利用的設想和具體規劃設計方案。幾位專家所論具象化了懸泉置遺址的保護和利用,為今后進一步開發懸泉置文化旅游資源提供了良好借鑒。
張強《簡牘學術資源數據庫建設與簡牘智能計算研究進展》圍繞簡牘智能計算研究,對簡牘學術資源數據庫的建設情況進行了匯報,簡牘學術資源數據共享平臺按照“六庫一平臺”的架構設計,開發了簡牘實物庫、釋文庫、字形庫、著錄庫、文獻庫和專家庫,提供了簡牘學術資源多源數據收錄和智能檢索功能,簡牘學術資源數據庫的建設對于推動簡牘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可以為學者提供便捷的學術資源獲取途徑,還可以促進學術交流和合作,推動簡牘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同時,該數據庫的建設也為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和傳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周亮、趙彥《懸泉漢簡研究的文獻計量學分析》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對懸泉漢簡相關文獻進行了系統梳理和分析,揭示了該領域的研究現狀、發展趨勢和研究熱點,結果表明懸泉漢簡研究的文獻數量逐步增加,研究熱點涵蓋了郵驛交通、文化交流和社會經濟等方面。李欣《新媒體時代簡牘文化的“雙創”傳播路徑初探》從簡牘文化傳播和傳承的目標群體及其特征、傳統傳播路徑的優勢和局限性等方面,探討了新媒體時代借助短視頻平臺和爆款游戲,將簡牘內容再媒介化和傳播再媒介化,力求打造簡牘文化的現象級IP、尋找簡牘文化“破圈”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多的受眾帶入一個充滿情感、思考和認同的文化領域,不斷激發和延續受眾的文化記憶,引起受眾對簡牘文化的關注,開辟了一條傳播簡牘文化的有效道路。
申寶濤《近百年來(1914-2024)西北漢簡整理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則通過梳理近百年來西北漢簡整理出版的大致歷史脈絡,盡可能展現了簡牘學研究領域的歷史發展歷程,在某種程度上為今后簡牘學的研究闡釋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簡牘文本與簡牘制度研究
簡牘文本整理是簡牘研究的基礎,亦是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涉及文字釋讀、綴合、編聯等。陳偉曾指出:“用竹片、木板作成的簡牘容易損壞,墨跡容易脫落,編連簡冊的繩索出土時大都腐朽無存。這使簡牘的整理異常艱難,必須通過釋字、斷讀、綴合、編連等多個環節的縝密考訂和反復推敲,才能在文本復原和內涵解讀上,逐漸貼近古人書寫的真相。”(《專注簡牘文獻整理與研究 保護傳承歷史文化遺產》,《中國教育報》2021年3月4日第10版)近年來,隨著大量簡牘的出土、刊布,不論是整理者還是研究者都十分重視簡牘文本整理研究,進而涌現出了數量可觀的學術成果,成為簡牘研究的一個重要學術增長點。本次會議上,學者提交論文中不乏關于簡牘文本整理的力作。如陳松長《本世紀以來湖南簡牘的發現與研究》介紹了21世紀以來湖南簡牘的出土情況,湖南簡牘出土批次多且數量巨大,時代序列完整且內容豐富,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朱赟斌《論天水放馬灘秦簡〈墓主記〉文本性質的多元性》提出從文體發生學的角度來認識《墓主記》文獻的“流動性”、文本的綜合性以及文體的“嵌套結構”等方面的特征,以此可以達到對文本的深度認識。
在簡牘釋文校讀方面,羅小華《西北漢簡名物雜識》將西北漢簡中的名物與南方漢簡所記名物進行對比,認為二者之間存在相同和異同,并就居延新簡中的“貫頭斧”“絮巾”、敦煌馬圈灣漢牘中的“小棓”、懸泉漢簡中有“皂復蓋蒙”等作了細致考論。李洪財《金關漢簡中書信木牘校釋札記》對金關漢簡中所有書信簡作了通盤考察,選取了10枚書牘,對其中的30多處釋文問題作了校讀討論。鐘佩炘《〈肩水金關漢簡〉釋文校札》對金關漢簡中13枚牘的24處釋文作了補釋和改釋。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進一步提升了肩水金關漢簡釋文的準確度,為后續金關簡的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簡文資料。謝計康《居延出土帛書拾零》則對居延舊簡中的一份帛書釋文作了考釋,并主張從書信中的文字對比來分析代筆問題。楊杉《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王祐書信〉校注及研究》對長沙尚德街027號木牘的關鍵字詞和閱讀順序進行了考察,所論為我們今后釋讀書信簡提供了新思路。劉亞濤《南越木簡所見職官考釋(六則)》結合傳世文獻,對南越木簡中所見居室、■弩令、游衛特將、常使、御府丞及監舍等六個職官進行了進一步考釋,豐富了學界關于職官的認識。此外,陳怡彬、吉強、洪帥對近年來新刊布之懸泉漢簡作了不少釋文校訂研究,可視作是當前懸泉漢簡再整理的代表性成果。
簡牘制度涉及簡牘的制作、書寫、編聯、形制等諸多方面,不同形態的簡牘,其性質、功能、制作、使用亦存在差別,而這樣的差別往往能體現出秦漢國家行政運作的細節。本次會議期間,學者就簡牘所見檢署制度、券書分類、封檢形制等展開了討論。張琦《里耶秦簡題署考略》在已刊布里耶秦簡檢署的全面整理、集成的基礎上,對題署用語、格式及其與秦文書律令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進一步闡釋了秦遷陵縣列曹的文書運作方式及其性質。羅晨《西北漢簡券書形制新探》提出將西北漢簡中的券書放入長時段內進行考察,梳理了券書形制的演變趨勢,并從形制與內容的角度,論證了西北漢簡中的“券”與“券墨”屬于兩種不同的文書。馬雪琴《日時在檢中與日時在齒中:兩種漢簡形制的對比考察》對西北漢簡中日時在檢中與日時在齒中兩種現象進行了考察,認為這兩種日時記錄方式,是漢代簡牘文書核查制度的不同表現形式,體現了漢代行政文書運行的多樣形態。
三、簡牘所見戰國秦漢政治制度史與法制史研究
職官制度是戰國秦漢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囿于史料不足,學界以往對戰國秦漢時期職官體系的研究仍有諸多不足,尤其是基層職官體系,學者的討論往往存在較大爭論。近年來,隨著簡牘資料的大量出土,這種窘境得到了改善。高曉軍《由清華簡〈皇門〉〈四告一〉中的“■士”看周代的賢能政治》通過清華簡《四告一》所見的“■士”一詞,認為清華簡《皇門》中的“■事”應讀為“■士”,“■士”問題背后反映了周代的“賢能政治”,是周代政治文明的一種體現。王彥輝、高佳莉《秦漢縣廷佐、史的供職方式與身份流變》聚焦秦漢時期縣廷佐、史的選任和供職方式,認為秦漢時期縣廷佐、史分別選任自“壯”而有爵及能史者,佐、史的供職方式分為常態化和非常態化兩種,通過積累功勞與定期考課等方式,普通的佐、史可以擔任斗食吏或令史等,但大部分縣廷佐、史很難突破僚屬的范圍,隨著基層吏員職役化的過程而被“吏役”所取代。
邱文杰《漢簡所見西域都護副職演變考——兼論西漢宣、元之際的西域經營》認為西域都護副職的演變是漢廷中央重新調整西域經營架構以應對西域形勢之新變化的舉措,副職從衛司馬到校尉的演變,反映了西域都護自元帝以降日漸實官化與地方化的特征,這一變化對兩漢西域經營產生了深刻影響。孫康《新莽史辨證三則——以西北漢簡為例》基于對西北漢簡所見新莽簡的考察,認為馬丞、徒丞、空丞應屬新莽官職,并指出王莽更改郡縣名稱與官制的不同步,造成了同一官印內既有漢郡縣名稱、又有新朝官職的現象。梁文羅《論漢代守官的特殊形式——從懸泉漢簡所見差遣守官出發》討論了懸泉漢簡中的差遣守官,認為這些守官的特殊形式在兩漢時期出現并持續演變,既是漢王朝行政實踐的需要,也反映和影響了漢王朝的政治進程。朱雨薇《漢代“上功勞”與基層官吏培育——以張家山三三六號漢墓〈功令〉簡為線索》認為漢代官吏從選官至任官,再到循環周期性的考課,每一過程都體現了中央對基層官吏進行德、法、能的三維培育導向,嚴格的選任標準、嚴謹的法制規范、嚴密的考核體系,維持了漢代職官體系的長久和穩定。
在史地考證方面,袁延勝《懸泉漢簡所見的“敦煌”》認為懸泉漢簡中的“敦煌”,大致有三種指稱:一是指敦煌郡,二是指敦煌縣,三是指敦煌置。記載有太守、長史、千人等職官的“敦煌”應指敦煌郡,記載有里名、戶籍及職官和地名的應指敦煌縣,記載有御、廄佐的應該是指敦煌置。李迎春《論“河西四郡”與“河西五郡”概念的嬗變》認為在漢人觀念中,并未真正形成“河西五郡”的地理意識,原因應是漢人對地理區劃的認知更重視的是交通因素和郡國行政功能,而非單純憑借自然地理形勢。
在行政運作方面,李玥凝《行政運作視角下的吏卒死亡處理》從行政運作的視角下,對吏卒死亡的相關事務環節進行了梳理,包括死亡原因調查與上報、遺物處理、遺體遣送、死亡統計以及死亡撫恤等五個方面。韓銳《懸泉置簿籍所見漢代民爵書寫與授杖記錄》圍繞漢代的優待措施,討論了漢代的授民爵和養老政策,認為漢王朝統治者通過這些優待措施踐行“敬天順民”“以孝治天下”等家國同構的思想,從而實現其皇權自上而下的滲透目的。艾中帥《懸泉漢簡中的郵人身份及相關問題》認為懸泉漢簡中文書傳遞人員身份的復雜性與懸泉置人員構成的復雜性相一致,懸泉置作為一處郵驛機構,地處交通要道,往來文書頻繁,但又位于西北邊遠之地,常有人手不足的情況,因而置中的官、卒、徒、御都要參與文書傳遞。熊正《說烏程漢簡中的“以格行”“以路次”——兼議“路中大夫”的身份問題》認為烏程漢簡中有“以亭格行”“以格行”“以路次”等以往未見的郵傳簡牘,這類簡牘為研究秦漢郵傳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使“以格為落”的觀點得以驗證。
在律令簡牘與秦漢法制史方面,林曉文《秦及漢初平民的告發體系》認為在秦及漢初基層行政組織、戶籍制度和連坐法將所有人納入法律體系,官民的合作更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的安全與穩定,然從告發體系所反映的法律考慮來看,法律的目的主要著眼社會的穩定和有序治理。王中宇《試論懸泉漢簡所見的一條〈囚律〉簡》認為《懸泉漢簡(壹)》Ⅰ90DXT0112①:1號簡是關于官吏失職的處罰條例,是漢代《囚律》的相關內容,并且可與張家山M247漢簡《二年律令·具律》簡112、張家山M336漢簡《漢律十六章·具律》簡110對讀,二者應是一脈相承的關系。
華迪威《再論隨葬律令簡的性質——兼談其利用問題》認為包括律令在內相當豐富種類的隨葬簡都是仿照現實所制,或直接將現實所用移用于地下世界,或者是為了使其在地下世界更加便于利用而制造新的律令簡或空白簡隨葬,甚至可能是因喪家對逝者懷有恐懼而將其生前物品全部埋入地下,主張將律令簡也視為一種人為的文本,而不是將其與漢代真實的行政過程等同而完全信從。孫占宇《西漢邊塞罪人勞役期問題再探》認為“髡鉗城旦舂”之刑期可推定為七年(宣帝時期),“復作”的勞役期在宣、元、成等朝,大致遵循“死罪令作縣官三歲、城旦舂以上二歲、鬼薪白粲一歲”的規定,西北邊塞上赦令的生效時間,既不是詔書的頒布之日,也不是邊塞機構接到詔書的時間,而是邊塞機構收到赦令后,經過宣傳期(約三天)之后,才正式生效。孫曉丹《懸泉、居延簡所見赦令減、免刑罰程序復原研究》通過考察不同層級機構所承擔的職能,對漢代減、免刑罰程序進行了整體、系統研究,對漢代的刑罰赦免程序進行了有益探討。
四、簡牘所見秦漢社會經濟史研究
簡牘作為第一手史料,對秦漢魏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糾謬補缺作用,尤其是秦漢文書簡牘保存了大量基層社會經濟方面的記錄,為細化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撐。王子今《敦煌懸泉置簡文記錄的風災》以漢代的氣候條件為切入點,圍繞懸泉漢簡及相關簡牘資料中的風災記錄,探討了“大風”“狂風”對河西社會生活與社會生產乃至交通行為產生的影響,深化了學界對絲綢之路交通史、絲綢之路生態史的認識。趙寵亮《懸泉漢簡所見官奴婢》對懸泉漢簡中官奴婢的具體生存狀況進行了探討,官府為官奴婢提供必要的衣食,官奴婢需要承擔文書傳遞、接收發放糧食等雜務,官府會編制不同的簿籍以實現對官奴婢的有效管理。莊小霞《何以御寒:簡牘所見漢代西北邊塞吏卒御寒措施》依據西北漢簡材料,認為漢代西北邊塞吏卒的御寒措施主要有飲食御寒、衣物御寒、器物御寒、建筑御寒等四個方面。黨藝璇《由居延漢簡“辟火”看河西邊塞的防火管理》通過對居延漢簡中“辟火”一詞的釋讀,探討了西北漢簡中漢代邊塞火災的發生情況及原因,考察了漢代制定的火災管理制度,為后世防火、避火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借鑒。
高佳莉《懸泉漢簡所見田畝刻齒簡性質考論——兼談縣置的運行與管理》認為懸泉漢簡中的田畝刻齒簡是記錄田民墾田數目的符券類簡牘,此類簡是出于效谷縣田民以墾田數目輸穀入置的合驗需要而制作,縣置機構在運行過程中受縣廷全方位的支配與管控,其行政體系密屬民政系統的一環。孫富磊《懸泉漢簡〈過長羅侯費用簿〉所見史實新探》認為懸泉置出土的《過長羅侯費用簿》是常惠等一行人前往烏孫迎娶聘禮的消費賬單,并根據懸泉漢簡勾勒出了長羅侯常惠等人在神爵元年及二年來回長安與烏孫的時間線。張亞偉《懸泉漢簡中物價的“時價”與“平賈”》認為在懸泉漢簡的物價材料中,存在“時價”與“平賈”兩種類型,這兩種價格的差異反映出懸泉置民眾日常生活與官員治事間的區別,也折射出河西地區的社會形勢、自然災害和幣制等諸多因素。高澤《漢廚有關問題探討——以新刊布敦煌懸泉漢簡為中心》聚焦懸泉置中的“廚”,探討了廚嗇夫的本職與兼職,將簡牘記載的與廚有關的生活用具和懸泉置出土的實物廚具進行了對比研究。
肖從禮《懸泉漢簡所載穬麥為皮大麥補證》認為漢簡中記載的穬麥為帶稃殼的大麥,而漢簡中記載的大麥應為青稞,也稱“元麥”,人、畜皆可食用。袁雅潔《論懸泉漢簡中的傳食簿籍》認為懸泉漢簡中的傳食簿可分為兩種,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注明“有(無)傳”,并提出“無傳”類傳食簿可能與失亡傳信的官吏傳食有關。吳雪飛《秦至漢初的運送物資之徭》認為秦至漢初的運送物資之徭,包括“委輸傳送”“載粟”和“長挽粟”三種,“委輸傳送”和“載粟”采用牛車運輸,以縣為單位接力進行,“長挽粟”采用輦車以人力運輸,不采用接力的方式,而是跟從軍隊長途運輸,運送的方式分為陸運和水運。
除此之外,部分與會學者還利用簡牘資料考察了秦漢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狀況。如武普照《財政視角下的秦漢馬政研究——以新出簡牘為中心》運用財政的收、支、管視角分析了秦漢馬政發展演變的脈絡,探究了馬政收入的沿革情況以及涉馬財政的支出狀況,全面地闡釋了秦漢時期馬政發展的樣貌及影響。孫寧《漢代西北屯戍機構手工藝品的制作與銷售》認為西北屯戍機構中部分具備手工技藝的戍卒會在吏員的組織下編制手工藝品,生產的產品,一部分可能作為所在機構的日常用品,一些也會委托相關吏民代為銷售,售賣手工制品所得的錢物可能是作為“稍入錢”的一部分,由出售物品的機構支配使用。符奎《東漢臨湘縣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以五一簡為中心的探討》認為臨湘縣及其周邊地區的商品經濟比較發達,但這種發達是建立在自然經濟穩定與發展的基礎上,國家對商業的重視,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但在重商的同時,仍然堅持以農為本,對土地實施嚴格的管控,奠定了鄉里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
五、簡牘所見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
西北漢簡特別是懸泉漢簡見有大量漢王朝與西域、中亞國家交流交往的真實記載,是漢代絲綢之路開通與繁榮的重要歷史見證。近年來,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利用學術研究服務國家戰略,是簡牘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李世持《懸泉漢簡所見西域諸國人名與漢名文化傳播討論》從語言學角度,討論了懸泉漢簡中的西域諸國人名,認為隨著漢朝與西域交往的逐漸深入,民族之間的融合也進一步加強,這一點可以從漢譯人名和漢名文化傳播與民族融合方面得到印證。李娜齊《橐佗:兩漢時期東西方物種交流、文化交融的見證——以簡牘資料為中心的考察》認為兩漢是東西方物種交流的繁盛時期,簡中記載橐佗通過域外入貢、歸義互市和戰爭等方式源源不斷地進入漢地,其引入不單可以豐富物種的多樣性,還擁有一定的政治象征意義,表明漢對西域的統治加蓋了印章,橐佗形象與本土化信仰結合,更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生動例證。蔡金媛《敦煌懸泉置張帷考——由懸泉置接待龜茲王王夫人的規格說起》結合漢代文獻記載和畫像磚等資料,對懸泉漢簡中記載的懸泉置配置的帷帳資料進行了梳理,對懸泉漢簡記載的張、帷形制、顏色、作用、懸掛方式與接待使用標準進行了分析,認為懸泉置的張、帷的使用與接待人員的身份、地位和職位有關,是漢代禮制的一種體現。
此外,也有學者就簡牘書法等相關議題作了討論。蔡副全《楷書的萌芽與流變——以漢晉簡牘、紙文書為中心》梳理了楷書的發展脈絡,認為楷書濫觴于漢宣帝神爵年間,經過不斷發展,在桓靈之際,楷書新體逐漸形成,并大量應用于官私文書中,而紙張的出現和普及使用則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楷書的形成。馬賢亭《從倒薤筆法看簡牘文字在隸變分期中的早晚——以岳麓秦簡為考察中心》以岳麓秦簡為考察中心,探討了倒薤筆法在秦簡牘隸變過程中的發展軌跡,通過舉例分析岳麓秦簡中倒薤筆法的表現形式及變化特點,結合倒薤筆法在不同時期特征表現的比較研究,揭示了倒薤筆法形態在隸變中的早晚演變規律,為秦簡牘的年代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周晶晶《敦煌懸泉漢簡草書的演進模式與狀況》認為懸泉漢簡中系統有序的草文字書寫是考察早期草書演進情況的絕佳標本,通過圖證分析,可從中看出懸泉漢簡草書的演進具有縱引主線和橫展輔線兩條基本線路,而書寫的捷易追求與字形的易識原則構成了懸泉漢簡草書得以正常演進的“推促—牽扯”的二元式引擎。張崗《出土古紙所見漢代紙張制作技術的演變及其使用問題》通過分析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紙文書,對漢代紙張的使用情況進行了探討,西漢時期紙張制作出來后起初被用于包裝或襯墊物品,隨著紙張表面加填料以及涂布施膠工藝的出現,紙張具備了書寫文字的條件,先后被用于書寫藥物名稱、進行書信交往等,伴隨著抄紙法的出現,紙張被用于抄寫典籍上的一些內容。椎名一雄《唐代簡牘使用情況來看東亞木簡文化圈》以“構建東亞木簡文化圈”的學術視角,回顧了唐代使用竹簡和木簡的情況,并從編纂的歷史文獻中考察唐代竹簡和木簡的使用情況,尤其是以唐代的詩歌為例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探討。
綜上所述,本次會議取得了豐碩的學術研究成果,既有簡牘文本整理與簡牘制度探討的基礎性研究,也有簡牘與戰國秦漢政治法制史、社會經濟史、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等專題性研究成果,還有簡牘資源保護與利用的應用性文章,基本涵蓋了簡牘研究的方方面面。與會學者提交的70余篇文章,均是簡牘學及相關領域的前沿之作,較好地展現了簡牘研究蓬勃發展的態勢。總結本次學術會議成果,不僅對推動簡牘學研究、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深化文化保護與傳承理念、提升地區文化發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西北師范大學簡牘學在學術界的美譽度,對加快推進“簡牘學”一流學科建設大有裨益。
[作者簡介]" "艾中帥(1996-),男,漢族,河南駐馬店人,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簡牘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