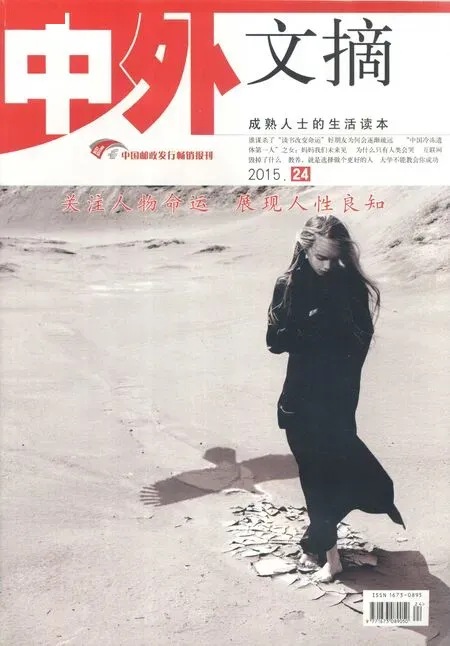為什么只有人類會哭
□ 李崢嶸
?
為什么只有人類會哭
□李崢嶸

人類和動物有什么不同?這個問題眾說紛紜。只有人類會制造和使用工具?不,很多動物也能夠制造和利用簡單的工具。只有人類有系統的語言?動物也有。《人類為何會哭》認為,人和動物的區別在于一種小小的排泄物:眼淚——這種排泄物也是唯一不讓人感到惡心的排泄物。《人類為何會哭》認為情緒性的哭泣是人類的專屬行為并將之發展成為一門悲劇藝術。
《人類為何會哭》開始于一個真實的新聞故事,德國動物園的大猩猩媽媽失去了剛出生三個月的寶寶,大猩猩一直悲傷地抱著兒子的尸體。這個畫面被媒體廣泛報道,很多人看后流下了眼淚。而大猩猩媽媽始終沒有流過一滴眼淚。作者由此步步論證,只有人類會流下情緒性的眼淚。當然,動物也會感到悲痛,也會對同伴的情緒做出同情反應,但是并沒有確鑿證據顯示動物會因為情感原因而流淚。即使你看到家里的寵物流淚,那也只不過是一種生物反應,部分原因是為了保護眼睛——就像人類因為剝洋蔥而流淚。
《人類為何會哭》作者邁克爾·特林布爾是倫敦大學神經病研究所名譽教授,致力于神經解剖學的研究,同時也是一名精神病醫生,在治療情緒障礙上有豐富的臨床經驗。這本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交叉的有趣認識,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解析情緒控制的機制、探索藝術靈感的起源、揭示智力進化的秘密。
人類因為情緒而流淚有什么意義?
其中一個原因正如中國人所說“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對任何年齡的人來說,哭泣都是獲得幫助和情感支持的有效手段。剛出生的嬰兒哭聲響亮,但是直到四個月才會出現眼淚。嬰兒能通過哭泣與周圍的環境進行交流,甚至會調整自己的哭聲表達特定的意圖。腦成像顯示,媽媽聽到嬰兒的哭泣時大腦的特定區域會出現異常活動,會做出哺乳或者其他安撫行為。這就是哭泣在嬰兒和母親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結,嬰兒對母親的依賴和彼此之間的緊密關系就是家庭的雛形。
在靈長類動物進化過程中的某一個時刻,面部表情在溝通中的重要性超越了手勢,人的雙手得以解放。還記得開始的故事嗎?大猩猩媽媽搖晃著自己死去的孩子,但是并沒有哭泣。在自然界中,猿猴媽媽會時時刻刻抓住自己的孩子,幾乎從不離手。但是人類媽媽不同,母子并不會時刻抱在一起,而是通過聲音和面部表情進行溝通。這樣媽媽就能騰出手來做別的事情。這一點對嬰兒新技能的產生也很重要。人類成長所需要的時間比任何目前已知的物種都要長,其中大部分的時間是為了掌握融入同類當中的技巧、學習生活和愛。
眼淚可以直接、明確地表達熱烈的情緒狀態,見證哭泣的人會因此做出反應,哭泣的一方會根據對方的反應,調整自己的行為和策略。研究人員讓男性聞女性的眼淚,聞過之后男性的性喚起指數明顯下降,睪丸酮水平也降低了。這就從生理學角度解釋了為什么女人的眼淚會讓男人心軟。
和所有的排泄一樣,人們一般不會在大庭廣眾哭泣,但是在葬禮、電影院或者劇場,人們卻毫不避諱地流下眼淚。葬禮或者追悼會上,在追憶逝者的時候,哭泣甚至會成為一種儀式,這再次說明哭泣在社會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看電影哭泣的意義則不一樣。2000多年來,人們一直通過觀看悲劇流下眼淚,今天人們夸獎一部電影也常常會感嘆:“太好看了,我哭濕了一包紙巾!”為什么人類需要悲劇藝術來釋放情緒并從中獲得滿足感?哲學家、文學家都有自己的角度,《人類為何會哭》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一探究竟。
研究表明,眼睛受刺激流出的眼淚和情緒性的眼淚,這兩者的化學成分并不相同。情緒性眼淚中蛋白質含量較高。和受洋蔥刺激流出的眼淚相比,觀看悲劇流下的眼淚中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含量明顯更多。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是壓力的指示劑,如果強忍眼淚則會導致壓力上升,引發疾病。
作者認為,悲劇藝術喚起的情緒,與人類的其他常見情緒大不相同。悲劇藝術喚起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與社會連接以及愛相關的情緒,同欣賞美麗的食物時的感受有些類似。從生理學的角度看,悲劇喚起情緒的過程不會起到宣泄的作用,但是能帶來情緒覺醒與平靜感交錯的舒適感覺。
我們的眼睛看到的只是客觀世界的表象,我們認識的世界,實際上是精密的中樞神經和大腦對萬物過濾后留下印象。在漫長的進化歷史中,人類產生了愛的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失落感,悲劇藝術將多種感覺融合,讓我們感動落淚,這種情緒也是祖先的經歷發出的歷史回聲。
(摘自《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