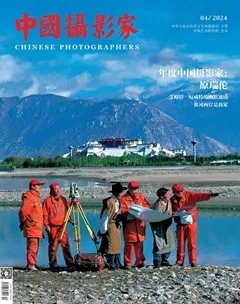“萬務有時”:劉瑾的荒誕影像之詩

劉瑾曾是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新聞攝影記者。自1997年開始,他拍攝了包括汶川地震在內的眾多重大新聞事件,其中還有一系列帶著時代氣息的紀實攝影作品。2002年,他未經戰前訓練,便趕赴阿富汗拍攝前線戰況,其戰地攝影生涯的開端是勇敢的,甚至略顯冒失。不久之后,在一次任務中,他趴在路基上,拿著長焦鏡頭準備拍攝一隊墻邊的士兵。取景框中,一位士兵正在調轉槍口,缺乏戰場經驗的他并未看出對方的目的,渾然不覺危險,如常按下快門。同一瞬間,那位士兵的槍口噴出火光與白煙,快門聲與槍聲幾乎響在了一起,子彈釘在他身旁兩三米遠的地面上,激起一縷塵土,劉瑾差點兒將性命丟在了阿富汗戰場。


戰地攝影的“危險”人盡皆知,但是,或許只有經歷那命懸一線的瞬間,這個詞所暗藏的分量才能被真正掂清。此后,他分別于2005年、2009年兩度以國際安全部隊隨軍記者的身份,深入伊拉克與阿富汗戰場前線,拍攝了一系列獨家新聞攝影作品,并于2021年出版戰地攝影回憶錄《巖石與棕櫚樹》(The Rock and the Palm Tree)。這部攝影作品集并未過多渲染戰爭的視覺張力或酷烈場面,而是將重點鎖定在被裹挾進戰爭旋渦的人們的日常生活:布滿戰爭瘡痍的街道上的行人、戴著黑頭巾的女學生露出的紅色指甲、暴風雪中牽著綿羊的男孩子、用花朵裝飾武器的士兵們、向街邊殘疾人施與錢財的路人等。可以說,這部作品集是劉瑾從戰地新聞攝影向攝影藝術創作轉型的縮影。
一、守序的影像與反思的影像
新聞攝影是呈現新聞信息的一種視覺手段,歸根結底是一項新聞工作,其性質由新聞特性決定,其邊界由新聞規則厘定。理論上講,新聞價值決定了新聞攝影的題材取舍,時效性決定了其當下意義,而新聞行業倫理與規范則為它設置了嚴格的底線,決定了何為適宜。從具體拍攝實踐上看,新聞攝影要“考慮媒介對稿件的要求和用途……追求個人判斷和影像風格表現也必須兼顧媒介發表的可能性”[1],其最終呈現則更是一項整合性的集體勞動。新聞信息的生產邏輯統攝著新聞攝影的拍攝思路,而這種邏輯自然也延伸到影像語言之中:明確的主體、準確的信息、精確的表意。質言之,新聞攝影是一種守序的影像。
“守序”并非貶義,僅是一種描述性特征。不過,藝術創作卻常構成對表層秩序或陳舊秩序的反思。反思性的內容也少許存在于新聞攝影之中。但是,不同于新聞攝影,攝影藝術的反思不能僅是技術性的,而必須通達文化,不能僅出于行業框架與文化慣例,而要更多地源自主體質詢與生命體驗,它是攝影藝術作品生命力的來源。
對于創作者來說,影像轉型總是十分不易。因為,經驗主義宰制下的路徑依賴廣泛存在于事物的演變邏輯中:對既有模式的熟稔程度,與路徑依賴程度和轉型難度二者成正比關系。走出路徑依賴,需要的是以自我剖解為前提的主體變革,常是一個殘忍且危險的過程。因此,創作轉型前后之間的風格撕裂十分常見。
劉瑾對既有模式相當熟稔,其新聞與戰地攝影久經磨礪,佳作頻出。但是,其影像轉型卻十分順滑,并未顯露出既有慣習的積重難返,也未見出彼時與此時之間的風格撕裂,更未見出主體的掙扎與扭曲的些許痕跡。這或許是因為,他的反思影像脫身于既有的守序影像,并獲得后者的滋養。這一滋養首先是視覺修辭意義上的:新聞攝影經驗使劉瑾的體驗與觀念得以在清晰且富有節奏感的視覺秩序中展開。因此,其轉型不僅不意味著割棄舊有的稟賦,反而是有所承續,甚或有所增添,最終通向一種兼得視覺素養與文化力度的影像成果。

其次,戰場猶如一個母體,以其酷烈的高壓情境,促逼著劉瑾反思凡俗生命的意義與日常生活的狀貌。身處戰場,“活在當下”這樣一句本來空泛無味的話,變得十分具體。劉瑾曾說,每天外出拍攝時,他總是不知是否還能夠回到營地吃晚飯,而哪怕用罷晚飯,也會對食堂沒有在飯間被炸掉充滿感恩。難以預知的來日、朝不保夕的生活,讓他斂起目光,回置于腳下的土地與周遭的日常。誠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日常生活批判 第二卷》(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Ⅱ)中所言:“最徹底的社會歷史辯證法存在于最深層次的微觀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在這投向生活細節的目光中,劉瑾的照片探察到了幽微的生命體驗,也重新發現了日常幕后的文化意義。他曾拍攝過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今,他發現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小事物,如一株草、一瓶罐頭、一只小動物、一座室內盆景,或許埋藏著足以匹敵那些重大事件的思想蘊意。這一創作經歷提供了關于藝術轉型的有益啟示:從既有創作模式中汲取轉型之養分,在自然而然的主體經驗中尋獲轉型之動力。
二、“萬務有時”:荒誕日常的詩性批判
于戰地攝影而言,“在恰當的時間處于戰爭中的恰當位置,有時意味著一個攝影師的成功”[2],但對日常生活而言,向來便不存在所謂“恰當”的時間與位置。觀照日常的直接攝影看似簡單,“咔嚓”一聲便可獲得一幅照片。但也正是在這“咔嚓”一聲中,它的難處默默顯現:攝影者的每一次拍攝都必須以即興的模式,去展露在面對恒常流變的日常生活時,其眼光的敏銳與周密。“日常”是我們浸于其中的環境,但卻從不是容易觀照的對象,因為在其滿懷的真意之上,總是附著著一層層的謊言與偽飾。觀照它,既需要思考,也需要眼力,而呈現它,既考驗判斷力,也考驗視覺素養。

劉瑾的影像語言并非如常規紀實攝影般大開大合、狀似隨意,而是始終透著謹慎,甚可稱為小心翼翼。在他的影像中,中近距離的人物并不多見。人的面龐最能表達與感染情緒,為照片提供臨場感。通過人物及其面龐的缺席,劉瑾的影像建立了一種狀似沉思的疏離感。不過,劉瑾并非不關注人,相反,其作品處處顯露著人類意志的多樣側面。空置的椅子、滿載磚頭的面包車、被木樁圍擋起來的林地,都以缺席的方式暗示著人類的強烈在場。顯然,這在場并不和諧,而是顯示出日常生活的荒誕。
從新聞攝影到攝影藝術,劉瑾的影像發生了諸多轉變:明確的主體轉變為懸置的主體、準確的信息轉變為模糊的絮語、精確的表意轉變為多義的表述。同時,我們還能清晰地感受到拍攝過程中劉瑾步調節奏的變化:從快步追尋新聞熱點,到駐足下來的凝望與思忖。由此,其影像經歷了逐漸冷卻的過程,也映射出了他在知覺形式上的某些變化。這生成了一種寧靜的觀感,它更能使人駐足下來,為生活乃至文化意義上的反思提供時間與空間。
守序的影像要求鏡頭前的外在世界變得馴順,而反思的影像則要求鏡頭前的外在世界展露其失控的一面:復雜性、異質性、非理性等。在劉瑾的影像中,這最終呈現為有序形式中的一派荒誕圖景。迄今為止,《萬務有時》(A Time for Everything)是劉瑾最為成熟的作品,因而匯聚了其轉型后的創作的主要特征:一種詩性的影像批判。


所謂“批判”一般體現為基于邏輯的哲性,而鮮少體現為出于直覺的詩性。不過,劉瑾的影像充滿詩性,其批判也由此內斂至幾近不可見的程度。此間,仿若因專注而魂靈出竅的一個個人物、以凝滯不動宣示其存在的一件件尋常事物,以及似乎時常有所缺略而有待填充的一個個場景,成為了一系列有待省思的視覺意象,使劉瑾的影像超脫于表層的紀實,轉而獲得一種潛藏著文化批判的詩性特質。
在題旨上,劉瑾對人的觀照頗具馬丁·帕爾(Martin Parr)的況味,意在從畫面內部要素的反差中,提示人類真實生活的荒誕樣貌。但不同的是,劉瑾的影像既不辛辣,也不露骨,反而透著一種淡然的氣質。不同于將自己也納入荒誕現實之中的帕爾,劉瑾始終與對象保持著一段堪稱彬彬有禮的距離。在他眼中,事物確乎千奇百怪,時有瑕疵,甚或怪誕,但是它們也都處在自身的變易過程之中,在這時間序列中,每一刻都是過去時刻的孕生,也是下一時刻的萌芽。表觀之怪誕,往往是時序之必然,此謂之“萬務有時”。
(鄭家倫,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1] 盛希貴:《新聞攝影》,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2] [意]帝奇亞諾 · 坦尚尼:《偉大的照片是思想的呈現》,載[美]劉香成:《中國:1976—1983》,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第20頁。
作者簡介:
劉瑾,1973年生于四川成都,1999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圖片攝影專業,后擔任法國新聞社攝影記者,2012年后開始從事攝影藝術創作,現生活工作于上海。曾獲第66屆全球年度圖片獎(Pictures of the Year International)杰出獎,曾參展2023麗水攝影節。2021年出版《巖石與棕櫚樹》自傳性戰地攝影書。
責任編輯/何漢杰 鄭家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