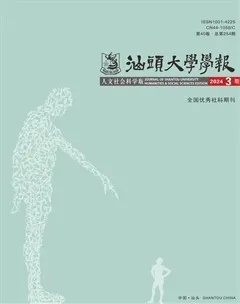趨同還是多元?比較視野下的監管型國家建設



摘 要:監管型國家的全球擴散意味著不少國家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去治理市場,因而不同國家在監管型國家的制度建設方面呈現出了一些共性。但更多地,監管型國家建設是一種差異化現象,地區間、國家間、行業間的監管型國家建設皆有不同。監管型國家既有可能服務于更強的國家干預目標,也有可能作為替代凱恩斯主義的新市場治理策略出現,還有可能因為受到外部壓力的影響而被國家移植和學習。不同背景下監管型國家建設的差異將主要表現為獨立監管機構在成立時間、覆蓋行業、獨立性水平、功能、行為等等方面的多元化特征。考察監管型國家建設的這些差異與其監管結果之間的聯系,分析中國監管型國家建設的理論位置及獨特貢獻有助于進一步發展監管型國家的比較理論。
關鍵詞:監管型國家;國家建設;獨立監管機構;監管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225(2024)03-0005-12
一、引言
中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妥善處理國家與市場關系、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成為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故而開展與此相關的理論研究至關重要。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市場治理策略,諸如古典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發展型國家、新自由主義等等策略皆曾因其對經濟增長或市場發展產生了顯著貢獻而備受矚目。相比之下,監管型國家(regulatory state)這一同樣重要的市場干預方式所受到的關注仍然有限。監管型國家的獨特之處在于其在組織安排上主要通過立法授權產生的獨立監管機構去實現其意圖,并在工具安排上通過制定和執行法律去糾正市場失靈。與既有策略緊緊圍繞國家干預市場的限度來展開辯論不同,監管型國家既強調國家與市場之間存在明晰的界線,也強調國家對市場失靈問題予以矯正的必要性。因此,對監管型國家而言更關鍵的是國家如何有效地進行市場干預,而這首先指向了監管型國家自身的理性化建設問題。
監管型國家建設描繪了一個國家逐步實現市場干預監管化、監管主體國家化、國家監管理性化的過程。圍繞監管型國家建設這一議題,既有研究不僅追溯了其最初誕生于美國的歷史,也考察了其后來從美國擴散至歐洲、拉美、亞洲等地的現象。這些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將不同國家的監管型國家建設視為以美國模式為原型的監管型國家全球化的過程,并將政治和經濟發展意義上的南方國家的監管型國家建設視為對北方監管型國家的學習和移植,因而不同監管型國家之間存在著基本的制度趨同。與此同時,監管型國家的制度移植還將與國內政治相互作用,從而賦予每個監管型國家獨特性,而這最終會使各國的監管型國家形態各異。
為了增進對監管型國家的認識,文章首先就監管型國家的概念展開辨析,澄清其含義與測量。其次以國家和地區為線索對監管型國家建設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以揭示比較視野下的監管型國家建設在形式方面趨同的同時也在實質方面多元這一發現。最后進行全文小結和討論,強調相關研究可繼續考察不同監管型國家建設與其監管效果之間的聯系,并應關注中國監管型國家建設在比較研究中的理論位置與獨特貢獻。
二、監管型國家的概念辨析
(一)監管、國家監管與監管型國家
認識“監管型國家”首先需要理清其與“監管”“國家監管”之間的聯系與區別。
監管是一個古老的現象,它可以追溯至羅馬時代的價格和生產控制,以及反壟斷[1-2]。時至今日,監管目的、監管主體等要素的組合使監管出現了多種形式。從目的來看,監管至少包括旨在防止壟斷、促進競爭的經濟監管,以及維護整體社會利益的社會監管[3]。從主體來看,監管者既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民間力量,還可以是監管對象本身。
盡管各類監管模式并非皆由國家主導,但不可否認的是,幾乎任何形式的監管都離不開國家參與,唯一的區別似乎是國家參與的多或少[4]。因此,國家可以說是監管活動中最關鍵的主體,這也意味著“國家監管”是監管中的重要形式。國家監管劃定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代表著國家約束私人活動的范圍[5-6],其在廣義上指國家對經濟展開的所有形式的干預,在狹義上則指國家對自然壟斷的控制[7]。同時,與其他國家治理方式相比,國家監管的特殊性在于以法律為核心工具,旨在通過頒布和執行規則來調整私人行為,從而引導個人和企業實現在沒有法律的情況下他們不會實現的結果[8-9]。
相比之下,“監管型國家”是諸多國家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主要采用的一種國家監管模式。在此之前,歐洲國家主要通過國家壟斷來消除私人壟斷,即通過公有制來維持經濟秩序。與之相比,監管型國家主要通過隔離于選舉政治和傳統官僚部門的獨立監管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ory agencies, IRAs)來規范市場活動。由于獨立監管機構的權力源于法律授予,因此監管型國家也被學者稱為法定監管(statutory regulation)模式[1]。可見,國家監管并不能直接與監管型國家畫上等號,盡管它們從字面上看起來相似,但實際上卻是包含關系,如圖1所示。
(二)監管型國家與發展型國家
對“監管型國家”更深入的理解可通過將其與“發展型國家”作比較來實現。監管型國家和發展型國家固然有著諸多區別,但也有著共通之處。
就區別而言,第一,發展型國家與監管型國家出現的時間和地域不同。發展型國家主要出現于二戰后面臨軍事備戰壓力、持有高漲的民族主義、懷揣強烈的發展愿望的東北亞地區,如日本、韓國[10]。而監管型國家最早出現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導致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傳統被侵蝕的美國[11],流行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西歐、拉美、亞洲等地[12-14]。第二,發展型國家和監管型國家有著不同的目標和政策工具。發展型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經濟增長,并以產業政策為核心手段來選擇性保護國家的支柱型產業發展[15]。而監管型國家主要追求的是彌補市場失靈,希望通過遏止壟斷、促進競爭、維護消費者權益來維持正常的市場秩序。為此,監管型國家通過制定并執行與監管有關的法律來規范偏離上述目標的企業行為[16]。進一步看,發展型國家的市場干預措施具有積極協調性質,即國家通過直接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干預來影響經濟結果。而監管型國家更注重對經濟運行過程的監督,體現出消極協調特征[17]。第三,發展型國家和監管型國家通過不同的組織安排來實現各自目標。領航發展型國家的機構主要是傳統的經濟精英官僚部門,如日本的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韓國的經濟規劃委員會(Economic Planning Board, EPB)[18]。與之不同,落實監管型國家目標的機構主要是通過單獨的立法授權產生的第四部門——獨立監管機構[11]。
就共性而言,第一,從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來看,發展型國家與監管型國家皆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運轉,它們共同的課題是管理、約束和保護市場運行,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二者都體現出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態度,與徹底的自由放任主義形成鮮明對比。第二,從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來看,不論是發展型國家還是監管型國家,國家目標能否實現皆與特定的政企關系息息相關。例如,發展型國家的嵌入式自主(embedded autonomy)、被治理的互賴(governed interdependence)等良性政企關系有助于促進經濟飛速增長[18-19],而裙帶資本主義下的政企關系卻會導致腐敗與尋租[20]。再如,在監管型國家,當監管者通過政治獻金、旋轉門等方式與被監管企業之間產生聯系時會出現監管捕獲現象并造成監管失敗[21-23]。第三,從國家內部關系的角度來看,發展型國家和監管型國家實現其目標的能力均取決于承擔相應職能的機構能否獲得獨立于其他機構的權力和地位。具體看,日本通產省對經濟的有效領航正是得益于立法、司法部門僅僅扮演著“保險閥”角色[15]。而拉美國家總統的干預阻礙了獨立監管機構的負責人按照法定授權如期履行其職能[24]。
(三)監管型國家的測量
概言之,監管型國家指國家在組織安排上主要通過立法授權產生的獨立監管機構來承擔監管工作,在工具安排上通過制定和執行法律來實施監管,以此實現彌補市場失靈的國家目標。顯然,監管型國家是對一系列經驗現象的抽象提煉。在了解其基本含義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準確地辨識監管型國家?換言之,在經驗研究中,作為一個變量意義上的監管型國家,我們應當如何測量它?針對這個問題,既有研究似乎不約而同地聚焦于獨立監管機構,畢竟它是監管型國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之一[25]。
獨立監管機構被認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擁有專屬的組織。獨立監管機構通常獨立于其他部門,并有著單獨的人事制度和財務權限。第二,擁有專屬的職權。獨立監管機構主要承擔產業的監管工作,其與產業的發展工作相分離。第三,獨立監管機構的組織和職權皆源于法律特別授予,具有合法性[13,24-28]。
三、美國監管型國家建設
(一)進步時代以前:全國性監管缺位
正如前文提到的,監管型國家最早出現于美國,正是美國模式奠定了現代監管型國家的基石。因此,監管型國家起源的歷史,也就是美國監管型國家建設的歷史。要完整地呈現該故事,需要從美國監管型國家誕生之前的監管傳統講起。
美國早期的國家監管正如托克維爾的觀察,充分地體現了地方自治特點。在監管型國家出現之前,美國的監管活動主要由地方而非聯邦負責,且高度依賴法院系統。此階段聯邦的監管法律僅涉及州際蒸汽船操作、經商海員的工作條件、西部毛皮貿易等事項,以及南北戰爭期間的銀行監管和保護性關稅。該時期聯邦監管的缺位與美國當時的背景有關。首先,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并不需要過多的監管。第二,奉行個人主義、自給自足傳統的農業生產者并不支持過多的國家干預。第三,經濟目標以重商主義為主,而非監管。第四,州足以應對必要的監管活動[11,29]。
(二)進步時代:監管型國家崛起
1887年,美國第一部全國鐵路運輸監管法案——《州際商業法案》(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 ICA)出臺。該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對州際鐵路運輸企業及其經營活動進行監管,并為此授權成立了美國史上的第一個獨立監管機構——州際商業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來負責相關監管事宜,這標志著現代監管型國家的起源[29]。
州際商業委員會反映了美國獨立監管機構的基本理念。在組織、人事、財政安排方面,其授權法案第十一條、第十八條規定,州際商業委員會經此法案授權成立,委員會設置五名委員和一名秘書,委員會還可經內政部長批準后聘請工作所需的雇員。五名委員中不得有三名來自同一政黨,委員人選由總統任命,并經參議院同意后上任。除第一屆委員任期由總統指定分別采取兩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外,委員繼任皆采取六年任期制。委員工作為專職,且不得與鐵路運輸承運人之間有任何形式的經濟聯系。委員年薪為七千五百美元,秘書年薪為三千五百美元,委員會成員出于工作目的所需的必要設備和費用由委員會主席和內政部長予以批準和支付。在監管內容方面,法案規定州際商業委員會可就鐵路承運人的不當定價、不當收費、不當獲取各種收益、給予托運人不當優惠、損害托運人權益、阻礙托運人從出發地到目的地的連續運輸、形成卡特爾組織等違法行為,以及鐵路承運人拒不履行向消費者公開價格規定、賠償責任等行為進行監管。在職權范圍方面,法案規定,州際商業委員會可依據該法案規定的情況對鐵路承運人的經營活動進行調查、取證、裁決,并要求鐵路承運人執行裁決結果(包括停止違法經營行為、作出賠償等等)。當鐵路承運人拒不履行,經法院判定合理的裁決,州際商務委員會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此外,州際商務委員會還可制定或修改與其工作有關的一般規定[30]。從中不難看出,獨立監管機構制度至少反映出兩個理念:第一,監管獨立,具體包括獨立于政治(民主選舉、傳統官僚部門、黨派),以及獨立于被監管者。第二,監管行使復合性質權力,集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于一身[11]。
在進步時代,除了州際商業委員會之外,美國還通過各部法律分別授權成立了其他幾個獨立監管委員會,它們包括:(1)于1913年由《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授權成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Board)。其負責有關聯邦儲備銀行的監管事務,如審計銀行賬目、規定銀行利率、重新劃分或增加儲備城市和銀行、任免銀行職員、暫停銀行業務等等[31]。(2)1914年由《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授權成立的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負責對個人、合伙人、企業的不公平商業競爭行為進行監管[32]。(3)1916年由《航運法案》(Shipping Act)授權成立的航運委員會(the Shipping Board,聯邦海事委員會前身),負責監管國內外航運貿易[33]。(4)1916年由一部綜合法案(Act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and for Other Purposes)授權成立的關稅委員會(Tariff Commission),負責海外貿易監管[3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伴隨著獨立監管機構的出現,美國出現了大量的全國性經濟監管活動和法律,進步時代因而被視為美國監管型國家崛起的年代。
進步時代美國監管型國家的形成可以從結構和行動兩個方面去解釋。在結構方面,首先,市場環境的變化催生了大量的監管需求。與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無需過多的監管相比,在進步時代,貿易、工業、科技、城市的發展共同導致市場運行變得日益復雜且混亂。企業在數量和規模上的擴張、資本力量的壯大和勞工問題的出現、工薪階層增加、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城市人口劇增等等變化皆有賴于通過國家監管來維持秩序。其次,國家原有監管能力的缺乏為獨立監管機構的設立創造了契機。不論是立法、行政還是司法機關,似乎都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術和效率來應對復雜多變的市場行為及其后果。同時,以地方為主的監管亦難以處理全國性經濟活動。因此,成立專門的機構來進行監管順理成章。最后,聯邦層面的國家建設為監管型國家崛起提供了可能性。南北戰爭的結束為聯邦政府的中央集權奠定了基礎,進步時代的文官改革和軍隊重組也幫助聯邦政府增強了中央集權,這些變化使美國得以重塑監管體系,將分散的地方監管調整為統一的中央監管。在行動方面,利益集團理論有助于解釋特定領域獨立監管機構的出現。例如,研究表明,1887年州際商業委員會的誕生是農民等追求降低鐵路短途運輸費率的利益集團努力游說的結果[11,29]。
(三)進步時代之后:監管型國家的停滯與發展
美國監管型國家自進步時代崛起以來,還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首先,在二十世紀前三十年左右,美國的獨立監管機構疲軟運轉。由于美國在一戰期間的主要目標是為戰爭動員國家經濟,因此諸如州際商業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等獨立監管機構被暫時忽視。此后數年間,州際商業委員會于1920年獲得了《運輸法案》(Transportation Act)授權,但實際上并未使用這些權力;聯邦貿易委員會被降級為調查機構;1920年,《聯邦水力發電法》(The Federal Water Power Act)授權成立水力委員會(Water Power Commission)來負責企業水力發電許可、電價管理、安全監管等問題,但該機構軟弱至無法為職員申請財政撥款;1927年,《無線電法案》(Radio Act)授權成立聯邦無線電委員會(Federal Radio Commission, 聯邦通訊委員會前身),但其因商務部仍然承擔部分相關職權而沒有獲得無線電監管的全部權力[22]。
其次,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迎來了監管型國家建設的第二波高潮。美國為了應對經濟蕭條、促進就業、實現經濟復蘇而再度加強國家干預,并為此設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聯邦海事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民用航空委員會(the Civil Aeronautics Board)、以及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等監管機構。盡管在二戰期間,再次的戰爭和國防動員使美國獨立監管機構的功能偏向了當時以擴大生產和組織分配為主的國家目標,這導致獨立監管機構的重要性經歷了短暫的下降。但與此同時,聯邦《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1946)的出臺使行政機關工作程序規范化,這有助于鞏固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增強監管型國家的能力[22]。
另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美國監管型國家迎來了自進步時代、新政時代之后的第三波建設高潮。一方面,此階段的監管從經濟領域向社會領域擴張,國家越來越重視由市場失靈造成的整體性、長期性社會后果,社會監管時代開啟。另一方面,監管機構不僅在傳統官僚部門中擴張,還在各種領域出現了新的獨立監管機構。例如,美國于1965年成立就業機會平等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1971年成立職業安全與健康檢查委員會(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y Review Commission)、1973年成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1975年成立國家交通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和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等等[35-36]。
最后,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浪潮,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美國開啟放松監管改革來改善過度監管和監管失敗問題,逐步推進監管型國家理性化。這場改革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解散了一些無法有效運轉的獨立監管機構,如州際商務委員會、民用航空委員會。第二,在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下設立信息和監管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OIRA),由其負責對監管計劃及其影響評估進行審核,以此保證監管效益、減少不必要的監管負擔。具體地,監管機構需就監管計劃進行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監管影響評估,并將其提交到信息和監管事務辦公室進行審核。若其無法通過審核,監管計劃則會被禁止[35-37]。
四、歐洲監管型國家建設
大約在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的歐洲,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僅扮演著守夜人角色的國家在經濟危機面前束手無策。為此,凱恩斯主義思想所倡導的國家干預迅速成為新的經濟治理戰略。在凱恩斯主義的指導下,歐洲國家通過關鍵經濟部門國有化來消除私人壟斷,以此實現市場監管。然而,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種戰略雖然竭力克服市場失靈問題,卻又帶來了更為嚴峻的政府失靈問題,致使國家不僅難以實現有效的經濟監管和控制,甚至難以實現公共責任和社會目標[1,38]。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歐洲國家開啟了新一輪的改革,其在經濟監管和社會監管領域建立了類似美國模式的獨立監管機構,以實現從凱恩斯主義國家向監管型國家轉型,從國有化監管模式向法定監管模式轉型[39]。更特別的是,監管型國家不僅在歐洲國家層面建立,還在超國家層面——歐盟建立[12]。這說明,以獨立監管機構來管理市場活動的監管型國家在歐洲備受青睞。
圍繞歐洲監管型國家建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其究竟是一個統一的現象,還是一個異質性現象?
就共性而言,首先,歐洲的監管型國家的確存在著某種共同模式,即由法律授權的獨立監管機構來進行經濟和社會監管。該模式承襲于美國,且比美國監管型國家的出現晚了將近一個世紀[40]。其次,歐洲監管型國家的出現還共享著一些背景和原因。第一,正如前文所說,歐洲國家共同面臨著凱恩斯主義危機和福利國家危機,這些危機迫使國家開展監管改革,以更有效的方式維護市場經濟運行。第二,它們處于相同的市場經濟環境當中,即監管改革與經濟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同步進行。凱恩斯主義下的政府失靈使歐洲國家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將大量國有部門私有化,并開放市場競爭。而正是這樣的改革產生了監管需求,因為國家從公共服務供給者、生產者的角色退出后不得不通過監管來確保私人部門的生產能夠服務于公共利益。第三,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催生了新的市場力量,他們成為了影響監管政策的重要行動者。第四,越來越多的歐共體監管也在對國內監管型國家建設產生影響。第五,歐洲國家都受到了美國監管型國家、新自由主義等新思想的影響,由此帶來政策學習。第六,基于功能主義視角的委托代理理論能夠解釋歐洲監管型國家的共同出現,政客委托獨立監管機構負責監管任務的原因在于它能夠幫助政客們解決信任危機。第七,監管競爭現象也有助于歐洲監管型國家的發展。歐洲國家出于引進企業到本國市場的目的會爭相向企業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監管框架,這種國家間的競爭行為能夠促進各國的監管改革[16,23,38,41]。另外,歐洲監管型國家的出現還都帶來了一些新問題。例如,監管機構和職權的改變造成了政策過程中參與者的變化,以及權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再如,獨立監管機構的出現使歐洲國家共同面臨著新的監管合法性與監管問責問題。獨立監管機構并不是民選機構,亦非多數主義機構,它在原則上不受聚合式利益的影響。因此,如何監管獨立監管機構,是歐洲國家共同面臨的課題[38,41]。
就差異而言,歐洲監管型國家之間在獨立監管機構成立的時間、數量、行業、運作程序、權限等等方面各有不同,如表1所示[16,41]。此外,歐洲監管型國家之間的差異還表現為建立了相似的監管機構但服務于不同的國家意圖方面。例如,英國監管型國家建設的意圖是向企業和選民提供關于維護開放、公平的市場環境的可信承諾,以此推進私有化改革。而法國監管型國家的意圖則是利用監管權力來在國際市場上培育出冠軍企業[27]。不同國家在上述方面的不同特征組合起來,共同塑造出歐洲地區多元的監管型國家形象。
歐洲監管型國家的多樣性可以解釋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家整體的經濟戰略差異造成了監管型國家目標的差異,并由此導致不同的監管型國家行為。第二,國家的監管傳統影響著推行監管改革的可能性和進度,國家的結構特征影響著監管改革的制度設計,二者共同決定了獨立監管機構建立的時間和權限。第三,有力的政治領導更有助于應對監管改革壓力,從而建立監管型國家。第四,監管改革中國家保留的權力(相對于獨立監管機構的權力)的差異影響著獨立監管機構的能力差異。第五,與監管改革相關的政策學習時間和內容差異能夠解釋歐洲國家授權成立獨立監管機構的時間和行業差異。第六,國家面臨的政策承諾壓力差異能夠解釋其對獨立監管機構授權的差異。第七,不同的行業特征為國家帶來了不同的監管改革壓力,而不同國家應對壓力有著不同的調節方式,從而塑造了行業監管差異和國別差異[16,27,41]。
五、拉美監管型國家建設
獨立后的拉美國家早在十九世紀就開始通過制定法律來進行監管。當時的國家監管方式主要承襲了十六世紀西班牙君主政體下的督察(superintendencia)和軍政府(junta)這兩種制度,它們是以政治精英為主的俱樂部式監管,經濟和社會精英較少參與其中。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一些拉美國家在金融行業出臺了監管法律并建立了相應的獨立監管機構,由此拉開了監管型國家建設的序幕。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拉美監管型國家迅速崛起,大量的獨立監管機構被創建,如圖2所示。與此同時,獨立監管機構開始在拉美國家的各個行業中出現,從最初的金融行業逐漸向競爭、公共事業、社會監管領域擴張[13,42]。
外部因素是解釋拉美監管型國家形成與擴張的關鍵。一方面,獨立監管機構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首次出現在拉美國家的金融行業是因為美國經濟學家E. W. Kemmerer所在的美國咨詢團幫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玻利維亞、智利等國家推行了金融機構改革,以確保貨幣穩定和償還外債[13,42]。可見,拉美監管型國家的形成直接得益于對美國監管型國家的學習。另一方面,致力于尋求外部經濟援助的拉美國家長期受到國際組織的影響,被要求遵循監管改革的“最佳實踐”,這使政策學習或移植成為了拉美監管型國家建設的重要路徑[43]。更多地,獨立監管機構在不同國家間、不同行業間的擴散模式能夠解釋拉美國家獨立監管機構數量的增加。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行業擴散模式,即某個行業的獨立監管機構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進行擴散,解釋了拉美國家獨立監管機構的出現。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獨立監管機構從國內某個行業擴散到其余行業的國家擴散模式,以及行業擴散模式共同解釋了拉美監管型國家的擴張。其中,行業擴散模式的影響比國家擴散模式的影響更為顯著[13,44]。
拉美監管型國家因為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響而在形式上趨同于歐美監管型國家,但與此同時,其也因為外部力量與拉美國家殖民遺產、國內政治的混合作用而出現了一些不同于歐美監管型國家的特征。首先,拉美監管型國家表現為美國模式和歐洲殖民遺產的混合物。來自歐洲殖民者的督察和軍政府監管傳統仍在影響著獨立后的拉美國家,它們與美國模式的碰撞使得拉美國家獨立監管機構的權力近乎掌握在委員會主席一人手中,而委員會本身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42]。其次,拉美監管型國家的獨立監管機構缺少獨立性。權力受到較大約束的歐美國家更愿意為了獲取社會支持而授權給獨立監管機構,相比之下,權力受到較小約束的拉美國家更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從而限制對獨立監管機構的授權[45]。另外,在更極端的情況下,拉美監管型國家的獨立監管機構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正如在阿根廷,盡管設立了正式的獨立監管機構,但傳統官僚部門仍然掌握著監管權力并圍繞經營規則直接與公共事業的私人投資者進行談判,而失敗的談判結果很有可能導致公共事業回歸國家供給[46]。最后,拉美監管型國家的特別之處還在于法院在監管過程中發揮著落實再分配政策的重要作用,是以被稱為憲政監管型國家(constitutional regulatory state)。就像在哥倫比亞,不同于歐美監管型國家對獨立監管機構的青睞,哥倫比亞一方面由獨立監管機構承擔水資源監管以提升經濟效率,另一方面由法院參與監管來保障水資源的合理分配符合人權目標,這使哥倫比亞的監管政治由兩股勢均力敵的力量共同塑造[47]。
拉美監管型國家不僅有著不同于歐美監管型國家的區域性特征,區域內不同國家間、國家內不同部門間亦有差異。拉美監管型國家在獨立監管機構的設立時機、數量、獨立性等等方面皆存在著明顯不同[13]。尤其是在獨立性方面,在否決權玩家越多、政治制度越民主的拉美國家,其監管機構將會更獨立[48]。就國家內的部門差異而言,國內政治因素更有可能造成部門間監管機構獨立性水平的差異。當監管改革受到了傳統官僚部門的更多抵制時,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更難得到制度保障[49]。
六、亞洲監管型國家建設
在二十世紀末期,日本、韓國、印度、菲律賓等等亞洲國家都被認為正在朝著監管型國家轉型,因為在這些國家紛紛出現了參照美國模式設立的獨立監管機構及相應的監管活動[14,50-51]。
該地區的監管型國家建設具有兩個共同特征:一方面,監管型國家建設與市場經濟的自由化改革同時進行,監管改革是亞洲國家經濟體制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52]。另一方面,監管型國家建設意味著國家干預角色的重大轉變。日本、韓國等國家向監管型國家的轉型不僅意味著發展型國家的衰弱,還意味著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從積極協調變為消極協調,即從發展型國家模式下國家對企業行為及其經濟結果的直接干預變為監管規則約束下國家對市場運行過程和程序的調整[17]。
更多地,亞洲國家的監管型國家建設呈現出了不同程度的進展和成效。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韓國的監管型國家建設似乎更為順利,因為監管型國家代表著金融危機后一種新的由國家主導的后發展路徑。換言之,監管改革本身符合國家意圖,其是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對自身經濟角色進行理性化重構的結果[53]。而在日本,監管型國家建設顯得形同實異。盡管日本被認為在形式上實現了從發展型國家向監管型國家轉型,但實際上國家仍然延續著自由裁量的監管風格,這與監管型國家的最佳實踐相去甚遠,且與本國的制度設計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這種形同實異的監管型國家建設由國家和企業之間長期延續的共生關系造成[54]。在印度,監管型國家建設同樣是名不副實的。監管型國家的制度移植過程與國內政治的互動使得本應與政治保持距離的監管決策實際上成為了新的利益分配場所,這使監管型國家更像以“走后門”的形式進入了印度[55]。同時,還有一些亞洲國家經歷了較為失敗的監管型國家建設歷程。在泰國,監管型國家建設不僅需要設立獨立監管機構,還需要培育適應于獨立監管機構的體制環境,這使國家面臨著艱巨的改革任務和巨大的改革風險,其在造成政策移植水土不服的同時,還導致了更糟糕的監管結果[56]。而在印尼,監管型國家建設的制度要求與本國的制度稟賦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世襲和恩必侍從的制度傳統、深度的國家干預、行業資源長期由國有企業壟斷等因素都在阻礙著監管體系的重塑[57]。
七、小結與討論
既有研究表明,監管型國家經歷了從美國向歐洲、拉美、亞洲等地區擴散的過程。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政治環境、不同經濟條件的國家都試圖通過建設監管型國家來治理市場,這不僅說明監管型國家具有優越的制度適應性,同時也意味著不同的監管型國家之間存在著一些共性。在此基礎上,監管型國家建設更多地呈現出差異化特征,其在地區間、國家間、行業間的三層差異共同塑造了多元的監管型國家形象。
就地區差異而言,一方面,美國、歐洲、拉美、亞洲的監管型國家建設各有不同。監管型國家起源于美國,故美國有著更長的監管型國家建設歷史。其最開始出現在國家試圖強化干預以矯正市場失靈的時代,在這之后的百余年以來,美國監管型國家建設主要圍繞著“監管的限度”這一問題展開,不同階段監管型國家的特征鮮明地體現在國家何時加強監管、何時放松監管方面,且監管型國家理性化的方向以審核監管本身的必要性為核心。與之不同,歐洲監管型國家的崛起是為了克服過多的國家干預所帶來的政府失靈問題。政府失靈困境迫使國家推行私有化改革,并從公共服務供給者、生產者的角色向對私有化生產與供給進行監管的角色轉變。而政府失靈背后的政策可信度缺失是歐洲國家授予獨立監管機構權力的關鍵原因。在拉美地區,強大的外部壓力是監管型國家建設的主要推力,但當其遭遇國內政治和殖民遺產的拉扯時,會使拉美監管型國家出現混合的、偏離“最佳實踐”的特征。而在亞洲地區,監管型國家建設較少呈現出區域的相似性,不同亞洲國家的監管型國家建設成效各異。另一方面,需要說明的是,監管型國家建設的地區差異還體現在以政治和經濟發展特征劃分的南北維度。來自南方的拉美、亞洲監管型國家大多因為外部壓力、國內盛行的分配政治以及有限的國家能力的影響而偏離于來自北方的歐美監管型國家的“最佳實踐”,并在監管機構的獨立性和有效性方面有所欠缺[58]。
就國家差異而言,即便是在具有較多區域共性的歐洲、拉美等地區,不同監管型國家在建設進程、組織安排等等方面都會有所區別,足見監管型國家的多樣性。不同國家的獨立監管機構在成立時間、涉及的行業方面各有不同,這些差異化的形式特征能夠反映出獨立監管機構在時間、空間、行業三個維度的發展規律,展示出監管型國家建設的歷史進程。另外,更重要的是,不同國家的獨立監管機構在人員、地位、功能方面的差異表明,盡管獨立監管機構的制度初衷是秉持監管獨立、避免監管捕獲,從而實施有效且公正的市場干預,但其可能會在本土化的過程中與各國的制度傳統相結合并在不同程度上偏離制度初衷。
就行業差異而言,由行業特征所塑造的差異化政治經濟利益將會對行業的獨立監管機構建設產生不同的影響。當特定行業的監管改革破壞了既有利益關系時,獨立監管機構的建設和運行將受到較大阻力。反之,當監管改革受到政治經濟力量的較小反對時,獨立監管機構將會獲得更多的授權并擁有更多的獨立性。
縱觀監管型國家的多樣性會發現,盡管既有研究對此展開了不少分析,但它們較少說明關注監管型國家差異的價值。事實上,討論不同監管型國家之間差異的意義正是在于判斷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更有效的市場治理,故而地區間、國家間、行業間的監管型國家差異與其監管結果之間的聯系是接下來需要關注的問題。監管型國家的特征是否傾向于造成特定的監管結果?不同獨立監管機構的組織安排和監管行為是否意味著不同的監管能力?它們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監管效果?什么樣的監管型國家更能矯正市場失靈?我們有必要繼續回答這些問題,以提煉有效監管的經驗來指導實踐。
另外,在開展監管型國家的比較研究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思考比較研究對中國監管型國家建設的借鑒意義和中國監管型國家的理論位置。一方面,中國亦置身于監管型國家的全球化浪潮當中,其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分別在公共事業、金融、食品藥品等等各行各業建立起專門承擔監管職能的監管機構,意圖將國家的產業監管職能與產業發展職能進行分離,從而實現更科學有效的經濟體制轉型和公共服務供給[59-62]。因此,中國監管型國家與其他監管型國家之間存在制度共性,其他國家的“最佳實踐”或者失敗教訓皆可為中國借鑒。另一方面,中國的監管型國家建設顯然走向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考察其對監管型國家比較理論的貢獻同樣重要。中國在近三十年來對各領域的監管機構和監管權力進行了反復調整,使監管體制經歷了從行業主管到獨立監管機構主管、從集權到分權、從分散監管到綜合監管的變化[63-64]。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中國于黨的二十大之際組建了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由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調整為國務院直屬機構。這些舉措意味著,中國的監管型國家建設尤為關心“如何通過體制優化來促進有效監管”這一問題。不論是通過監管改革來促進政企分離,還是通過設立獨立監管機構來統籌碎片化監管權力[65],又或是通過對縱向監管權力的反復調整來改善監管效能,亦或是通過加強金融監管機構建設來防范新風險,都體現了國家干預的強烈意愿以及國家對自身系統有效運轉的高度依賴[66]。中國這種專注于優化國家監管體制的監管型國家建設思路是否意味著更好的監管能力和監管結果?其是否代表著監管型國家移植的典范?是否揭示了某些成功的監管型國家建設的必要條件?繼續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助于進一步充實監管型國家的比較理論。
參考文獻:
[1]MAJONE, GIANDOMENICO. Regulation and Its Modes[M]//
Giandomenico Majone. Regulating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9-27.
[2]MORAN, MICHAEL. The British Regulatory State: High Modernism and Hyper-Innova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8.
[3]LEVI-FAUR, DAVID. Regulation and Regulatory Governance[M]//David Levi-Faur.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11: 3-21.
[4]BARTLE, IAN, PETER VASS. Self-Regulation Within the Regulatory State: Towards A New Regulatory Paradigm?[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7, 85(4): 885-905.
[5]CHRISTENSEN, J?覫RGEN GR?覫NNEGARD. Competing Theories of Regulatory Governance: Reconsidering Public 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M]//David Levi-Faur.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11: 96-110.
[6]GERBER, BRIAN J, PAUL TESKE. Regulatory Policymaking in the American States: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Evidence[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0, 53(4): 849-886.
[7]DAL BO, ERNESTO. Regulatory Capture: A Review[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6, 22(2): 203-225.
[8]LOUGHLIN, MARTIN, COLIN SCOTT. The Regulatory State[M]//Patrick Dunleavy et al. Developments in British Politics 5.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205-219.
[9]OGUS, ANTHONY. Comparing Regulatory Systems: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Legal Form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M]//Paul Cook et al. Leading Issues in Competition,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04: 146-164.
[10]禹貞恩.導論:查莫斯·約翰遜暨民族主義和發展政治學[M]//禹貞恩.發展型國家.曹海軍,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1-37.
[11]ANDERSON, JAMES E.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Regulatory State[M].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2: ix, 1,2-7, 92-118, 145-150.
[12]MAJONE, GIANDOMENICO.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Europe[J].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994, 17(3): 77-101.
[13]LEVI-FAUR, DAVID, JACINT JORDANA. Toward a Latin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 The Diffusion of Autonomous Regulatory Agencies Across Countries and Sec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 29(4-6): 335-366.
[14]JAYASURIYA, KANISHKA. Beyond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From the Developmental to the Regulatory State[J].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0(3): 381-387.
[15]約翰遜,查默斯.通產省與日本奇跡——產業政策的成長(1925-1975)[M].金毅,等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20-36.
[16]THATCHER, MARK. Analysing Regulatory Reform in Europe[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2, 9(6): 859-872.
[17]JAYASURIYA, KANISHKA.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Architecture of the State: the Regulatory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Negative Co-ordination[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1, 8(1): 101-123.
[18]WEISS, LINDA. Governed Interdependence: Rethinking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East Asia[J]. The Pacific Review, 1995, 8(4): 589-616.
[19]EVANS, PETER.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康燦雄.裙帶資本主義——韓國和菲律賓的腐敗與發展[M].李巍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1]HUNTINGTON, SAMUEL P. The Marasmus of the ICC: The Commission, the Railroad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J]. The Yale Law Journal, 1952, 61(4): 467-509.
[22]BERNSTEIN, MARVER H. Regulating Business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48-49, 53-69, 86-95.
[23]MORAN, MICHAEL. Review Article: Understanding the Regulatory State[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2, 32: 391-413.
[24]JORDANA, JACINT, CARLES RAMIO. Delegation, Presidential Regimes, and Latin American Regulatory Agencies[J].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2010, 2(1): 3-30.
[25]GILARDI, FABRIZIO. Policy Credibility and Delegation to Independent Regulatory Agencies: A Comparative Empir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2, 9(6): 873-893.
[26]JORDANA, JACINT ET AL.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Regulatory Agencies: Channels of Transfer and Stages of Diffusion[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11, 44(10): 1343-1369.
[27]THATCHER, MARK. Regulatory Agencies, the State and Markets: A Franco-British Comparison[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7, 14(7): 1028-1047.
[28]JORDANA, JACINT ET AL. Agency Prolife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Introducing a Data Set on th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Regulatory Agencies[J]. Regulation amp; Governance, 2018, 12(4): 1-17.
[29]LAW, MARC T., SUKKOO KIM.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 A View from the Progressive Era[M]//David Levi-Faur.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11: 113-128.
[30]Interstate Commerce Act(1887)[EB/OL].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interstate-commerce-act.
[31]THE 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EB/OL].https://fraser.stlouisfed.org/files/docs/publications/books/fract_iden_1914.pdf.
[32]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of 1914[EB/OL].https://business.laws.com/business-law/federal-trade-commission-act-of-1914.
[33]Shipping Act of 1916[EB/OL].https://www.fmc.gov/shipping-act-of-1916-centennial-legislation-established-forer unner-of-fmc/.
[34]DOBSON, JOHN M. Two Centuries of Tariffs: The Background and Emergence of the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M]. U.S. Govt. Print. Off, 1976: 87.
[35]WILSON, GRAHAM K. Social Regulation and Explanations of Regulatory Failure[J]. Political Studies 1984, 32: 203-225.
[36]王湘軍,邱倩.大部制視野下美國獨立監管機構的設置及其鏡鑒[J].中國行政管理,2016,6:145-149.
[37]EISNER, MARC ALLEN. Beyo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Regulatory Reforms[M]//David Levi-Faur.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11:129-141.
[38]MAJONE, GIANDOMENICO. From the Positive to the Regulatory Stat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anges in the Mode of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7, 17: 139-167.
[39]MAJONE, GIANDOMENICO. The Rise of Statutory Regulation in Europe[M]//Giandomenico Majone. Regulating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47-60.
[40]LODGE, MARTIN. Regulation, the Regulatory State and European Politics[J].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8, 31(1-2): 280-301.
[41]THATCHER, MARK. Delegation to Independent Regulatory Agencies: Pressures, Functions and Contextual Mediation[J].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2, 25(1): 125-147.
[42]JORDANA, JACINT.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Latin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M]//David Levi-Faur. Handbook on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2011: 129-141.
[43]LODGE, MARTIN, LINDSAY STIRTON. Regulatory Reform in Small Developing States: Globalisation, Regulatory Autonomy and Jamaican Telecommunications[J].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02, 7(3): 415-433.
[44]JORDANA, JACINT, DAVID LEVI-FAUR. The Diffusion of Regulatory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Sectoral and National Channels in the Making of a New Order[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5, 598(1): 102-124.
[45]LEVI-FAUR, DAVID. The Politics of Liberalisation: Privatisation and Regulation-for-Competition in Europe’s and Latin America’s Telecoms and Electricity Industr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3, 42: 705-740.
[46]POST, ALISON E., M. VICTORIA MURILLO. The Regulatory State Under Stress: Economic Shocks and Regulatory Bargaining in the Argentine Electricity and Water Sectors[M]//Navroz K. Dubash, Bronwen Morgan.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n Emerging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5-135.
[47]URUENA, RENE. Global Water 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gulatory State in Colombia[M]//Navroz K. Dubash, Bronwen Morgan.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7-52.
[48]MEDIANO, ANDRES PAVON. Agencies’ Formal Independence and Credible Commitment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ulatory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8 Countries and 13 Sectors[J]. Regulation amp; Governance, 2020, 14: 1-19.
[49]PRADO, MARIANA MOTA. Implementing Independent Regulatory Agencies in Brazil: The Contrasting Experiences in the Electricit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s[J]. Regulation amp; Governance, 2012, 6: 300-326.
[50]DUBASH, NAVROZ K., BRONWEN MORGAN.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J]. Regulation amp; Governance, 2012, 6:261-281.
[51]MOGAKI, MASAHIRO.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Japa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gulatory State[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52]OECD. Regulatory Reform in Japan[R]. OECD Reviews of Regulatory Reform, 1999.
[53]PIRIE, IAIN.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o-Liberal Regulatory Regime in Korea[J]. Competition amp; Change, 2006, 10(1): 49-71.
[54]WALTER, ANDREW. From Developmental to Regulatory State? Japan’s New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J]. The Pacific Review, 2006, 19(4): 405-428.
[55]DUBASH, NAVROZ K. Regulating Through the Back Door: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Institutional Transfer[M]//Navroz K. Dubash, Bronwen Morgan.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98-114.
[56]JARVIS, DARRYL S. L..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nd Regulatory Risk: A Case Study of the Thai Energy Sector[J]. Regulation amp; Governance, 2010, 4: 175-202.
[57]JARVIS, DARRYL S. L.. The Regulatory Stat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It Exist and Do We Want It? The Case of the Indonesian Power Sector[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012, 42(3): 464-492.
[58]DUBASH, NAVROZ K., BRONWEN MORGAN.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M]//Navroz K. Dubash, Bronwen Morgan.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3.
[59]OECD. China: Defin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R]. OECD Reviews of Regulatory Reform, 2009.
[60]YANG, DALI L..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97-101.
[61]YANG, DALI L.. China’s Illiberal Regulatory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Chin. Polit. Sci. Rev, 2017, 2: 114-133.
[62]胡穎廉.“中國式”市場監管:邏輯起點、理論觀點和研究重點[J].中國行政管理,2019,5:22-28.
[63]劉鵬.從獨立集權走向綜合分權:中國政府監管體系建設轉向的過程與成因[J].中國行政管理,2020,10:28-34.
[64]劉亞平,蘇嬌妮.中國市場監管改革70年的變遷經驗與演進邏輯[J].中國行政管理,2019,5:15-21.
[65]胡穎廉.層層失守:豬肉質量監管的困局[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2:127-137.
[66]黃冬婭,楊大力.考核式監管的運行與困境:基于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考核的分析[J].政治學研究,2016,4:1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