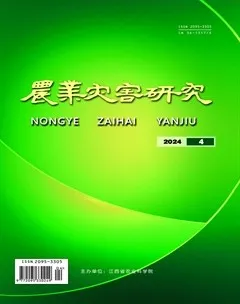2022年6月4—5日內蒙古一次強降水天氣過程分析



收稿日期:2023-12-10
作者簡介:李巖艷(1985—),女,黑龍江遜克人,工程師,主要從事預報工作。
摘 要:利用常規氣象資料、NCEP分析資料等數據對2022年6月4—5日內蒙古地區一次強降水天氣過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此次天氣發生之前,500 hPa形勢場西風槽不斷增強,亞歐大陸中高緯環流形勢表現為“2脊1槽”型,低槽增深且分裂產生了1個很強的冷渦,副高顯著朝北延伸,其分裂的冷渦南下對內蒙古中部以及東部一帶造成影響。850 hPa切變呈“人”字形,暖濕切變線在此次極端降雨天氣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促進了暖濕氣流輻合上升。強降雨天氣出現時,暖鋒鋒生促使熱力環流形成,同時有上升氣流存在于鋒區暖空氣一側,且和高低空急流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次級環流上升支保持重疊,這些共同為此次強降水天氣的發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流形勢。隨著偏南低空急流的建立,源于渤海灣一帶的水汽持續向內蒙古東部輸送,為此次強降雨天氣的發生給予了有利的水汽條件。內蒙古中東部水汽條件較好,近地層比濕值處于
12.0~14.0 g/kg之間,低空水汽通量散度都屬于負值,輻合中心偏東氣流為內蒙古中東部帶來諸多水汽。內蒙古中東部區域從6月4日午后到6月5日白天均具備良好的水汽條件。此次強降水落區處在低空急流左側以及高空急流左前方。內蒙古中東部呈現高溫高濕特征,K指數達到35 ℃以上,0~6 km垂直風切變達到12 m/s,這些均推動了此次強降水天氣的發生。
關鍵詞:內蒙古地區;強降水天氣;環流形勢;物理量
中圖分類號:P458.121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2095–3305(2024)04–0-03
全球異常變化形勢下,我國局部地區極端降水天氣出現率不斷攀升,給許多地區的經濟造成了極大損失[1]。為此,近年來我國許多學者均非常注重極端降水天氣的研究。張艷艷等[2]分析了2015年7月初發生在河西走廊中部的一次暴雨天氣過程,認為此次暴雨天氣過程是受巴湖西北急流、華中東南氣流、地面冷鋒等共同作用下產生的。陳添宇等[3]通過分析西北地區東部一次降水天氣的成因,得出此次極端降水天氣為中等強度的α和β中尺度對流云團引起的強對流降水。楊彩云等[4]分析了內蒙古局部地區的一次暴雨天氣過程,指出高空急流入口區右側與西南風低空急流左前側對應著暴雨落區。王榮梅等[5]分析了新疆哈密的一次暴雨天氣過程,認為這次暴雨天氣由伊朗副熱帶高壓向北延伸、里海長脊和烏拉爾山高脊的反氣旋型連接引起;低層風場的輻合和中上層強烈的西南氣流繼續向暴雨區輸送水汽;深層低值系統表現出從低到中的強烈輻合向上運動,為強降水天氣的出現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條件。
內蒙古地區地處中國北方地區,境內降水大部分集中在夏季,一旦出現強降水天氣,極易引發洪澇災害。因此,加強內蒙古地區降水天氣的研究十分必要。通過分析2022年6月4—5日內蒙古地區一次降水天氣過程,相關部門可以深入掌握內蒙古地區極端降水天氣發生發展的規律,有利于提升降水天氣預報預警的準確率及防汛減災水平。
1 天氣實況
2022年6月4—5日,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通遼市、興安盟、赤峰市等中東部一帶出現了強降水天氣,局地雨勢強勁,風力較大。錫林郭勒盟東部、通遼市中北部、興安盟南部、赤峰市北部24 h雨量達到25 mm,
局部區域超過50 mm。降水資料統計顯示,此次強降水過程中,內蒙古地區達到暴雨量級的測站累計達122個。降雨量最多達118.2 mm,出現在興安盟白音哈拉測站,最大小時雨強為24.1 mm/h(6月4日10:00~11:00,
出現在內蒙古地區赤峰市翁牛特旗校準站。
2 環流形勢
500 hPa形勢場上,2022年6月3日08:00,西風槽
生成且不斷加深增強(圖1a)。2022年6月3日20:00,亞歐大陸中高緯環流形勢表現為“2脊1槽”型,2個高壓脊分別處于烏山以及鄂海,前者較強,后者屬于穩定的阻塞高壓[6],副高主體分布在海上,副熱帶高壓脊所處區域稍南,貝湖區域的低槽逐漸朝著南部區域延伸,溫度槽要比高度槽落后。源于北方的冷空氣在脊前西北氣流的作用下持續朝南發展,到了6月4日08:00,低槽增深且演變為1個很強的冷渦,副高顯著朝北蔓延,其演變成的冷渦南下對內蒙古中部以及東部一帶造成影響(圖1b)。內蒙古中部以及東部處在冷渦東南象限,在其上游分布著短波槽,適宜于降水天氣的發生發展。由于冷中心落后于冷渦拓展的高度槽,同時有很強的冷平流分布在槽后,適宜冷渦強度的增強,副高處在北緯30°一帶,且表現為帶狀。在此之后,冷渦主要走向屬于西北東南向,副高脊線逐漸朝西邊區域發展。6月4日14:00~20:00(圖1c),
500 hPa冷渦系統發展加強,逐漸東移發展,持續有冷空氣補充,并與短波槽積聚產生新的冷渦。700 hPa冷渦中心屬于后傾配置,所處區域較500 hPa 冷渦中心偏東,冷中心區域依然比高度場低值中心落后。伴隨著溫度槽逐漸前移,平流作用越來越強,冷渦也在不斷發展[7]。6月5日08:00(圖1d),冷渦東移且不斷影響內蒙古東部區域,到了6月5日之后冷渦中心逐漸移離降水落區。
850 hPa切變處于內蒙古地區,主要呈“人”字形,暖濕切變線在本次極端降雨天氣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促進了暖濕氣流輻合上升。由地面形勢場進行分析可知,內蒙古地區中部、東部均存在暖舌,溫度梯度在強暖平流的影響下越來越大,并且逐漸產生暖鋒鋒生。強降雨出現的時候,暖鋒鋒生促使熱力環流形成,有上升氣流存在于鋒區暖氣流一側,且和高低空急流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次級環流上升支保持重疊[8]。鋒面和高、低空急流的共同影響導致次級環流越來越強,在暖鋒一帶產生較深的上升運動區。由地面形勢場進行分析發現,地面倒槽內蒙古中部以及東部造成影響,低層暖平流以及渦前的正渦度平流共同推動地面氣旋持續增深,產生顯著的輻合上升運動,使得內蒙古地區降水強度越來越強。
隨著系統逐漸朝東部區域發展,偏南氣流增強成偏南低空急流。水汽通道的建立,源于渤海灣一帶的水汽持續向內蒙古東部輸送,為此次強降雨天氣的發生給予了有利的水汽條件。850 hPa處屬于濕區,具備豐富的水汽資源,500 hPa處屬于干區。由此可知,干冷空氣以及暖濕氣流共同在中東部積聚,大氣層結呈“上干下濕”的結構,從而推動了本次強降水天氣的形成。
3 物理量場診斷分析
3.1 水汽條件
通過對此次降水落區比濕以及散度場進行分析可知,2022年6月4日08:00內蒙古中東部水汽資源好,近地面比濕值處于12.0~14.0 g/kg之間,500 hPa高度層以上高度層濕度條件不好,從而產生的大氣不穩定結構呈“上干下濕”的特點,低空水汽通量散度都屬于負數,其表現為輻合,輻合中心偏東氣流為內蒙古中東部帶來諸多水汽,為本次強降水天氣的形成給予了豐富的水汽資源[9]。
在此次天氣過程中,冷渦朝東邊移動期間與較好的水汽輸送條件相配合。由6月4日08:00的10 m/s上升到6月4日20:00的20 m/s,使得水汽輸送以及輻合抬升增強,相對濕度超過90%,整層水汽含量為35 mm,
這些均為強降水天氣的發生帶來了有利條件[10]。
通過相對濕度沿45°N剖面場進行分析可知,6月4日08:00(圖2a),內蒙古中東部在無論是低層還是高層均具備良好的相對濕度條件,然而中間層還存在干區,而6月4日20:00(圖2b),整層濕度條件具備較好的條件。總體來說,內蒙古中東部區域從6月4日午后到6月5日白天均具備良好的水汽條件。
3.2 動力條件
通過對此次天氣發生期間200 hPa及850 hPa風場進行分析可知,在本次降雨出現期間,高低空急流存在調整適應過程。2022年6月4日14時,高空急流軸處在北緯42°一帶,在內蒙古中、東部區域分布著一風速值為54.0 m/s的急流核,且朝東發展期間逐漸增強;6月4日20:00(圖3),急流軸發展至北緯40°一帶,急流核不斷東移到東南一帶,風速達到55.0 m/s以上,同時低空南風急流非常強,數值達20.0 m/s。低空急流左邊區域與高空急流左前方疊加,產生高、低空急流耦合[11]。此次強降水落區處在低空急流左側以及高空急流左前方。
3.3 不穩定能量條件
通過此次天氣期間K指數、0~6 km垂直風切變、假相當位溫(θse)場進行分析可知(圖4),2022年6月4日14:00,高能舌從低緯度朝北延伸至內蒙古中東部,內蒙古中東部呈現高溫高濕特征,K指數達到35 ℃
以上,0~6 km垂直風切變達到12 m/s,共同給予了本次強降雨不穩定的能量條件。
4 結論
(1)此次天氣發生之前,500 hPa形勢場西風槽不斷增強,亞歐大陸中高緯環流形勢表現為“2脊1槽”型,低槽增深且分裂產生了1個很強的冷渦,副高顯著朝北延伸,其分裂的冷渦南下對內蒙古中部以及東部一帶造成影響。850 hPa切變呈“人”字形,暖濕切變線在本次極端降雨天氣中發揮著顯著的作用,促進了暖濕氣流輻合上升。強降雨天氣出現時,暖鋒鋒生促使熱力環流形成,同時有上升氣流存在于鋒區暖空氣一側,且和高低空急流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次級環流上升支保持重疊,共同為本次強降水天氣的發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流形勢。
(2)隨著偏南低空急流的建立,源于渤海灣一帶的水汽持續向內蒙古東部輸送,為此次強降雨天氣的發生給予了有利的水汽條件。
(3)內蒙古中東部水汽條件較好,近地層比濕值處于12.0~14.0 g/kg之間,低空水汽通量散度都屬于負值,輻合中心偏東氣流為內蒙古中東部帶來諸多水汽。內蒙古中東部區域從6月4日午后到6月5日白天均具備良好的水汽條件。
(4)此次強降水落區處在低空急流左側以及高空急流左前方。內蒙古中東部呈現高溫高濕特征,K指數達到35 ℃以上,0~6 km垂直風切變達到12m/s,這些均推動了本次強降水天氣的發生。
參考文獻
[1] 宮德吉,孟里亞.內蒙古中西部地區成災暴雨的形成機制[J].內蒙古氣象,1997(6):1-5.
[2] 張艷艷.河西走廊中部一次罕見區域性強降水天氣過程分析[J].農業開發與裝備,2021(7):87-88.
[3] 陳添宇,陳乾,付雙喜,等.西北地區東部一次持續性暴雨的成因分析[J].氣象科學,2009,29(1):115-120.
[4] 楊彩云,韓仙桃.杜文娟.內蒙古一次區域性暴雨的濕位渦診斷分析[J].內蒙古氣象,2014(1):3-6.
[5] 王榮梅,道然,屠月青.哈密地區7·17暴雨天氣過程分析[J].沙漠與綠洲氣象,2010,4(1):36-40.
[6] 常煜,韓經緯.一次阻塞形勢下的內蒙古暴雨過程特征分析[J].高原氣象,2015,23(3):741-752.
[7] 任麗,欒晨,王曉雪,等.持續性冷渦暖鋒暴雨成因及特征分析[J].氣象與環境學報,2022,38(3):37-44.
[8] 常煜,張平安,王洪麗,等.高低空急流耦合對內蒙古東部持續性暴雨的觸發作用[J].中國農學通報,2014,30(23): 211-217.
[9] 斯琴,荀學義,王佳津.一次東北冷渦暴雨過程成因分析[J].氣象科技,2016,44(6):1016-1023.
[10] 王黎黎,魏婷婷.近50年來東北冷渦暴雨過程動力條件診斷和水汽條件分析[J].氣象災害防御,2014,21(4):10-13.
[11] 趙旻.一次東北冷渦暴雨的成因分析[J].農業災害研究, 2023,13(1):1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