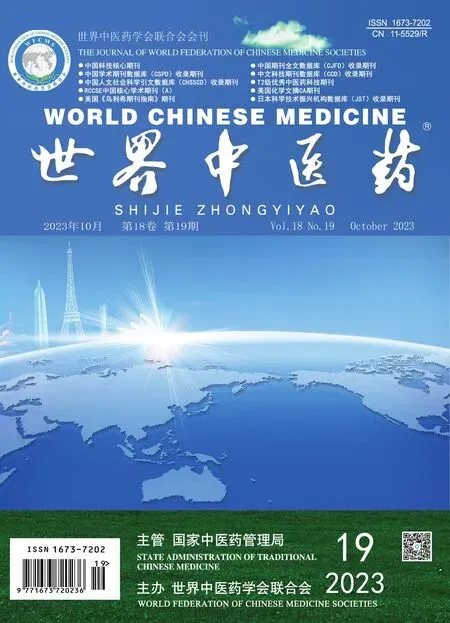中醫正邪理論與抑癌基因和癌基因在腫瘤中的相關性
顧知恩 王 磊 陳 悅 翟嘉威 洪 專 楊宇飛
(1 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腫瘤診療中心,北京,100091; 2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1000291; 3 江蘇省腫瘤醫院,南京,210009)
正邪理論是中醫認識疾病的重要工具和基本模型。然而僅在《黃帝內經》中,“正”與“邪”就代表多種含義。近年來有關《黃帝內經》中正邪含義的研究表明,正邪理論表示基本病機的內涵其實在宋朝才成熟并明確。此后各家各派對正邪理論亦存在不同解釋和闡發[1-2]。科學技術發展至今,癌癥相關基因的行為可以說是借助現代科技觀察到的一種“癥狀”,因此從分子微觀層面亦可對正邪理論做出新的闡述和補充。此外,當代有學者認為中醫基礎理論的核心是關系哲學,強調疾病是人體內一切“關系”失衡所致[3]。正邪理論中同樣蘊含有對立統一的思想。運用正邪理論中的哲學思想理解基因的種種行為也將更有利于將現代醫學的成果與中醫基礎理論相聯系,擴大中醫認識疾病、治療疾病的視野,從而更好地繼承與發展中醫學理論。
1 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氣之在人,和則為正
正氣,相對于邪氣而言,指人體內具有抗病、祛邪、調節、修復及對外環境適應等作用的一類細微物質[4]。由此可見,只要是維系人體正常功能的物質,均可被稱為正氣。人體的生理功能可歸屬于“正氣”范疇。
原癌基因存在于正常細胞基因組中,不僅無害,反而對于細胞增殖等正常功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其編碼的蛋白也是細胞生存的必要蛋白[5]。以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RAS)基因為例,其編碼細胞內具有三磷酸鳥苷酶(Guanosine Triphosphatase,GTPase)活性的蛋白,當與三磷酸鳥苷(Guanosine Triphosphate,GTP)偶聯時RAS蛋白被激活以增加細胞增殖與生存[6]。這類功能對于細胞更新及創傷愈合的意義十分重大,若失去RAS基因的功能使細胞無法更新,則會出現一系列的健康問題。這一點在化療的不良反應方面體現得尤其明顯:皮膚上皮無法更新,輕則皮疹,重則手足脫皮;腸上皮細胞無法更新則會引起惡心嘔吐,血細胞無法更新則易出現出血、貧血及感染。此外,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家族編碼的某些受體酪氨酸激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基因家族編碼的VEGF等都是廣泛存在于各種組織中維持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7-10]。因此,原癌基因及其生理狀態下產生的功能應歸屬于“正氣”范疇。
同理,抑癌基因指存在于正常細胞內抑制細胞生長并具有抑癌作用的基因[5]。以P53基因為例,其所編碼的蛋白具有對環境壓力作出應激反應的功能,當細胞受到大量紫外線輻射傷害時該蛋白會被誘導增加。P53途徑激活的最終結果是使受損細胞周期停止在DNA合成預備期(G1期),進而修復脫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DNA)損傷,損傷嚴重時促進細胞老化,甚至啟動細胞凋亡。P53途徑的上述行為是因機體感受到環境中如“紫外線輻射忽然增多”等不利損傷而產生的,其通過細胞周期負調控,無論是修復損傷DNA還是促使損傷細胞凋亡,都可歸于“正氣祛邪”的過程。由此可見,野生型P53基因的作用同樣與中醫正氣的含義基本相合。
從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兩方面的作用綜合來看,二者均在創傷修復過程中發揮作用。創傷愈合可被視為典型的正氣“自我修復”過程,研究表明細胞外調節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1/2)信號通路及原癌基因c-Fos是創傷修復的重要組分且會被誘導而增強表達。另一方面,創傷愈合的關鍵在于血管新生,因此VEGF也與修復過程密切相關,VEGF介導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rotein Kinase B,PI3K/AKT)信號通路激活,使細胞增殖、分化及遷移能力增強并抑制細胞凋亡,從而發揮促進血管網絡重建的作用。然而原癌基因c-Fos發生激活突變會成為誘發腫瘤的因素之一,PI3K/AKT信號通路也與腫瘤血管新生關系密切[9,11-13]。之所以創傷愈合是機體自我修復的生理過程,是因為其中還有抑癌基因及相關信號通路在與之平衡。上述過程所引發的強增殖信號會與創傷應激一同作為激活抑癌基因P53的刺激因素。所以在原癌基因及相關信號通路被激活產生細胞效應的同時,抑癌基因也產生了阻止細胞增殖、生長遷移的效應,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互相牽制的平衡過程使機體得以適應外界變化、修復疾病損傷的同時又不使細胞過度增殖產生腫瘤,這也是正氣發揮功能的體現。故而“體內各種關系達到平衡”的生理狀態應歸屬于“正氣“范疇。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上述生理過程中的平衡也是正邪理論中對立統一關系的體現。
2 抑癌基因的二次打擊學說——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提及“正”與“邪”,則必然要聯系到“虛”與“實”。虛與實,體現了人體正氣與病邪相互對抗消長運動形式的變化[14]。所謂“正虛”即是人體失去了應該有的正常功能。
在惡性腫瘤中,抑癌基因功能的喪失是“正虛”的典型代表。1971年由Alfred G.Knudson教授首次提出的二次打擊學說與中醫“先天不足,后天失養”的理論不謀而合。“二次打擊學說”定義為:存在某種基因(抑癌基因)的2個拷貝(等位基因)都突變/缺失后會驅動腫瘤的發生。KNUDSON[15]教授認為,第一次抑癌基因突變發生在生殖細胞,因此個體內所有細胞均帶有一個失活的等位基因,其各系統出現腫瘤的概率比正常人大大增加,這也可用于解釋腫瘤遺傳易感性的問題。現代中醫認為腫瘤的發生發展受基因調控,與先天密切相關。《靈樞·天年》中“人之始生……以母為基,以父為楯”,所表達之意與人體基因組源于父母雙方的染色體這一理論相符。“腎-十二經-奇經”理論與循經部位上的腫瘤基因異常也有聯系。故而“腫瘤遺傳易感性”可以歸屬于先天不足所致“正虛”的范疇[16]。
抑癌基因第二次突變發生在出生后的體細胞中。突變后的基因會與各類環境因素如飲食等相互糾合引發腫瘤。P53基因在體細胞中的突變就十分常見,近年研究證明,少數P53基因突變可產生抑制惡性腫瘤形成的作用,而腸道中持續存在的沒食子酸卻會將這種抑癌作用轉換為促癌作用。沒食子酸由腸道中某些菌株產生。腸道菌群是在出生后構建并不斷變化的。出生后的各種不良生活方式均可造成菌群失衡[17-18]。可見此類基因突變致癌過程與中醫對“后天失養”的認識更為相合。如今中醫將“脾為后天之本”與腸道菌群的功能相聯系,認為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從《黃帝內經》起始,“顧護脾胃”的思想便為歷代醫家所重視。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更是認為“脾胃內傷,百病由生”[19]。
先天不足加后天失養導致正氣虧虛,正氣虧虛無力修復機體損傷,邪氣乃生,疾病由此而成。隨著更多腫瘤相關基因的發現,二次打擊假說也在不斷更新完善。抑癌基因中必需基因(Essential Genes)的發現建立了抑癌基因的連續模型,旨在說明抑癌基因促進腫瘤發生的作用并非一個離散的“是與否”過程,而是與抑癌基因突變劑量相關的連續過程[20-21]。在中醫理論中,“正虛”這一病機過程恰恰也多是日久而成。
3 癌基因——氣之在人,不和為邪
邪氣是對應于正氣而存在的概念。沒有正氣,則無法區分邪氣。正如同沒有正常就無法區分異常。《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曰:“當其位則正,非其位則邪。”張介賓在《類經·情志九氣》中也提到:“氣之在人,和則為正氣,不和則為邪氣。”可見以正邪立論需把正邪視為對立統一的整體,邪氣依靠正氣而體現。如果說人體的生理功能歸屬于“正氣”范疇,生理功能的減弱歸納為“正虛”范疇,那么機體內未見“正虛”而出現了原本生理功能的異常增多或出現了不應有的特殊功能則可歸屬于“邪實”范疇。這些異常的功能其實是正氣系統內各種關系失去平衡的產物,即“氣之在人,不和則為邪氣”[22]。
這一點首先體現在原癌基因激活突變為癌基因上。近年來多項研究表明,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KRAS)基因的突變至少會引起以下功能的異常增多。其一,KRAS突變使其表達出更多KRAS蛋白。與此同時,胞質內異戊烯化酶的表達增加了具有成熟功能的膜KRAS蛋白數量,不斷激活如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B,MAPK)、PI3K/AKT等下游信號通路促進細胞增殖。其二,KRAS 12D基因突變的細胞中替代性致癌基因(如基因Myc)的拷貝數增加,與KRAS雜合突變會共同驅動腫瘤的發生。其三,KRAS基因突變與細胞代謝改變密切相關。有研究表明KRAS突變提高了小鼠成纖維細胞糖酵解通量并增加了細胞對于生物合成過程中谷氨酰胺的利用。在體外培養的人乳腺組織中,幾種與糖酵解有關的基因如己糖激酶(Hexokinase 1,HK1)基因、磷酸果糖激酶血小板(Phosphofructokinase Platelet,PFKP)等在具有KRAS基因突變的乳腺腫瘤組織中表達水平明顯比正常乳腺組織更高。此外,KRAS基因突變可以驅動免疫逃逸。近年來研究顯示,KRAS基因突變的細胞會表達更多的細胞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從而使其躲避免疫細胞的殺傷[23-29]。
綜上所述,原本體內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的功能處于相互平衡的狀態,KRAS基因突變后使得一系列對于細胞增殖有利的功能不斷激活,抑制腫瘤生長的因素就顯得處于“弱勢”,此時多余出來的功能便是一種異常的功能,邪氣便隨之得以體現。正所謂“氣之在人,不和則為邪”。邪氣本不會無源而起,內生之邪必因“一身之氣”本身出現異常而起。故薛雪在《醫經原旨》中提到:“萬物之生,皆由陽氣。但陽和之火則生物,亢烈之火反害物,故火太過則氣反衰,火和平則氣乃壯。”
深入研究發現,細胞的KRAS基因激活突變不僅會使某些功能異常增多,甚至會“打壓”細胞中的正常功能。例如,KRAS基因突變細胞中糖酵解增加的同時也可以發現氧化三羧酸循環(Tricarboxylic Acid Cycle,TCA cycle)的降低;KRAS基因突變促進波形蛋白的表達卻降低E-鈣黏合素的表達,從而增加細胞侵襲轉移的能力[25-29]。這便體現出邪氣內生后反過來又會損耗正氣,引發正氣愈虛邪氣漸增的病理過程。
4 基因異常的腫瘤轉移——邪勝正衰,癌毒傳舍
經典模型認為,細胞積累突變,首先驅動原發腫塊的形成[30]。這是邪氣在體內積累由量變引發質變的過程。有研究表明,替代性致癌基因拷貝數增加與雜合KRAS突變共同作用激活下游信號通路從而驅動腫瘤發生,但上述改變引發腫瘤轉移可能性較低[29-30]。無法排除某些情況下,腫瘤的發生可能單純是邪氣過盛的結果。然而邪氣一旦在體內形成便會引發惡性循環使得邪氣不斷加重加深,進而化生成毒。中醫癌毒的概念雖然沒有嚴格定論,但絕大多數醫家認同癌毒具有病位深伏的特點,這與基因的特點相一致——基因是人體一切生命活動的總指揮,其深居于細胞核內,是機體最深層次、最本質的生命活動。癌毒在體內不僅會逐漸積累,還會不斷損傷正氣,形成重復惡性循環[31]。
近年來研究表明,僅有KRAS基因突變會導致腫瘤具有侵襲性和部分去分化的特點,但與轉移性腫瘤團的形成關系并不明顯[28]。正常情況下,上皮細胞之間的擠壓會觸發一系列信號通路促使細胞凋亡從而維持上皮的功能及細胞密度,這可以部分解釋接觸抑制這種生理現象。而KRAS V12突變或者其他具有侵入性的腫瘤基因突變細胞會“劫持”這一通路,從而促進腫瘤細胞突破基底膜進而出現轉移。同時,KRAS突變在誘導上皮細胞-間充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信號上調波形蛋白的同時會下調E-鈣黏合素的表達,使細胞容易從原組織中脫落,并逐漸遷移到其他組織中。而只有在P53基因缺陷的基礎上再出現了侵襲性KRAS V12突變,細胞才會在具有侵襲性的同時形成腫塊[28-30]。以上腫瘤在分子層面上的轉移行為可以解釋為:邪氣在體內引發一系列惡性循環致使邪氣不斷積累,最終形成癌毒;邪氣不斷耗損正氣,致使正虛無力固著癌毒兩方面的過程,二者對于腫瘤轉移都必不可少。
5 基因突變的腫瘤治療——正邪兼顧,以和為貴
腫瘤的發生是正氣系統內部各因素失衡導致邪氣內生的結果,邪氣盤踞于體內損傷正氣,正氣不斷損傷而邪氣因惡性循環而不斷積累,以致邪氣積累、正氣漸虧。正氣虧損與邪氣積累均達到一定程度后,正虛無力固著邪氣,導致毒邪流注而發生轉移。從基因、分子層面解釋,可以得到相似結論,雖然以“正虛”為主的二次打擊足以引發部分癌癥,但更多腫瘤仍需額外的突變才會被誘發。非遺傳性腫瘤可能需要4種及以上引發關鍵信號通路異常的突變事件才會發生[20-21]。這也從分子角度解釋了為何多數醫家認為腫瘤的發生發展是“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的復雜過程[32-35]。一系列病理狀態其實皆起因于失衡。無論是疾病還是證候其實都是在不同層次上基因網絡失衡的表現[36-37]。疾病起于失衡,故而治療時應“以平為期”。具體到正邪理論上便是“補其不足,損其有余”。如前所述,腫瘤的發生發展是一個“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的復雜過程,故而治療無論何期,均應正邪兼顧,辨清主次,一般不可純攻純補[38]。
以邪實為主時,治療關鍵在于祛邪消癌,輔以扶助正氣。南京中醫藥大學以周仲英教授“癌毒”理論為基礎擬定的參白解毒方是此類治療的典型代表。方以苦參、白花蛇舌草為君藥,取其解毒祛邪之效。輔以黨參、白術益氣健脾,使祛邪不傷正。全方以祛邪為主,邪正兼顧。現代藥理學研究也表明,參白解毒方下調了B細胞淋巴瘤-2基因(B Cell Lymphoma-2,Bcl-2)等原癌基因的表達。原癌基因功能被異常激活后抵抗細胞凋亡促進增殖則為典型的邪實狀態[39-40]。
以正虛為主時,治療則應培補正氣,兼以祛邪。轉移是正氣難與邪氣相抗衡的體現,說明正邪斗爭中的微妙平衡被打破。此時正氣虧虛無力固著邪氣于原位導致邪氣流竄,矛盾主要集中在正氣虧虛之上,故以益氣為主培補正氣之不足,活血為輔祛除瘀滯之邪。現代分子機制研究表明,益氣活血方可顯著上調惡性腫瘤細胞株的E-鈣黏合素表達,從而加強相鄰細胞間的聯系,減少細胞侵襲轉移的概率。前述研究發現KRAS突變會引起細胞中E-鈣黏合素表達減少,進而促進腫瘤轉移是邪氣傷正的體現。此次研究表明,益氣活血方可顯著上調腫瘤細胞E-鈣黏合素的表達,解救被KRAS激活突變所“打壓”的生理功能屬于恢復機體正氣的過程。同時益氣活血配伍組合(黃芪-莪術)抑制MAPK信號通路下調VEGF表達,抑制腫瘤血管生成,從而干預荷瘤小鼠轉移瘤的生長轉移。前述KRAS突變激活MAPK信號通路增加腫瘤細胞侵襲轉移的能力是邪氣進一步積累的結果。益氣活血配伍組合(黃芪-莪術)抑制MAPK信號通路,是典型祛邪的過程。此外研究表明,對于轉移的抑制作用,黃芪-莪術配伍組合明顯高于單獨使用黃芪或莪術[41]。這就表明腫瘤發生發展病機復雜,中醫治療腫瘤需邪正兼顧。
“氣之在人,和則為正,不和則為邪”。從邪正盛衰基本病機考慮,采用“和法”治療腫瘤亦不失為良策。趙景芳教授提出的“微調平衡治癌法”即是“和法”在惡性腫瘤治療的代表。調,和也。從整體觀出發,協調全身原本不和諧的狀態以達到平衡的目的,既不是單純的扶正,又不直接使用活血化瘀等祛邪藥物,只在辨證基礎上因人而異適當選用[38]。其中逍遙散、四逆散均為“和法”經典方劑,柴胡-赤芍配伍組合則是其中核心藥對,在趙景芳教授“微調二號方”中也作為核心配伍出現。現代基礎研究表明,南柴胡-赤芍藥具有調控PI3K/AKT通路的作用。PI3K/AKT通路對葡萄糖代謝、細胞增殖與凋亡等具有調節作用。KRAS基因突變增加糖酵解的同時會降低氧化TCA cycle通量導致能量代謝異常,又可以異常激活PI3K/AKT通路增加細胞的侵襲性。柴胡-赤芍中多種有效成分可調節PI3K/AKT通路上多種蛋白的表達,進而抑制肝癌細胞增殖[42]。以上表明“和法”理論指導下的選方用藥有其相應的物質基礎與證據支撐。
6 討論
近代有學者認為中醫基礎理論的核心是關系哲學[3]。正邪作為中醫概括疾病的基礎模型之一,可歸屬于關系認識論中。由正氣的概念可知,機體的生理功能屬于“正氣”范疇。故而正常細胞中的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及其在功能上的相互平衡均可歸屬于“正氣”范疇。抑癌基因的失活突變致其對應生理功能的丟失則屬于“正虛”概念。關系認識論中,疾病的產生是各部分間關系失衡的緣故。原癌基因與抑癌基因原本在功能上對立統一,原癌基因發生激活突變使其對應功能增強而抑癌基因無法與之平衡時,正邪關系出現失衡,從而導致邪氣的產生。此時原癌基因轉為癌基因,正氣化邪。邪氣居于體內,可引發機體惡性循環,一是邪氣不斷積累日久成毒;二是邪氣暗耗,正氣漸虧。例如,KRAS基因突變的細胞既會繼續激活其下游基因,又會減少細胞正常E-鈣黏合素的表達,從而增強細胞侵襲轉移的能力[30]。當邪氣深重且正氣虧虛到達一定程度時正氣難以固著邪氣致使邪氣流竄,量變產生質變而發生轉移。基于關系認識論,疾病因關系失衡而產生,故而治療大法應“以平為期”,務求恢復機體內的平衡。臨床上一般正虛邪實并見,此時辨證論治則應分以邪實為主還是以正虛為主。此外,從邪正盛衰的基本病機考慮,從整體觀出發,協調全身原本不和諧狀態的“和法”也是腫瘤治療中的良策[38]。多項現代藥理學實驗也證明了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遣方用藥治療腫瘤具有多靶點、多層次的機制。中醫取象比類的思維是將看到的現象(癥狀)進行歸納辨證,而基因的種種行為可以說是借助現代科技觀察到的一種“癥狀”。我們可以利用現代研究以補充中醫辨證的依據,從而進一步支撐中醫自己的理論。以惡性腫瘤為切入點,探討抑癌基因、原癌基因及癌基因中的正邪關系,以期為中醫辨證論治提供更多的依據。由于疾病的復雜性,只對中醫正邪理論與腫瘤相關基因做了簡單歸納,更加細化基因與證候之間的關系仍需進一步臨床實踐與思考歸納。
致謝:本文在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腫瘤診療中心楊宇飛教授指導下,與多位博碩研究生合作完成,在此對中國中醫科學院提供的科研平臺以及給予幫助的老師及同學們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