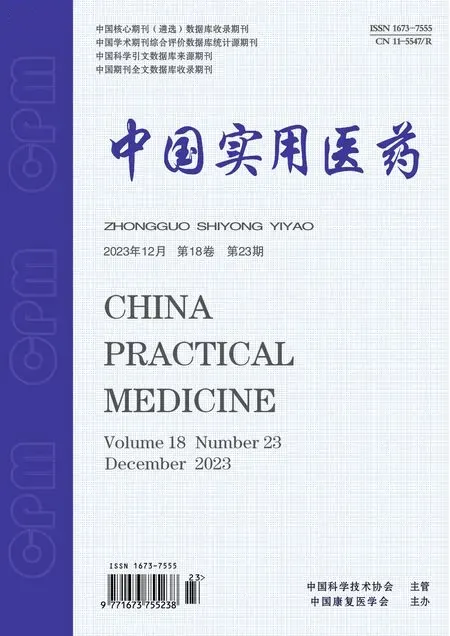脊柱外科術后并發應激性潰瘍5 例臨床病例分析
張存鑫 孫磊 王倩 呂超亮 靳留忠
應激性潰瘍(stress ulcer, SU)是一種急性消化道黏膜病變, 主要表現為胃腸道黏膜的糜爛、潰瘍、穿孔、出血等病理改變[1]。其臨床癥狀輕重不一, 部分患者可表現為無癥狀、內鏡下發現的淺表病變或隱匿性潰瘍, 也可有腹痛、燒心等表現, 伴隨嘔吐咖啡樣胃內容物、黑便或者柏油樣變, 嚴重者可伴有消化道大出血危及生命[2]。脊柱外科手術誘發的SU 病例相對較少,但文獻報道其致死率高達23.07%[3]。本研究回顧性分析2017 年1 月~2022 年12 月在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脊柱外科行全麻手術治療的患者, 發現5 例患者術后發生SU, 其中2 例(40.00%)患者死于消化道大出血導致的失血性休克, 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7 年1 月~2022 年12 月在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脊柱外科行全麻手術治療的患者, 其中5 例患者術后發生SU, 患者年齡(59.60±8.59)歲;男3 例, 女2 例;腰椎間盤突出癥2 例, 頸椎病2 例, 頸部脊髓損傷1 例;均在全麻下行手術治療;1 例患者術前存在胃穿孔術后史, 1 例患者有慢性胃炎病史, 其余患者既往均無消化道潰瘍病史;手術時間(127.00±26.38)min, 術中出血量(142.00±104.19)ml;2 例患者采取術中自體血回輸治療, 其余患者術中出血較少, 未采用自體血回輸;術后3 例患者因失血性休克采取輸血治療, 2 例患者無輸血及血液制品治療;5 例患者均出現明顯癥狀, 表現為腹痛、腹脹、惡心、嘔吐, 嘔吐物呈現咖啡色, 并伴有黑便, 生化檢查均發現血紅蛋白呈下降趨勢。
1.2 輔助檢查 本組患者在術后2~7 d 確診SU。2 例患者伴有血紅蛋白下降、胃管內抽出咖啡樣液或黑便確診。1 例患者在完善胃腸鏡后確診, 鏡下見食管、胃底靜脈曲張、破裂出血。1 例因急腹癥完善腹部CT 后確診, CT檢查提示十二指腸穿孔。1例患者因黑便確診,經治療后復黃, 拒絕進一步檢查, 未能明確出血部位。
2 結果
5 例患者中, 2 例患者給予胃腸減壓、止血藥物、質子泵抑制劑、保護胃黏膜等保守治療后病情逐漸控制, 糞便常規檢查大便隱血試驗陰性。1 例患者因急腹癥行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修補術治療, 手術后康復出院。2 例患者因持續血紅蛋白降低, 給予輸血、胃腸減壓、應用止血藥物、質子泵抑制劑、保護胃黏膜等治療, 病情加重后轉入ICU進一步搶救治療, 但病情危重,因失血性休克死亡。
3 討論
SU 多表現為急性消化道黏膜損傷和淺表出血, 也可能導致嚴重的消化道大出血等臨床癥狀[4]。其發病機制主要是應激通過破壞促進損傷的侵襲性因子和保護黏膜的防御性因子之間的平衡而引起消化道黏膜侵蝕而形成[5]。脊柱外科術后并發SU 相對罕見, 一項納入30000 例腰椎間盤切除術的研究顯示, 術后消化道穿孔的發生率僅為0.016%[6]。Lin 等[3]回顧了24026 例接受脊柱外科擇期手術治療患者的臨床資料,僅有13 例(0.05%)患者出現SU, 其中3 例死亡。本研究在回顧了15000 余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后, 發現也僅有5 例(0.03%)患者確診為SU, 其中2 例(40.00%)死亡。鑒于脊柱外科術后并發SU 起病隱匿、發展迅速、后果嚴重, 因此積極預防和治療術后SU 對保證患者圍手術期的生命安全至關重要。
3.1 脊柱外科術后SU 的發病機制 SU 的發病機制可簡單理解為復雜的致病因素導致消化道黏膜防御機制的崩潰, 引起了胃腸道管壁的損傷。研究表明, 前列腺素、粘蛋白、水、碳酸氫鹽、三葉因子家族肽、磷脂和熱休克蛋白等, 對維持消化道黏膜的結構完整和損傷后修復具有重要調節作用[7]。因此, 能夠影響上述保護因素的應激環境(包括精神、心理、藥物、創傷、感染等)均可以導致SU 的發生。研究發現, 胃腸道黏膜缺血是誘導SU 的主要原因[8]。患者在手術應激狀態下, 會通過各種調節機制導致胃腸道黏膜血供減少,如:應激狀態下的血液再分配;麻醉狀態下心輸出量減少、低血壓;交感神經系統興奮, 兒茶酚胺釋放增加導致的胃腸道血管收縮等。因此, 維持患者術中及術后血壓穩定對預防SU 有一定的作用。此外, 本研究總結發現, 在本組5 例患者中, 4 例采取了俯臥體位接受手術, 由于重力的作用和手術醫師的操作, 導致患者腹部壓力始終高于其他部位。這也進一步加重了胃腸道黏膜缺血的程度, 成為誘發SU 的重要原因。
3.2 脊柱外科術后SU 的危險因素
3.2.1 藥物相關因素
3.2.1.1 術前用藥 非甾體藥物通常用于減少疼痛、發燒和炎癥, 是脊柱退行性疾病的首選藥物。在全球范圍內, 與非甾體藥物相關的潰瘍患病率為9%~22%,每年服用非甾體藥物的患者發生嚴重出血或穿孔的比例約為1%[9,10]。非甾體藥物導致SU 的機制主要包括以下4 種:①直接損害消化道黏膜;②影響消化道黏膜的血供;③抑制血小板的凝集, 干擾人體的凝血機制;④影響人體免疫調節功能等[11]。糖皮質激素具有強大的抗炎作用, 通常用于治療各種免疫和炎癥性疾病[12]。糖皮質激素除了其本身的副作用外, 更為重要的是可以顯著增加非甾體藥物的致潰瘍作用。當兩種藥物合用時, 其致潰瘍作用會被疊加放大。此外, 由于多數老年患者常合并其他心腦血管疾病, 具有長期口服抗凝藥物病史, 也大大增加了術后SU及出血的風險。
3.2.1.2 術中用藥 研究發現, 多種麻醉用藥, 如丙泊酚、依托咪酯、芬太尼、右美托咪定等, 均可誘發惡心、嘔吐等胃腸道反應[13-16]。特別是在鎮痛泵中的應用, 可能會導致患者持續數小時乃至數十小時的惡心、嘔吐癥狀, 使消化道肌群長期處于痙攣、缺血狀態,誘發SU。此外, 術中使用的多種抗生素均會影響凝血而增加手術出血和SU 出血風險。見表1。為了減輕手術操作對脊髓和神經根的激惹, 術中往往使用激素沖擊治療, 進一步增加了手術SU 的風險。

表1 各種抗生素的消化和血液系統毒副作用
3.2.1.3 術后用藥 患者術后用藥之間的相互作用往往容易被醫生忽視。糖皮質激素類藥物和非甾體藥物合用顯著增加了致潰瘍作用[17,18]。為了預防深靜脈血栓的形成, 預防性地使用抗凝藥物已經成為共識。但是當肝素鈣與非甾體藥物、右旋糖酐、雙嘧達莫合用時, 會增加患者的出血危險, 誘發消化道大出血[19-21]。脊柱外科全麻術后患者的用藥品類多、藥量大, 且多為靜脈用藥[22-25]。因此, 術后用藥要充分考慮藥品的作用、副作用及藥品之間的相互作用, 避免不良后果的產生, 而這也往往是外科醫師的薄弱之處。在本組患者中, 均在術后同時使用了非甾體藥物、糖皮質激素類藥物、抗凝藥物和抗生素。這些藥物的組合應用,顯著增加了患者術后SU 及消化道出血的風險。
3.2.2 心理相關因素 研究表明, 大腦和腸道之間的相互作用與胃腸道疾病的發生密切相關[26]。中樞神經系統和胃腸道之間存在雙向信號調節網絡, 即腦-腸軸[27], 這一概念闡述了神經系統(包括中樞神經系統、自主神經系統和腸道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和免疫系統之間相互串擾的理論[28]。研究表明, 心理應激與腸道的通透性、運動性、敏感性和分泌、腸道微生物組成以及腸道炎癥的發生、再激活密切相關[29,30]。心理應激可以激活人體神經內分泌調節網絡, 促進下丘腦分泌過多的促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激素, 導致垂體前葉釋放過多的促腎上腺皮質激素。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又刺激腎上腺皮質分泌過多的糖皮質激素[31]。此外, 心理應激還可以通過刺激交感神經系統來控制自主神經反應, 促進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的釋放,誘導中樞和外周組織分泌過多的炎癥介質/促炎細胞因子, 促進炎癥核因子-κB 信號通路的激活, 加速胃腸道黏膜的損傷[32]。由此可見, 心理應激與SU 的發生密切相關。患者面對手術產生的心理應激主要表現為恐懼、焦慮、抑郁、煩躁等, 這些負面情緒不僅給患者帶來精神上的困擾, 而且增加了手術風險[33]。因此,術前專業的心理輔導可能會有效減少術后SU 的發生。
3.2.3 自身疾病因素 患者自身健康狀況對脊柱外科術后SU 的發生有直接作用, 特別是既往存在消化道疾病史的患者。研究表明, 15%~30%的消化道潰瘍患者不會表現出任何明顯的癥狀, 特別是老年人。因此, 詳細的詢問病史和必要的輔助檢查對預防術后SU 至關重要。此外, 患者凝血功能、肝腎功能、骨髓造血功能異常均會增加SU 出血的風險,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術后SU 的發生率顯著升高。
3.2.4 手術相關因素 脊柱外科手術, 特別是側彎矯正、腫瘤切除、上頸椎等手術, 具有創傷大、出血多、風險高等特點, 手術時間往往在數小時以上。研究表明, 當手術時間>3 h, 其各種風險均顯著增加。此外,患者的俯臥體位會影響胃腸道黏膜血液回流, 導致胃腸道黏膜缺血, 誘發SU。
3.3 脊柱外科術后SU 的診斷 脊柱外科術后SU 的診斷主要依賴于癥狀體征、實驗室和影像學檢查以及內鏡檢查等。SU 最常見的癥狀為不明原因的黑便。對無顯性癥狀的患者, 若出現胃液或糞便潛血試驗陽性,或者不明原因血紅蛋白濃度降低≥20 g/L, 應考慮有SU伴出血的可能。嚴重的SU 可伴隨嘔吐、嘔血、腹脹、腹痛、腸鳴音活躍/亢進等表現, 有胃腸道穿孔時可伴腹膜刺激征, X 線或CT 檢查可見液平面或氣腹征。X 線鋇餐檢查可見壁龕或龕影。胃腸鏡檢查可見消化道糜爛、潰瘍或者穿孔。伴有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可表現為嘔血、便血、低血容量休克等表現。雖然在胃腸鏡下發現消化道潰瘍、穿孔是SU 診斷的金標準, 但不適用于所有患者。大便常規+潛血雖不能明確潰瘍的確切部位, 但其靈敏度高, 可作為常規的篩查手段。
3.4 脊柱外科全麻術后SU 的治療 多數SU 患者經抑制胃酸分泌、保護胃黏膜等治療可有效緩解。對于伴有消化道出血的患者需在抑制酸保胃治療的基礎上,給予抗感染、抗休克, 糾正低蛋白血癥、電解質和酸堿平衡紊亂, 靜脈營養支持和抗炎等對癥治療。適量的鎮靜藥或安定劑可安撫患者的緊張情緒, 必要時給予胃腸減壓、胃內注入凝血酶、輸血輸液補充循環血量等治療。同時需要定期監測胃液pH 值, 必要時動態監測胃內pH 值, 定期監測血紅蛋白水平及糞便隱血試驗。對于持續消化道活動性出血的SU 可采取胃腸鏡下電凝、套扎止血等治療。內鏡治療難以治愈的出血性潰瘍可能需要對相應血管進行栓塞術以緩解出血。當進行內鏡或血管栓塞治療后, 癥狀仍未得到緩解或血流動力學仍未得到穩定, 則需要外科手術干預。
3.5 脊柱外科術后SU 的預防 全面預防術后SU 的發生對提升患者圍手術期安全性非常重要。本研究認為預防脊柱外科術后SU 的發生包括術前、術中及術后3 個方面。具體內容如下。
3.5.1 術前預防 術前詳細詢問病史, 明確是否存在消化道潰瘍病史、相關藥物史、胃腸道手術病史等。常規完善大便潛血試驗, 排除隱匿性潰瘍。如有相關危險因素, 可進一步完善胃腸鏡檢查明確診斷。既往存在活動性潰瘍的患者可經治療后再擇期手術。術前對患者進行心理輔導, 降低患者的心理應激水平。
3.5.2 術中預防 與麻醉醫師緊密配合, 術前合理規劃手術方案, 減少手術操作和麻醉時間。術中嚴密觀察患者生命體征, 避免出現低血壓、低心率, 導致腹腔臟器灌注不足。嚴格使用體位墊擺放體位, 特別是俯臥位手術, 注意腹部懸空, 減輕腹壓。嚴格遵守無菌操作和抗生素使用原則, 避免抗生素濫用。術中輕柔操作,置釘過程減少對脊柱的劇烈按壓和對軟組織的破壞。術中及時止血, 推薦采用自體血回輸以減少失血。
3.5.3 術后預防 術后用藥充分考慮藥物的適應證、不良反應及藥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避免使用或少用致潰瘍藥物。嚴格控制術后疼痛, 減少疼痛刺激。對存在以下危險因素的患者, 術后及時應用抑酸藥, 相關危險因素包括:①手術困難、復雜, 手術時間>3 h;②凝血功能障礙或有服用抗凝藥物史;③既往有潰瘍或消化道出血病史;④肝腎功能衰竭;⑤術中出現休克或持續低血壓;⑥嚴重感染或心理創傷等。術后病情允許時盡早恢復飲食。密切觀察患者的生命體征,注意患者是否存在反酸、噯氣、腹痛、腹脹、黑便等癥狀, 同時注意觀察患者切口引流情況, 明確是否存在出血傾向。此外, 還要對患者進行宣教, 指導患者自我觀察是否有牙齦出血、黑便等隱匿性癥狀, 做好心理疏導, 減輕患者心理應激水平。
脊柱外科術后SU 起病隱匿、發展迅速、后果嚴重,需要醫生、護士和患者共同防治, 對于術后存在SU 風險的患者應積極采取預防, 對于術后確診SU 的患者應積極采取措施, 做到早發現、早治療, 努力挽救患者生命并提高預后。
4 附病例報告
患者, 男, 53 歲, 因腰椎間盤突出癥在全麻下行腰椎后路減壓融合內固定術, 術后第2 天進食后出現腹痛、腹脹、惡心、嘔吐。腹部CT 檢查見腹腔大量積氣,提示十二指腸穿孔。行腹腔鏡下十二指腸潰瘍穿孔修補術, 術中于十二指腸竇處發現直徑約0.6 cm 的潰瘍穿孔。患者腹部CT 檢查見圖1。

圖1 1 例腰椎術后消化道穿孔患者的CT 影像資料注:A:矢狀位見上腹部、肝臟前方大量積氣;B:冠狀位肝臟周圍積氣;C、D:T11 和L1 水平橫斷面見腹腔大量積氣;☆:積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