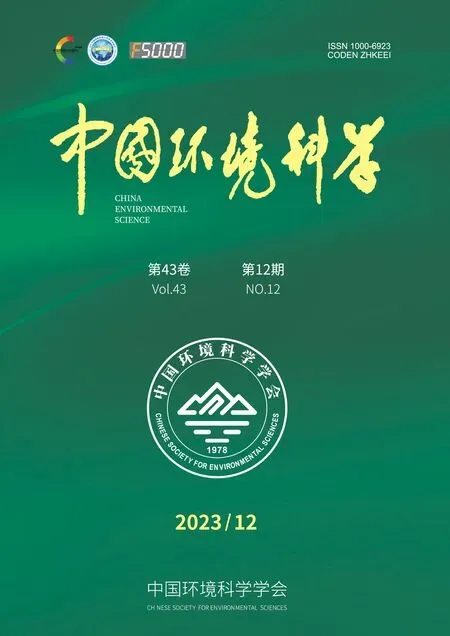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作用機制
吉雪強,崔益鄰,張思陽,孫紅雨,袁崠銘,張躍松*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作用機制
吉雪強1,崔益鄰1,張思陽1,孫紅雨2,袁崠銘3,張躍松1*
(1.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北京 100872;2.貴州大學經濟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3.國家統計局新余調查隊,江西 新余 338099)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分析有利于推進農地流轉過程中碳減排工作深入開展,但現有研究較少分析其空間效應及空間作用機制,更未識別地區異質性.參考現有成果,在理論分析后,基于2005~2021年中國大陸30省份面板數據,利用面板回歸模型檢驗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結合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其空間作用機制,并討論其空間效應的地區異質性.結果表明:研究期內,農地流轉通過多種機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負向空間效應,農地流轉既能降低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也能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是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的關鍵作用機制;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存在地區異質性,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負向空間效應比北方地區程度更深.為此,建議加快推進農地流轉,多途徑發揮農地流轉的空間減排效應.
農地流轉;農業碳排放;碳達峰;碳中和;農業污染
中國政府承諾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1].為實現目標,需科學分析各類碳源以制定有效對策.農業是世界碳排放第二大來源[2],農業碳排放約占中國總排放量的17%[3].雖然,農業碳排放并非中國碳排放首要來源,但由于中國農業規模龐大且碳排放總量巨大,因此,中國農業碳排放絕對數值不可忽視[4].在推進碳排放這一污染防治核心議題解決時應充分考慮農業碳排放問題.另一方面,.農作物生長過程產生的甲烷、農業化學物資使用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等都會加劇地區氣候變化,導致溫度、降水等氣象因素改變,也會間接增加極端事件、病蟲害等發生的概率,影響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5-6].農業碳排放強度綜合考慮農業產值和農業碳排放,能同時反映地區農業生產水平和農業綠色發展情況,相關研究對農業農村發展具有重要現實價值.
學界圍繞農業碳排放、農業碳排放強度主題開展了大量工作,包括農業碳排放、農業碳排放強度測度[7-9]、農業碳排放及其強度影響因素分析[10-12]、農業碳排放及其強度時空變化規律探索[13-14]等.這些成果為農業碳減排相關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科學參考.尋找農業碳排放及其強度影響因素,識別各因素的作用效果與路徑,調節影響因素以降低農業碳排放及其強度,是推進農業碳減排的有效思路.為此,學界對地區農業經濟發展情況[10]、地區農業聚集水平[11]、地區科技進步[12]等諸多可能影響農業碳排放或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因素進行了討論,且進一步分析了各因素對農業碳排放或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為區域協調發展背景下農業碳減排策略設計提供了理論支持.
農地流轉作為近年來中國農業農村領域重要活動,對農業農村發展產生了顯著沖擊.雖然,多數學者關注于農地流轉的經濟社會效應[15-17],但仍有部分學者認識到了農地流轉的環境效應.如龍云等[18]研究發現農地流轉會加劇農業面源污染;鄭紀剛等[19]指出轉出農地后農戶化肥投入顯著增加.但是,也有學者指出農地流轉能改善農業環境,如鄒偉等[20]和李政通等[21]都認為農地流轉活動對化肥使用具有負向影響.可見,農地流轉對環境的影響仍無定論,該問題有待結合具體情況進行分析.農業碳排放及其強度是農業環境問題重要組成,更是現階段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現實約束條件,在農業環境問題中具有特殊地位.當前,僅個別學者探討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或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龍云等[22]通過對湖南省平江縣113個農戶的調查,分析發現農地流轉將導致農業碳排放增加.吉雪強等[23-24]指出農地流轉對中國農業農村發展具有廣泛且深遠的影響,農業碳排放作為農業活動的負外部性表現,會受到農地流轉沖擊,其基于中國30個省份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農地流轉顯著增加了地區農業碳排放,但降低了農業碳排放強度.Tang等[25]進一步分析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的門檻效應.
現有研究為農地流轉過程中碳排放問題解決提供了一定學術支持.但是,現有研究還存在較多空白之處有待進一步分析:(1)現有研究較少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雖然吉雪強等[23]初步討論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影響的空間效應,但這與本研究存在本質不同,農業碳排放強度包含內容比單純的農業碳排放更為復雜;(2)現有研究未探明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或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作用機制,空間影響路徑不清晰制約了空間分析框架的建立;(3)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可能存在地區間差異,現有研究未分析這一異質性問題.
考慮農業碳排放強度相比農業碳排放包含更豐富內涵,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現實價值.為此,參考現有成果,在理論分析后,基于2005~2021年中國大陸30省份面板數據,利用面板回歸模型檢驗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結合空間計量模型討論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空間作用機制,并結合空間計量模型探索地區異質性,以充實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分析體系,為區域協調發展背景下農地流轉過程中碳排放問題解決提供新的科學支撐.
1 理論與假設
1.1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
農業碳排放強度,是單位農業產值所產生的碳排放.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負向影響[24],主要表現為農地流轉能通過減少農地拋荒,提升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等途徑增加農業產值[26];此外,農地流轉能通過減少農業活動資源消耗與促進綠色農業技術應用而降低農業生產經營過程部分碳排放[27-28].可見,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有著負向作用.
現有研究指出農地流轉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本地區,更會對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29]、社會情況[30]、生態環境[23]產生沖擊,即農地流轉的影響存在空間效應.因此,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可能同樣呈現空間特征.

圖1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其機制分析框架
具體來看,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實現(圖1).
一則,農地流轉能推動本地區農業規模經營,為先進農業技術嵌入農業實踐活動創造可能,為本地區農業增產技術、綠色農業技術創新提供實踐場所,促進農業技術創新與發展,降低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其次,農業技術創新也能通過技術擴散渠道推進周邊地區農業技術更新,提升周邊地區農業產值并降低農業碳排放,最終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因此,農地流轉能夠通過推動技術發展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技術發展機制).
二則,農業產值提升和農業碳排放降低是糧食安全和農業綠色發展這兩大農業發展目標的具體表現,當一地區農地流轉活動取得積極效益時,其未來將繼續堅持,以持續取得更好成績;此外,周邊地區也可能會學習和模仿這一經驗,加快推動本地區農地流轉,以增加農業產值,并減少農業碳排放,降低農業碳排放強度.因此,一地區農地流轉能通過示范和學習而促進本地區與周邊地區未來農地流轉活動開展從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示范效應機制).
三則,由于中國地方政府間存在競爭機制[31],當農地流轉推進地區農業發展并降低農業碳排放時,該地區可能得到上級政府部門更多關注和政策傾斜,使該地區在競爭中處于相對優勢,該地區將繼續采取更多措施以降低農業碳排放強度從而獲取更多競爭優勢.而在競爭機制作用下,其周邊地區也會更加重視農業工作,進一步采取措施提升農業產值和減少農業碳排放,以避免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農地流轉在競爭機制作用下會促使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投入增加進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地區競爭機制).
可見,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同樣是負向的.而且,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負向空間效應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實現.
綜上,作出假設:
假設1: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負向空間效應,農地流轉既能降低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也能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
假設2:農地流轉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
1.2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空間效應的地區異質性
中國南北農業生產經營差異較大,雖然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顯著為負,但這一空間效應在地區間存在差異.
就空間總效應而言,南方地區耕地破碎程度相比北方地區更為嚴重,農業發展受到土地要素限制更多;而北方地區農業規模化水平相對較高,東北、西北等地區更是多采取國營農場等規模化經營方式,故北方地區農地流轉帶來的土地要素變動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可能較小.因此,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比北方地區程度更深.
就空間效應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而言,南方地區耕地破碎程度嚴重,農業發展受到土地要素限制更多.因此,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其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顯著.此外,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同樣可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實現對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的作用.所以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體現為對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的抑制效應.
北方地區農業規模化水平相對較高,因此農地流轉帶來的土地要素變動對其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可能并不顯著.但是,北方地區農地流轉仍可能通過技術發展、示范效應、競爭機制等途徑影響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因此,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間接效應可能比直接效應更顯著.
綜上,做出假設:
假設3: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比北方地區程度更深,且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都顯著,北方地區間接效應更為顯著.
2 實證設計
2.1 實證分析思路介紹
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其空間作用機制、地區異質性等問題,從而充實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分析體系.
首先,利用雙固定效應回歸模型驗證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雖然,現有研究[24]已對此分析,但考慮不同研究時間差異可能造成的計量失誤.再次進行實證檢驗.
其次,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當農地流轉對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都產生負向影響時,假設1成立.
再次,利用空間計量模型論證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作用機制.現有研究[32-33]多利用三階段中介效應模型對作用機制問題進行分析.但現階段,中介效應模型存在較多爭議[34],空間中介效應模型可靠性更缺乏論證.江艇等[34]指出中介效應檢驗不可靠,并不意味著作用渠道分析無法進行,在分析核心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作用機制時,可先通過各種方法識別核心解釋變量對中介變量的因果作用,而中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則基于理論或已有文獻進行證明.因此,本研究將采用以下思路論證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作用機制:(1)以農業生產效率、農業碳排放效率作為農業技術和低碳農業技術發展情況替代指標,農業生產效率反映農業投入要素轉化為產出的能力,一般情況下農業生產效率越高,農業技術水平越高;考慮了農業碳排放量的農業碳排放效率則進一步考慮了技術進步的碳減排效應,當該效率越高,表明農業生產要素產生相對更高的產量或更少的碳排放,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低碳、綠色等帶有環保作用的農業技術發展情況.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技術發展影響的空間效應,若農地流轉對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技術發展產生正向空間效應,進一步結合現有文獻,分析農業技術發展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抑制作用,論證"農地流轉通過推進農業技術發展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2)利用滯后一期農地流轉面積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滯后一期農地流轉活動作為被解釋變量,一是考慮共線性問題,當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都是同一期農地流轉時,模型存在共線性干擾無法估計,此外示范效應產生需要時間,等一地區農地流轉取得成效時,其他地區才會學習和模仿,因此會產生滯后.,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下一期農地流轉活動的空間效應,若當期農地流轉對下一期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地流轉活動存在正向空間效應,進一步結合現有研究[23]已經證明的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顯著負向影響結論,論證"農地流轉通過示范效應影響帶動未來農地流轉活動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3)利用農林水事務支出作為地區農業投入水平替代指標,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林水事務支出的空間效應,若農地流轉對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林水事務支出產生正向空間效應,進一步結合實際說明地區農業投入增加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負向影響,從而論證"農地流轉通過競爭機制增加農業投入從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當上述論證都成立時,假設2成立.
最后,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空間效應的異質性.當南方地區空間總效應更大,且南方地方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都顯著,北方地區間接效應顯著,假設3成立.
2.2 實證模型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雙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如下:

式中:ACEP表示農業碳排放強度,LTR表示農地流轉;X表示控制變量;表示地區固定效應;表示時間固定效應;表示隨機誤差項;1為式(1)截距項;LTR為農地流轉的系數;為控制變量系數.不考慮地區固定效應與時間固定效應時,式(1)化為隨機效應面板回歸模型.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空間計量模型如下:


2.3 變量設定
被解釋變量:農業碳排放強度,為農業碳排放量與地區農業產值的比值.農業碳排放的計算參考文獻[7-8,23-24]等研究,包括稻田的CH4排放,各類作物、化肥和土壤引起的N2O排放,農業化學物資、農業機械和農業灌溉所產生的CO2排放.農業產值使用以2005年為基期的不變價產值.
解釋變量:農地流轉情況,參考研究[23-24,30]以各省家庭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替代.這一指標包含了各省農村家庭承包耕地轉讓面積、互換面積、流轉面積,可以較好的反映農地流轉活動的開展情況.
空間效應中介作用變量:①農業技術發展情況,利用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碳排放效率作為替代指標,分別用SBM模型、SBM非期望產出模型測度.農業生產效率的投入指標為勞動力、土地、農藥、化肥、農膜、機械、灌溉面積,產出指標為農業產值.農業碳排放效率相比農業生產效率進一步將農業碳排放作為非期望產出納入.②下一期農地流轉情況,以下一年各省家庭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替代.③農業投入水平,利用農林水事務支出進行替代.
控制變量:參考現有農業碳排放及其強度影響因素研究[10-12,24],選擇農業聚集水平、地區產業結構、創新與技術發展水平、生態環境規制、受災率等作為控制變量.①農業聚集水平反映農業產業在一地區的集中情況,當農業聚集時,更有利于耕作經驗積累和農業技術發展,進而能提升農業產值、降低農業碳排放.②地區產業結構反映地區各產業發展情況,由于研究主題聚焦于農業,為此考慮第一產業在地區經濟中所占比重.當第一產業占地區經濟比重高,表明地區經濟發展階段處于相對早期,整體技術發展水平較低且資金積累不足,農業活動可能更多依靠勞動力、土地要素和化學資源投入,其農業碳排放強度可能較高.③創新與技術發展水平反映地區科技發展情況,農業技術水平提升將顯著降低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借助于技術擴散渠道,也將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④地區生態環境規制反映地區政府對污染防治問題的重視程度,當環境規制處于較高水平時,地方農業活動將在生態補償的引導下以及環境稅費的制約下而重視污染防治,從而促進農業碳排放強度降低.⑤受災率反映農業活動受自然災害影響情況,當受災率提升,農業生產活動將受到毀滅性沖擊,農業產值將下降;但此時,農業碳排放所受影響可能較小,因為部分碳排放已經在災害發生前產生,如前期的化肥、農藥、農膜、灌溉、機械使用已經產生CO2等溫室氣體.因此,受災率可能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正向影響.
變量描述見表1.
2.4 數據來源
以中國30個省級行政單位為研究對象,西藏、香港、澳門、臺灣由于農業發展與國內其他地區存在較大差異,未納入分析體系.研究時間設定為2005~2021年.其中,基礎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農業年鑒》;農地流轉數據來自農業農村部官方網站與《中國農村經營管理統計年報》.空間權重矩陣、空間距離矩陣為基于Arcgis計算所得.個別空缺數據,利用插值法補全.具體計量分析時,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減少變量單位對效應估計的影響.

表1 變量描述
注:環境規制出現負值是由于插值法估算.

圖2 部分年份農業碳排放強度
審圖號:GS(2020)4619
3 實證分析
3.1 農業碳排放強度分析
通過計算,得到2005~2021年間農業碳排放強度,其部分年份情況如圖2所示.發現2005~2021年間,農業碳排放強度整體呈現下降趨勢,農業碳排放強度由2005年的2.99萬t/億元下降到2021年的1.64萬t/億元,下降了45.15%.該結果初步說明中國十余年來農業穩產增產和農業綠色發展取得較好成績.就不同地區來看中部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相對較高,可能的原因在于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滯后于東部地區,其農業技術相對落后,單位農業產值實現更需要依靠化肥等農業物資投入;此外,中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承擔更多農業生產任務,在更高的政策壓力下其農業活動較頻繁且農業化學資源投入更多.
3.2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效應分析
3.2.1 基準回歸分析 基于式(1),利用雙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模型和隨機效應面板回歸模型估計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見表2.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表明農地流轉面積擴大會抑制農業碳排放強度.究其原因,農地流轉能推進農業生產水平提升和降低農業碳排放.

表2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
注:***、**和*表示1%、5%和10%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差.
就控制變量而言,農業聚集水平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原因在于產業聚集下的規模效應、經驗積累與技術發展提升農業產出和減少農業污染.地區產業結構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表明地區第一產業占地區經濟比重越高,農業碳排放強度越高,其原因如理論分析所言,第一產業占比較高情況下經濟發展相對處于早期,制約了農業技術與裝備應用,使農業碳排放強度較高.創新與技術發展水平影響為負,表明技術發展抑制了農業碳排放強度.環境規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顯著為負,表明環境規制降低了農業碳排放強度.受災率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顯著為正,如理論分析指出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具有破壞性,但對前期投入產生的溫室氣體影響小.
3.2.2 穩健性分析 為驗證基準回歸模型穩健性,采取調整控制變量、調整研究地區、調整研究時間等方法重新估計基準回歸模型,多數結果顯示農地流轉依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負向影響.此外,為解決內生性,參考研究[24],利用工具變量法檢驗模型(選擇的工具變量如表1).選用1983年各省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戶數為工具變量基礎變量,是由于其作為歷史數據具有外生性,但能反映地區農地改革趨勢,和當前農地流轉具有相關性.分析時,進行了弱工具變量檢驗、不可識別檢驗,結果都通過,排除內生性后結果依然穩健.可見,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負向影響具有穩健性.
3.3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其空間作用機制分析
3.3.1 莫蘭指數 以空間鄰接矩陣、空間距離矩陣為權重矩陣,計算農地流轉和農業碳排放強度的空間莫蘭指數(表3),以分析其空間相關性.

表3 莫蘭指數
注:***、**和*表示1%、5%和10%顯著性水平.
由表3可知,農地流轉在后續年份具有較顯著的空間相關性,農業碳排放強度在研究期每年都呈現顯著的空間相關性,兩變量整體上拒絕了"無空間自相關"的原假設.進一步可知,農地流轉和農業碳排放強度都呈現正向空間聚集關系.
3.3.2 空間模型選擇 確定核心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具有空間自相關效應后,分別就空間鄰接矩陣、空間距離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下的空間計量模型選擇情況進行分析.
首先,就空間鄰接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的一般空間計量模型進行LM檢驗.分析發現非空間面板模型的LM檢驗顯著拒絕原假設,表明空間效應存在,再次說明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時應考慮空間效應.而后,進行LR與Wald檢驗,以判斷實證分析應選擇的模型.結果顯示空間滯后模型與空間誤差模型的LR檢驗值為16.46及17.01,都在5%的統計水平顯著;Wald檢驗值為12.85及43.60,分別在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該結果表明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分析中空間杜賓模型不能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為此,利用空間杜賓模型進行分析.然后,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以明確選用何種效應空間杜賓模型.Hausman檢驗中Prob>=chi2 = 0.21,表明拒絕固定效應的零假設.因此,應當選擇隨機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分析以空間鄰接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的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
類似的,對以空間距離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的空間計量模型進行LM檢驗、LR與Wald檢驗、Hausman檢驗.發現同樣應當使用隨機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
3.3.3 空間效應分析 以隨機效應空間杜賓模型估計空間效應,結果兩類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的空間自回歸系數(rho)都在1%的統計水平顯著,再次表明空間效應的存在.空間回歸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模型(1)(2)與模型(6)(7).為清晰描述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利用偏微分法分解各變量的空間總效應,結果見表4模型(3)~(5)與模型(8)~(10).
雖然模型(1)與模型(6)顯示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負向影響并不顯著,但該結果可能忽略了反饋效應的存在.相比于直接的空間回歸結果,偏微分方程分解結果更能真實反映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
深井定向隨鉆擴孔鉆井作業,所使用的鉆頭須同時具備三方面的能力,即高效的擴孔能力、良好的定向能力和較強的穩定性。而定向隨鉆擴孔PDC鉆頭(簡稱“擴孔鉆頭”)的定向和隨鉆擴孔性能,可通過對鉆頭擴孔結構、冠部形狀、布齒結構等方面的改進得以實現。

表4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其分解
注:***、**和*分別表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括號內為穩健標準誤差,下同.
由模型(3)與模型(8)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為負且在10%統計水平顯著,表明農地流轉會較顯著降低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由模型(4)與模型(9)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間接效應為負且在1%的統計水平顯著.表明農地流轉會顯著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即存在顯著的負向空間溢出效應.正如理論分析指出,農地流轉能通過技術發展、示范效應、競爭機制等途徑促進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降低.進一步對比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間接效應系數值和顯著性都要大于直接效應,可見空間溢出效應更為明顯,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時應當考慮其空間溢出效應,否則將降低分析結果的可靠性.由模型(5)與模型(10)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總效應為負且在1%統計水平顯著,再次論證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顯著的負向空間效應.綜上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存在顯著負向空間效應,農地流轉既能降低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也能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假設1成立.
結合微分方程分解結果來看,控制變量中,農業聚集水平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顯著為負,間接效應不顯著,說明農業產業聚集更多作用于本地區農業活動.地區產業結構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總效應均顯著為正,表明地區產業結構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并不局限于本地區,還具有空間溢出效應.本地區經濟發展處于初期,不僅制約了技術、資金等對本地農業發展的支持,更難以通過技術擴散、示范效應等渠道對周邊地區農業發展產生積極影響,還會在一定程度分散周邊農業資源,使本地區及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都處于相對高值.創新與技術發展水平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總效應均顯著為負,表明技術發展可以顯著降低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技術擴散對于整體空間農業碳排放強度下降具有重要價值.生態環境規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顯著為負,表明環境規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于本地區.受災率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總效應均顯著為正,表明自然災害對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產出都具有破壞,但對前期投入產生的溫室氣體影響較小,使空間農業碳排放強度整體提高.
3.3.4 空間作用機制分析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負向空間效應可能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實現.下面分別就這三個空間作用機制進行驗證.
技術發展機制基于上文所述實證分析思路,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業生產效率、農業碳排放效率影響的空間效應.經過LM檢驗、LR與Wald檢驗、Hausman檢驗,發現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更為合適,進一步對比模型rho顯著情況,并考慮本研究對于空間問題的重視,決定利用地區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作為分析模型.以空間鄰接矩陣和空間距離矩陣作為空間權重矩陣并經過偏微分分解的農地流轉對農業技術發展情況影響的空間效應結果見表5.

表5 農地流轉對農業技術發展情況的空間影響
由表5模型(1)(4)(7)(10)可知,農地流轉對本地區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碳排放效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農地流轉有利于推進本地區農業技術和綠色農業技術發展,結合現有研究[35-36]可知農業技術發展和農業綠色技術發展有利于提升農業產值和降低農業碳排放,是農業碳排放強度降低的重要途徑,這驗證了農地流轉對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技術作用機制.
由表5模型(2)(5)(8)(11)可知農地流轉對周邊地區農業生產效率和農業碳排放效率影響的空間效應顯著時均為正,可知農地流轉對周邊地區農業技術和農業綠色技術發展同樣具有一定的積極影響,這一對周邊地區農業技術的積極影響根據現有研究可知[35-36]同樣有利于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因此,農地流轉通過推進農業技術發展而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
綜上,農地流轉通過推進農業技術發展對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
(2)示范效應機制基于上文所述實證分析思路.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下一期農地流轉的空間效應.經過LM檢驗、LR與Wald檢驗、Hausman檢驗,發現固定效應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適合.考慮模型的空間lambda值和空間rho值,決定利用時間固定、空間固定、雙固定效應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進行測度.以空間鄰接矩陣為權重矩陣的空間誤差模型結果見表6模型(1)~(3)(空間誤差模型未能進行偏微分分解),空間滯后模型的偏微分分解結果見表6模型(4)~(12),以空間距離矩陣為權重矩陣的結果見表7,以此作為對比.
由表6和表7模型(1)(2)(3)(6)(9)(12)可知,農地流轉整體對下期農地流轉產生顯著的正向空間效應.

表6 農地流轉對下期農地流轉的空間影響(空間鄰接矩陣)

表7 農地流轉對下期農地流轉的空間影響(空間距離矩陣)
由表6和表7模型(4)(7)(10)可知,農地流轉對本地區下期農地流轉產生顯著的正向空間效應.究其原因,本地區在當期通過農地流轉取得農業碳排放強度降低效益后,未來會延續這一正確做法.
由表6模型(5)(8)(11)可知,以空間鄰接矩陣作為空間權重矩陣以空間滯后模型為空間計量模型時,農地流轉對下期周邊地區農地流轉產生顯著正向空間效應.雖然表7模型(5)(8)(11)中這一空間效應不全部顯著,但是依然為正.結合表6和表7的空間lambda值和空間rho值顯著情況可知,表6結果更可靠,更能反映農地流轉對下期周邊農地流轉的空間影響.
整體而言,農地流轉對下期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地流轉都會產生正向空間效應.當一地區農地流轉推進后,本地區和周邊地區下一期農地流轉活動可能加強.而現有研究[23]和本研究前文都論證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負向影響.因此,一地區農地流轉活動具有示范效應,能帶動本地區和周邊地區未來農地流轉,進而降低農業碳排放強度,即農地流轉通過示范效應帶動本地區和其他地區的農地流轉活動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
(3)地區競爭機制基于上文所述實證分析思路,利用空間計量模型分析農地流轉對農林水事務支出的空間影響效應.經過LM檢驗、LR與Wald檢驗、Hausman檢驗,并對比模型rho顯著情況,且進一步考慮本研究對于空間問題的重視,決定利用地區固定效應空間杜賓模型作為分析模型.偏微分分解的空間效應結果見表8.
由表8的模型(3)(6)可知,農地流轉對農林水事務支出影響的空間總效應顯著為正,表明考慮空間效應時農地流轉能顯著增加農林水事務支出,提高農業投入.由模型(1)(4)可知,農地流轉對本地區農林水支出事務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由模型(2)(5)可知農地流轉對周邊地區農林水事務支出產生正向影響,且在以空間距離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時,這一正向影響更是在1%統計水平顯著. 表明農地流轉活動對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投入產生正向空間效應.原因在于當一地區通過農地流轉取得農業領域積極效益時,其周邊地區在競爭壓力下會更重視農業工作而擴大農業資金、技術投入,避免在競爭中失敗.在地區對農業相關投入增多的情況下,地區農業產值更可能得到提升,其農業碳排放也更可能降低.因此,一地區農地流轉可能加劇地區農業競爭,使本地區和周邊地區增加農業投入,從而降低農業碳排放強度,即農地流轉通過競爭機制而增加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投入從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
綜上,農地流轉能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影響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農業技術發展情況、農地流轉推進情況、農業投入水平,從而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因此,假設2成立.

表8 農地流轉對農林水事務支出的空間影響
3.3.5 穩健性分析 為檢驗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分析與空間作用機制分析的穩健性,上文已經利用空間鄰接矩陣、空間距離矩陣分別作為空間權重矩陣進行檢驗和運算,結果整體上較為相似(雖然個別分析中顯著性不同,但是當相關變量顯著時,其符號方向一致);此外,通過減少控制變量的方式驗證控制變量調整后上述空間回歸模型及其分解結果變化,發現上述結論依然成立.因此,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存在負向空間效應,農地流轉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等結論具有一定穩健性.
4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空間效應的異質性分析
4.1 異質性分析
由于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可能存在地域差異.因此,以秦嶺淮河為界將中國大陸30個省份劃分為北方地區和南方地區,分別測算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
參考上文,以空間鄰接矩陣為權重矩陣,在進行系列檢驗后,就南方地區、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進行測度,并對結果進行偏微分分解,分解結果見表9.

表9 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空間效應異質性分析
由表9可知,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總效應為-0.63,北方地區為-0.16,且兩者都在1%的統計水平顯著,表明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比北方地區程度更深.
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均顯著為負.原因在于,南方地區農地流轉有效緩解了本地區耕地細碎化制約,提升了農業經營規模,使南方地區先進的農業技術、豐富的資金得以在更合適的經營規模中發揮作用,以提升地區農業產值,并降低農業碳排放,從而降低了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間接效應顯著為負.原因在于,南方地區經濟技術交流渠道豐富,農地流轉通過技術擴散途徑較好降低了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使其影響為負.整體而言,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呈現負向空間效應.
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不顯著,間接效應顯著為負.原因在于,北方地區多數區域如西北、東北本就采取規模化農業經營,農地流轉對其本地農業經營規模影響較小,難以顯著提升其農業產值與降低農業碳排放,故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不顯著.北方地區農地流轉雖然較難通過擴大農業經營規模而對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作用,但由于其本身具備較好的農業規模化經營基礎,農地流轉推進背景下仍可能通過技術發展、示范效應、競爭機制等途徑影響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
整體而言.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比北方地區程度更深,且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都顯著,北方地區間接效應更為顯著,所以假設3成立.
4.2 穩健性檢驗
利用空間距離矩陣替代空間鄰接矩陣作為空間權重矩陣,按照上述思路進行分析,發現異質性分析主要結論成立(可參看附件).此外,通過調整控制變量對分析結果進行檢驗,發現結論依然成立.因此,異質性分析結果具有一定穩健性.
5 結論
5.1 農地流轉通過多種機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的負向空間效應,農地流轉既能降低本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也能降低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
5.2 農地流轉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負向空間效應.
5.3 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比北方地區程度更深,且南方地區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都顯著,北方地區間接效應顯著.
6 建議
6.1 由于農地流轉能通過多種機制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產生顯著負向空間效應.因此,建議通過加快土地確權頒證、擴大農地流轉宣傳教育、加強農地流轉交易平臺建設等方式加快推進農地流轉,以發揮農地流轉的碳減排效益.
6.2 由于農地流轉通過技術發展機制、示范效應機制、地區競爭機制等降低本地區和周邊地區農業碳排放強度.因此,建議推進跨區域農業技術交流平臺建設,以更好推廣農地流轉下規模化經營環境所實現的技術創新成果,發揮農業技術的空間減排效應;建議構建農業減排示范表彰機制,對農業減排先進地區進行財政獎勵和公開表彰,以鼓勵其他地區學習;建議將農業碳排放強度作為地區農業發展指標納入考核體系,促進圍繞"穩產增產"與"低碳發展"兩大目標展開的地區間農業良性競爭.
6.3 由于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存在地區異質性.因此,建議北方地區在農業規模化經營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低碳農業技術、農業信息化技術等兼顧農業生產和污染防治的先進技術應用,以穩定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負向空間溢出作用.建議南方地區進一步打通地區農業技術交流渠道,加快農業減排示范表彰機制、低碳農業考核體系建設,進一步強化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溢出效應,
相對現有研究,本研究同樣識別到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顯著負向影響,驗證了現有研究分析結果的準確性.但是,本研究深入討論了現有研究較少涉及的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空間作用機制,并分析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空間效應的地區異質性,得到了一些新的結論,實現了該主題的拓展.然而受制于研究進展,仍存在一些局限:(1)研究雖然基于空間計量模型就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作用機制進行了初步分析,但是沒有探討相關分析的內生性等諸多問題,這有待未來空間中介分析方法完善后進一步研究.(2)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是否存在著非線性特征,這一問題需要待相關空間門檻模型完善后進行深入分析. (3)研究從宏觀角度分析了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空間作用機制以及地區異質性,但是農戶視角下該作用是否成立?這需要結合微觀調研結果進一步分析.
[1] 高國力,文 揚,王 麗,等.基于碳排放影響因素的城市群碳達峰研究[J]. 經濟管理, 2023,45(2):39-58.
Gao Guoli, Wen Yang, Wang li, et al. Study on carbon peaking of urban clusters based 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s [J]. Economic Management, 2023,45(2):39-58.
[2] 信 猛,陳菁泉,彭雪鵬,等.農業碳排放驅動因素——區域間貿易碳排放轉移網絡視角[J]. 中國環境科學, 2023,43(3):1460-1472.
Xin Meng, Chen Jingquan, Peng Xuepeng et al. Driv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regional trade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network.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3,43(3):1460-1472.
[3] 趙文晉,李都峰,王憲恩.低碳農業的發展思路[J]. 環境保護, 2010, (12):38-39.
Zhao Wenjin, Li Dufeng, Wang Xian’en.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agriculture [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0,(12):38-39.
[4] 田 云,林子娟.中國省域農業碳排放效率與經濟增長的耦合協調[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22,32(4):13-22.
Tian Yun, Lin Zijua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32(4):13-22.
[5] 曾賢剛,余 暢,孫雅琪.中國農業農村碳排放結構與碳達峰分析 [J].中國環境科學, 2023,43(4):1906-1918.
Zeng X G, Yu C, Sun Y Q. Carbon emission structure and carbon peak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3,43(4):1906-1918.
[6] 潘根興,高 民,胡國華,等.氣候變化對中國農業生產的影響[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11,30(9):1698-1706.
Pan Genxing, Gao Min, Hu Guohua, et 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1,30(9):1698-1706.
[7] 閔繼勝,胡 浩.中國農業生產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測算[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2,22(7):21-27.
Min Jisheng, Hu Hao. Estimation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2,22(7):21-27.
[8] 尚 杰,楊 果,于法穩.中國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測算及影響因素研究[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15,23(3):354-364.
Shang Jie, Yang Guo, Yu Fawen. Agricultural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Eco-Agriculture, 2015,23(3):354-364.
[9] 原 野,李太平.糧食增產與農業碳排放強度降低——基于中國糧食主產區政策的準自然實驗證據[J]. 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3,26(1):84-94.
Yuan Ye, Li Taiping. Increased grain yield and reduced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Quasi natur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policies in China's main grain producers [J]. Journal of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26(1):84-94.
[10] 何艷秋,戴小文.中國農業碳排放驅動因素的時空特征研究[J]. 資源科學, 2016,38(9):1780-1790.
He Yanqiu, Dai Xiaowen. Pha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griculture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J]. Resources Science, 2016,38(9):1780-1790.
[11] 賀 青,張 虎,張俊飚.農業產業聚集對農業碳排放的非線性影響[J]. 統計與決策, 2021,37(9):75-78.
He Qing, Zhang Hu, Zhang Junbiao. Nonlinear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1,37(9):75-78.
[12] 張金鑫,王紅玲.環境規制、農業技術創新與農業碳排放 [J]. 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47(4):147-156.
Zhang Jinxin, Wang Hongl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J].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47(4):147-156.
[13] 何艷秋,王鴻春,劉云強.產業集聚視角下農業碳排放的空間效應[J]. 資源科學, 2022,44(12):2428-2439.
He Yanqiu, Wang Hongchun, Liu Yunqiang. Spatial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J]. Resources Science, 2022,44(12):2428-2439.
[14] 孟慶雷,殷宇翔,王煜昊.我國農業碳排放的時空演化、脫鉤效應及績效評估 [J]. 中國農業科學, 2023,56(20):4049-4066.
Meng Q L, Yin Y X, Wang Y H.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decoupling effect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J].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2023,56(20):4049-4066.
[15] Chen L, Peng J, & Zhang Y.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non-farm employment of farm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Hubei Province,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19(23).
[16] 符秋瑤,張棟浩.農地流轉如何影響農村家庭養老計劃——基于農地轉出與農地轉入視角的綜合分析[J]. 農業技術經濟, 2022, (5):128-144.
Fu Qiuyao, Zhang Donghao.How does farmland transfer affect the rural household retirement planning:Comprehensive analysis based on farmland outflow and farmland inflow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2,(5):128-144.
[17] 黎 毅,羅劍朝.農地確權對農戶收入異質性的影響研究——基于西部六省份調研數據[J]. 財貿研究, 2022,33(11):27-38.
Li Yi, Luo Jianchao.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armland certification on farmers' income heterogeneity:Evidence from six provinces of western region [J]. Finance and Trade Research, 2022,33(11):27-38.
[18] 龍 云,任 力.中國農地流轉制度變遷對耕地生態環境的影響研究[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5):39-45.
Long Yun, Ren Li.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farmland transfer system change on farm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J]. Fujian Tribune, 2016,(5):39-45.
[19] 鄭紀剛,張日新,曾 昉.農地流轉對化肥投入的影響——以山東省為例[J]. 資源科學, 2021,43(5):921-931.
Zheng Jigang, Zhang Rixin, and Zeng Fang.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ertilizer input:Taking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J]. Resource Science, 2021,43(5):921-931.
[20] 鄒 偉,崔益鄰,周佳寧.農地流轉的化肥減量效應——基于地權流動性與穩定性的分析[J]. 中國土地科學, 2020,34(9):48-57.
Zou Wei, Cui Yilin, Zhou Jianing.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farmers’ fertilizer reduction: An analysis of transferability and security of land rights [J]. China Land Science, 2020,34(9):48-57.
[21] 李政通,顧海英.農地權能、勞動力流動與化肥用量[J]. 農村經濟, 2021,(9):34-43.
Li Zhengtong, Gu Haiying. Agricultural land rights, labor mobility and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J]. Rural Economy, 2021,(9):34-43.
[22] 龍 云,任 力.農地流轉對碳排放的影響:基于田野的實證調查[J]. 東南學術, 2016,(5):140-147.
Long Yun, Ren Li.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on carbon emissions: a field-base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Southeast Academic Research, 2016,(5):140-147.
[23] 吉雪強,李卓群,張躍松.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的影響及空間特性[J]. 資源科學, 2023,45(1):77-90.
Ji Xueqiang, Li Zhuoqun, Zhang Yuesong. Influenc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J]. Resource Science, 2023,45(1):77-90.
[24] 吉雪強,劉慧敏,張躍松.中國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J]. 中國土地科學, 2023,37(2):51-61.
Ji Xueqiang, Liu Huimin, Zhang Yues.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its mechanism in China [J]. China Land Science, 2023,37(2):51-61.
[25] Tang, Y., & Chen, M. Impact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Mediating Effect Test and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J]. Sustainability (Switzerland), 2022,14(20).
[26] 郭小琳,鄭淋議,施冠明,等.農地流轉、要素配置與農戶生產效率變化[J]. 中國土地科學, 2021,35(12):54-63.
Guo Xiaolin, Zheng Linyi, Shi Guanming, et al. Land transfer,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ural household production efficiency [J]. China Land Science, 2021,35(12):54-63.
[27] 李文明,羅 丹,陳 潔,等.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規模效益、產出水平與生產成本——基于1552個水稻種植戶的調查數據[J]. 中國農村經濟, 2015,(3):4-17,43.
Li Wenming, Luo Dan, Chen Jie, et al. Agricultural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economies of scale, output level and production cost ——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552rice farmers [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5,(3):4-17,43.
[28] 龍 云,任 力.農地流轉對農業面源污染的影響——基于農戶行為視角[J]. 經濟學家, 2016,(8):81-87.
Long Yun, Ren Li.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behavior [J]. Economist, 2016,(8):81-87.
[29] 夏玉蓮,曾福生.農地流轉的經濟效應及其空間溢出——基于"三化"發展的視角[J]. 技術經濟, 2012,31(11):56-62.
Xia Yulian, Zeng Fusheng. Economic effe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modernizations"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Technology Economics, 2012,31(11):56-62.
[30] 盧新海,王洪政,唐一峰,等.農地流轉對農村減貧的空間溢出效應與門檻特征——省級層面的實證[J]. 中國土地科學, 2021,35(6):56-64.
Lu Xinhai, Wang Hongzheng, Tang Yifeng,et al. Spatial spillover and threshold effects of farmland transfer in poverty red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J]. China Land Science, 2021, 35(6):56-64.
[31] 傅 強,朱 浩.中央政府主導下的地方政府競爭機制——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制度視角[J]. 公共管理學報, 2013,10(1):19-30,138.
Fu Qiang, Zhu Hao. The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mechanism guided by central government———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to explai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3,10(1):19-30,138.
[32] 溫忠麟,葉寶娟.中介效應分析:方法和模型發展[J]. 心理科學進展, 2014,22(5):731-745.
Wen Zhonglin, Ye Baojuan.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22(5):731-745.
[33] 周 迪,劉奕淳.中國碳交易試點政策對城市碳排放績效的影響及機制[J]. 中國環境科學, 2020,40(1):453-464.
Zhou Di, Liu Yichun. Impact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on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carbon emission and its mechanism.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0,40(1):453-464.
[34] 江 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 中國工業經濟, 2022,410(5):100-120.
Jiang Ting. Mediating effects and moderating effects in causal inference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22,410(5):100-120.
[35] 范東壽.農業技術進步、農業結構合理化與農業碳排放強度[J]. 統計與決策, 2022,38(20):154-158.
Fan Dongshou.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ation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J].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2,38(20):154-158.
[36] 楊 鈞.農業技術進步對農業碳排放的影響——中國省級數據的檢驗[J]. 軟科學, 2013,27(10):116-120.
Yang Jun.The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J]. Soft Science, 2013,27(10):116-120.
The spatial effect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JI Xue-qiang1, CUI Yi-lin1, ZHANG Si-yang1, SUN Hong-yu2, YUAN Dong-ming3, ZHANG Yue-song1*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3.Xinyu Investigation Team,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Xinyu 338099, China)., 2023,43(12):6611~6624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consider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evel and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s scientific value for promot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land transfer promotion, but few existing studies have analyzed its spatial effects. After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s mainland from 2005 to 2021, the panel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 spatial effects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were discussed by combining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rural land transfer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intensity. Rural land transfer can not only reduce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intensity in the local area, but also reduce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intensity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s more obviou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echanism, demonstration effect mechanism and regional competition mechanism are the key mechanisms of the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 spatial effe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spati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southern China is deeper than that in northern China.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peed up rural land transfer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patial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 various ways.
rural land transfer;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carbon peaks;carbon neutral;agricultural pollution
X32,F301.24
A
1000-6923(2023)12-6611-14
吉雪強,崔益鄰,張思陽,等.農地流轉對農業碳排放強度影響的空間效應及作用機制研究 [J]. 中國環境科學, 2023,43(12):6611-6624.
Ji X Q, Cui Y L, Zhang S Y, et al. Study on the spatial effect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rural land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3,43(12):6611-6624.
2023-04-1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227420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7BRK023)
* 責任作者, 教授, yuesong51@sina.com
吉雪強(1996-),男,江西吉安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土地經濟與政策、房地產經濟與管理、農業生態經濟研究.發表論文10余篇.jixueqiang@ru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