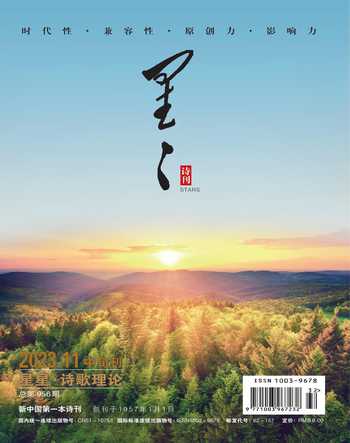觸機成趣,妙緒紛披
吳平安
操持“以詩論詩”這一獨特文體的作者,必須是詩人,而且必須是優秀的詩人。這一判斷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文學史上,都可以得到充分印證,這與沒有寫過詩的人可以評詩論詩不可同日而語。詩擅抒情,說理非其長項。“論詩”則貴在歸結或在“論”中道出某些見解、提出某種理論,同時必須滿足詩的質的要求,不可以概念范疇邏輯推演的方式行文。因此,“論詩”必須是一首詩而不是分行的散文。“以詩論詩”中外皆有,影響較大的有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感應》等,中國詩人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等。波德萊爾的十四行詩《感應》,將宇宙比喻為一座“象征的森林”,被尊為“象征派的憲章”;杜甫的《戲為六絕句》“以詩論文,于絕句中又屬創體”(《唐宋詩醇》),批評文人相輕陋習,“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力倡繼承前人而絕非“遞相祖述”的這一美學主張至今仍不無意義;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奉《詩三百》風雅為“正體”,漢魏樂府與建安詩歌為后繼,對所處宋金詩壇“偽體”盛行的現狀撥亂反正,提出以“詩中疏鑿手”為己任。
中國新詩剛過百年,詩壇氣象萬千“亂象”亦萬千,新詩理論建設正處于一重要節點,與波德萊爾、杜甫、元好問所面對的時代有相似性,沈葦今效法前賢出版《論詩》(長江文藝出版社2023年1月)可謂正當其時。當然,如果試圖建構起一套邏輯自洽、嚴密完整的詩學理論體系,“以詩論詩”的方式顯然是不大可能的。不過詩人沈葦吟哦多年,對詩的心得了悟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夫子自道;主編刊物,對當今詩壇現狀與走向了然于胸;執教大學,對詩學也有高屋建瓴的理論思考。具備了以上三項,沈葦便具備了“以詩論詩”的資質與底氣,可以提出自己對全書起支撐性的詩學觀。
“詩是無言之言,無用之用/從‘無中一再化生”,是“缺席在場”和“不在之在”。所謂的“缺席在場”和“不在之在”,顯然不是指傳統詩學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而是先于詩人存在的詩。詩如同頭頂的三尺神靈“俯視”著詩人,直到詩人“十分小心、慎重”地寫下,遂顯形為三尺頭頂的一首詩。受當前AI技術突飛猛進的啟發,沈葦將“一首新出爐的詩”比喻成無人駕駛的汽車。這首詩不受詩人操控,“無人、無己”,只接受“以太至高之善的派遣”(《無人駕駛》)。不難看出,其間有柏拉圖“神靈憑附說”的影子在晃動。古人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與今人所言“詩來找我”庶幾近之。這是帶有本體論色彩的詩歌美學,也有某種神秘論意味。
沈葦批評當今詩壇“像流水滑過玻璃、大理石表面”。在我看來,那些“過于順滑”的詩是網絡時代傳播便捷的必然伴生現象,即便優秀之作也少有品味與闡釋空間,其極端便是口語詩或口水詩的大行其道。究其底里還是語言如何處理的問題,這與實用性功能和詩性功能既聯系又相區分。為此《論詩》首篇開宗明義提出了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概念——“內置”,即我們常說的“去阻斷它”。沈葦顯然受到了俄國形式主義美學“陌生化”理論的影響,但“阻斷”順滑在詩學處理的操作性上無疑需要更具體,更明確。如在《痛飲》一詩中,沈葦隔空邀約讀者并和讀者交換詩心,讀者的接受維度顯然也在沈葦的考慮范圍之內。以此觀之便已經具備了搭建詩學理論大廈的基本梁柱,余下就是擺放大廈內部的陳設了。
如同杜甫“論詩”必要論及詩人一樣,詩集《論詩》也語涉李白、杜甫、蘇軾、阮籍、陸游、元好問、劉半農、荷馬、莫扎特、布萊希特等多位中外廣義上的詩人,一是禮贊先賢,二是承繼傳統。如《詩仙》中,用八個不避重復、不懼單調的排比句“……的李白”,概括了李白多姿多彩的一生,第九句以“終化為騎鯨捉月去不返的詩仙”,完成由“李白”到“詩仙”的升華。再如《杜甫》一詩,從標題到寫法完全不走“杜甫”到“詩圣”之路,而是盛贊其“在風雨和鬼神之間”開拓出“無邊現實主義”的巨大貢獻。沈葦推崇劉半農的歌謠,尤其贊賞他從第三人稱的“他”字創造出另一個“她”字沿用至今,取代了民國時期的“伊”字而廣受認可。自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為漢語言文字做出過貢獻的歷代中國文人,都應該受到后人的尊敬。同樣在許多國家的民族語言形成過程中,詩人都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沈葦在此提醒中國當代詩人要對中國的語言文字擔負責任。
《論詩》中所謂承繼傳統,是針對當今再現歷史中相似現象的警策。如《放翁》一詩,借陸游力戒江西詩派堆垛、僻澀的“啄琱之病”,批評當下部分詩歌“過度順滑”后的另一極端——“技術至上和修辭過度”的弊端。又如提出莫扎特的樂曲將諸多對立性的元素熔于一爐,總結出“賈寶玉+孫悟空”的操作模式,以求呈現紛繁中和諧的詩美。再如《混沌》一詩,以鑿七竅而亡的故事誡勉以二元論眼光看世界,力主詩人需保持混沌的第三只眼。作為一個在大漠冰山和煙雨江南間游走的詩人,沈葦的文化性格必然會影響到他的審美理想,并秉持這種理想介入當下文學現場,為營造一個健康的文學生態盡一份責任。
《青年》一詩中,“整個晚上/都在喋喋不休攻擊同行/……/我們的智力,不是用來/攻擊別人,而是用來完善自己的/……/捧殺別人/建設自己,也是一個好辦法”。這是一首精短敘事詩,直接針對當下詩壇時弊,寥寥數行,時間、地點、人物、場景、話語,敘事各要素悉數到位,且三人各有其面目,濃郁的喜劇色彩,令人莞爾。詩題《青年》更將個體上升為群體,遂把當今詩壇“亂象”表露無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曹丕、杜甫有所不知的是當今文人除了“相輕”之外,“相捧”也成為一大風氣,當然是各樹山頭,各搖旗幡,黨同伐異而已。《誤會》一詩中,“全身終于掛了點廢銅爛鐵”亦可作如是觀。這首詩的靈感來自里爾克,針對的卻是當下中國詩壇;“終于”一詞,言其榮譽、獎項、頭銜等來之不易,自然不甘錦衣夜行,一定要招搖過市顯擺顯擺,問題是一旦把這些虛名真當回事,那就真的“誤會”了。
相對于舊體詩形式和內容嚴格的自律以至于格式化,剛剛走過百年的新詩仍然在路上。新詩之新,新在自由,新在不斷地生成、不斷地變化,誰也不能規定新詩只能這樣寫不能那樣寫。正如柏拉圖所言,詩有別于技術,不受規則限制。因此,所謂“正體”“偽體”之辨,很難用之于新詩。如果有所謂的“底線”,應堅守詩之為詩,而非其他美學的質的規定性,這是舊詩、新詩共同的恪守。明乎此,則可以判定沈葦在詩集《論詩》中所生發的哪怕是吉光片羽式的真知灼見,對新詩建設也都是有價值的貢獻。若從文學評論著眼,廁身高校的沈葦不俯就學院派的學術評價體系,“以詩論詩”,觸機成趣,妙緒紛披,讓古老的詩美傳統發揚光大,也算是給當今的文學評論注入了一股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