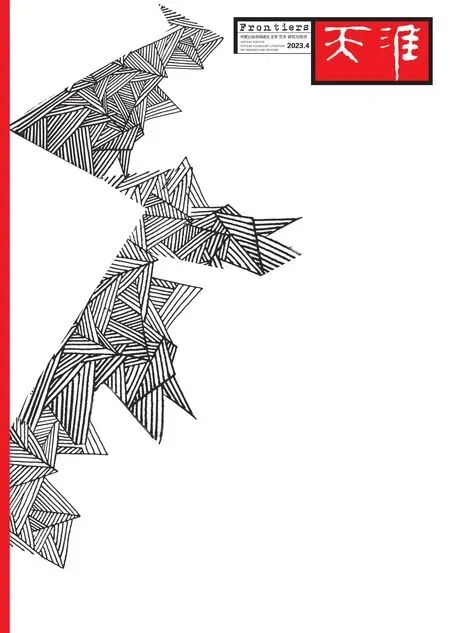為了我們不再脆弱
萬俊人
幾年前,拜讀好友、香港大學慈繼偉教授的大作《正義的兩面》,頗有心得,把讀后感概括成了一個疑問句:“正義為何如此脆弱?”近日,趁節假閑暇,重讀美國倫理學界前輩老友麥金泰爾先生的《依賴性的理性動物——人類為什么需要德性》一書,讀后心得竟然還是歸結到“脆弱”二字,不過不再指向社會正義秩序,而是直接指向人類生命本身:毫無疑問,在全球范圍肆虐延宕三年多且無情奪走數以百萬計人類生命的新冠疫情,讓我深感麥金泰爾先生是書提問背后的錐心之痛——我們的生命為何如此脆弱?
麥金泰爾先生把提問當作其新著的副標題:“人類為什么需要德性?”但他直接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并把答案當作該著的正題:因為人類只不過是一種“依賴性的理性動物”。這意思是說,人類并非一群各自獨立無依的生命個體,更不是萬類霜天的主宰,而只是且只能是相互依賴、甚至也依賴外部非人類(自然)世界的“理性動物”,是自然眾生之一,只不過因為人類能夠自覺到其生命的脆弱性和依賴性,并找到了社會化生存方式和諸如德性、語言一類的文明暨文化之方式,故而使其獲得強于其他生物的生存發展能力。在某種意義上,意識并學會憑借這種相互依賴和外部依賴,以克服自身固有的“脆弱性”和“殘疾性”,正是人類之有“理性”的“人類生物學”證明。在書的“前言”中,麥金泰爾先生開篇即亮明自己最新關注的兩個問題:(1)“對我們來說,關注并理解人類與其他智能物種之間的共同之處為什么重要?”(2)“對道德哲學家而言,關注人類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殘疾(或無能,disability)為什么重要?”后一個問題尤其突出,因為該問題“迄今為止在道德哲學領域尚未得到足夠的關注”。讓人意外的是,麥金泰爾緊接著坦承了自己在《追尋美德》——我以為,或許還應包括他隨后的《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和《三種對立的道德探究觀》等系列著述——一書中所犯的錯誤,即:他曾經相信,道德哲學應當擺脫亞里士多德曾經主張的“形而上學的生物學”。現在他則確信,若要充分回應并解答上述有關人類脆弱性和殘疾性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尤其是解答人類為什么需要德性(美德)來克服其脆弱,必須重建某種形式的人類(道德)生物學基礎。唯其如此,我們才能解答人類脆弱的生命如何可能維持,又如何可能克服其生命的脆弱與殘疾(殘障或無能),獲得其文明生活的永續發展。
我越來越相信某種帶有歷史主義情懷的文化闡釋學見解:任何文本解讀不僅與上下文(contexts,或譯為“互文”)直接相關,而且也與閱讀者所處的時空背景或歷時情景息息相關。若非如此,很難解釋為何同一古典文本能夠歷經數千年而新解層出不窮、甚或歷久彌新?!《依賴性的理性動物》1999 年初版,曾蒙作者惠贈,我很快讀到,可當時的感覺并不強烈,此次讀到譯林出版社友人惠寄的劉瑋教授翻譯的中文版新書,卻怦然心動,不時掩卷沉思,感慨不盡。這句話仿佛是對三年全球新冠疫情,尤其是癸卯春節前后的舉國疫災的預言甚或讖言:“我們人類在各種各樣的苦難面前非常脆弱……在很多情況下,我們的生存,更不用說幸福,都要依靠他人……這種為了尋求保護和維持生計對他人的依賴性在幼年和老年格外明顯。”因此,對于人類自我認識來說,我們自身的生命脆弱性和苦難史,以及我們相互之間的相互依賴,具有“核心地位”,而這一點恰恰是現代社會和現代人所最容易遺忘的。事實上,很多時候或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早已“忘記了(我們的)肉體,忘記了我們的思考乃是一種動物物種的思考”。長期以來,特別是近代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習慣于把理性或理性思考看作是特屬于人類的一種超拔于所有“非人類物種”之上的特殊能力,似乎人類只需憑此能力便可卓然獨立,無所不能。可血與淚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教訓我們,僅僅擁有理性并不能使我們生存無憂,更不能確保人類的幸福生活一勞永逸。這不,在諸如新冠的自然災難和戰爭的人為災難面前,人類——更不用說,年邁和年幼的人類個體——的生命多么脆弱!不知道該詛咒上蒼的無情,還是該感謝上蒼的及時警示!正在我斷斷續續地敲擊電腦鍵盤撰作此文時,又傳來土耳其大地震的消息,頃刻間土耳其和接鄰地震中心區域的敘利亞邊界地區的數萬人便在睡夢中逝去,一如那一棟棟脆弱不堪、紛紛坍塌的樓宇,以及隨著坍塌而起的縷縷煙塵,還有人數更多的傷者、無家可歸者、無物可食者、被掩埋在廢墟中的那些絕望者……這不是催促我寫作的悲劇性節奏么?!
諸如新冠瘟疫、地震、颶風及戰爭、恐怖主義之類的所有天災人禍,都是作為脆弱生命物類的人類所不得不時刻直面和警惕的不確定性。一俟這種不確定性與我們如影隨行、須臾不離,它便不再是外在強加的,而是直接成為我們生命和生活中無法剝離的構成部分。用哲學的術語來說,所有這類不確定性本身即是人類生命或生活的構成性樣態。它同我們自身的生物學生命體質構成一起,鑄就了人類的生命脆弱性、無能性,從而內在地決定了人類作為一個生命物類的依賴性。從表面看,人類的依賴性似乎是所有這些外部因素帶來的不確定性的結果,實質上,這種不確定性不僅僅是造成人類之依賴性的外部原因,它本身即是或者同時就是人類依賴性的結果,只不過它反映的是人類之生命脆弱的另一面而已:作為一種生物或動物,人類非但并不強大,反而是諸多生物或動物中較為弱小的。
因此,麥金泰爾號召我們回歸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的動物學”文本,“從重申人的動物性入手”。因為“我們的肉體是與動物肉體具有同一性和連續性的動物性肉體。不僅如此,人類的身份在首要的意義——即便不是唯一的意義上——是肉體的身份,因此也是動物的身份,正是通過這種身份,我們部分地定義了與他人關系的連續性”。說到人的動物性,我自己有著持久不舍的牽掛和記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北大讀研究生時,曾同朱光潛先生的弟子們一起聽恩師周輔成先生的人道主義授課,其時,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學術討論剛剛興起,而那時候北大老文科的許多研究生課程都是在老先生們的家里開講的。受導師的提醒,我們都特別注意朱光潛先生對人性人道主義的看法,在當時關于人性人道主義的百家爭鳴中,朱先生是極少數幾位堅持人性二重說的學者之一。他反復強調,無論人的社會化程度如何充分、高升,其自然本性或動物性都不可能完全被其社會化所消解。人首先是自然生物,然后才是社會(文化)生物,因而人的本性必定是二重的(自然的與社會的),而不可能只是單一的社會本質。這種觀點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我也抱有很深的認同。聽過我講課或講座的朋友們都了解,央視趙忠祥先生曾經主持的《動物世界》是我時常引用的例證。這檔實證性的電視節目用生動可視的畫面告訴觀者,絕大多數動物的生命力遠強于人類。即使是被視為豺狼虎豹之日常食物的羚羊、小鹿,出生十多分鐘便能站立,一個多小時后便能小跑,七八個小時后便能快速奔跑;高寒山區的山羊羔出生兩三個小時后便能隨父母在陡峭險峻的崇山峻嶺間上躥下跳。這樣的初生能力固然是動物們在自然狀態下受殘酷的生存法則驅使所然,但無疑成了人類生命脆弱性的鮮明鏡鑒:人類的初生能力幾乎為零,十月方能站立,繼而才能開跑,獨立生存則要更晚,更甭說如今的“啃老族”所表現的生存依賴性了。
然則奇妙也正在于此:生命脆弱的人類卻成了這個星球上萬類霜天的主宰,最起碼也是基督教所說的“看護者”,雄獅、猛虎、大象之類反而成了“瀕危動物”,人類卻成了它們的拯救者和保護者。道理何在?從亞里士多德到近代進化論尤其是社會進化論者、馬克思,再到麥金泰爾——更不用說中國古代先哲們了——都不約而同地揭示了個中緣由:因為人類能夠自覺自身的脆弱性和依賴性,并采取了社會群集的生存方式,也就是先哲們所說的能群、社會性或社會化。人類考古學的諸多發現已然證實,人類早期的群居、圍獵、集體圖騰、群體崇拜等社會經驗,促使人類逐漸發明、掌握并不斷改進其社會(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相互依賴與相互團結的社會生存和發展方式。自然的人類個體生命固然脆弱不堪,但其生命群體的相互團結和社會化行動卻使人類生命(力)變得堅強、堅韌,且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不斷增強。亞里士多德曾經發現,“依靠技藝和推理生活”,人類自身變得越來越堅強,用現代話語來說,科學技術與理性文化是人類克服自身生命脆弱性的兩種最強大的生命力裝備。事實上,人類文明和文化的進步既是人類社會創造的成果,也是其自身生存和生活得到不斷改進、增強的技術裝備。
不過,麥金泰爾沒有泛泛地討論人類依賴性的技藝與推理兩個向度,而是以個案解析的方式,通過對海豚語音能力的分析,從語言這一最基礎也最具根本意義的文化現象,來解析人類及其行動的社會依賴性。他甚至把動物性看作是人的第一本質,把由文化塑造的語言和語言使用看作是人的第二本質,且相信人的“第二本質不過是對第一本質的部分轉化”而已。盡管如此,對于作為動物的人類與非人類動物之間的分別而言,語言卻有著關鍵的意義,正是語言,使得人類的生命和生活世界獲得了超出純粹動物的關于價值(如好)的信念。麥金泰爾援用了哲學和心理學界已有的四種相關論證,包括語言分析哲學家唐納德·戴維森所提供的兩種論證、心理學家斯蒂芬·斯蒂克的語言心理學論證和語言哲學家約翰·塞爾的論證,以闡明擁有語言和使用語言能力的人類及其行動所表現的價值指向和價值信念意味。不過,麥金泰爾似乎并不因此而認為,沒有語言和語言使用能力的動物,就一定沒有任何信念和價值判斷能力,只不過我們還不能充分地了解并理解它們的這種能力罷了,更何況像海豚這樣具有較高語音(聽、說)能力的動物,或多或少擁有同我們人類相似的“信念”,比如,知好歹,明安危,等等。
也許,重要的還不只在于使用語言來表達信念(價值偏好)的能力,更在于運用這種能力來建構、維護和創建自身生活世界以克服——或者,至少是降低——自身生命脆弱性和依賴性的行動能量。麥金泰爾借用海德格爾的哲學話語,來進一步論證這一論斷。海德格爾認為,人類是能夠“構成世界的(weltbildend)”,石頭或非動物之物完全“沒有世界(weltlos)”,而動物則“缺乏世界(weltarm)”。因為動物——甭說非動物之物了——只知道行動,卻不能“領悟”其行動和世界的意義,唯有人類才具備既能行動又能領悟其行動的人類意義和行動所指的世界意義。動物確乎擁有其獨特的語言,但它們缺乏使用語言去表達、推理、構造、直至實現其行動目的(價值和價值信念)的文化能力,而這恰恰是人類的優勢所在。人類不僅可以言說,還可以通過言說而達于言道,可以進行推理、辨析或論辯、概括或結論。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人類不僅能夠發明自己的語義學,還能建構其語用學、闡釋學、語言文化學,等等。語言是人類領悟自身及其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海德格爾說:“語言是‘人’存在的家。”
然而,麥金泰爾似乎并不認同戴維斯、斯蒂克、塞爾等人的語言哲學和語言學解釋,也不接受海德格爾對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存在本體論區分。他認為,人與動物之間的語言學差別只是簡單與復雜的程度差異,而非有無之別。事實很可能是,一些諸如海豚的動物能夠擁有并運用語言,只不過其語言和語言使用方式尚不足以達到人類“實踐理性”的高度。然而,人類自身的語言能力也是從“前語言”到初級語言再到高級語言的,人在幼年時期的語言能力未必比某些非人類的幼年動物(如海豚)高出多少。在語言的初級運用階段,人類與非人類動物都能借助語言建立其與同類的聯系,但到生命成熟期,人類的語言能力則足以使其建構其自身的行動理由,確定清晰的目的意愿,從而形成其充分完備的實踐理性,成為實踐理性的推理者和行動者。人的德性或美德行為正是基于這種實踐理性所產生的主要成就之一。
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的重要成果,美德或德性無疑是人類用以克服其生命脆弱性和無能性的內在品質。麥金泰爾相信,人類的社會關系或相互依賴不僅是人類克服自身脆弱或增強自身生活能力所必需的條件,也是人類尋求其生活幸福所必需的,這是基于人類實踐理性(推理)所得出的必然結論。美德是人類建構并保持好這種相互依賴的社會關系之主體條件或必備品質,因為它們蘊涵著人類行動的基本理由,構成了人類合理行動以追求其幸福生活的基本理由或信念。“好(善)”是我們用來表達行動理由和信念最基本的價值詞,但該價值詞至少含有三層不同的價值(評價)意義:第一種是手段或工具意義上的“好”,具有行為技藝的外在價值意味;第二種是目的或目標意義上的“好”,表示行動本身的內在價值;第三種是人類社會意義上的“好”,反映出特定的社會價值/評價標準。三種意義上的“好”都表明自我對他人的依賴性,因而也都是人類個體克服自身脆弱或增強自我能力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品質。換句話說,任何人若要降低和克服自身的脆弱,都需要具備這些品質,因此,可以說美德或德性是人類必備的生存條件或生活品質,比如,正義或慷慨的正義、誠實、信任、勇敢、寬容、仁慈、互助、友誼、愛,等等。這也正是人類為何需要美德或德性的內在緣由。在此意義上,或可說,美德不是外在附加——更不是強加——給人類的,它們是人類克服自身脆弱性和無能性所必需的。作為人類的我們若要成為“獨立的實踐推理者”或實踐理性的行動者,就需要具備各種各樣的美德或德性,它們是每個人得以進入社群和人類共同體的人格通行證。
問題是,絕大多數道德哲學家在絕大多數時候都預設了人作為“獨立的實踐推理者”的身份,仿佛美德或德性是人與生俱來的。普遍的客觀事實是,美德和德性并非人類自然而然的品性,而是逐漸習得和養成的品質。每個人的一生都要經歷從無知、幼稚到成熟、衰老的完整過程,人的美德同樣也要經歷從無到有、聚少成多、由低向高的積淀和提升過程。人的童年和暮年既是人的生命最為脆弱的生命階段,也是其德性品質較弱或實現程度較低的道德階段。這讓我想起法國生命哲學家居友的觀點:嬰兒是“天然的利己主義者”,母親是“天然的利他主義者”,而風燭殘年的老人則是有著仁慈之心的美德導師,同時卻又是已無慈愛之力的生命依賴者。麥金泰爾強調這一客觀事實,但他的看法比居友的觀點要慎思周全得多。他指出,人在孩提時代遠非“獨立的實踐推理(理性)者”,小孩對大人或長輩的依賴性程度甚高,尤其依賴于父母、老師等具有哺育能力和教養身份的成年人。所以我們常見的情形是,孩子們總是想方設法地“取悅”媽媽或其他大人,因為他們需要媽媽的哺育或其他大人的撫養,而父母和老師等負有哺育和教養責任的大人們,則不僅必須擔負起哺育孩子和教養學生的“自然義務”,而且還必須且應該最懂得如何去履行這種天然使命。事實上,父母、老師及所有的大人都明白,他們曾經也是孩子,也曾經無助、依賴、取悅和吁求過大人的幫助。麥金泰爾不乏幽默地“揶揄”道:“老師的缺陷不僅因為這個任務(指教養學生的自然義務——引者注)難度很大,而且因為老師也曾經是有缺陷的學生。”
如此看來,每一個人其實都無法免于生命的依賴和美德的需求,只不過有時明顯、強烈(如孩提時代),有時隱而不見或覺察不到(如成年時代)而已。所以,麥金泰爾強調,每一個人若要認識真實的自我或人生,都必須首先自覺承認并充分意識到自身生命的依賴性和美德或德性的內在(目的)意義,即是說,作為人類,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承認并懂得,對他人或他物的依賴不可避免,“依賴性也是‘人的’一種美德”,而人對美德或德性的需求并非是為了某種其他的目的或者是為了別人(作為人生手段或外在條件),而是為了我們自己(作為人生目的和人生的內在價值)。“承認依賴性是‘人’走向獨立性的關鍵。”不過,麥金泰爾并不完全同意其美德倫理學同仁伯納德·威廉姆斯對美德之于人生的關系理解:后者將美德或德性與人格直接關聯,而麥金泰爾則更相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古希臘哲人的美德倫理學解釋,將美德或德性與人的角色或身份直接關聯,甚至直接對應起來,以確保美德或德性的獨特價值特性——作為智者的智慧,或作為武士的勇敢;作為父母的仁愛,或作為長輩或慈善者的仁慈。美德總是具體的,與美德實踐主體的身份直接相關的,不存在任何抽象的、空洞的、無關于行動者身份角色的所謂一般美德或普遍德性。職是之故,麥金泰爾贊賞威廉姆斯“考慮到了‘人的’某些類型的道德發展”,同時也不無遺憾地抱怨他“掩蓋了行動者在不同階段學習如何超越動機集合帶來的局限性的方式……”因為他沒有意識到,美德或德性問題首先是人的角色和身份問題,也總是人以其特定的角色出現或擔負的行動者的目的實現和價值達成。
在麥金泰爾看來,正是因為人的身份具有自我認知與他人認知的雙面性,且人的身份認知的雙面性能夠達于一致,因之可以避免美德或德性的特殊角色屬性所可能帶來的人類相互認知的不可通約性局限。他寫道:“正是因為對身份無標準、無依據的自我歸屬(self-ascription)與絕大多數情況下他人對我們身份有標準為依據的歸屬相一致,我們才能擁有現在的人類身份概念。而且正是因為這種判斷上的一致性,我們每個人才能夠將自己的自我歸屬視為大體可靠的。我可以被認為確實知道自己是誰、為何物,正是因為其他人可以被認為確實知道我是誰、為何物。”這其中內含的人際關系或社會關系不僅使人與人的相互依賴成為可能,而且也使得人類“實現充分的自我認識永遠是一項共同的成就”。這也意味著,人類的身份認知為作為生命群體的人類能夠相互依賴以克服個體生命的脆弱性提供了認知基礎。人類的身份認知即是一種人類自我同一性確認,它也意味著人類的依賴性具有內在、必然而永久的特征,一個人無論多么強大或富有,其“獨立推理(理性)”實踐都無法全然免除其對他人或同類的依賴。人的依賴性是終身的,從生到死,須臾無免,差別只在于程度不同而已。也正因為如此,人類總是需要美德或德性,需要各種文化的、社會經濟的、政治的等生活條件,它們共同構成了人類克服自身脆弱的依賴性條件。
然而,美德或德性本身也是脆弱的。在許多時候或情形下,美德或德性的脆弱性一如人類生命自身,或可曰,人的生命有多么脆弱,美德或德性就有多么脆弱。作為同一個生命物類,人類既有遠甚于許多非人類動物的生命脆弱性,更有遠甚于其他非人類動物的社會復雜性和內在風險。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自身的社會化如同一把雙刃劍,既是人類克服或降低自身脆弱性的防護武器,也是造成人類自傷風險、加深人類自身脆弱性的原因。更直率地說,人類是一種既可相互依賴也可相互傷害的自我反噬型動物,而且這種同類相互傷害或反噬同類的本性,并沒有因為其擺脫霍布斯意義上的“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或改善,有時候甚至更殘忍、更瘋狂。不是嗎?在我們這個星球上,還有哪一種非人類的動物能夠像人類這樣,發動兩次世界大戰和數不勝數的戰爭,一次又一次地實施同類種族清洗,制造奧斯維辛集中營那樣的人間地獄?人們已然承認,人類習得的社會組織化能力使人類獲得了超強的群體行動能力,而社會化行動方式所產生的行動后果也往往比單個行為主體或小型群體行動主體所可能造成的行動后果更為嚴重。比如,國際或族際戰爭,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等,它們所暴露的人類之生命脆弱性和生活風險度實在是太過于殘酷,以竟至罄竹難書的地步。麥金泰爾在這部著作中倒是沒有討論這類嚴厲的問題,但他顯然意識到了人類依賴性的社會維度及其復雜性,并花了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公益性的社會制度、家庭、朋友等人類外部依賴性條件。他把這些討論歸于繼脆弱性、德性需求之后的人的依賴性之“第三組論題”。只不過,麥金泰爾的討論比較窄化,并未拓展到羅爾斯所說的社會基本制度(社會基本結構),或者哈貝馬斯所說的社會公共理性和公共論壇,也未能深入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面,展開較為充分的討論,其結論總體看來也似乎比較消極。
在這一組論題上,麥金泰爾似乎仍然遵循著他一向偏愛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理路,確信“實踐推理在本質上通常是在某套確定的社會關系之中與他人一起進行的推理”:“首先是家庭關系,其次是學校和學徒關系,之后是特定社會和文化中成人所參與的一系列實踐關系。”也就是今人所習慣了解的從家庭到學校再到社會,呈現一種不斷擴展的社會關系網絡,一種從較為直接親近的“熟人關系”進至較為間接復雜的“陌生關系”之人際/群體關系圖式。在這一不斷擴展的演進過程中,人的“關系網絡”逐漸從“本地共同體”擴展到更大的“公益共同體”,“個人的好(善,personal good)”隨之獲得“公益(共同的好或善,common good)”的意義。家庭無疑是人類最可依賴的關系共同體,不僅擁有血緣血親的自然關系基礎,還有其確定熟悉的親情親緣之情感關系基礎。通過學校建構的關系網絡主要是一種人生的學習成長型關系共同體,人們借此學會如何認知他人、學習他人,并從學習中理解相互依賴的社會化意義。進至各種形式和規模的社會關系網絡,是人們獲取更加廣泛的社會依賴從而最終在社群或共同體中實現其幸福生活的標志,也是人們成為“獨立的實踐推理(理性)者”的必經之路。
麥金泰爾指出,“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的確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基于利益交易或社會合作的人我關系,它是以“理性選擇”和“遵守規則”為基礎的;另一類是基于特定情感和同情的人倫關系(親朋、同胞),它常常超越于利益算計的“理性選擇”,其所遵守的行為規則也常常超脫于一般社會倫理規法,有時甚至超脫于社會法律,比如,我們所熟悉的“親親互隱”之類的人倫親情關系。但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關系,都蘊涵著某種形式的“給予與接受”或“自為與為他”的交互性意味,也就是說,人類相互之間總是含有某種相互“虧欠”的道義承諾。正因為如此,互通有無(交易)、依賴與幫助、慷慨的正義或正義的慷慨、同情與愛等等,便成為人類所習慣、鐘情、贊賞并受到普遍而持久激勵的美德。在人類遭遇某些極端困境或處于緊急狀態的非常時刻,必定產生某些“迫切和極端的需要”,因而產生更為強勁、果斷的行動理由,凸顯出人類的脆弱性和依賴性。麥金泰爾總結道:“為了實現幸福,我們既需要使我們成為獨立的、負責任的實踐推理者的德性,也需要使我們承認依賴他人的本質及其程度的德性。要獲得和運用那些德性,只有在我們參與了給予和接受的社會關系之后才有可能,這些社會關系受到自然法的規范的支配,并且在某種意義上由自然法的規范定義。”換句話說,人類對自然法則的堅定信念首先基于人類自身生命的自然本性。
麥金泰爾的書重讀完畢,但他留下的問題依然存在,一篇不足萬字的心得體會顯然無法提供哪怕是初步的解答。作為生命物類的人類,生命的脆弱性和依賴性也許可以逐漸降低,但永遠不可能完全解除,無論我們可能創造出多么強大的技術裝備和自護條件,諸如最新的ChatGPT一類的人工智能技術或信息工程裝置,都無法完全消除我們自身的脆弱與無能,更不用說作為社會生物的我們還會且一直都在各自主張,做著相互傷害我們自己同類的事,譬如,該死的戰爭和恐怖主義行為。因此,我們對于自身的脆弱性、殘疾性和依賴性所具有的內在憂慮也不會消失。悲劇與喜劇似乎都是作為人類的我們所不得不扮演的生命演出。這也是為什么即令是偉大卓越如愛因斯坦、霍金這樣的科學家也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尊重科學真理的本義其實是尊重宇宙萬物,尊重所有的生命和生命共同體。想到這里,我決定再去看看《流浪地球》和《三體》等影視作品,讓我的閑暇思想變得再充實一些。當然我也明白,增加這份充實同時也意味著增加一份沉重,恰如人類明知無論怎樣裝備自己都無法解除自身的脆弱和依賴,卻仍然樂此不彼、孜孜以求一樣。因為我相信并確信,普遍的公平正義和仁愛美德,一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甚或萬物生命共同體,依然是值得所有人類社會尊重和追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