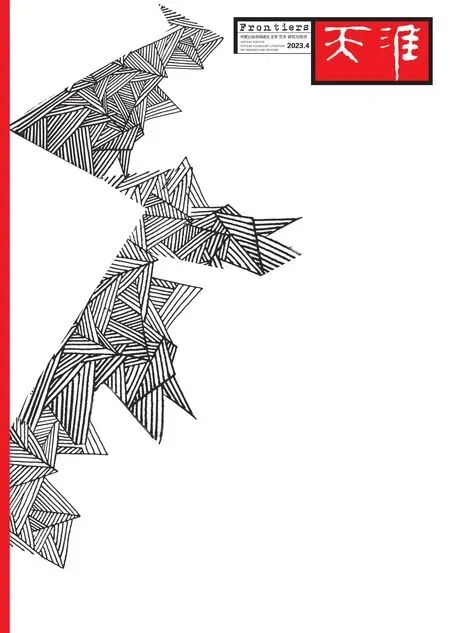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媒介/環境"
2023 年第3 期的《批判性探尋》刊物上,刊載了以“媒介/環境”為主題的一組專題文章,包衛紅、雅各布·加博里和丹尼爾·摩根為這組文章撰寫了介紹性文字:《引言:媒介/環境》。在文中,三位作者對近年來“媒介/環境”研究的基本狀況進行了描述。
處于資本主義壓力中的技術轉型所引發的生態危機,也促成了人文和社會科學中關乎環境之思考的新模式的誕生。其中的核心地帶,就是媒介研究——媒介既環繞我們,又連接我們(以及媒介形式的生產和流通對資源也有巨大需求),此一環境特性使得人們開始重新思考該學科的研究對象與方法。當技術正浸潤我們整個星球,媒介也膨脹到開始占據了我們整個生存領域。我們的生存環境——空氣、土地、海洋、天空——都正被媒介技術所浸潤,比如人造衛星、海底電纜、監控攝像頭以及無處不在的屏幕,以至于我們也開始從環境的角度來理解媒介。在此,媒介并非處于靜態的對象,而是一系列具體技術,并因此演化為有著靈活邊界的復雜生態,比如基礎設施、系統和網絡。在這一擴大了的框架中,一切媒介都可被理解為環境性的:這倒不是要老生常談地說媒介反映自然或者是自然的中介,而是要說一切自然或人造環境都構成了生命系統的中介場所;這也不是要舊事重提地說媒介結構了我們的外在和內在經驗,而是說如果媒介結構了我們的環境感覺,那么我們就不僅應該關注電影、電視、廣播等特定的媒介形式,還應該關注一切空間或時間技術,比如鐘表、門窗、輪船、建筑或其他基礎設施。
進而言之,媒介研究的這一環境轉向,又與媒介理論中更為寬泛的物質主義轉向密不可分:媒介經常被視為轉瞬即逝或非物質,但它卻又執拗地具有基礎設施特性,它依賴物質環境,甚至作為物質環境在運作,并因此產生具有物質性的后果。另一方面,與“媒介環境”(強調的是技術性媒介構造了我們的環境)或“環境性媒介”(強調的是有些媒介具有環境性,有些則沒有)的用法不同,“媒介/環境”的討論并不將這兩者的含義視為理所當然,而是試圖進一步探討二者在不同語境中的相互構造。換言之,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將“環境”從“自然”那里剝離出來,即不是將環境視為某種客觀存在,而是將其視為某種知識范疇,如此,技術哲學、政治理論和系統思維有望重新得到連接,且美學與政治、技術與權力之間的細微張力也有望得到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