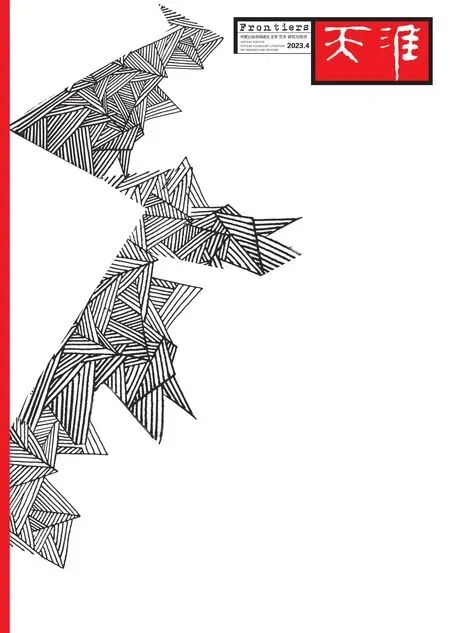賣書記
今年四月,在北京懷柔八道河嶺一處對外出租的民宿里,我問朋友華山,你見過有我這樣賣書、寄書的作者或詩人嗎?他沉吟了一陣,說,還真沒見過。那正是春夏交接的時節(jié),懷沙河兩岸山坡上的野杏花開得無邊無涯,著名特產(chǎn)油栗樹新芽青嫩。因為有一部書稿,我打算和華山合伙完成,就在他們幾個文藝青年租住的民宿里住了下來。那一陣,要簽名詩集的信息每天有上百條,我從當當、京東、淘寶訂購,然后騎電動車去渤海鎮(zhèn)的快遞點,發(fā)給全國各地的讀者賺一點差價。圖書市場也有旺季淡季的特征,比如讀書主力軍的大學生們的開學季,會有一段時間的爆銷,但什么時間有哪些人對某本書突然有了興趣需求,卻全無規(guī)律。
賣書,是我這幾年的主要生活內容,也是收入的來源之一。
2019年,在我工作的貴州景區(qū),我的工作是專職文案,每天打卡坐班,寫寫改改,心無可戀。三月的一天,我收到出版社寄來50 本《炸裂志》,將一部分送給了熟悉的朋友,剩余的無處可放。按照出版合同規(guī)定,銷售3000 冊以內,作者沒有稿酬。這也是對詩集出版投入風險化解的方法之一,畢竟,詩歌圖書市場早成了明日黃花。這50 本,是唯一的收益。我在朋友圈發(fā)了一條消息:有興趣要詩集的,包郵簽名35 元一本。當時惴惴不安,不想,當天就收到了幾十條私信,需求遠遠大于存書的數(shù)量。這是我賣簽名書的第一步。后來,在《小說選刊》編輯部工作過多年的一位編輯老師寄給我一枚印章,那是一枚精巧的篆刻小印,巴林石,寄托著他的支持和暖意。鮮紅的章蓋在扉頁上,真有點像模像樣了,讓人平添許多底氣。
2019 年,我大概寄出了1500 本《炸裂志》,它們穿越關山,到了北京、上海、新疆、西藏,最遠的到達了加拿大、澳大利亞。我記得快遞到國內最遠的一個地址是日喀則,購書者是一位醫(yī)生,那是我此生再也不能抵達的地方。2011年在山西侯馬,一位工友給我講過他在日喀則開采銅礦的故事,他說那里海拔5500 米,不敢感冒,感冒了不能及時送到拉薩就可能會引發(fā)肺炎,說有些銅礦石爆破下來,能直接煉成手鐲。這是一位可以用傳奇來形容的伙伴,他現(xiàn)在在塔吉克斯坦的苦盞。那位購書的醫(yī)生現(xiàn)在成了我的朋友,他喜歡發(fā)一些風景的圖片,它們填補了我人生目力的空白,而我喜歡問他一些有關藏藥藏醫(yī)的問題。
書的來源是最令人糾結的問題,它直接和效益利潤相關聯(lián)。在老家所在的縣城,唯一的新華書店早已名存實亡,差不多成了雜貨鋪。書的來源自然只能是網(wǎng)購平臺。我?guī)缀趺刻於家贸鲆徊糠謺r間去關注查詢圖書信息,哪怕手里已經(jīng)有了充裕的存書。有價格合適的,打折的,立即放進購物車。我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的節(jié)點商品打折都有貓膩,只有圖書的折扣是真實的,最純潔的。很多很嚴肅的圖書,有的半價,有的到了一折兩折甚至大甩賣,我不知道,這該欣喜,還是該悲哀。
寄書最煩惱的是包裹丟失,選擇靠譜的快遞商家和盯單就顯得尤為重要。在丹鳳縣城,大約有十家快遞公司在開展快遞業(yè)務,據(jù)說每天進出的包裹有三萬多件,實體店因之在風中發(fā)抖。我最早選擇的是百世快遞,百世網(wǎng)點在主城區(qū)的312 國道邊,包裹多的時候,我會早晚送兩趟。我坐在店里,看小姑娘根據(jù)收件地址和數(shù)目一件件打包,一本,兩本,三本,打成不同體積的包裹,然后貼單條。這個過程也是我最緊張的時候,生怕混亂導致差錯了。百世的致命處是運費沒得商量,后來我選擇了極兔快遞。包裹多了,難免會丟失,有一個10本裝的包裹由廣東轉運墨爾本時在轉運倉丟失了,至今沒有找到。購書者是一位在國外定居多年的讀者,他說,如果是有人收藏了它們而不是丟掉,那也值了。自去年以來,我常常騎著摩托車在家和快遞點間循環(huán)往復,成為312國道上疾馳的事物的一部分。
賣書還有最主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和購書者互動,和一個人說十句話,一天下來就有幾百句話,這些讀者的地址和身份信息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是遙遠的又是切近的,它們交織起來,就是一幅人間圖景,是地理,也是煙火,是個體,也是時代。有一位女孩子,說要把簽名詩集送給她的姑姑,她的姑姑受疾病困擾,已經(jīng)二三十年沒有出過門了。我默默在扉頁上簽了一句祝福語:愿我的人生是你的山河歲月!我想說,孩子,你的善良和愛,已經(jīng)超越了人間所有的詩,但我什么也沒有說出來。
2022年,因為疫情我回到了老家峽河。這是自1999 年之后,我在老家生活得最久的時間之一。看樣子,還將會一直生活下去,漸漸地,我已經(jīng)習慣了這里的散漫和寂靜。老家海拔1100 米,四季分明,有風有雨,我查過資料,這是人體心臟和肺最好的適應高度,如果沒有別的因素,它也將是我這一輩人的歸址。只是那些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的少年,大多我都不認識。
在老家,很多時間,依舊是賣書。我在2022 年出版的三本書,在寒冷的圖書年景里艱難生長,接受讀者的取舍。我發(fā)現(xiàn),純文學圖書市場以2014 年為界,此前為夏,此后成秋,爾后將漸漸入冬。如果稍稍留心你會看到,作家富豪榜的大咖們,吃的還是早些年的飯,很少有后期的爆款。
峽河的東面是河南盧氏,南面是商南,北面是洛南,只有向西方向與70 公里外的丹鳳縣城相連。這里的人煙與生活就處在這樣的四面不結盟地帶。前年,我聽到一個消息,說丹盧高速正在規(guī)劃,將會穿峽河而過,河兩岸的人們歡欣鼓舞,結果今年洛盧高速開工,像給了每個人一巴掌。其實,有什么好高興的呢?我見過高鐵高速橫穿卻窮得掉渣的地方,關鍵是得有產(chǎn)業(yè)和資源,以及匹配的頭腦。
小鎮(zhèn)上只有一家郵政快遞公司可以發(fā)快遞件,另外一家只負責處理外地來件。從我家到鎮(zhèn)上,路程30里。我隔三差五騎著摩托車在兩地之間往返,把快遞件發(fā)出去、收回來。我發(fā)現(xiàn),快遞件發(fā)不發(fā)得出去的地區(qū)圖,是另一張疫情晴雨表,它比公布的風險數(shù)據(jù)準確得多。有一個苦惱處在于,從家里到通村公路是兩公里泥巴路,雨天,摩托車成了泥豬,好在我有近三十年的騎行經(jīng)驗,它像我的礦山工作經(jīng)驗一樣豐富。
峽河公路與峽河有一段十公里的并行,那是我們少年時光里無數(shù)次上學放學的必經(jīng)之路。公路與河水像一個少年與另一個少年永不再相交的命運,各自發(fā)光和暗淡。她矮小、膽怯,有時走在路里邊,有時走在路外邊,路中央仿佛是一個禁區(qū)。她穿一件花襯衫,白底藍花,從初一穿到初三,又穿到另一個世界。有時候,我突然恍惚,車座上的書是寄給她的,那個地址準確又不詳。書里是一個人半生的風雨冰雪,它想讓她看見。而收到的每一個包裹,仿佛是一個人的回復。
峽河今天早晨落霜了,又一年的冬天真的來到了。
若干年后,當我回過頭來打量這一段賣書時光,它無疑是生命里無法抹去的重要章節(jié),這也包括你和他,以及所有曾經(jīng)穿越關山相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