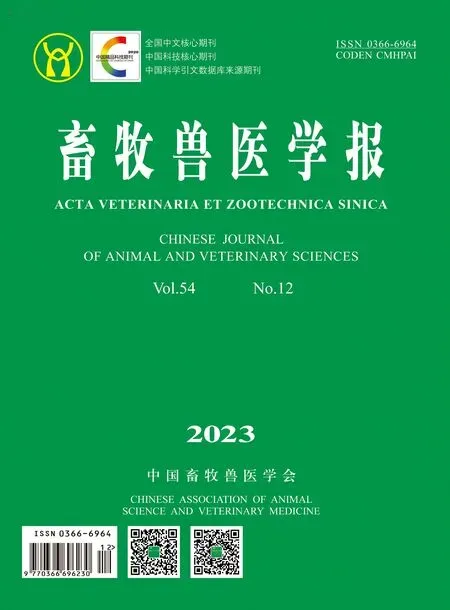新疆地區牛冠狀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學調查
王夢嬌,蔣 倩,馬學軍,夏瑞陽,郭雪萍,孫 磊,鐘 旗,馬雪連,2*,姚 剛*
(1.新疆農業大學動物醫學學院,烏魯木齊 830052;2.新疆農業大學畜牧學博士后流動站,烏魯木齊 830052;3.新疆昌吉市二六工鎮農業(畜牧業)發展服務中心,昌吉 831100;4.新疆畜牧科學院獸醫研究所,烏魯木齊 830099)
養牛業是新疆畜牧業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近年來發展迅速,引進品種、數量日益增加,2021年全疆的牛存欄量達528.13萬頭,牛肉產量達43.9萬噸。犢牛腹瀉是養牛業中的常見疾病,嚴重影響犢牛生長發育,腹瀉嚴重時可使動物發生血便并導致死亡[1],對養牛業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BCoV和牛諾如病毒(bovine norovirus,BNoV)是引起犢牛腹瀉的主要病原[2-3]。而其中由BCoV導致的腹瀉呈全世界流行趨勢,BCoV主要通過糞口傳播和呼吸道傳播[4],檢測時可從糞便和鼻液中分離到病毒粒子[5],病情轉歸與犢牛的日齡、免疫狀態及病毒毒力有關[6]。BCoV感染新生犢牛可引起犢牛腹瀉,也可以導致成年牛冬痢,或引起呼吸道疾病[7-9]。自然狀態下可感染羊駝[10]、駱駝[11]、馴鹿[12]和羊[13]等反芻動物,該病發病率較高,感染率與牛的年齡相關[14]。
BCoV屬于冠狀病毒科冠狀病毒屬,是一種單股正鏈有囊膜的RNA病毒。其基因組長度約32 kb。結構上,BCoV粒子呈球狀,外圍呈日冕狀,大小為 62~210 nm,是目前已知最大的RNA病毒[15]。包括10個開放閱讀框(open reading frames,ORFs),兩端是5′和3′非翻譯區域。ORF1編碼多聚蛋白(polyprotein,PPla),通過核糖體轉移為PPlab,然后被蛋白酶水解成多個非結構蛋白(nonstructural protein,NSP)。ORF3、ORF4、ORF8、ORF9和ORF10分別編碼該病毒粒子的5種主要結構蛋白:N(核蛋白)、S(纖突蛋白)、M(膜蛋白)、E(小膜蛋白)、HE(血凝素酯蛋白),其余的ORFs編碼額外的NSPs[16]。不同國家和地區的BCoV毒株存在區域差異。例如,中國的BCoV毒株與新西蘭、阿根廷、荷蘭、愛爾蘭、丹麥、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毒株不同[17]。這些毒株的致病力、傳播力以及對疫苗和治療的敏感性均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宿主種群的差異、環境條件以及其他病毒或細菌混合感染導致的。
隨著新疆規模化養牛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國內外引進品種以及數量的增加,BCoV感染病例的報道越來越多,但對新疆規模化養牛場的BCoV感染現狀、流行特點和主要流行毒株的生物學特性尚缺乏較全面的調查研究。本研究對新疆南、北疆養牛業主產區BCoV感染的流行情況進行調查監測,探明其流行規律,分析其演化過程中的分子流行病學特性,為后續針對新疆BCoV毒株的精準防控提供數據支撐。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MolPure?Plasmid Mini Kit質粒提取試劑盒和MolPure?Gel Extraction Kit瓊脂糖凝膠回收試劑盒購自翌圣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TRIzol購自Invitrogen;Hifair?III 1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gDNA digester plus)、2×Taq PCR Mix、DL2000 DNA Marker和瓊脂糖購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pEASY-T1載體購自Promega公司。
1.2 流行病學調查
本研究于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份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塔城地區、伊犁州、喀什地區、博樂市、呼圖壁縣的12個規模化養牛場犢牛的BCoV感染情況進行持續監測。根據BCoV感染后犢牛的典型癥狀,采集1~3月齡具有腹瀉臨床癥狀的犢牛糞便樣品共652份,其中肉用犢牛424份,奶用犢牛228份。對樣品進行BCoV檢測,分析不同地區、不同季節和不同品種犢牛BCoV的流行規律。
1.3 病料采集與處理
使用棉簽采集犢牛直腸糞便樣品,放到凍存管里存入液氮,糞便樣品以1∶3的稀釋比用PBS溶液稀釋,渦旋充分混勻后保存于-80 ℃冰箱。使用時,解凍后再放入-20 ℃冰箱反復凍融3次,以破壞組織釋放病毒粒子。取處理后的糞便樣品,4 ℃ 8 000×g離心后取上清,用TRIzol進行RNA提取,利用Hifair?III 1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進行反轉錄,獲得的cDNA -20 ℃凍存。
1.4 RT-PCR鑒定
根據GenBank中公開發表的BCoV病毒基因序列,利用Premier 5.0軟件設計特異性引物,由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以實驗室前期構建的質粒作為陽性對照,以樣品cDNA作為模板,全程置于冰盒上進行操作,將提取出的樣品 RNA 模板加入無酶無菌離心管,配置體系為15 μL,同時每管加入3 μL 5×gDNA Digester Mix,RNase-free H2O補至15 μL并輕輕吹打混勻,混合液42 ℃條件下孵育2 min。逆轉錄反應20 μL體系配制,反應條件為 25 ℃ 5 min,58 ℃ 50 min,85 ℃ 5 min使用特異性引物進行PCR擴增,PCR擴增體系(15 μL):2×Taq PCR Master Mix 7.5 μL,dd H2O 4.5 μL,上、下游引物(10 μmol·L-1)各0.5 μL,cDNA 2.0 μL。反應條件為:預變性95 ℃ 4 min;95 ℃ 30 s,55 ℃ 60 s,72 ℃ 45 s,35個循環;延伸10 min。擴增結束后進行1%瓊脂糖凝膠電泳,于凝膠成像系統觀察結果。PCR反應涉及的相關引物見表1。

表1 引物合成Table 1 Primer synthesis
1.5 BCoV結構蛋白引物設計及擴增
以MW711 287.1為參考序列,設計BCoV 結構蛋白N、S、M、E、HE的擴增引物(表2),引物由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通過RT-PCR方法對病料提取的cDNA進行擴增,PCR擴增體系(15 μL):2×Taq PCR Master Mix 7.5 μL,dd H2O 4.5 μL,上、下游引物(10 μmol·L-1)各0.5 μL,cDNA 2.0 μL。反應條件為:預變性95 ℃ 4 min;95 ℃ 30 s,55 ℃ 60 s,72 ℃ 45 s,35個循環;延伸5 min。擴增后,膠回收目的片段并構建于pEASY-T1載體,送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測序,獲得目的基因序列。

表2 引物序列及反應條件Table 2 Primer sequences and reaction conditions
2 結 果
2.1 BCoV陽性檢測結果
RT-PCR檢測結果顯示(圖1),在774 bp處可以看到明顯特異的片段(第1、2、3、5和9泳道),電泳結果經測序與預期片段序列符合。對2020—2022年新疆養牛主產區的652份糞便樣品采用RT-PCR方法檢出陽性156份,BCoV陽性總檢出率為23.93%。

M. D2000 DNA Marker;P. 陽性對照;N. 陰性對照;1~10. 樣品M. D2000 DNA Marker; P. Positive control; N. Negative control; 1-10. Sample圖1 BCoV N基因RT-PCR 擴增結果Fig.1 BCoV N gene RT-PCR amplificationthe results
2.2 BCoV流行情況
2.2.1 BCoV感染地區差異 對六個地區12個規模化養牛場犢牛BCoV感染調查結果如圖2所示,喀什地區陽性率和陽性數量均最高,陽性率約35%。而烏魯木齊、伊犁和博樂地區均未檢出陽性。BCoV在南、北疆流行情況見表3,可見BCoV在全疆均有分布,南、北疆地區的感染率呈現較大差異,南疆地區發病率較高。

圖2 BCoV感染的地區差異Fig.2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BCoV infection

表3 南、北疆腹瀉犢牛BCoV檢測結果Table 3 BCoV incidence of diarrhea calves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Xinjiang
2.2.2 BCoV感染的四季差異 BCoV在各個季節的流行情況詳見表4,可知在新疆地區,BCoV的流行受季節因素影響較大,集中于冬季流行,冬季檢出率高達50.85%,遠高于總檢出率23.93%,這也符合此前其它地區研究對BCoV感染特征的認識[18-20]。

表4 不同季節腹瀉犢牛BCoV檢測結果Table 4 BCoV incidence of diarrhea calves in 4 seasons of Xinjiang
2.2.3 BCoV感染的品種間差異 BCoV在奶、肉用犢牛中的流行情況詳見表5,可見BCoV在奶、肉用犢牛均可傳播,但兩者的感染率呈現較大差異,與奶用犢牛相比,肉用犢牛的發病率較高。

表5 新疆奶、肉用犢牛BCoV的檢測結果Table 5 BCoV incidence of diarrhea calves in dairy and beef calves of Xinjiang
2.3 BCoV基因序列分析
將本文分離到的BCoV病毒,暫定名為:BCoV/China/XJ-CJ/2022,采用RT-PCR方法進行擴增,獲得BCoV的N、S、M、E、HE基因序列并送往生物公司測序,將測序獲得的BCoV主要結構蛋白S、HE、E、M和N的序列進行同源性、進化樹和基因重組分析、N蛋白抗原表位預測。
2.3.1 BCoV同源性分析 為了比對鑒定的BCoV/China/XJ-CJ/2022與現存其它毒株的異同,本研究于GenBank上挑選14條國內外各地區BCoV參考毒株進行比對,根據BCoV的五個結構蛋白S、HE、E、M和N進一步做同源性分析,結果可見(表6):BCoV/China/XJ-CJ/2022與國內參考株MW711 287.1_SWUN/NMG-D10/2020的核苷酸相似性最高,為97.4%,主要在M蛋白區域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相似性最高,分別為99.4%和100.0%。與加拿大參考株AF220 295.1_Quebec的核苷酸相似性最低,為95.8%,主要是E蛋白區域的核苷酸相似度最低,為92.9%。

表6 分離株與代表性毒株片段核苷酸和氨基酸的相似性分析Table 6 Homology analysis of gene fragments of isolated and representative strains
2.3.2 BCoV的S、N、M、E和HE基因的進化樹和基因重組分析 S、N、M、E和HE基因的進化分析結果表明(圖3),除與MW711 287.1_SWUN/NMG-D10/2020的S基因比對部分基因缺失外,同源性平均數值高于95%。本研究的分離株S基因與2018年毒株MN982 199.1進化關系最近,N基因與2018年毒株MK095 169.1BCOV-China/SWUN/LN4/2018進化關系最近,M基因與2017年毒株MK095 148.1 China/SWUN/SC1/2017進化關系最近,HE基因與2017年毒株MK095 136.1 BCOV-China/SWUN/SC2/2017進化關系最近。使用RDP 4和Simplot軟件分析Bo/XJ-KS/02/CHN可能存在的重組事件,結果顯示未出現基因重組現象。
3 討 論
犢牛腹瀉包括非感染性腹瀉和感染性腹瀉,其中非感染性腹瀉是受到飼養管理不當、環境氣候惡劣、應激反應等非感染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犢牛自身免疫力降低,增加了犢牛腹瀉的概率,但發病率和危害性低于感染性腹瀉,制定并實施合理的生物安全措施可以有效防控非感染性腹瀉[3]。感染性腹瀉根據病因可分為病毒性腹瀉、細菌性腹瀉、寄生蟲性腹瀉,BCoV常與其它病毒混合感染,并引發細菌感染,導致臨床診斷的癥狀表現復雜,臨床上難以凈化[20-21],其中引起腹瀉的病毒包括BCoV、BNoV、牛病毒性腹瀉病毒 (bovine viral diarrhea virus, BVDV)、牛輪狀病毒(bovine rotavirus, BRV)、牛紐布病毒(bovine nebovirus,BNeV),其中BCoV的感染率最高[2],可感染新生犢牛引起犢牛腹瀉,也可以導致成年牛冬痢,或引起呼吸道疾病,嚴重時可導致犢牛死亡。在國外,一項2019—2021年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表明,波蘭奶牛群的BCoV感染率約為30%[22],2022年巴西的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患病牛群中BCoV的感染率高達56%[23],土耳其BCoV感染率為29.92%[24]。在國內,BCoV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其實際感染率較高,其中四川、西藏、青海、云南省份BCoV檢出率均高于60%。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一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腹瀉牛中BCoV陽性率為15.45%[25]。可見BCoV在世界范圍內廣泛的流行。本研究于2020—2022年期間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塔城地區、伊犁州、喀什地區、博樂市、呼圖壁縣的12個規模化養牛場共采集樣品652份,檢出BCoV陽性156份,檢出率為23.93%,其中喀什地區陽性率達到35%。
造成BCoV感染的原因除了與飼養管理不當、環境氣候惡劣有關外,也與養殖場犢牛自身免疫力不足等因素有關。本團隊前期研究結果顯示,南疆牧場在防疫制度、人員物流管控、飼養管理等生物安全控制方面存在隱患,養殖場人員防控意識有限,缺乏有效針對BCoV的疫苗接種,這些因素成為BCoV在新疆南疆地區廣泛、反復傳播的有利因素[3]。本研究發現,新疆BCoV毒株的傳播具有冠狀病毒傳播的典型特征,即冬春傳播,氣溫對病毒傳播影響較大,冬季為該疾病的高發季節,發病率可達到50.85%,冬季應著重防范BCoV。從地區分布上,南疆氣溫相對于北疆較高,降水量少,日照時間充足,氣候較為干旱,換季時期晝夜溫差可達到20 ℃,BCoV發病率高達36.09%,應加強區域管理,減少跨區域引種。另外,本研究還發現,新疆BCoV毒株更易感染肉用犢牛,發病率達到30.9%,奶用犢牛發病率僅為10.96%,也有相關的研究報道顯示,肉牛初乳乳糖含量及pH較高,可能會增加新生犢牛腹瀉率[26-27]。奶、肉用犢牛患病率的差異可能與初乳攝入量有關。初乳中含有免球蛋白、生長因子、細胞因子、非特異性抗菌因子和營養物質等,不當的初乳管理可能會影響初乳中的免疫成分及營養物質等,進而影響新生犢牛的免疫狀態和生長發育情況[28]。據報道,肉牛的平均初乳產量為2.7 L(0.6~5.6 L),奶牛的平均初乳產量為6.7 L(3.7~9.5 L),受產量影響,肉用犢牛對初乳奶量相對攝入較少,免疫球蛋白的攝入也相應減少,免疫球蛋白不足會造成犢牛被動免疫轉移失敗,導致犢牛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以及后期生產力的下降[29-30],所以更應加強肉用犢牛的初乳補飼。
本研究從遺傳演化分析的結果分析,進化樹的主要分支是以地區、國家為分界各自形成譜系,說明目前BCoV沒有通過物流或動物遷徙等因素形成全球傳播,病毒的進化和傳播主要集中在各自地理分界內,這與各國貿易對生物安全的嚴格管控有關,且與BCoV的自然宿主多為缺乏全球遷徙能力的偶蹄目動物有關[31]。BCoV的傳播存在地域性和季節性的特征,因此對BCoV的防控也應具有地域性和季節性[32-33]。
4 結 論
犢牛腹瀉BCoV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表明,新疆養牛業主產區廣泛存在BCoV感染。南疆地區BCoV感染率較高,肉用犢牛BCoV感染率高于奶用犢牛。同時與季節呈現較強相關性,以冬季感染為主。遺傳演化分析結果表明,BCoV感染以本土毒株為主,中國毒株形成獨立譜系,傳染存在地域性特征,未見重組事件。本研究為BCoV的精準防控和后續的疫苗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