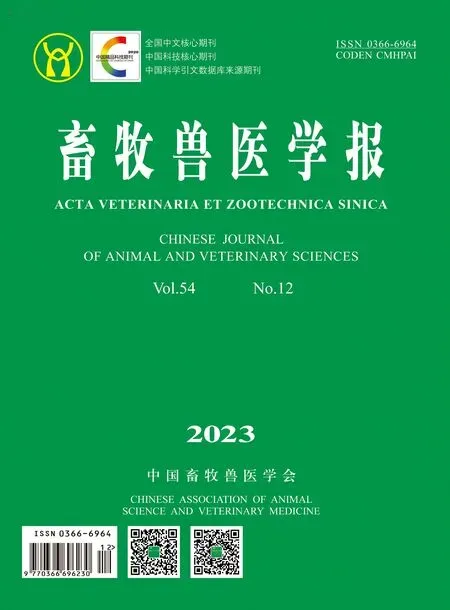副雞禽桿菌毒力因子研究進展
支 巖,梅 晨,劉珍邑,烏云格日樂,王宏俊*,胡 格*
(1.北京農學院動物科學技術學院,北京 102206;2.北京市農林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北京 100097;3.扎魯特旗畜牧業良種繁育中心,通遼 029100)
副雞禽桿菌(Avibacteriumparagallinarum, Apg)為革蘭陰性菌,無鞭毛,其毒力菌株常常存在莢膜結構。Apg是一種兼性厭氧菌,目前常用的Page分型方法[1]可將其分為A、B、C三個血清型。研究表明,這三個血清型菌株均有致病性。Apg是引起雞傳染性鼻炎(infectious coryza, IC)的病原菌。IC最明顯的癥狀是鼻道和鼻竇等上呼吸道有漿液性或黏液性分泌物流出、面部水腫和結膜炎,導致蛋雞的產蛋率下降和生長停滯[2]。該病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分布。最新的調查顯示,在國內17個省市地區的240個規模化養殖場中,Apg陽性場有119個,場陽性率高達49.6%[3-4]。國際上,在印度,該病是僅次于沙門菌感染的第二大細菌性疾病[5],在南非和美國的部分地區肉雞中也廣泛感染,引起嚴重的肉質下降,增加淘汰率,給養雞業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6]。
深入研究病原菌的毒力因子和致病機理是建立科學防控策略的基礎和前提[7]。近年來,對Apg毒力因子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這對于挖掘疫苗候選抗原和研究弱毒疫苗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將從該病原菌的結構成分和功能性分泌物等方面進行系統綜述,以便深入研究Apg的致病機制和防控策略。
1 細菌被膜及組分
1.1 莢膜和莢膜多糖
莢膜是許多細菌的關鍵毒力因子,其位于細菌細胞壁表面。莢膜表現為一層邊界不明顯,易被洗脫的松散黏液物質,具有介導免疫反應和抵抗物理應激的作用[8]。細菌莢膜多糖(capsule polysacharides, CPS)是莢膜上的多糖結構,可以保護細菌免受吞噬作用和補體介導的殺傷,直接影響細菌的毒力[9]。一些細菌能夠在感染的不同階段調節莢膜表達,這對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至關重要。CPS具有阻止細菌與宿主受體結合、干擾細菌定植的作用,因此被認為是一種優質的疫苗候選抗原[10]。
Wu等[11]研究發現,Apg中的莢膜生物合成位點有兩種基因型(I和II),但與血清型無關。基因型I和II的莢膜生物合成基因座分別由6個和5個基因組成。基因型I編碼的蛋白質與多殺性巴氏桿菌莢膜A型和F型的蛋白質最相似,而基因型II編碼的蛋白質與多殺性假單胞菌莢膜D型和大腸桿菌K5的蛋白質最相似。這些蛋白質分別含有合成軟骨素和肝素的特異性基因。同時,提取并純化Apg莢膜多糖,并以Apg血凝素(hemagglutinin, HA)為目標抗原,結合后進行免疫保護,發現可以顯著提高血清抗體水平[12]。以上結果表明HA和CPS作為兩種不同性質的細菌外膜成分,均具有一定的免疫原性,可以作為候選抗原,具有研發重組疫苗的應用潛力。
Sawata等[13]發現一種含有透明質酸的莢膜,它與細菌定植有關,也是引起IC及其相關病變的主要因素。該莢膜能抵抗正常雞血清的殺菌活性,從而起到保護細菌的作用。具有莢膜結構的Apg分離株往往擁有更強的毒力[14]。
為了進一步驗證莢膜對Apg毒力的影響,Tu等[15]通過TargeTronH基因敲除系統構建了hctA基因沉默的Apg莢膜突變株,發現該突變株的血凝活性與野生型菌株相比有明顯提升。此外,突變株表現出對雞胚成纖維細胞DF-1更強的黏附性和在非生物表面上形成生物膜的能力。毒力測定表明,莢膜突變株的毒性低于野生型菌株,敲除莢膜在增加了血凝和黏附活性的同時降低了毒力。
1.2 脂多糖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是革蘭陰性菌細胞壁外壁的組成成分,與致病菌的黏附、侵染和宿主細胞間的擴散有關。脂多糖是一種“內毒素”,細菌在生長過程中不會主動分泌,只有在細菌死亡時才會從破碎的菌體中被釋放出來。現有研究表明,Apg的毒力強弱與脂多糖有關,從血清型A、C菌株培養上清液中分離的脂多糖能引起心包積液,導致動物發生中毒癥狀,產蛋率下降[16]。
1.3 磷酸膽堿
磷酸膽堿(phosphorylcholine, ChoP)是在許多黏膜病原體表面發現的重要毒力因子,其主要在LPS上表達,具有增強細菌在黏膜上定植的作用[17]。Chiang等[18]研究發現在Apg臺灣分離株TW07的全基因組測序中,含有與流感嗜血桿菌(Haemophilusinfluenzae)的lic1ABCD操縱子[19]和多殺巴斯德菌(Pasteurellamultocida)的pcgDABC操縱子[20]具有高度序列相似性的四基因操縱子,編碼膽堿激酶、膽堿通透酶、磷酸膽堿胞苷轉移酶和磷酸膽堿轉移酶;兩個操縱子都參與細菌LPS上ChoP的代謝和合成。在雞抗菌肽的殺菌試驗中,ChoP的高表達增加了Apg的存活率。這些結果表明,ChoP與LPS的生物合成有關,并具有一定保護效果,是影響Apg毒力強弱的重要因子。
1.4 外膜蛋白
外膜蛋白(outer membrane protein, OMPs)是革蘭陰性菌外膜的主要結構成分,同時也是最先與宿主細胞相互作用的部位,在維持細菌自身結構、營養運輸、致病性和免疫保護性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OMPs還具有較強的免疫原性且能誘導保護性免疫反應[21]。HMTp210是Apg外膜蛋白上最主要的抗原之一,它包含一種在致病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外膜血凝素[22],具有血凝、細胞黏附和影響生物膜形成活性的功能[23]。其全長約6.1 ku,分為“區域1”“區域2”和“區域3”三個區域。區域2的序列(大約位于HMTp210的編碼核苷酸3300-4800處)已被確定為高變區[24],可以作為抗原起到有效保護效果[25],并且與Apg的血清型分型有關[1],也是亞單位疫苗研發的重要靶點。全細菌滅活苗因為含有大量內毒素等非保護性抗原成分,毒副作用比較強,而亞單位疫苗克服了這一缺點,在降低生產成本的同時減輕了毒副作用,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保護效力。早期進行過以外膜蛋白HagA作為Apg亞單位疫苗的抗原的相關研究,但由于免疫保護效果較差,因此未用于疫苗開發[26]。隨著對于Apg外膜蛋白的深入研究,發現利用HMTp210區域2構建的重組融合肽可以起到和全菌滅活疫苗相同的保護效果,并且無明顯毒副作用,為新型IC疫苗的制備提供了思路[25]。
2 細菌分泌物
2.1 外膜囊泡
致病菌毒力因子的釋放有賴于專屬的分泌系統,許多革蘭陰性菌通過分泌系統將毒力因子從細菌的胞內分泌到宿主細胞或環境中。外膜囊泡(outer membrane vesicles, OMVs)是一種在革蘭陰性菌中普遍存在的包含生物學活性物質的球狀囊泡狀結構[27]。目前已知的大多數革蘭陰性菌如銅綠假單胞菌、幽門螺桿菌等分泌的OMVs可攜帶多種生物活性物質[28-29],不僅是致病性病原的毒力因子[30],而且具有很好的免疫原性,是極具潛力的新型疫苗抗原[31]。早在2005年Ramón等[32]就發現Apg的外膜囊泡中含有RTX蛋白、血凝素抗原等毒力因子。Mei等[33]通過質譜分析發現Apg的OMVs蛋白組分包含膜蛋白、ATP依賴的RNA解旋酶、磷酸甘油酸激酶等。將該OMVs與雞巨噬細胞共培養,細胞中炎癥相關基因表達水平顯著升高。將提取的A型Apg的OMVs制成疫苗進行動物免疫攻毒試驗,發現接種疫苗的雞血清中IgG水平顯著提高,說明OMVs刺激了雞的體液免疫。但是免疫后的試驗雞僅對A型Apg菌株的攻毒保護率高達80%,對于B型和C型菌株的保護率不超過30%[33],這表明OMVs攜帶的抗原成分具有特異性,并且沒有血清型之間的交叉保護作用。
Xu等[34]對Apg分離株P4chr1及其OMVs進行比較基因組分析,發現OMVs具有攜帶和轉移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s resistance genes, ARGs)的能力。測序和數據分析表明,分離株P4chr1的基因組大小約為2.77 Mb,包含一個大小為25 kb,涵蓋11種ARGs的耐藥基因島。該OMVs囊括的基因組大小約為2.69 Mb,覆蓋了97%的基因組長度和P4chr1株幾乎所有基因序列。經過純化和DNase處理后,來自耐藥分離株的OMVs與抗生素敏感的參考株在含有氯霉素、紅霉素、四環素或鏈霉素的培養基平板上共同培養,發現均有菌落生長,并可在這些菌落中檢測到對應的ARG,表明OMVs具有傳遞攜帶Apg耐藥基因的特性。
2.2 金屬蛋白酶
細菌蛋白酶,特別是由病原體產生的蛋白酶,會對其宿主產生毒性作用[35],并與毒力和致病性有關。金屬蛋白酶(metalloproteinases, MPs)是一類活性中心含有金屬離子的蛋白酶[36],可以有效地水解蛋白質和多肽[37]。金屬蛋白酶最初以不活躍的酶原形式產生,由胞內和胞外蛋白(如纖溶酶)激活。Rivero-García等[38]就發現Apg在體內生長時,黏膜表面可以分泌一種金屬蛋白酶,能降解雞免疫球蛋白IgA和IgG,盡管不能做到完全降解,但這種蛋白酶活性可能是一種毒力因子,促進細菌定植并逃避免疫防御或獲得營養,在Apg引起致病過程中發揮作用。
2.3 RTX毒素
RTX毒素(repeats in the structural toxin)是由多種革蘭陰性細菌產生的一種外毒素,可對人和動物致病,也是評估細菌毒力的重要標志物[39]。Mena-Rojas等[40]在Apg中純化出一種相對分子質量為110 ku的蛋白,并通過試驗證明該蛋白可能屬于RTX蛋白家族,被認為是不同于革蘭陰性病原體的重要毒力因子,該蛋白家族還包含溶血毒素、金屬蛋白酶和脂肪酶等[41]。以前的報道也提到嗜血桿菌中有潛在的RTX毒素基因[42],這些基因在Apg中更可能以細胞毒素的形式出現。2014年,Küng和Frey等[43]發現一種名為avxA的二價絲氨酸蛋白酶-RTX孔蛋白毒素(bivalent serine-protease-RTX-porin toxin),并構建得到Apg突變株JF4965(包含特定的重組基因avxA-RTX、avxC和hlyBD)。該毒素編碼RTX操縱子結構,具有激活基因avxC、結構絲氨酸蛋白酶-RTX毒素基因avxA和適當的I型分泌系統基因avxBD。AvxA屬于復合RTX毒素,在結構毒素中具有兩個主要結構域,這在RTX毒素中相當罕見。在AvxA中,N端結構域代表絲氨酸蛋白酶,C端結構域代表RTX細胞毒素,這兩個結構域相互切割。因此,AvxA被稱為多功能自動處理RTX毒素(MARTX),屬于具有多種活性的RTX毒素[44]。AvxA-RTX對禽巨噬細胞HD11具有細胞毒性,但對牛巨噬細胞BoMac無細胞毒性。來自血清A型Apg菌株的重組AvxA-RTX單特異性兔抗血清中的IgG能夠中和Apg血清型A、B和C培養物上清液的細胞毒活性[43],表明AvxA是Apg的主要細胞毒力因子。
3 鐵離子獲取和利用
鐵是大多數細菌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參與細胞內酶的合成,影響細胞代謝過程。細菌的獲鐵系統在其感染宿主及致病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細菌獲鐵系統相關的蛋白也是重要的毒力因子。然而,宿主中游離鐵的濃度不足以支持細菌的生長[45]。為了實現有效的鐵穩態,細菌已經進化出復雜的鐵獲取系統,以從周圍環境(鐵載體、血細胞或宿主分子結合蛋白)中獲取鐵,以確保充足的供應[46],從而發揮其毒力。
3.1 鐵載體轉運系統
能夠獲取游離無機鐵的鐵載體轉運系統由細菌外膜上的鐵載體和TonB依賴性轉鐵蛋白受體(TonB-dependent transferrin receptors, TBDR)組成[47]。三價鐵載體通過外膜受體運輸時需要耗能,而這種能量是由TonB能量系統提供的。因此,在鐵限制條件下,細菌會增加一些與TonB能量系統相關的蛋白表達,以促進鐵載體穿過外膜進入胞質。TonB依賴性轉運蛋白(TonB-dependent transporters, TBDT)是一種膜蛋白,能夠高親和地結合鐵、維生素B12、鐵載體和碳水化合物,其中一些成分還可能作為毒力因子發揮作用[48]。
TonB ExbB-ExbD蛋白存在于許多革蘭陰性細菌中,其中大多數存在于大腸桿菌系統中。Huo等[49]研究發現在鐵刺激條件下,Apg中發生了TonB系統轉運蛋白ExbD和ExbB共轉錄現象,很可能還存在TonB ExbB-ExbD蛋白質復合物。由于將鐵從周質轉運到細胞質需要細胞質膜上的ABC轉運蛋白(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BC transporter)參與,因此轉運蛋白ATP結合蛋白的表達也被上調,以更好地促進鐵進入細胞質并提高細菌對鐵的利用率。以上試驗結果表明,ExbD和ExbB通過鐵載體轉運系統發揮作用,影響細菌的鐵獲取和毒性。
3.2 血紅素利用系統
血紅素利用系統在細菌的鐵獲取和致病性中起到重要作用[50]。通常,血紅素攝取系統由TonB依賴性外膜受體蛋白、周質結合蛋白和內膜相關ABC轉運蛋白組成[45]。對病原菌而言,游離鐵的可用性受到嚴格限制,導致鐵載體獲取不足[51]。因此,為了從血紅素中獲取鐵,細菌利用了復雜的血紅素獲取機制[46]。革蘭陰性菌還可以通過外部TBDR將血紅素轉運至周質,然后周質血紅素結合蛋白將其轉運至細胞質[52]。在細胞質中,血紅素可以被血紅素降解酶降解,從而獲得鐵離子[51]。
HutZ是一種儲存血紅素的蛋白,它在血紅素利用、生物膜形成和某些細菌的致病性方面起著重要作用[50]。研究發現,HutX是一種細胞質血紅素轉運蛋白,有促進血紅素向HutZ的轉移的作用,通過特定的蛋白質相互作用實現[53]。在鐵限制條件下,HutZ和HutX蛋白會優先表達[52],這表明血紅素攝取可能是獲得鐵的重要途徑之一。HutZ也可以被視為在細胞質中釋放鐵的血紅素降解酶,而HutX則是HutZ的細胞質血紅素轉運蛋白,有助于Apg獲得鐵和利用血紅素。
4 內源性質粒
質粒是一種獨立于細菌基因組之外的攜帶遺傳信息并具有自主復制能力的環狀DNA分子,可以攜帶耐藥基因或其他功能元件,是細菌產生耐藥性以及額外功能的重要途徑,同時也是影響細菌毒力的一個重要因素[54]。
質粒可能還攜帶一些特殊基因,會對菌株的生長特性或者毒力產生影響。最早在2003年,Terry等[55]在Apg分離株HP250中首次檢測到一種大小為6.29 kb的質粒p250。該質粒上存在一個細菌素編碼位點,該基因與流感嗜血桿菌素的細菌素(haemocin)編碼基因高度同源,但因其基因座中的基因無法擴增,所以蛋白功能尚不清楚。
直到2007年,Hsu等[56]從18株中國臺灣地區Apg分離株中檢測鑒定了兩種質粒:pYMH5和pA14。pYMH5是一種大小為5 047 bp的耐藥性相關質粒,編碼功能性鏈霉素、磺胺、卡那霉素和新霉素的抗性基因,并顯示出與廣泛宿主范圍質粒pLS88具有顯著的同源性,這是Apg中報道的第一個多重抗生素抗性質粒。pA14是另一種質粒,可以通過克隆獲得兩種表達載體:pYMH11和pYMH12。測序發現它們分別編碼MglA蛋白和外切核糖核酸酶(RNaseⅡ)。已有研究表明,在流產布魯氏菌(Brucellaabortus)和土拉弗朗西斯菌(Francisellatularensis)中也中也存在MglA蛋白,并且對其毒力產生重要影響。MglA通過誘導巨噬細胞產生細胞因子,導致細胞存活能力下降[57],并且影響土拉弗朗西斯菌中噬菌體與溶酶體的結合[58]。其他Apg分離株的全基因組測序分析也發現了RNase II基因序列的存在[34]。編碼RNase II的主要蛋白VacB在先前的試驗中已被證實是福氏志賀菌(Shigellaflexneri)和腸侵襲性大腸桿菌(Escherichiacoli)中表達毒力所必需的基因,缺乏RNase II會導致細胞無法正常生長[59-60]。2018年,在我國的Apg分離株中也重復發現了這三種質粒[61],表明這些質粒的存在并不是偶然事件。2023年,劉洋洋等[62]誘導構建了質粒p250和p A14缺失株APG-HuΔ,攻毒試驗表明,質粒缺失株的毒力顯著下降。綜上所述,這些結果表明質粒是Apg的重要毒力因子,需要進一步研究其作用機制。
5 其他毒力因子
隨著對Apg的研究愈發深入,人們發現了更多的毒力因子,例如Tn10轉座子、菌毛蛋白和CDT毒素等。然而,這些毒力因子的作用機制尚不十分明確。
5.1 Tn10轉座子
Tn10是一種大小為9 147 bp的復合轉座子,攜帶四環素抗性基因(tetR/A/C/D)[63]。Tn10被廣泛應用于誘變研究,以研究突變對適應度的影響,并用于構建標記的mini-Tn10質粒庫,以削弱病原體的毒力,可用于減毒活疫苗的制備[64]。2013年,Requena等[65]在秘魯Apg分離株中發現一個與轉座子Tn10相似性高達99%的6 488 nt片段,其中包含四個四環素抗性基因。此外,基因組中還發現了IgA蛋白酶,表明其可能具有水解雞的IgA樣免疫球蛋白的能力。這種蛋白酶可以切割宿主分泌的IgA免疫球蛋白,從而繞過宿主黏膜防御機制,增強感染呼吸道的能力[66]。
5.2 菌毛蛋白
菌毛是許多病原菌表面的蛋白質細絲,參與細菌對宿主細胞的黏附和侵襲,在微生物的定植中起重要作用[67]。2016年Liu等[68]通過對Apg TW07的測序發現了一個flfA蛋白,它是F17樣菌毛基因簇的一部分。研究發現,在攻毒試驗中,fifA蛋白可以誘導機體產生特異性抗體。同時,發現flfA基因缺失株TW07-DflA的毒力低于其親本野生型菌株TW07,表明flfA基因也可能是Apg的一個重要毒力因子。
5.3 CDT毒素
細胞致死性膨脹毒素(cytolethal distending toxin, CDT)是由革蘭陰性致病菌產生的基因毒素。完整的CDT是由CdtA、Cdt B和Cdt C三個亞基組成的異源三聚體,其主要功能是破壞真核細胞的染色體DNA,導致細胞分裂周期阻滯,進而引起細胞凋亡,這有助于細菌有效突破宿主的防御并實現定植感染[69]。2013年Chen等[70]通過對Apg分離株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分析,發現了一段全長約為2.1 kb的CdtABC基因。PCR結果顯示,不同的Apg分離株中均能擴增CdtABC基因,并且其序列高度保守。采用HeLa細胞和DF-1細胞進行細胞毒性測定試驗,結果表明Apg中的CDT毒素可以完全殺死DF-1細胞,并引起HeLa細胞出現細胞質膨脹和細胞核增大等中毒病變。免疫試驗結果顯示,使用CdtABC基因制備的多克隆抗體可以有效中和CDT毒素的活性,為Apg疫苗的研發提供了新的方向。
6 小 結
Apg作為IC的病原菌,近年來在國內外廣泛傳播,持續受到關注。最近有學者報道在發病的鵝和鵪鶉中分離到Apg,表明Apg的宿主動物不再單一,有可能感染其他禽類,造成更嚴重的經濟損失。
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對Apg毒力因子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斷有新的毒力因子被發現,其中部分毒力因子間具有協同作用。然而,至今還沒有完全闡明與Apg毒力分泌系統調控、信號轉導以及涉及的轉錄調控因子、群體感應系統、外膜囊泡攜帶ARG轉移等上游機制有關的信息。鑒于細菌毒力系統的重要性,了解各毒力因子在致病過程中的地位和協同作用至關重要。通過結合生物信息學分析,可以綜合研究Apg的毒力相關基因表達、蛋白功能和生物學特性。同時還可以運用蛋白-蛋白/蛋白-核酸互作技術,深入探究Apg毒力因子的作用機制。希望通過這些研究,解決不同血清型Apg疫苗無法提供有效交叉保護的難題,為IC的防控和新型疫苗的開發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