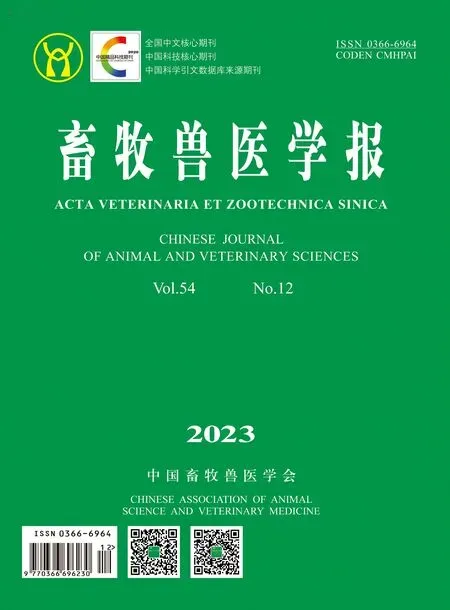海南省奶源和養殖環境主要腸桿菌科細菌的分布及基因分型
郝若晨,唐敏嘉,劉光亮,張 艷,Muhammad Shoaib,尚若鋒,曹宗喜*,蒲萬霞*
(1.海南省農業科學院畜牧獸醫研究所 海南省熱帶動物繁育與疫病研究重點實驗室,海口 571100;2.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農業農村部獸用藥物創制重點實驗室/甘肅省新獸藥工程重點實驗室,蘭州 730050;3.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獸醫研究所,蘭州 730046)
近十年來乳制品的生產和消費大幅增加,并存在強勁增長的勢頭,同時乳制品污染成為全世界非常關注的問題。乳制品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礦物質,可以促進微生物的生長[1]。200多種已知的病原體可以通過食物傳播,其中有幾種腸桿菌科細菌屬于對人類和動物會造成嚴重影響的重要食源性病原體,如產生毒素的沙門菌(Salmonella)、志賀菌(Shigella)和大腸埃希菌(Escherichiacoli,E.coli)[2]。食品中的致病性E.coli污染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這些細菌會造成嚴重的腸道疾病[3]。
細菌的致病力與其攜帶的毒力基因種類與數量高度相關。毒力基因種類繁多,包括黏附素、鐵攝取系統、脂多糖、多糖莢膜和侵襲素等,這些毒力基因通常位于致病島(pathogenicity islands,PAIs)、質粒和其它移動遺傳元件(mobile genetic elements,MGEs)上[4]。高致病性毒力島(high-pathogenicity island,HPI)是一種重要的毒力基因,其核心功能區由fyuA和irp2組成,因此fyuA和irp2是檢測HPI的標志性基因[5]。ibeB是重要的致病因子[6],與免疫逃避相關的毒力基因主要包括莢膜、補體抗性蛋白和外膜蛋白酶等,ompA、ompT、traT、cvaC和iss分別編碼外膜蛋白、外膜蛋白酶、補體抗體蛋白、定殖因子以及抗吞噬作用因子[7]。鐵是許多細菌生長所必需的,攝鐵系統是細菌重要的生存機制,iroN編碼鐵載體受體,iucD編碼NADPH依賴性賴氨酸N(6′)-單加氧酶,該酶與鐵載體生物合成蛋白相關[7]。
質粒是能夠在細胞之間進行自我傳遞的自主DNA分子,攜帶的基因對宿主的生長或生存是不必要的[8]。幾乎所有的細菌都有質粒,它們可以垂直傳播到后代,也可以水平傳播。質粒通過轉座子或插入序列等MGEs獲得新基因,并能夠在廣泛的宿主中復制,使它們成為腸桿菌科細菌的耐藥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AMR)和致病性傳播的完美載體[9]。六種主要的質粒家族已被證明可以介導腸道細菌物種之間的抗菌素耐藥性傳播,即Inc F、Inc A/C、Inc L/M、Inc N、Inc I和Inc HI2[10]。由于毒力因子可增加細菌存活率并可能影響抗生素耐藥性表達[11],因此,對不同細菌宿主中毒力基因和質粒特征的鑒定是了解細菌致病力和耐藥性的基礎。
生物被膜是由細菌在生長過程中為適應生存環境而黏附于物體或活性組織表面并包被其自身而產生的細胞外多糖基質形成的,是細菌的特殊存在形式。它的形成一方面促進細菌逃避機體免疫系統的作用,阻礙細胞吞噬或減少吞噬作用與氧活性降低后的應激反應[12];另一方面可以阻止或延緩藥物的滲透,生物被膜內細菌的生理學特點影響了細菌對藥物的敏感性[13-14]。生物被膜結構可以破壞人類的防御系統,為微生物提供庇護所,導致免疫逃避和細菌耐藥性[15]。E.coli、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pneumoniae,K.pneumoniae)、Salmonella、銅綠假單胞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炭疽桿菌等大多數細菌能產生生物被膜[16]。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表示80%的慢性感染與生物被膜形成相關[17],因此檢測細菌生物被膜形成能力是了解其致病力和耐藥性的另一個主要的生物學特性。
了解特定地理區域內流行菌株的遺傳關系對于疾病的預防是至關重要的。腸桿菌科細菌基因間重復一致序列-聚合酶鏈式反應分型(enterobacterial repetitive intergenic consensus-PCR, ERIC-PCR)技術是一種用于細菌流行病學分析和基因分型的分子方法,基于基因間重復共有序列進行PCR擴增,由條帶數目及大小進行分型,可以評估菌株的親緣關系和遺傳多樣性。我國要將海南省建設為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試驗區,食品安全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海南省奶牛養殖業欠發達,目前很少有研究聚焦于牛奶生產環境中被細菌污染相關的風險因素。
因此本研究從海南省兩個奶牛場采集鮮乳、工人手臂、擠奶設備、牛舍護欄、糞便和商品奶樣本,共52份。對其進行了樣本中腸桿菌科細菌的分離與鑒定、腸桿菌科細菌質粒型的檢測、腸桿菌科細菌生物被膜表型的檢測以及腸桿菌科細菌基因間重復序列分子分型,旨在探明海南省腸桿菌科細菌在生乳、商品奶及奶牛養殖環境的分布及分型情況,分析菌株的遺傳關系。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PCR和全自動紫外凝膠成像儀(美國Applied Biosystems公司);移液器、高速離心機和紫外分光光度計(德國Eppendorf公司);電泳槽和高壓電泳儀(北京六一儀器廠);多功能酶標儀(美國Gene公司);瓊脂糖購自西班牙Biowest公司;剛果紅培養基(Congo Red Agar,CRA)購自上海中秦化學試劑有限公司;Premix TaqTM、10×Taq Buffer(Mg2+)和Taq酶(5 U·μL-1)均購自寶生物工程(大連)有限公司(大連TaKaRa公司)。
1.2 樣品采集
樣品于2021年采集自海南省兩個奶牛養殖場,其中A牛場養殖規模為200頭,采集健康奶牛鮮乳10份、工人手臂拭子4份、擠奶設備拭子4份、糞便5份和商品奶8份;B牛場養殖規模為100頭,采集健康奶牛鮮乳9份、工人手臂拭子3份、牛舍護欄拭子7份和糞便2份。
奶樣采集時,先將乳房擦拭消毒,丟棄前3把奶,分別采集每頭牛4個乳區的奶3~4 mL,混合后為一份樣品;采集工人手臂、牛舍護欄以及擠奶設備源樣品時,先將滅菌棉簽蘸取適量生理鹽水,然后用棉簽分別在工人手臂、牛舍護欄以及擠奶設備處涂抹,放入有培養基的采樣管中;糞樣采用五點采樣法收集。
1.3 細菌分離鑒定和去重
稱取糞樣100 g,加入400 mL滅菌BHI肉湯,混勻,吸取5 mL上清液接種于100 mL滅菌BHI液體培養基中,37 ℃ 180 r·min-1增菌15 h。吸取1 mL奶樣,接種至9 mL BHI肉湯中進行增菌。無菌條件下蘸取增菌液,在MAC平皿上進行單劃線接種,37 ℃靜置培養18 h,挑取形態不一致的單菌落接種至MAC上培養,直至菌落形態單一。采用水煮法提取細菌基因組DNA,以純化菌株的DNA為模板,進行ERIC-PCR擴增,ERIC-PCR反應體系為25 μL:10×Taq Buffer(Mg2+)2.5 μL、dNTP 2 μL、Taq酶1 μL、ERIC引物各0.5 μL(10 μmol·L-1),模板DNA 1.5 μL,ddH2O 17 μL。反應條件:94 ℃預變性5 min,94 ℃變性45 s,52 ℃退火1 min,72 ℃延伸5 min,35個循環;72 ℃最后延伸10 min。產物在2.0%瓊脂糖凝膠上進行電泳并拍照,將分離自同一樣品中條帶數目、大小完全一致的菌株視為重復,僅保留一株。以純化非重復菌株DNA為模板,擴增其16S rDNA序列,PCR反應體系(25 μL):Premix TaqTM12.5 μL,上下游引物各1 μL(10 μmol·L-1),模板1 μL,加ddH2O至25 μL。反應條件:94 ℃預變性5 min;94 ℃變性30 s,退火30 s,72 ℃下1 kb·min-1延伸,30個循環;72 ℃延伸5 min。擴增產物在1.0%瓊脂糖凝膠上進行電泳并拍照記錄結果。將符合預期大小的PCR產物送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進行測序,在NCBI中將測序結果進行BLAST比對分析,按相似性≥99%判定,確定分離菌株的種屬地位。經分離、純化與鑒定的非重復性腸桿菌科細菌科菌株,于-70 ℃超低溫冰箱保存菌種。
1.4 腸桿菌科細菌的毒力基因檢測和質粒分型
根據參考文獻合成了11種毒力基因的引物,引物由北京擎科生物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擴增片段大小及退火溫度見表 1。對49株腸桿菌科細菌菌株進行ibeB、iucD、iroN、fyuA、irp2、ompA、ompT、traT、iss、cvaC和tsh毒力基因的檢測。與鐵轉運相關的fyuA和irp2基因采用雙重PCR檢測,反應體系為20 μL:fyuA和irp2基因的上下游引物各0.5 μL(10 μmol·L-1),Premix TaqTM10 μL,模板1 μL,再補充去離子水至20 μL。其余毒力基因的檢測均使用單反應PCR方法,反應體系與反應條件與“1.3 ”中16S rDNA擴增體系一致。以實驗室保存的攜帶相應特異性基因的菌株作為陽性對照,滅菌超純水為空白對照。在1%的瓊脂糖凝膠上電泳,然后使用全自動凝膠成像系統拍照并記錄結果。

表1 毒力基因引物序列Table 1 Primer sequences of virulence genes
采用Carattoli等[27]開發的基于腸桿菌科主要質粒不相容性組的復制子分型(PCR-based replicon typing,PBRT),分析所分離腸桿菌科菌株的質粒攜帶情況。根據參考文獻合成了識別parA-parB、iterons和RNAI 等目標位點的HI1、HI2、I1、X、L/M、N、FIA、FIB、W、Y、P、FIC、A/C、T、FII、F、K和B/O等18種常見的復制子引物[27],通過PCR方法對上述菌株攜帶的質粒型進行檢測。該方法包括5組多重PCR和三個單重PCR反應,其引物序列、擴增片段大小及退火溫度見表2。以細菌總DNA為模板,使用可識別Inc復制子的18種引物進行基于PCR的復制子分型。

表2 質粒分型引物信息Table 2 Plasmid typing primers information
質粒分型基因檢測的反應體系:上下游引物各0.4 μL(10 μmol·L-1),DNA模板1 μL,Premix TaqTM10 μL,ddH2O 8.2 μL,總體積為20 μL。質粒分型PCR的set 1~5和7~8反應條件:預變性94 ℃ 5 min;94 ℃變性30 s,60 ℃退火30 s,72 ℃延伸1 min,35個循環;最后72 ℃延伸7 min。質粒分型PCR set 6的反應條件:預熱變性94 ℃ 5 min;94 ℃變性30 s,52 ℃ 退火30 s,72 ℃延伸1 min,35個循環;最后72 ℃延伸7 min。
1.5 菌株生物被膜定性檢測
復蘇菌株,將復蘇后的菌株劃線接種于CRA上,37 ℃培養22~24 h,觀察菌落在培養基上的顏色和菌落形態。如果菌落在CRA上呈干燥、黑色、光亮結晶和周邊培養基褪色,指示為生物被膜陽性菌株;菌落在CRA上呈濕潤、紅色和周邊培養基不褪色,指示為生物被膜陰性菌株。
1.6 腸桿菌科分離株的ERIC-PCR分子分型
以所分離菌株的基因組DNA做模板,利用ERIC引物對其進行PCR擴增,擴增產物在2%的瓊脂糖凝膠上進行電泳,使用DL5000 DNA Marker,電泳后用紫外凝膠成像系統觀察并拍照記錄,并通過BioNumerics軟件進行遺傳進化關系分析。
2 結 果
2.1 細菌分離鑒定
52份樣本中有31份樣本中能獲得可培養的菌落,總分離率為59.6%(31/52),共分離77株菌。分別為A牛場分離率64.5%(20/31),分離得到57株菌;B牛場分離率52.4%(11/21),分離得到20株菌。糞樣的分離率最高,為100.0%(7/7);其次為鮮乳樣,分離率為78.9%(15/19),其中A牛場為90.0%(9/10),B牛場為66.7%(6/9);工人手臂源樣本的分離率為57.1%(4/7),其中A牛場為75.0%(3/4),B牛場為33.3%(1/3);擠奶設備或牛舍護欄源樣本的分離率為36.4%(4/11),其中A牛場為50.0%(2/4),B牛場為28.6%(2/7);商品奶樣本的分離率為12.5%(1/8)(表3)。整體而言,A牛場的分離率較B牛場高,需要提到的一點是,B牛場無商品奶。

表3 不同來源樣本細菌分離率Table 3 Bacterial isolation rate of sample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將疑似菌株的16S rRNA序列與NCBI數據庫進行BLAST比對,鑒定結果如表4所示。腸桿菌科為49株,其它菌株24株,NCBI數據庫中未鑒定的有4株。在鑒定的所有物種中,E.coli的檢出率最高,為41.6%(32/77);其次為K.pneumoniae,檢出率為16.9%(13/77)。陰溝腸桿菌(Enterobactercloacae,E.cloacae)的檢出率為3.9%(3/77);產氣腸桿菌(Enterobacteraerogenes,E.aerogenes)檢出率為1.3%(1/77)。

表4 不同來源樣本細菌分離鑒定情況Table 4 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bacteri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表5 毒力基因在不同樣品來源分離株中的分布Table 5 Distribution of virulence genes in isolates from different sample sources
2.2 腸桿菌科細菌的毒力基因和質粒分型
毒力基因結果顯示,ompA的檢出率最高,為93.9%。A牛場鮮乳源菌株中ompA的檢出率最高,為95.5%(21/22),未檢出iroN和iss基因。A牛場工人手臂源菌株中,ompA的檢出率最高,為100.0%(7/7),未檢出iucD、fyuA、irp2、ompT、traT、iss和cvaC基因。A牛場擠奶設備或牛舍護欄源菌株中只檢出了ibeB和ompA基因。A牛場糞源菌株中,ompA的檢出率最高,為100%(15/15)。B牛場中工人手臂源菌株中只檢出了ompA基因,糞源菌株中檢出了ibeB、ompA和ompT基因。
質粒型檢測結果顯示(表6),K質粒的陽性率最高,為44.9%(22/49);其次為W(40.8%,20/49)、FIB(36.7%,18/49)、Y(18.4%,9/49)、FrepB(14.3%,7/49)、FIA(6.1%,3/49)和HI2(2.0%,1/49)質粒。本研究中未檢測到HI1、I1、L/M、N、X、P、FIC、T、A/C、FIIS和B/O質粒。2.0%的菌株攜帶6個質粒,4.1%的菌株攜帶5個質粒,12.2%的菌株攜帶4個質粒,20.4%的菌株攜帶3個質粒,6.1%的菌株攜帶2個質粒,8.2%的菌株攜帶1個質粒,46.9%的菌株未攜帶所檢測的質粒。攜帶質粒的菌株中,96.2%(25/26)為E.coli,3.8%(1/26)為E.aerogenes。

表6 分離菌株攜帶質粒型情況Table 6 plasmid type of isolated strains
2.3 菌株生物被膜定性
49株腸桿菌科細菌中有37株(75.5%,37/49)在CRA上有不同程度的黑色菌落出現,指示具有生物被膜形成能力,見圖 1a。其中E.coli20株(62.5%,20/32),K.pneumoniae13株(100.0%,13/13),E.cloacae3株(100.0%,3/3),E.aerogenes1株(100.0%,1/1)。其余12株(24.5%,12/49)在CRA上為紅色菌落,沒有生物被膜形成能力,見圖 1b,均為E.coli。

a. 剛果紅染色陽性;b. .剛果紅染色陰性A. Congo red-positive;b. Congo red-negative圖1 剛果紅瓊脂上培養的菌株外觀Fig.1 The appearance of strains cultured on Congo red agar
2.4 腸桿菌科分離株的ERIC-PCR分子分型
以條件位置差異容許度為1.5%,優化值為1.5%對ERIC-PCR指紋圖譜進行分析,依據UPGMA方式進行聚類,以70%為標準劃分[28],最終49株腸桿菌科菌株被劃分為Ⅰ-ⅩⅦ共17型,Ⅵ型為優勢型,共20株,其次為ⅩⅤ型(6株)、Ⅷ(3株)、Ⅸ(3株)、Ⅳ(2株)、Ⅹ(2株)、ⅩⅠ(2株)和ⅩⅢ(2株),剩余的9株菌分布在其它9種型中,聚類關系見圖 2。Ⅵ型全部為E.coli,其中19株分離自A牛場(包括鮮乳、工人手臂源和糞源),1株分離自B牛場糞源,說明A牛場菌株的聚類關系較近。ⅩⅤ型全部為K.pneumoniae,均分離自A牛場(包括鮮乳和工人手臂源)。

圖2 腸桿菌科細菌ERIC-PCR基因分型的聚類樹圖Fig.2 Cluster tree of ERIC-PCR genotype of Enterobacteriaceae
3 討 論
一些致病性腸桿菌科細菌不僅給畜牧業發展造成危害,還威脅人類健康,而牛是致病性腸桿菌科細菌引起人類感染(牛肉、乳制品、牛糞便污染)的重要來源[29]。因此,了解牛養殖環境腸桿菌科細菌流行情況對動物和人類預防疾病和維護健康至關重要,海南省的養殖業欠發達,對養殖環境和商品奶中腸桿菌科細菌的研究較少,故本研究以養殖環境和商品奶的腸桿菌科細菌為研究對象。本研究中鮮乳樣細菌的分離率較高,為78.9%,其中A牛場更是高達90.0%。分離率較高的原因可能是樣本來源牛場中奶牛飼養密度和活動量較大,接觸污染源多,未及時清洗或未徹底清洗乳頭;除此之外,海南省氣候濕潤,氣溫高,也容易滋生細菌。本研究中工人手臂源樣本和擠奶設備或牛舍護欄源細菌的分離率分別為57.1%和36.4%,可能是因為擠奶工人或擠奶過程中消毒不當,這會導致牛奶或其衍生物被污染,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因為攝入受病原體污染的牛奶或其衍生物可能會導致嚴重的人類感染,提示應對食品行業的工人提出安全和耐藥性的建議和持續教育,以防止食品污染和耐藥菌株的出現。對飼養環境勤消毒,勤通風與勤打掃,以及及時正確的清潔手臂和擠奶設備等。商品奶的分離率為12.5%,主要的原因是運輸過程中樣本意外暴露,但未及時處理導致樣本被污染。
自然界中E.coli分布廣泛,故本研究中,E.coli檢出率最高,為41.6%。該菌可以通過糞便和廢水等途徑排放到環境中,由食物鏈進入人體,但大多數E.coli都是動物腸道中的正常寄居菌,只有很小一部分才會在一定條件下引起疾病。K.pneumoniae是一種革蘭陰性菌,也是機會性和環境性病原體,廣泛存在于動物黏膜、水和土壤等環境中,不僅導致奶牛乳腺炎,還會引起醫院醫療相關感染[30]。在本研究中,A牛場的鮮乳、工人手臂源和糞樣中均能分離得到K.pneumoniae。隨著消費鮮乳的趨勢,A牛場的鮮乳和工人手臂上分離到該菌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因為攜帶該菌的鮮乳被人類食用后可能會引起嚴重的感染,而手臂上存在該菌也有可能造成攜帶者的感染或者進一步的傳播。
為進一步確定分離株的致病潛力,又對其毒力基因進行了檢測。有研究顯示,只要同時含有papC、iucD、irp2、tsh、vat、aatA、iss和cva8個基因中4個以上即為強毒株[28],本研究中來自A牛場的糞源E.coli菌株HNAF202140同時攜帶了所檢測的11個毒力基因(ibeB、iucD、iroN、fyuA、irp2、ompA、ompT、traT、iss、cvaC、tsh),說明該菌株存在著較大的致病風險。A和B牛場毒力基因檢測率最高的是ompA。研究報道ompA是不同毒力基因中的流行率最高,最常見的基因,它在生物膜形成、維持膜完整性和抗生素轉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31],這會加強細菌的抗生素耐藥性,不僅如此,該基因中的L3位點可能與K.pneumoniae的致病性有關[32],所以ompA在本研究中的高檢出率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目前,已有一些關于基因敲除技術的研究表明,iucD和E.coli的致病力存在著某種聯系[33]。賈青輝等[34]報道雞源致病性E.coli中iucD的檢出率為95.2%,而在本研究中iucD的檢出率為4.1%,明顯低于上述報道,說明海南省奶源和養殖環境中致病性菌株較少,向環境、人或其它動物傳播致病風險的可能性較低。徐政平[35]報道的APEC中的iss的檢出率為69.8%;在Manita等[36]的研究中,APEC分離株中ompT和iroN的檢出率為100%;De Carli等[37]報道的APEC菌株中ompT和iroN的檢出率分別為100%和98.8%。本研究中iss、ompT和iroN的檢出率分別為2.0%、8.2%和4.1%,遠遠低于上述報道。Asai等[38]發現這5種毒力基因(iutA、hlyF、iss、iroN和ompT)與APEC的高致病力相關,而本研究中的E.coli并未確定為APEC,這可能是iss、ompT和iroN的檢出率較低的原因。總體來看本研究中毒力基因總體檢出率相較于其它報道低,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樣品來源于養殖環境和鮮乳樣。
病原菌對抗菌素的耐藥情況可以從調查菌株中質粒攜帶情況入手。PBRT具有較高的特異性和靈敏性,但該方法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只能檢測18種常見的質粒,對于一些新型的或變異的質粒可能無法識別。本研究中質粒類型多樣,其中Inc K、Inc W和Inc FIB為優勢質粒,這些優勢質粒也經常在動物源E.coli中發現[39-40]。有研究顯示攜帶AMR基因的質粒主要在典型的Inc組質粒上[30]。其中Inc K質粒主要與blaCMY-2和blaCTX-M-14抗性基因在歐洲傳播有關,尤其是西班牙和英國。而CMY型和CTX-M型β-內酰胺酶是E.coli中最常見的超廣譜β-內酰胺酶(the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ESBLs)家族,但是產生 CMY 和 CTX-M 的腸桿菌科的直接人畜共患食源性傳播并不常見[41]。表明本研究中奶牛場的E.coli危害人類健康的可能不大。Inc W質粒被認為是最小的接合質粒,1980年代,在許多細菌中發現了Inc W質粒[42]。研究顯示,Inc W質粒攜帶氯霉素、四環素、磺胺類、慶大霉素和甲氧芐啶等耐藥基因(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genes,ARGs),也有研究顯示攜帶blaKPC-2和blaVIM-1抗性基因[43-44],這兩個抗性基因都與碳青霉烯類藥物耐藥性有關[43]。Inc F組質粒是大小在45~200 kb的低拷貝接合質粒,Inc F質粒上最常見的耐藥基因有編碼ESBLs、碳青霉烯酶、氨基糖苷類修飾酶的基因[45]。這些質粒不僅會對細菌的生存做出貢獻,其介導的耐藥機制也是抗生素耐藥性增加的原因。
CRA是生物被膜定性常用的方法之一。本研究生物被膜定性檢測結果顯示49株腸桿菌科細菌中有37株指示具有生物被膜形成的能力,在E.coli、K.pneumoniae、E.cloacae、E.aerogenes中都能發現生物被膜形成的能力,而且E.coli中也有無生物被膜形成能力的菌株,表示生物被膜形成能力似乎不是菌種依賴性的。Staji等[46]發現,ERIC-PCR檢測結果中同一來源分離菌株基因存在差異,不同來源也可有較近的親緣關系。鄭曉風等[47]用ERIC-PCR方法發現菌株間存在交叉傳播。本研究ERIC-PCR檢測結果顯示49株腸桿菌科細菌被分為17型,參照我國華東地區的103株臨床乳房炎E.coli被分為10型[48],可見本研究中腸桿菌科細菌廣泛的DNA多樣性。DNA多樣性的原因可能是頻繁使用抗生素導致的選擇性壓力引起的基因修飾。Ⅵ型菌株來源于鮮乳、糞便和工人手臂源,XⅤ型來源于鮮乳和工人手臂,說明糞便和工人手臂是鮮乳污染或者乳腺感染的主要來源,會進一步導致乳腺炎的發生。
4 結 論
本研究樣品的總分離率為59.6%(31/52),共分離出77株菌,不同來源的樣品均有分布,糞便檢出率最高,為100.0%;其次為鮮乳,檢出率78.9%。經鑒定疑似菌株覆蓋了5個科11個種,主要為腸桿菌科。所分離腸桿菌科細菌毒力基因的檢測中ompA的檢出率最高,為93.9%,其余毒力基因均有不同程度的檢出;質粒類型多樣,攜帶3個質粒型的菌株較多,攜帶質粒的菌株中,96.2%為E.coli,其中75.5%指示有生物被膜形成能力;分子分型中Ⅵ型為優勢型,全部為E.coli;其次是ⅩⅤ型,全部為K.pneumoniae。腸桿菌科細菌在奶源環境中廣泛存在、生物特性多樣,推測具有一定的致病力和耐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