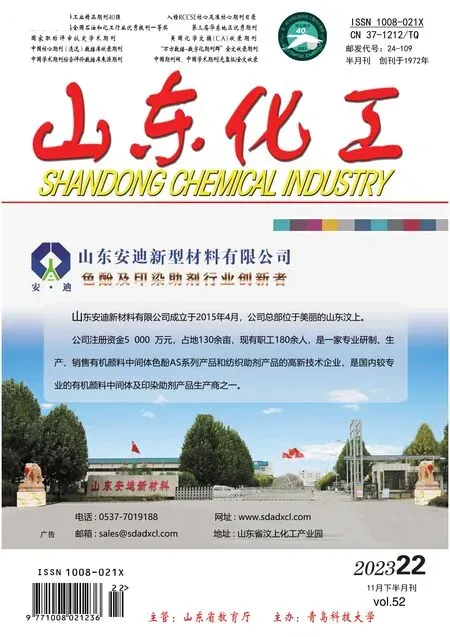沒食子酸乙酯的生物活性研究進展
武濤,張絢,劉慧,劉菲,郝婷婷,韓婷婷,楊素珍
(福瑞達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山東 濟南 250101)
重點綜述了近年來關于沒食子酸乙酯生物活性的相關研究。沒食子酸乙酯(Ethyl gallate,EG),屬沒食子酸烷基酯的一種,化學名為3,4,5-三羥基苯甲酸乙酯,白色結晶粉末,溶點149~153 ℃,可溶于水。EG主要存在于鉤錐葉、余甘子果實、小果薔薇根、五倍子根部和芍藥等中草藥植物,具有廣泛的生物活性,能夠有效清除自由基,抑制炎性細胞激活,調節脂質代謝和保護神經系統等,涉及眾多與疾病防治相關的研究領域,圖1為EG的藥理作用。

圖1 EG的藥理作用
1 抗氧化作用
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作為調節生物體生命活動的信號分子,在生命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ROS種類繁多,主要包括過氧化氫(H2O2)、次氯酸、羥基自由基(·OH)、過氧亞硝酸鹽(ONOO-)和超氧陰離子自由基(·O2-)。ROS水平的變化與許多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1]。EG的抗氧化作用使其成為抗氧化失衡相關疾病的有效化合物。
內源性低水平的H2O2可作為信號轉導的重要調節因子,激活多種信號通路[2]。然而,過量的細胞H2O2會觸發毒性反應過程[3]。在血管組織中,當H2O2擴散到鄰近的血管平滑肌時,可引起局部肥大現象,嚴重者可誘發血管炎癥,最終導致慢性血管疾病。
EG的抗氧化性能使其成為一種良好的H2O2清除劑。有研究表明,在膿毒癥犬中注射EG后,血清中H2O2濃度明顯降低,低血壓癥狀緩解。EG阻止了過氧化氫酶被過氧化氫類似物過氧乙酸轉化,從而保護過氧化氫酶活性。這證明,EG通過清除過量的H2O2,抑制過氧化氫酶(Catalase,CAT)變性,從而發揮抗氧化作用,調節血壓穩定,抑制血管功能障礙[4]。
除H2O2外,羥自由基還會損傷體內蛋白質、DNA等生物大分子,導致癌癥、動脈粥樣硬化和神經變性的患病率增加。EG加入Fenton反應體系(Fe3+/H2O2/抗壞血酸)后,可與DNA形成插入式復合物,保護DNA大分子免受氧化應激損傷,并通過提供氫離子中和羥自由基,發揮自由基清除機制,保護DNA和蛋白質免受氧化損傷[5]。體內的過氧化產物,如脂質過氧化物,會降低抗凝因子的活性,導致血液處于高凝狀態形成血栓,而EG可降低羥自由基對抗凝血酶Ⅲ活性的氧化損傷,發揮抗氧化作用抑制血栓形成[6]。
EG在體外能夠清除超氧陰離子自由基、羥基自由基和過氧化氫,表現出抗氧化作用[7]。Sawai等學者[8]通過核磁共振方法,分析了EG清除DPPH自由基的分子機制,即作為供電子化合物,在清除DPPH自由基的同時自身被氧化為沒食子酸乙酯自由基(氧化形式),該產物具有非常穩定的結構,難從自由基清除后產生的氧化形式還原,從而可以表現與α-生育酚(抗氧化劑)相當的抗氧化能力。
氧化應激在神經退行性疾病和腫瘤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EG的抗氧化特性使其成為一種良好的抗氧化應激藥物,可通過調節氧化應激反應的平衡來緩解相關疾病的發展。
Ren等學者[9]利用H2O2刺激PC-12細胞建立典型的氧化應激神經損傷細胞模型,發現不同劑量EG(10、20、40 μmol/L)干預PC12細胞后可增強H2O2誘導的細胞活力,阻斷核碎裂和DNA凝集,顯著改善細胞狀態。通過流式細胞術、qRT-PCR、免疫熒光和western blot等檢測方法證明其減少PC12過度釋放ROS、抑制半胱天冬酶(caspase )9/3活化、破壞DNA修復酶(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PARP)和維持線粒體膜電位,調控凋亡相關Bax/Bcl-2比值和細胞色素C(Cytochrome C)釋放,減緩了氧化應激。此外,EG還會激活細胞防御機制的主要調節因子核紅細胞2相關因子2(Nrf2)的核移位,增強其下游靶點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γ-glutamylcysteine synthetase,γ-GCS)和NAD(P)H:醌氧化還原酶1[NAD(P)H:quinone oxidoreductase 1,NQO1]的表達和上調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水平,從而在內源性途徑中發揮抗氧化作用。
Chandrasekaran等學者[10]發現,EG(10 mg/kg)灌胃治療4-硝基喹啉-1-氧化物(4- NQO)誘導的口腔癌小鼠后,與4-NQO組相比,改善小鼠體重,降低腫瘤負荷50%,減少異常增殖細胞50%,未發生鱗狀上皮細胞癌,并降低脂質過氧化水平。通過增強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過氧化氫酶(Catalase,CAT)和谷胱甘肽過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等抗氧化酶的活性,提高還原型谷胱甘肽(GSH)、維生素C(Vitamin C,VC)和維生素E(Vitamin E,VE)等非酶抗氧化劑的釋放水平,可逆轉異常增生的腫瘤細胞為正常上皮結構,從而發揮抗癌作用。
過量的糖攝入會增加葡萄糖代謝的有毒代謝物產生,從而加重內源性抗氧化和解毒系統的負擔。HoYin Lip等學者[11]發現EG干預大鼠肝細胞后,通過減少ROS生成和保護線粒體膜電位發揮抗氧化作用,保護肝細胞免受乙二醛、甲基乙二醛等毒性代謝物引起的氧化損傷。
2 抗炎作用
炎癥反應是機體重要的防御過程,有助于維持機體的完整性,抵御物理、化學和病毒的感染性損傷,而過度的炎癥會損害正常的器官和身體狀態。因此,抑制炎癥反應的過度發生對保護機體至關重要。
2.1 抑制動脈粥樣硬化中的炎癥反應
單核細胞和T淋巴細胞與血管內皮的黏附是動脈粥樣硬化炎癥反應中最早且必不可少的過程之一。這一過程由內皮-白細胞黏附分子(endothelial-leukocyte adhesion molecules,ELAMs)介導,ELAMs表達于血管內皮表面,覆蓋動脈粥樣硬化和炎癥病變。
Murase等學者[12]檢測了HL-60(一種早幼粒細胞單核細胞系)在靜態條件下與細胞因子激活的人臍靜脈內皮細胞(HUVECs)的黏附,發現EG(3 ~ 10 mmol/L)預處理HUVECs后,可抑制NF-kB p65的核轉位,降低白細胞介素-1α (IL-1α)或腫瘤壞死因子-a (TNF-a)誘導的NF-kB活性進而減少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VCAM-1)、細胞黏附分子-1(ICAM-1)和e-選擇素的表達、降低白細胞黏附發揮抗炎特性。
Liu等學者[13]研究發現,不同劑量的EG腹腔注射于ApoE-/-小鼠后,降低了血清中炎性因子IL-6、TNF-α和趨化因子MCP-1等相關因子的濃度,免疫熒光檢測發現EG可降低小鼠動脈弓部位的炎性細胞浸潤情況。在斑馬魚模型中,研究發現EG可抑制中性粒細胞的生成與遷移。EG可通過抑制炎癥反應發揮抗動脈粥樣硬化作用。在體外模型細胞實驗中,EG還能抑制RAW264.7中炎癥因子IL-6和TNF-α發揮抗炎作用,與體內試驗結果一致。
2.2 抑制肺損傷中的炎癥反應
炎癥及其伴隨的過度氧化應激反應與肺損傷(acute lung injury,ALI)的進展和結果密切相關。Mehla等學者[14]發現,不同劑量(1,5和10 mg/kg) EG腹腔注射小鼠可減輕肺泡水腫、出血,以及中性粒細胞在血管和肺泡區及其周圍的積累,對小鼠的肺損傷具有保護作用。
EG可上調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損傷小鼠模型中血紅素氧合酶(Hemeoxygenase -1,HO-1)的表達,降低Keap-1水平,增強Nrf2的核內聚集,并上調SOD3的表達來發揮抗炎作用。此外,單核細胞釋放的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啟動中性粒細胞內流現象,在LPS誘導的急性肺損傷的免疫應答中發揮關鍵作用。以人單核細胞系THP-1作為體外模型,模擬LPS誘導的急性肺損傷的炎癥狀態,發現EG在體外抑制炎癥因子TNF-α,并通過激活Nrf2上調THP-1中HO-1的表達,發揮抗炎作用保護肺損傷[14]。
Zhang等學者[15]也發現以EG為主要活性成分的中藥湯劑對LPS誘導的急性肺損傷大鼠模型具有保護作用。EG預處理顯著抑制肺水腫,減輕肺組織學病變,減少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的中性粒細胞、ROS、促炎細胞因子和白蛋白水平,在體內(BALB/c)和體外模型(人單核細胞)中均減輕ALI中的炎癥狀態。富含EG提取物顯著減少LPS誘導的肺組織炎性細胞浸潤。EG預處理可降低BALF中 W/D比值和蛋白含量,減少BALF中活化的中性粒細胞浸潤,顯著抑制肺水腫,減輕肺組織學改變。
2.3 抑制皮膚病中的炎癥反應
天然成分也經常用于治療炎癥和疼痛相關疾病,如傷口、關節炎癥、炎癥性皮膚病和其他炎癥性疾病[16]。
除上述抗炎作用外,EG也具有其他部位炎癥的抑制作用,比如過敏性疾病和傷口發炎等。過敏性皮炎的發展機制與肥大細胞脫顆粒現象、組胺釋放水平等密切相關[17]。Minami等學者[18]發現,EG干預肥大細胞后,可以顯著抑制C48/80誘導的組胺釋放,抑制率為36.7%±1.33%。這表明EG可以抑制組胺釋放,進而發揮抗炎作用緩解過敏性疾病。
IL-6在急性炎癥中被誘導生成,并通過促進單核細胞募集觸發急性炎癥向慢性炎癥的轉變。雖然正常水平的促炎細胞因子可以防止感染并加速傷口的正常愈合,但過度生成細胞因子是有害的,因為它會導致炎癥和傷口愈合延長[19]。因此,對抗促炎細胞因子的過度產生可以介導慢性傷口愈合的治療效果。Toafode等學者[20]在體外實驗中發現,用TNF-α刺激的人角質形成細胞(HaCaT)作為皮膚炎癥模型來鑒定EG的治療效果,發現EG可以通過抑制促炎細胞因子IL-6的釋放來發揮抗炎作用。
2.4 其他抗炎的相關研究
炎癥反應貫穿在各種疾病發生發展中,除了炎性因子IL-1α、IL-6和TNF-α外,NO等炎性介質及其相關酶也對炎癥的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
Wang等學者[21]研究發現,從分心木提取分離的EG干預小鼠巨噬細胞系RAW 264.7后,可抑制巨噬細胞釋放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水平,發揮抗炎作用。Park等學者[22]進一步研究發現,EG干預RAW 264.7巨噬細胞后,抑制LPS刺激巨噬細胞后NO的釋放水平,顯著減弱LPS誘導的誘導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表達,顯著抑制LPS誘導的iNOS mRNA的積累,提高細胞核內Nrf2的水平,證明EG可阻斷LPS誘導的巨噬細胞內iNOS活性表達和激活Nrf2/HO-1信號通路從而發揮抗炎作用。
3 治療代謝性疾病
代謝性疾病在我國的患病率逐年上升,這主要是人們生活水平和飲食結構發生變化引起。此類疾病主要包括糖代謝和脂質代謝兩個領域。糖脂代謝性疾病主要包括糖尿病、動脈粥樣硬化、高脂血癥和戈謝病等。目前眾多研究學者對此類疾病的攻克集中于天然產物方向,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進展。
3.1 糖代謝疾病
糖脂代謝性疾病主要以糖脂代謝紊亂為特征,由遺傳因素、環境因素和生活方式等多種因素參與。Ⅱ型糖尿病(T2D)已成為一種常見的糖代謝疾病。若控制不當,會增加大血管、微血管及代謝性并發癥的風險,適當的血糖控制對糖尿病患者非常重要。目前預防Ⅱ型糖尿病的方法包括抑制α-葡萄糖苷酶、刺激胰島素分泌、增加胰島素敏感性和抑制腸道葡萄糖轉運等。
Ahn等學者[23]發現EG干預后3T3-L1細胞內脂滴積聚減少,通過降低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s γ,PPARγ)和增強子結合蛋白α轉錄調節因子(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s α,C/EBPα)的表達來抑制3T3-L1細胞內早期脂肪形成。解析出EG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5-AMP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抑制3T3-L1細胞脂肪生成,刺激葡萄糖攝取,從而發揮抗糖尿病和抗肥胖作用。此外,通過分子對接研究EG與蛋白酪氨酸磷酸酶非受體6型(Protein tyrosine phosphatase non receptor type-6,PTPN6)和PPARγ的結合能力,以此佐證了EG的抗糖代謝作用機制。
降低餐后血糖和隨后胰島素峰值水平是抑制腸道對葡萄糖轉運的治療途徑之一。Wang等學者[24]在Caco-2細胞中用一定劑量的EG進行干預后,可控制餐后腸道葡萄糖轉運水平,使餐后血糖水平降至穩定狀態。
α-葡萄糖苷酶又稱α-d-葡萄糖苷水解酶,是參與機體葡萄糖代謝過程、影響體內血糖濃度的一種重要水解酶。薛琛等學者[25]通過紫外分光光度法、同步熒光光譜法和分子對接技術發現,EG ( IC50=2.97 mg·mL-1)通過氫鍵與疏水作用力與α-葡萄糖苷酶自發結合形成穩定的復合物,對α-葡萄糖苷酶活性表現出良好的抑制作用。另外,分子對接顯示EG與α-葡萄糖苷酶的疏水口袋結合并形成氫鍵,對接能量為-26.48 kJ·mol-1,這佐證了EG對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作用,其具有抗糖代謝的潛力。
3.2 脂質代謝疾病
脂質代謝疾病中典型的是動脈粥樣硬化,這是一種由炎癥和脂質代謝紊亂引起的慢性疾病。因此,研究和治療脂質沉積和炎癥是抑制動脈粥樣硬化早期病變發展的有效途徑。
Liu等學者[13]發現給ApoE-/-小鼠(一種以脂肪條紋為典型特征的早期動脈粥樣硬化病變模型)腹腔注射EG (20 mg/kg)可顯著減少主動脈和主動脈弓內脂質沉積斑塊面積和炎性細胞浸潤。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濃度升高2倍,且MCP-1、IL-6和TNF-α水平顯著降低。
斑馬魚作為一種新興的疾病動物模型也常用于研究脂質代謝紊亂性疾病的研究[26]。一項研究證明,一定劑量EG喂食斑馬魚后,顯著改善了體內的血管膽固醇沉積以及中性粒細胞的生成和遷移[13]。
在細胞實驗中,EG (20 μmol/L)處理巨噬細胞和內皮細胞減少泡沫細胞的數量,并抑制細胞內促炎細胞因子IL-12p70、IL-6、MCP-1和TNF-α的釋放。EG可通過激活脂質轉運蛋白ABCA1(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A1)和ABCG1((ATP-binding cassette transporter G1)),促進膽固醇外流,減少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ox-LDL)蓄積,抑制巨噬細胞泡沫細胞轉化,從而調節脂質紊亂[13]。
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的氧化修飾與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密切相關。LDL在血管壁的沉積和修飾會導致單核細胞募集到血管內皮下間隙,進而分化為巨噬細胞。巨噬細胞大量地吞噬經過氧化修飾的LDL顆粒,向泡沫細胞狀態轉變,隨后泡沫細胞破裂,觸發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的惡化。EG抑制細胞因子誘導的NF-kB核轉運和血管內皮細胞中白細胞黏附分子的表達,抑制巨噬細胞過量吞噬ox-LDL,緩解細胞內脂質代謝紊亂,具有調控脂質平衡的潛力[27]。
4 其他作用
除上述作用外,EG還有多種生物活性。EG可以調節血壓。Lim等學者[28]發現EG及其提取物通過抑制Ca2+和Na+內流進入腎上腺髓質嗜鉻細胞,激活iNOS增加NO生成來介導Ca2+攝取減少進入細胞質Ca2+儲存,從而抑制乙酰膽堿誘發的兒茶酚胺類激素分泌,發揮有益的抗高血壓活性。
EG具有抗過敏和鎮痛作用。組胺是觸發過敏反應的重要介質,抑制其在細胞內的分泌可起到抑制過敏的作用。 Minami等學者[18]發現,EG抑制化合物C48/80誘導的大鼠腹腔肥大細胞組胺釋放。此外,EG以劑量依賴性通過調控K+通道的激活和Gi/o蛋白的痛覺敏感機制,在小鼠和大鼠的不同化學、機械和熱傷害性感受模型中發揮抗痛覺過敏、抗傷害性感受作用[29]。
5 小結與展望
EG是一種存在于多種藥用植物和天然食物中的代謝產物,如余甘子、葡萄酒和白芍等。近年來,EG在醫藥領域的研究和應用呈上升趨勢。雖然EG的抗炎、抗癌和抗菌作用已被研究,但具體作用機制尚未明確。在調節糖脂代謝方面,多數研究為理論和體外細胞實驗,缺少動物模型等,仍需進一步研究。這一不足之處也是后期重點研究的潛在方向。另外,EG作為一種多酚類化合物,雖然具有廣泛的生物活性,但具有易氧化的缺點限制了其應用。如果對其進行大分子包封和修飾或將擴大研究范圍,加速其開發與應用。EG的研究和利用越深入,對EG的認識就越全面,這將為今后的科學制藥和臨床用藥提供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