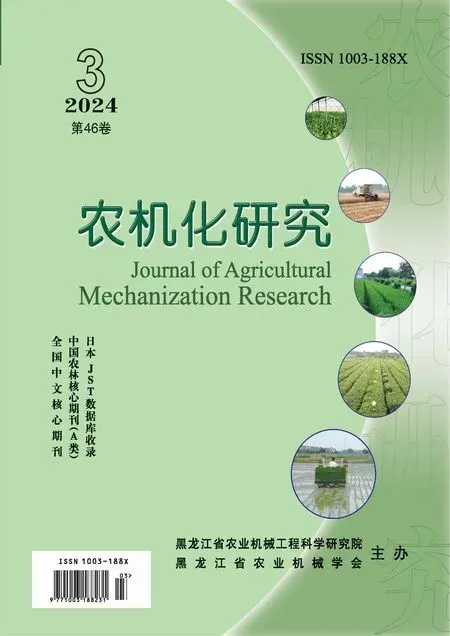基于離散元法的胡蘿卜挖掘鏟優化設計
趙智豪,王家勝,楊麗麗,邵珠同
(青島農業大學 機電工程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9)
0 引言
我國胡蘿卜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均居世界前列[1-2],但大多數地區仍以人工收獲為主,且目前國內的種植模式難以適應國外現有的胡蘿卜收獲機械,造成收獲效率低成本高,嚴重制約了我國胡蘿卜規模化種植的發展。松土挖掘鏟是胡蘿卜收獲機的核心部件,其結構參數和工作參數直接影響到收獲機的作業性能。王金武等人通過建立挖掘鏟與土壤間的力學分析模型,設計并分析了狗獾爪趾形仿生挖掘鏟的減阻機理,最終確定了影響挖掘鏟松土效果的挖掘鏟結構參數,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收獲阻力與胡蘿卜漏拔率[3]。王家勝等人設計了一種胡蘿卜聯合收獲機平面單鏟,入土性較好,但在粘壤土中容易壅土[4]。東北農業大學韓鳳研制了一種用于雙行拔取式胡蘿卜收獲機的箭型鏟頭,工作阻力降低,但兩側土壤擾動較小,松土效果較差[5]。
本文基于離散元方法,建立了挖掘鏟-胡蘿卜-土壤離散元模型,通過試驗優化與回歸分析,探究三角翼形挖掘鏟結構參數對工作過程中挖掘阻力、土壤破碎率的影響關系,并對結構參數進行優化,旨在為胡蘿卜聯合收獲機挖掘部件的設計提供技術支持。
1 胡蘿卜挖掘鏟結構設計
1.1 挖掘鏟受力分析
以應用較為廣泛的三角鏟作為研究對象,收獲工作狀態下挖掘鏟受力如圖1所示。其中,鏟的入土角為α,挖掘鏟在鏟柄推力作用下以勻速度v在土壤中切割行進。

圖1 挖掘鏟工作受力Fig.1 Performance force of digging shovel
對挖掘鏟受力分析后,獲得施加給鏟柄的前進方向的推力為
Py=Nsinα+(Ff+Fa+T)cosα
(1)
式中N—土壤對鏟面正壓力(N);
Ff—土壤-鏟面間滑動摩擦力(N);
Fa—土壤對鏟面粘滯力(N);
T—土壤切割力(N);
α—入土角(°)。
影響挖掘阻力的因素中,土壤正壓力是由鏟面土壤塊的重力、土壤塊對鏟面的慣性沖擊力組成,土壤塊重力與挖掘鏟的工作寬度、長度和挖掘深度有關,慣性沖擊力則與土壤塊質量和前進速度有關[6]。土壤-鏟面間滑動摩擦力、土壤對鏟面粘滯力及土壤切割力則與土壤的力學參數和鏟面光滑度有關。
1.2 關鍵參數設計
根據胡蘿卜的生長特點和收獲要求,所設計的三角翼形挖掘鏟為平面單鏟形式,鏟形為雙翼分開的三角狀(見圖2),可減小鏟面觸土面積,有利于降低挖掘阻力。針對雙行收獲要求,為同時鏟松兩行,避免漏挖,鏟面寬度需要覆蓋大于兩行的有效寬度。鏟面寬度可按下式計算,即
B≥w+s+2σ+c
(2)
式中w—胡蘿卜種植行距(mm);
s—胡蘿卜分布寬度均值(mm);
σ—胡蘿卜分布寬度標準差(mm);
c—收獲機行駛偏差(mm)。
胡蘿卜種植行距w=200mm,經試驗測量s=60mm,σ=10mm, 取c=50~70mm,則鏟面寬度為B≥320mm。
鏟刃斜角γ是決定挖掘鏟具有良好的切割性能的關鍵參數,鏟刃斜角取值滿足下式[7],即
γ<90°-φ
(3)
式中γ—鏟刃角(°);
φ—土壤對鏟面的摩擦角(°)。
土壤對鋼的摩擦因數tanφ=0.4~0.7,所以γ<55.1°~68.2°。

圖2 挖掘鏟結構Fig.2 Structure of digging shove
2 離散元建模與仿真試驗
2.1 離散元模型建立
土壤是一種典型的松散介質,可以利用相互粘連的顆粒離散元模擬土壤聚團及在挖掘鏟作用下的破裂行為。將土壤顆粒的半徑設為3mm,在保證仿真準確性的同時以減輕計算機仿真壓力,同時為了模擬土壤環境的真實性,土壤顆粒模型分別設定為粒狀顆粒、團粒狀顆粒、塊狀顆粒、桿狀顆粒等4種模型[8-10],形態如圖3所示。同時,在EDEM中Size Distribution類型設置為正態分布(normal)。土壤接觸模型選擇Hertz-Mindlin with Bonding模型[11],可以通過土壤之間設置的粘結鍵給相鄰的土壤顆粒施加粘結力,使其能同時承受切向和法向位移。

圖3 土壤顆粒模型Fig.3 Soil particle model
胡蘿卜模型以“紅映二號”為例設計,對“紅映二號”胡蘿卜結構尺寸測量統計后,取胡蘿卜長度220mm,最大直徑40mm,最小直徑20mm,纓長200mm,按照以上參數先在SolidWorks中對胡蘿卜建立三維模型,再導入EDEM進行顆粒填充,如圖4所示。

圖4 胡蘿卜離散元模型Fig.4 Carrot discrete element model
土壤類型為壤土,挖掘鏟材料選擇錳鋼,通過查表獲得模型的離散元模型參數如表1所示。

表1 離散元模型參數值Table 1 Parameter values of discrete element model
2.2 仿真試驗方案
為模擬胡蘿卜收獲機實際作業狀態,運用EDEM土壤模型建立長×寬×高為1000mm×30mm×50mm的壟,將壟面設置為土壤顆粒工廠,產生顆粒15萬個,顆粒工廠生成形式設為static;建立6個box顆粒工廠產生胡蘿卜離散元模型,株距設置為60mm,行距為200mm,數量為18個。
試驗時,將挖掘鏟入土角設置為25°,前進速度為0.8m/s。為了對挖掘鏟參數進行優化設計,以鏟面長度、鏟面寬度及鏟刃傾角為試驗因素,鏟面長度為200~350mm,鏟面寬度為350~500mm,鏟刃傾角為55°~65°。試驗因素編碼如表2所示。

表2 試驗因素編碼Table 2 Coding of test factors mm
仿真試驗以工作阻力、土壤破碎率為試驗指標。在仿真過程中,由于挖掘鏟對土壤破壞作用造成顆粒生成過程中形成的bond鍵的破壞,故統計 bond鍵破碎的數目來評定挖掘鏟的碎土性能,計算破碎鍵個數與生成bond鍵總數的比值,求解出土壤破碎率。
為保證仿真精確性和連續性,將仿真步長設置為3.14e-06,網格單元尺寸設置為土壤最小顆粒半徑的3倍即9mm,仿真土壤顆粒件粘結半徑設置為3.5mm;土壤顆粒經過0.25s生成完畢,仿真總計時長為2s,仿真完畢后在處理工具中加載出三角翼形挖掘鏟挖掘阻力,并通過bond鍵破壞數量觀察整體土壤破碎率。挖掘鏟仿真模型如圖5所示。

圖5 挖掘鏟工作離散元仿真模型Fig.5 Discrete element simulation model of excavator work
2.3 試驗結果與分析
2.3.1 挖掘試驗時間歷程
挖掘鏟作用下胡蘿卜與土壤在不同時間段的變化狀態,如圖6所示。

(a) t=0.3s

(b) t=0.5s

(c) t=0.9s

(d) t=1.1s圖6 仿真試驗矢量圖Fig.6 Simulation test vector diagram
由圖6可知:當挖掘鏟剛入土時,鏟上方的土壤首先受到擾動,擾動區域的土壤有了初始速度,此時挖掘鏟兩側胡蘿卜沒有受到土壤擾動作用,胡蘿卜速度幾乎為0,挖掘鏟受力逐漸增大;隨著挖掘鏟不斷深入,到0.5s時完全入土,此時挖掘鏟受力最大,對土壤擾動增強,挖掘鏟上方土壤失效區域范圍變大,土壤的隆起高度也有所增加,且隨著土壤層的位移,挖掘鏟兩側胡蘿卜隨著土壤開始移動,正上方胡蘿卜速度最大為0.17m/s,鏟尖處胡蘿卜開始受到土壤擾動,逐漸有移動趨勢;0.9s時,鏟柄開始進入土壤,此時對鏟兩側胡蘿卜破壞能力進一步增強,鏟上方土壤失效區域范圍和隆起高度劇增,此時鏟兩側胡蘿卜速度在0.14~0.34m/s范圍內;1.1s時,隨著挖掘鏟和鏟柄對土壤的進一步破壞,對土壤的擾動能力進一步提高,胡蘿卜隨土壤的運動趨勢越明顯。
2.3.2 影響因素分析
正交試驗后不同試驗因素組合下挖掘鏟阻力與土壤破碎率如表3所示;表4、表5為經Design-Expert軟件處理后得到三角翼形挖掘鏟工作阻力和挖掘過程中土壤破碎率的方差分析結果。

表3 正交試驗結果Table 3 Orthogonal test results

表4 工作阻力方差分析Table 4 ANOVA of work resistance

表5 土壤破碎率方差分析Table 5 ANOVA of soil fragmentation rate
根據表4分析,工作阻力二次多元回歸方程為
Y1=1420.10+124.86A+55.02B+7.39C-
4.38AB-12.60AC+6.93BC-68.73A2-
42.65B2+52.37C2
(4)
回歸診斷顯示,回歸模型顯著性檢F=17.26,P=0.0006,模擬的一次項鏟面長度A和一次項鏟面寬度B、二次項A2對工作阻力的影響極其顯著(P<0.01),二次項B2、A2對工作阻力影響顯著(P<0.05)。經過單因素水平分析,各因素對工作阻力的影響順序為鏟面長度>鏟面寬度>鏟刃傾角。響應面分析如圖7所示。

圖7 影響工作阻力的各因素響應曲面Fig.7 Response surface of each factor affecting the working resistance
根據表5分析,土壤破碎率二次多元回歸方程為
Y2=93.46+0.25A+0.50B+0.57C+
0.025AB+0.025AC-0.13BC+0.26A2-
0.24B2+0.56C2
(5)
回歸診斷顯示:回歸模型顯著性檢F=6.82,P=0.0096,模擬的一次項鏟面寬度B和一次項鏟刃傾角C對土壤破碎率的影響極其顯著(P<0.01),二次項C2對土壤破碎率影響顯著(P<0.05)。經過單因素水平分析,影響挖掘鏟工作阻力的各因素順序為鏟刃傾角>鏟面寬度>鏟面長度。響應面分析如圖8所示。

圖8 影響土壤破碎率的各因素響應曲面Fig.8 Response surface of each factor affecting soil fragmentation rate
2.4 試驗優化
為得到挖掘鏟結構各個試驗因素間的最佳參數組合,通過建立數學模型對挖掘鏟進行優化設計,并結合設計過程中各個參數的邊界條件最終達到降低工作阻力F和提高土壤破碎率Y的目的。在此,對三角翼形挖掘鏟的工作阻力和土壤破碎率進行回歸分析,建立非線性規劃參數模型,即
(6)
利用Design-Expert 10.0.7對數學模型進行分析求解,得鏟面長度260mm、鏟面寬度370mm、鏟刃傾角57°為最優參數組合,此時工作阻力為1343.81N,土壤破碎率為92.73%。將最優參數進行EDEM虛擬仿真試驗驗證,其工作阻力為1268.56N,土壤破碎率為92.25%,與優化結果基本一致。
3 田間試驗
3.1 試驗條件與方案
在相同工作參數下,用鑿型鏟進行仿真試驗,工作阻力為1423.65N,土壤破碎率為88.6%,表明優化設計后的三角翼形挖掘鏟在工作阻力和土壤破碎率方面具有良好的松土性能,為胡蘿卜挖掘裝置理論分析和仿真試驗設計提供理論基礎。田間試驗的目的是檢驗設計的三角翼形挖掘鏟作業性能,結合理論分析與仿真模擬結果進行。試驗地點為山東省萊西市店埠鎮萬畝胡蘿卜收獲基地,胡蘿卜種植模式為壟作,行距為200mm,植株高度在360~550mm之間,直徑在35~60mm之間,胡蘿卜的塊根長度在180~200mm之間。田間試驗如圖9所示。
將三角翼形挖掘鏟和鑿型鏟分別安裝在胡蘿卜聯合收獲機上,將機器作業速度設置為0.8m/s,將工作阻力和土壤破碎率作為試驗指標,利用拉力傳感器、角度傳感器、測力框架及信號板組成的測力系統進行工作阻力測定。根據GB/T 5668-2008對試驗土地地塊進行破碎率測量,在已經挖掘松土的地塊上標定出一塊0.3m×0.3m面積的測定區域,將收集到的土塊按照長邊小于3cm、3~6cm之間和大于6cm進行分類。土壤破碎率表示為小于3cm的土塊質量占總質量的百分比,每壟隨機測量10點,其公式為
(19)
式中Sb—土壤破碎率(%);
ma—標定試驗區域內全耕層收集土塊總質量(g);
mε—標定試驗區域內邊長大于3cm的土塊質量總和(g)。

圖9 胡蘿卜田間試驗Fig.9 Carrot field trial
3.2 試驗結果與分析
試驗重復進行6次,結果表明:三角翼形挖掘鏟最高阻力為2032.5N,最低阻力為1856.6N,土壤破碎率最高為96.5%,最低為94.3%;鑿型鏟最高阻力為2223.8N,最低阻力為1998.3N,土壤破碎率最高為93.8%,最低為91.5%。通過對比試驗發現(見圖10、圖11):三角翼形挖掘鏟在工作阻力和土壤破碎率性能方面均優于鑿型鏟,工作阻力降低了9.4%,土壤破碎率提高了2.8%,滿足胡蘿卜的收獲要求。

圖10 田間試驗工作阻力Fig.10 Field test work resistance

圖11 田間試驗土壤破碎率Fig.11 Soil fragmentation rate in field test
4 結論
1)通過對胡蘿卜收獲狀態下三角翼形挖掘鏟進行受力分析和計算,確定了鏟面寬度和鏟刃角的取值范圍。根據胡蘿卜種植模式,建立了挖掘鏟-胡蘿卜-土壤離散元仿真模型,以鏟面長度、鏟面寬度及鏟刃傾角為試驗因素,以工作阻力、土壤破碎率為試驗指標開展了胡蘿卜挖掘仿真試驗,仿真時間歷程顯示了土壤與胡蘿卜隨挖掘鏟的運動的變化過程。
2)利用仿真試驗數據擬合建立不同試驗因素影響下挖掘鏟阻力與土壤破碎率的二次多元回歸方程,通過Design-Expert 10.0.7對數學模型進行分析求解,得出了最優參數組合,即鏟面長度260mm、鏟面寬度370mm、鏟刃傾角57°。通過與鑿型鏟進行對比試驗可知:優化設計后的三角翼形挖掘鏟在工作阻力和土壤破碎率方面都具有更為優良的性能,可胡蘿卜挖掘裝置優化設計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