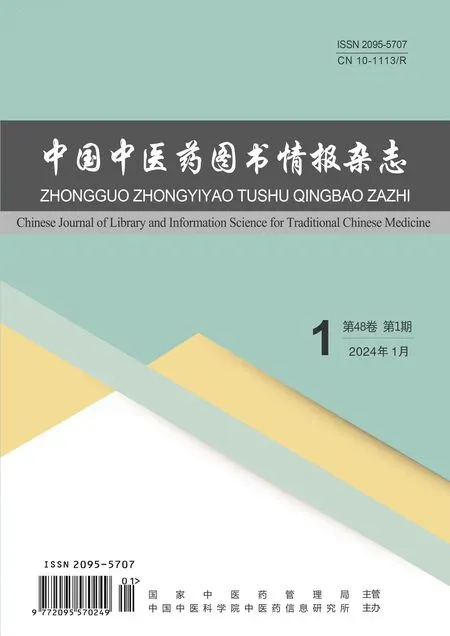柳寶詒與吳鞠通治療痢疾病案異同研究
張迎泉
泰安市中醫(yī)醫(yī)院,山東 泰安 271000
吳鞠通(1757-1841年),名瑭,字配珩,創(chuàng)立“三焦辨證”學(xué)說。先生不僅擅長治療溫病,更是內(nèi)科雜病高手,從其著作《溫病條辨》《吳鞠通醫(yī)案》中可管窺一斑。柳寶詒(1842-1901年),字谷孫,號冠群,江陰縣周莊鄉(xiāng)人[1]。《江陰縣志》記載:“其人和厚好學(xué),能文工書,尤長于醫(yī)。蘇常一帶,婦孺皆知。著有醫(yī)學(xué)書籍12種,其中以所評《柳選四家醫(yī)案》,人尤稱之。”
本文對《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與《吳鞠通醫(yī)案》中痢疾相關(guān)醫(yī)案的理法方藥進行分析,比較柳寶詒和吳鞠通對痢疾病機的認(rèn)識和治法異同,探討二者治療痢疾的用藥規(guī)律,以期與同道共饗。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收集
收集《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2]、《吳鞠通醫(yī)案》[3]中治療痢疾的醫(yī)案,納入有“痢疾”“下痢”“滯下”“下利”“休息痢”“腸澼”等記載的醫(yī)案,排除無處方的醫(yī)案。
1.2 數(shù)據(jù)錄入與規(guī)范化處理
采用Excel2010軟件錄入醫(yī)案數(shù)據(jù),雙人分別錄入。參考《中藥學(xué)》[4]對中藥名稱、功效分類進行規(guī)范化處理,如“紅曲”規(guī)范為“神曲”、“本山術(shù)”規(guī)范為“蒼術(shù)”、“當(dāng)歸身”規(guī)范為“當(dāng)歸”、“鮮藕”規(guī)范為“藕節(jié)”等。炭類藥物如當(dāng)歸炭、川芎炭、牡丹皮炭等歸入止血藥進行分類。
1.3 研究方法
采用Excel2010軟件統(tǒng)計醫(yī)案中藥物使用頻次及功效分類,分析柳寶詒和吳鞠通對痢疾病機的認(rèn)識和治法異同。
2 結(jié)果
2.1 藥物使用頻次分析
《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治療痢疾醫(yī)案9則,處方13首,使用中藥66種,其中出現(xiàn)頻次較高的藥物為木香、白術(shù)、枳殼、桔梗、砂仁、荷葉蒂、茯苓、炮姜炭、山楂炭、白芍、厚樸、當(dāng)歸等,見表1。

表1 《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治療痢疾醫(yī)案單味藥物使用頻次
《吳鞠通醫(yī)案》治療痢疾醫(yī)案9則,處方55首,使用中藥70種,其中出現(xiàn)頻次較高的藥物為黃芩、白芍、木香、黃連、神曲、陳皮、當(dāng)歸等,見表2。

表2 《吳鞠通醫(yī)案》治療痢疾醫(yī)案單味藥物使用頻次
2.2 藥物功效分類分析
《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治療痢疾的藥物中,以理氣藥(30次)、止血藥(28次)、補氣藥(21次)、利水滲濕藥(16次)為主,其中理氣藥多用木香、枳殼、陳皮等;止血藥以炭類藥物居多,如炮姜炭、山楂炭等;補氣藥多用白術(shù)、炙甘草、西洋參等;利水滲濕藥多用茯苓、通草、豆卷等。見表3。

表3 《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治療痢疾醫(yī)案藥物功效分類
《吳鞠通醫(yī)案》中出現(xiàn)頻次較高的藥物為清熱藥(89次)、理氣藥(76次)、補血藥(61次)、利水滲濕藥(55次),其中常用的清熱藥有黃芩、黃連等;理氣藥常用木香、陳皮;補血藥常用白芍、當(dāng)歸;利水滲濕藥常用茯苓。見表4。
3 討論
3.1 用藥規(guī)律異同比較
通過對《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與《吳鞠通醫(yī)案》中痢疾相關(guān)醫(yī)案進行用藥規(guī)律分析,發(fā)現(xiàn)二者治療痢疾的共同藥物為理氣藥、利水滲濕藥、補益藥(多為補氣藥、補血藥)。不同的是,吳鞠通應(yīng)用清熱藥較多,而柳寶詒應(yīng)用止血藥較多,這可能與患者痢疾的病性及分期有關(guān)。2位醫(yī)家皆喜用炭類藥物,炭類藥物色黑入血分,“血見黑必止”,常用藥物有山楂炭、牡丹皮炭、炮姜炭、地榆炭、大黃炭等。《本草蒙筌》謂炭類藥物“制藥貴在適中,不及則功效難求,太過則氣味反失”,中藥制炭既不是完全炭化,也不是灰化,而是要存性,即外部炭化,內(nèi)部保存其固有的性能。炭類藥物也可用于收斂止瀉,起到澀腸止瀉作用。炭類藥物還可緩和藥性,如炮姜炭溫?zé)嶂晕礈p,辛散之性降低;枳實炒炭后可消其辛燥之性,有助消導(dǎo)化積。
3.2 病機異同比較
2位醫(yī)家對痢疾的病機認(rèn)識與現(xiàn)代中醫(yī)臨床大致相同,即濕熱之邪,內(nèi)蘊成毒,熏灼腸道,血敗肉腐,發(fā)為下利膿血,日久耗傷氣血則成久痢之虛證。《溫病條辨·中焦篇》云:“濕溫內(nèi)蘊,夾雜飲食停滯,氣不得運,血不得運,遂成滯下,俗名痢疾。”此條可視為吳鞠通辨治痢疾的大綱,雖載于《溫病條辨》,在《吳鞠通醫(yī)案》中亦有明顯體現(xiàn)和重要指導(dǎo)作用。柳寶詒亦有類似的論述,如《柳寶詒醫(yī)論醫(yī)案·痢疾門》中記載史姓案“腸腑中積垢未凈”;朱姓案“濕熱積滯,阻窒氣機”;楊姓案“脾營下陷”;趙姓案“病邪本在陰分,更兼暑熱積滯,蒸蘊營分”;劉姓案“肝脾營氣受傷”,“氣機阻窒于中,滯陷于下,營分中余邪,至今未能盡化”;方姓案“中氣虛寒,由氣分傷及血分”;馬姓案“血痢久而不止,脾氣與胃津俱傷……刻下因積滯”;龐姓案“肝氣乘久痢下虛之隙……暑濕余邪留于腸腑”等;均指出痢疾的發(fā)生與濕熱之邪、氣血等因素密切相關(guān)。
柳寶詒在前輩醫(yī)家的基礎(chǔ)上,提出痢疾的病理因素為“宿垢”。宿,《說文解字》注為“止也”;垢,《說文解字》注為“濁也”,穢濁之邪停滯腸內(nèi)為患。“人之精液氣血,流行輸貫每至其處,即留滯于此,蒸化而為垢”。其中,“傷氣液者化為白垢,傷營血者化為紅垢”是柳寶詒提出的獨特觀點,宿垢這種病理因素和現(xiàn)代醫(yī)學(xué)認(rèn)為炎癥性腸病發(fā)病機制中的免疫因素十分類似。其在《呂文清痢疾論治》中稱休息痢“余邪未盡,余垢留匿于大腸曲折之處”,“凡腸中稍有阻窒,即能致痢”,正如現(xiàn)代醫(yī)學(xué)認(rèn)為,免疫因素作用于腸道,存在“免疫耐受”缺失的患者對免疫因素發(fā)生調(diào)節(jié)障礙,免疫反應(yīng)不能被正常抑制,最終導(dǎo)致過度激活和難于自限,身體的免疫細(xì)胞和腸道黏膜的非免疫細(xì)胞參與免疫反應(yīng)和炎癥過程,通過相互作用釋放各種細(xì)胞因子及炎癥介質(zhì),導(dǎo)致腸道炎癥的發(fā)生和發(fā)展[5]。“凡經(jīng)年累月,垢下已多,而其中仍不能盡者,即此故也”,“此病由余垢而起,本無純虛證”正是痢疾易反復(fù)、難以治愈的原因,“余垢”即與現(xiàn)代醫(yī)學(xué)的免疫因素在炎癥性腸病中發(fā)揮的作用相似。
3.3 治法異同比較
從歷史傳承上講,吳鞠通治療痢疾的思路、方法及用藥均受葉天士先生的影響,一般痢疾初起,祛邪為先,宜解表、宜清化、宜分利、宜辛苦、宜甘苦,多禁忌固澀法,可根據(jù)具體情況分別施用;久痢虛證多見,兼挾邪氣,宜攻補兼施,固護正氣為要,其中補虛法有護胃救陰、升陽舉陷、溫補脾腎、溫補奇經(jīng)八脈、陰陽雙補等法;固澀有截斷陽明、溫攝下焦、養(yǎng)陰固澀法,根據(jù)實際情況應(yīng)用。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吳鞠通醫(yī)案》中治療痢疾初起的醫(yī)案居多,用藥偏重清熱解毒利濕、行氣止痛和血,藥物如黃芩、黃連、白芍、木香、陳皮、當(dāng)歸。正如吳鞠通云:“以風(fēng)藥之辛,佐以苦味入腸,芳香涼淡也。蓋辛能勝濕而升脾陽,苦能滲濕清熱,芳香悅脾而燥濕,涼能清熱,淡能滲濕也,俾濕熱去而脾陽升,痢自止矣。”代表性方劑為加減芩芍湯、斷下滲濕湯和加減瀉心湯。時振聲教授[6]認(rèn)為,吳鞠通不僅是溫病大家,而且是內(nèi)科雜病圣手,《溫病條辨》是對多種急性熱病進行辨證論治的專著,其中有關(guān)痢疾的條文,共有中焦、下焦二篇共29條,絕大多數(shù)出自葉天士《臨證指南醫(yī)案》。
柳寶詒所處年代,正是傷寒、溫病之爭盛行和溫病學(xué)說自成體系而有分歧的時期,柳氏自身亦是溫病名家,并著述《溫?zé)岱暝础芬徊浚⒉秽笥谝患抑裕瑢畬W(xué)說、溫病各家學(xué)說,各取其長,融匯變化,為我所用。如陳氏案,“由瘧轉(zhuǎn)痢,經(jīng)腑交病,所下垢膩如痰者甚多。神倦肢清,脈弱舌滑,苔色白燥,脾陽與胃陰兩受重傷,而痰氣尚阻而未暢。擬仿理中法加味”。由此看出,柳寶詒并不一味強調(diào)清熱之法,而是處處顧及素體和胃氣的學(xué)術(shù)思想,善于從整體識證,治病求本,標(biāo)本同治,執(zhí)簡馭繁,用藥獨具一格。柳寶詒提出的宿垢理論,為現(xiàn)代治療痢疾提供了思路,并提供了相應(yīng)的治法,原文如用“鴉膽子、龍眼肉一包錢服”,“俟宿垢一凈,即用培補之品以善其后”,可稱為專藥專用法,他還提出“疏化”的方法,包括溫補疏通、疏濁清營、溫中疏邪、溫脾疏濕、芳香疏化、和營疏邪、疏肝運脾、溫營暢氣、疏肝寬暢調(diào)氣等。從這些具體治法來看,疏化法主要用于調(diào)節(jié)氣機、調(diào)節(jié)升降,解除“腸中稍有阻窒”,恢復(fù)腸道的運動功能,使得留置于腸道的“精液氣血”重新“流行輸貫”,避免生成“余垢”。柳寶詒在治療痢疾時,以理氣藥、止血藥、補氣藥居多,常用方劑如平胃散、四逆散、順氣散等,加用炭類藥物,史姓、陳姓患者應(yīng)用理中丸加補氣藥、止血藥。在《柳選四家醫(yī)案》按語中,柳寶詒多提及應(yīng)用理中湯、黃土湯合治之法,亦有黃土湯加清化濕熱藥香連丸的記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