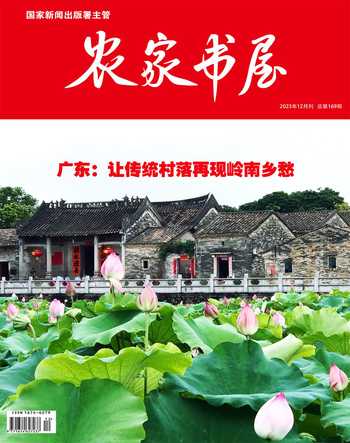吹回來的鄉土氣息
施崇偉
作家劉亮程,與他神交已久,卻遲了對他作品的閱讀。一捧上他這本始版于2005年的《一個人的村莊》,恰如他文中大量使用的隱喻——一股鄉村之風迎面而來,吹回那些年鄉村生活的記憶與情感。
豈止是“風”,其筆下的一頭牛、一只鳥、一片葉、一把锨、一柄犁,都傾注了獨特的感情,并與人類一樣具有了獨特的生命內涵。“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樹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蟲的鳴叫都是人的鳴叫。”他對一切鄉土的東西毫無保留地贊頌,所有的雞鴨貓狗、驢馬牛羊、草木魚蟲、風土山水,都被他賦予詩情畫意般的升華。他可以從一塊石礫、一棵樹木、一把鋤頭上發現生命的獨特內涵、發現人生的哲理所在。
劉亮程生活的村莊黃沙梁,有逃跑的馬、歡脫的狗,野地里有麥子,還有好多樹,而村里有一村懶人、一頓晚飯,還有一個長夢。大地落日下,劉亮程生活的村莊單純而明朗,里面的一草一木都蘊涵無盡的情趣,他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被時間遺忘的遠古部落。
《一個人的村莊》是一扇窗子,打開了我的村莊記憶。
我生活的村莊幺店子,雖與新疆的黃沙梁相距遙遠,卻有著相同的鄉村命運。一村百十戶人家,有的聚居村頭,有的散布山溝。我家老屋所在的綦江河邊住著七八戶人家。小河邊是竹園,竹園里是房舍,房舍前是河岸,清清河水映著河邊草。這片院落和河岸,時常傳來雞鳴和犬吠。有時,漁船上的船夫在嚷嚷著,向岸上報告喜訊;有時,一群浣衣女子用捶衣棒擊打衣裳,臉上洋溢著歡笑。老屋前有棵老黃葛樹,立在家門口,枝冠伸到竹園,團團樹葉和尖尖竹葉,扶肩攜手般親密。那樹,那竹,春來枝綠,秋去葉落,別有一番景致。
石頭壘,泥磚砌,搭上木檁子,覆蓋茅草或青瓦,各家各戶的老屋,經祖先建造一代代傳承。有的墻泥脫落,用灰泥補上;有的梁生蟲蟻,拿鐵絲捆個五花大綁;遇到大風,茅屋在搖晃,隨時都要倒塌一樣;如果暴雨來了,好多戶人家都是屋外大雨,屋里小雨,從破瓦縫漏下的雨滴落在接水的盆里,敲得滿屋叮叮當當。我家老屋是照壁墻房子,仄仄斜斜、老態龍鐘的樣子,像冬天就會犯氣管炎的爺爺。關嚴門窗,卻堵不住墻上的裂縫。爺爺禁不住漏進的寒風,他的咳聲驚天動地,也揪痛家人的心。
《一個人的村莊》帶我回到故鄉,并深刻激起我的情感共鳴。
劉亮程在不斷觀察和日積月累的過程中打開了思想之門,他的思想從這個村莊逃了出去。人在困境中更能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因而人的掙扎和抗爭是對命運的不屈服。他看到了人生,看到了人活著的價值與意義。
《兩窩螞蟻》講了一窩大黃螞蟻和一窩小黑螞蟻的故事。螞蟻差不多是渺小的代名詞,每一個農村孩子少不了這樣的螞蟻篇章。在劉亮程筆下,螞蟻的世界很豐富。有一種白蟻會建造結構精巧的巢穴,巢穴底下還有一個它們精心栽培的木耳花園。作者從螞蟻的生活中看到了人的生活。假如真有造物主,他看我們一定就像我們看螞蟻那樣,“其視下亦若是則已矣”。我們在天地間是如此脆弱,那我們是否就可以渾渾噩噩,排隊等死?但我們的世界又是如此的絢麗多彩。
誰不生而如蟻?誰不是在抗爭中生存并強大超越?即使經歷了大半生的今天,我們在蕓蕓眾生中仍如蟻蟲,但這并不能阻止我們努力、奮斗與抗爭。讀過劉亮程用充滿濃郁詩性的語言,對枯燥村莊生活的詩意表達,再回過頭來看自己那些年的鄉村生活,是多么美好的生命歷程啊!
讀罷《一個人的村莊》,正值老母親打來電話。沒有什么能夠阻擋我回家的腳步,立即懷揣這本墨香,拎起行裝,匆匆踏上回家路。“我的生活容下了一頭驢,一條狗,一群雜花土雞,幾只咩咩叫的長胡子山羊,還有我漂亮可愛的妻女。我們圍起一個大院子、一個家。這個家里還會有更多生命來臨:樹上鳥、檐下燕、冬夜悄然來訪的野兔……從每個動物身上我找到一點自己。我飼養它們以歲月,它們飼養我以骨肉。”劉亮程的這段文字,像是村莊發來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