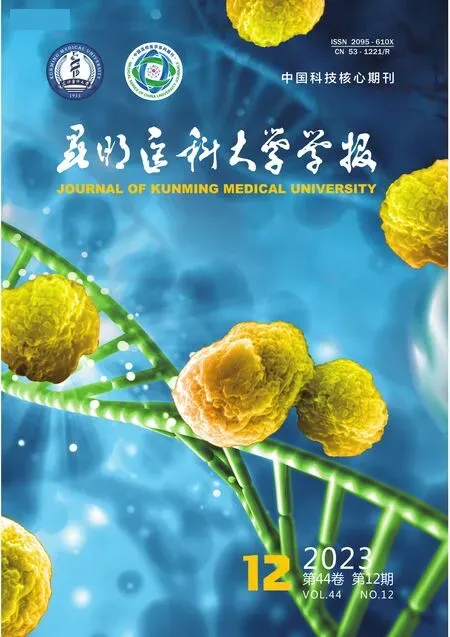兒童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癥31 例的臨床分析
李海金,段正鋮,周 燕,王柳方,楊春會,田 新
(昆明市兒童醫院/昆明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科,云南 昆明 650228)
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癥(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是1 種相對罕見的組織細胞增生癥。致癌性的BRAF-V600E 基因突變在超過50%的LCH 病理組織中被發現[1],目前認為LCH 是一種起源于樹突狀細胞的髓系前體細胞的炎性髓系腫瘤,是免疫失調和腫瘤克隆性增殖共同作用的一類疾病[2-3]。LCH 臨床表現多樣、異質性突出,盡管傳統化療方案不斷優化,但頻繁復發、難治和后遺癥問題仍突出,針對BRAFV600E 基因的靶向治療逐漸廣泛應用于臨床,遠期預后有待繼續觀察。因此,本研究回顧性分析昆明市兒童醫院血液腫瘤科2017 年2 月至2021年12 月收治的LCH 患者的臨床特點及預后情況,旨在探討BRAF-V600E 突變與臨床特征及預后情況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資料
收集昆明市兒童醫院血液科2017 年2 月至2021 年12 月期間收治的診斷明確、資料完整的31 例兒童LCH 病例進行回顧性分析。所有病例均參考國際組織細胞協會《朗格罕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癥評估與治療指南》療效標準[4],經組織病理學及免疫組化確診,均完善全身系統檢查,根據器官受累情況及BRAF-V600E 突變情況進行分組,綜合分析患兒臨床特征及預后。
1.2 診斷標準[4]
臨床表現符合,同時符合以下病理診斷標準:在光鏡下發現典型LCH 細胞基礎上,具備以下4 項中至少2 項可初步診斷:(1))ATP 酶陽性;(2)CD31/S-100 蛋白陽性;(3)α-D-甘露糖酶陽性;(4)花生凝集素受體陽性。在初步診斷基礎上,具備以下3 項中至少1 項可確診:(1)Langerin 蛋白(CD207)陽性;(2)CD1a 抗原陽性;(3)病變細胞電鏡下發現Birbeck 顆粒。
1.3 治療前評估及分類
所有確診病例均進行全身系統檢查(血常規、血生化、CT/MRI、骨骼、腹部超聲、骨髓檢查等),對患兒病情及器官功能狀況進行全面評估。臨床分類[4]主要分為單系統受累組(SS-LCH)和多系統受累組(MS-LCH)2 大類,SS-LCH 指單一器官/系統的單發或多發病灶,如骨骼、皮膚、淋巴結等,MS-LCH 指≥2 個器官/系統受累,伴或不伴危險器官受累。危險器官特指肝臟、脾臟、骨髓/造血系統。
1.4 治療方案
納入分析的31 例病例采用上海兒童醫學中心LCH-2011 修訂版治療方案(SCMC-LCH-2011)進行治療。BRAF-V600E 突變陽性患者,經監護人知情同意,在化療基礎上加用靶向抑制劑達拉非尼口服治療[達拉非尼5 mg/(kg·d),分2 次口服]。
1.5 療效判定
參考SCMC-LCH-2011 方案的療效評價標準[4],于誘導治療6 周后進行療效判斷,療效評價分為反應好和反應差,其中反應好包括完全緩解和好轉,反應差包括疾病進展和復發。完全緩解:無疾病證據,所有癥狀、體征消失;好轉:癥狀、體征好轉但未達完全緩解標準且無新發病變;進展:病變好轉但出現新發病變,疾病活動性進展;復發:疾病達完全緩解或好轉后,病變再度發作或合并新發病變。
1.6 隨訪
末次隨訪時間截止至2022 年2 月28 日。
1.7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26.0 進行數據統計處理,計量資料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采用中位數和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描述;計數資料采用率或百分比(%)表示;兩樣本率比較采用卡方檢驗或Fisher 精確檢驗。以P< 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及危險度分組情況
31 例患兒中男性18 例(58%),女性13 例,男女比例1.38∶1。發病年齡分布在1 個月至7 歲之間,中位年齡為10 個月,其中28 例(90.3%)初診年齡小于3 歲,21 例(67.7%)初診年齡小于1 歲。31 例患兒中22 例為MS-LCH(71%),9 例為SS-LCH(29%),首發癥狀中:皮疹/皮膚軟組織損害21 例,骨質損害12 例,肝和/或脾腫大17 例,發熱15 例,淋巴結腫大7 例,至少2 系減少7 例,肺受累6 例,中耳炎5 例,垂體受累(尿崩癥)3 例,口腔/肛周潰瘍2 例,體表腫物1 例等。5 例患兒臨床表現為尿崩癥,并經影像學證實有垂體受累,其中2 例(MS-LCH 和SS-LCH各1 例)分別在維持化療階段和結療后復發時出現垂體受累。9 例SS-LCH 患兒首發癥狀中,4 例為皮膚受損,4 例為骨質受損,1 例為前胸壁腫物。22 例MS-LCH 患兒首發癥狀涉及多個系統,皮膚損害、骨質損害、發熱、淋巴結腫大等,見表1。

表1 SS-LCH 與MS-LCH 患兒的臨床特征[n(%)]Tab.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of SS-LCH and MS-LCH children[n(%)]
2.2 BRAF-V600E 突變情況
31 例病例中,有27 例通過病灶活檢組織進行BRAF-V600E 基因檢測,20 例檢測陽性,其中MS-LCH 組陽性率89.5%(17/19),SS-LCH 組陽性率37.5%(3/8),2 組間BRAF-V600E 突變陽性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isher 精確檢驗,P=0.011)。BRAF 基因突變陽性組與陰性組之間性別與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2。

表2 BRAF 基因突變陽性與陰性患兒臨床特征[n(%)]Tab.2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BRAF gene mutations[n(%)]
2.3 治療評價及隨訪觀察
31 例患兒初治均參考SCMC-LCH-2011 化療方案化療,20 例BRAF-V600E 突變陽性患兒在化療基礎上均加用靶向藥治療。31 例患兒均于誘導治療6 周后進行療效評價,9 例SS-LCH 為治療反應好,總有效率100%(9/9);MS-LCH 中18例治療反應好,4 例治療反應差,總有效率81.8%(18/22),反應差中有3 例合并危險器官受累。隨訪至觀察期止(隨訪時間3 個月~62 個月),共有10 例出現疾病進展/復發,進展/復發率達32.3%(10/31),其中3 例為SS-LCH,7 例為MSLCH;3 例死亡,均為MS-LCH 合并危險器官受累。
3 討論
LCH 在兒童及青少年(15 歲以下)的發病率在2.6 至8.9/100 萬,任何年齡段均可發病,診斷時年齡中位數在3~3.5 歲,1 歲以內發病率最高[5-6],本研究納入的31 例病例中,90.5%的患兒初診年齡小于3 歲,67.7%的患兒1 歲以內起病,與文獻報道一致。LCH 臨床表現多種多樣,異質性顯著,嚴重程度不一。約80%的患兒首發表現是缺乏特異性的皮膚損害,尤其是嬰幼兒[7]。本研究中最常見的首發表現是皮膚損害,骨質破壞、危險器官受累和發熱亦較常見,SS-LCH 病例中以皮膚損害或骨質破壞最常見。下丘腦-垂體軸受累常表現為尿崩癥,顱骨長期受累更易合并尿崩癥和中耳炎[4,8-9]。本研究中有5 例合并垂體受累/尿崩癥,其中1 例發生在維持化療階段,1 例發生在結療后,提示尿崩癥可以發生在LCH病程的任何階段,臨床需引起重視。
BRAF-V600E 基因突變是BRAF基因最常見的基因突變之一,這是1 種致癌性基因突變,在多種惡性腫瘤中(如黑色素瘤、結直腸癌、甲狀腺癌等)被發現,該突變使BRAF 持續性激活,經RAS-RAF-MEK-ERK 通路促進細胞增殖,最終導致腫瘤細胞克隆性增殖[2-3,10]。針對BRAFV600E 突變的分子靶向治療也逐漸廣泛應用于臨床[4,11]。本研究中27 例患兒進行該突變檢測,MS-LCH 組陽性率89.5%,SS-LCH 組陽性率37.5%,提示BRAF-V600E 基因突變更常見于多系統受累的病例,與文獻報道一致[12]。多數研究認為[13-15],多器官/系統受累、危險器官受累均與預后不良相關,而BRAF-V600E 基因突變與LCH 患者臨床特征及預后的相關性仍不十分明確。一些大樣本的回顧性研究[12,16]發現BRAFV600E 基因突變與多系統受累、化療耐藥、復發及LCH 相關神經系統退行性病變相關。同時有研究發現[3,17],BRAF-V600E 基因在不同類型病變細胞中表達的預后風險有所不同,骨髓造血干細胞存在BRAF-V600E 基因突變的LCH 常常表現為高復發風險。來自歐洲的1 項多中心研究發現[18],BRAF 靶向抑制劑—維莫非尼(Vemurafenib)可以顯著降低BRAF-V600E 突變陽性的難治性、多系統受累LCH 兒童的疾病活動度,并迅速獲得臨床緩解,但并不能完全根除BRAF-V600E 突變載量,大多數患兒停藥后迅速復發。一些小樣本的臨床研究[19-20]發現達拉非尼(Dabrafenib)單藥或聯合曲美替尼(Trametinib)治療復發、難治性LCH 均顯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中20 例BRAF-V600E 突變陽性患者加用了靶向抑制劑達拉非尼治療,BRAF-V600E 突變陽性與陰性2 組間生存率比較無統計學差異,可能提示靶向藥物的應用改善了BRAF-V600E 突變帶來的不良結局,但鑒于樣本量相對較小及隨訪時間等潛在影響因素,BRAF-V600E 突變靶向治療的臨床療效仍需更多高質量臨床研究進一步探索。
本研究結果表明,LCH 在嬰幼兒中常見,垂體受累并發尿崩癥可發生在病程任何階段,應引起臨床重視并長期隨訪,多數患兒對化療敏感、6 周誘導治療后反應良好,但病情進展、復發問題仍然突出。本研究中BRAF-V600E 突變在MSLCH 病例中更常見,但BRAF-V600E 基因突變對LCH 臨床特征及靶向藥物達拉非尼對預后的影響,有待進一步開展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進行驗證,以探索更優化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