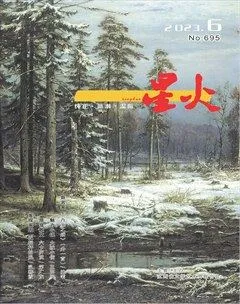嗦螺
漆宇勤,1981年生,江西萍鄉(xiāng)人。中國(guó)作協(xié)會(huì)員、中國(guó)詩歌學(xué)會(huì)會(huì)員,魯迅文學(xué)院第34屆高研班結(jié)業(yè),參加第35屆青春詩會(huì)。在《人民文學(xué)》《人民日?qǐng)?bào)》《詩刊》《星星》《青年文學(xué)》《北京文學(xué)》《散文》等報(bào)刊發(fā)表詩歌散文3300余首(篇)。出版作品集《在人間打盹》《靠山而居》《翠微》《放鵝少年》《抵達(dá)》等21部。
嗦螺是一個(gè)名詞,嗦螺也是一個(gè)動(dòng)詞。
作為名詞的嗦螺指帶殼烹炒的螺螄,作為動(dòng)詞的嗦螺指吸食螺螄的動(dòng)作。
螺螄是個(gè)古老到了極致的物種。我們看遙遠(yuǎn)時(shí)代的化石,螺貝是品類繁多又最常見的類別。與它同時(shí)代的那些物種,后來有的進(jìn)化出奇怪兇猛的外表,有的演變出更加?jì)扇醯捏w質(zhì)。狹窄的食物譜系和適應(yīng)空間,讓它們其中的很多現(xiàn)在都成了要靠特殊保護(hù)才能維持基本種群數(shù)量的珍稀動(dòng)物。
而螺螄要隨性得多,幾乎適應(yīng)各類水生態(tài)環(huán)境。不拘江河湖海,不拘灘涂濕地,不拘池塘稻田,不拘山溝水渠,螺螄隨遇而安,落地就繁衍。有一年春天,我從村子里的灌溉渠里撿了幾個(gè)螺螄扔進(jìn)家里的魚缸。幾個(gè)月過去,整個(gè)魚缸爬滿了細(xì)密的小螺螄。
它們不挑食。濕地里的植物水藻、細(xì)碎的有機(jī)物、水中可以濾出的各種浮游生物都是螺螄的食物。
它們也耐旱。母親一直跟我說,螺螄不怕干三年,就怕扔過三丘田。我對(duì)這句俗語的理解是,螺螄耐旱,但是不耐震撞磕碰。以前鄉(xiāng)下有的池塘沒有水源,全靠春天里下雨蓄起滿塘的水,然后逐漸被灌溉消耗或蒸發(fā)滲漏掉。中秋過后,池塘漸漸就干枯見底了。到第二年春天漲春水前,我們?nèi)コ靥晾锇褰Y(jié)的泥地上玩,看見一個(gè)個(gè)圓形的深凹坑,往下掏摸,總能在十幾二十厘米深處掏出螺螄。在池塘干枯四五個(gè)月后,它們依舊活著。
即便到了現(xiàn)代,除了自己種的植物與養(yǎng)的動(dòng)物之外,采集、漁獵依舊是人類滿足生活所需的一種補(bǔ)充,更不用說古代了。采集野果野菜野蜂蜜,獵取山里的飛禽走獸爬蟲,捕撈水里的各類水生物。這其中,撿拾螺螄可能是相對(duì)容易的事情。螺螄沒有尖牙利爪,撿拾時(shí)也不需進(jìn)入深水區(qū)和深山區(qū),不需掐準(zhǔn)草木時(shí)令,甚至不需要長(zhǎng)途跋涉、目的明確地去尋找。它一年四季就在村頭村尾,稻田間,水渠中,池塘里。因此,螺螄仿佛具有了某種身邊物與家常物的性質(zhì)。
很小的時(shí)候就聽過那個(gè)讓人神往的故事。故事說,勤勞老實(shí)的農(nóng)民撿回家的大田螺每日化身為少女給他做飯。后來我長(zhǎng)大一些,通過不同的書本,發(fā)現(xiàn)在這個(gè)故事梗概下,衍生出了細(xì)節(jié)稍異的各種版本。故事的發(fā)生地,幾乎遍布了中國(guó)南方和中部多數(shù)有水有湖有田的地方。
中國(guó)的民間傳說故事都有典型的現(xiàn)實(shí)根基。田螺姑娘寄寓了眾多鄉(xiāng)村獨(dú)身青年的憧憬,也寄寓著眾多農(nóng)民的幻想。他們選擇了日常多見的田螺作為載體,讓夢(mèng)想的可能性與可親性比那些虛無縹緲的神仙幻想強(qiáng)了許多—畢竟,將同樣可能成精的狐貍和田螺進(jìn)行比較,田螺還是更接近身旁。
想一想吧,在日常勞作、日常途經(jīng)的田間地頭,俯身就可撿拾到數(shù)量繁多的田螺。如果稍微多花費(fèi)一點(diǎn)時(shí)間,就可以為晚餐添加一碗佐餐的佳肴。這可是比魚類更容易獲取、比蔬植更富營(yíng)養(yǎng)的肉食葷腥。它們背著厚厚的外殼,卻又沒有用來跑路的腳。因此即便是被驚擾了,田螺也只是迅速收回外探的觸角和大半個(gè)身子,整體縮回自己的殼里,然后一動(dòng)不動(dòng)。所以贛西俗語說,“三個(gè)指頭抓田螺,十拿九穩(wěn)”。
我相信,定曾有過那么一些村子與村民,依靠螺螄緩解食物匱乏的困窘。
在我生活的龍背嶺,人們也時(shí)常在夏秋兩季到溝渠水田和池塘里撈田螺。我們叫撿螺螄。是的,在這里,我們將田螺與螺螄簡(jiǎn)單地進(jìn)行了模糊處理。實(shí)際上,龍背嶺常見的螺螄有幾種。其中一種外殼狹長(zhǎng),我們稱其為石螺;另外一種外殼短圓,我們稱其為田螺。但是這種具體化的專業(yè)稱呼只在很少的時(shí)候使用。更多的時(shí)候,我們將村子里能夠看見的一切螺螄都統(tǒng)稱為田螺—我們也不知道中華圓田螺、環(huán)棱螺這一類的名稱。
春天里,田螺完成了它一年中的第一次繁衍。夏天開始,我們便下到水里撿田螺了。河流淺水洄旋處的田螺經(jīng)常是成群成堆地出現(xiàn),撿田螺的人躬下身便捧起一大把,可惜一般都是中小個(gè)頭的;池塘里的田螺總是縮在淤泥里,撿田螺的人得靠雙腳或雙手一路摸索過去,泥巴里捏出一個(gè)硬物,基本就是田螺或河蚌了;稻田里的田螺顯露于田埂邊、稻苗下,人們總是在干耘田除草放水等農(nóng)活時(shí)順手將它們給撿回家;而溝渠里的田螺一目了然,站在水圳邊上便可以看到,這里一枚,那里一枚,撿田螺的人基本都是挑個(gè)頭碩大的往臉盆或者荷葉芋頭葉里放,往往有二三十枚就可以炒上一小菜碗。
撿田螺的最佳時(shí)間是早晚時(shí)分。這時(shí)氣溫不高,田螺們都從泥洞里鉆出來了,一目了然。當(dāng)然還有一個(gè)原因,早晚是一天勞作之余的零星時(shí)間,撿田螺不耽擱干活。
田螺們都保持磊落的古風(fēng)。它們?cè)谟倌嗬锇布遥厝粫?huì)在泥面上留下特點(diǎn)鮮明的凹洞,掏下去一抓一個(gè)準(zhǔn)。即便是外出覓食或者遷徙,也會(huì)留下一路滑行的明顯痕跡。可能再?zèng)]有其他動(dòng)物像田螺一樣在大地上留下如此真實(shí)連貫的足跡了。
有時(shí)候,淺水清澈透底的田間和水圳里,一只螺螄、兩只螺螄在平整的泥底劃出曲線,像一個(gè)外出旅行的人留下深深的軌跡或車轍。這抽象的線條與倒映在水中的草木之影相得益彰,很適宜一個(gè)無聊又無事的少年在田埂上觀望和想象,消耗時(shí)光。二十多年前,我初學(xué)攝影,最喜歡拍攝家門口泥池里田螺的移動(dòng)軌跡,那些透過水面顯露的光影線條,仿佛在底片上形成了某種神秘的符篆。
撿回家的田螺都會(huì)暫養(yǎng)在水盆水桶里三五天,待到它們吐凈泥沙了,再進(jìn)入烹飪的程序。要將田螺肉從曲廊回旋的螺螄殼里取出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龍背嶺的主婦們習(xí)慣將吐凈泥沙的田螺放進(jìn)開水里迅速焯一下,然后拿尖竹簽、鋼針之類的工具將螺肉挑出。挑螺螄肉也是個(gè)技術(shù)活,要迅速地去掉粘連在螺肉上圓蓋一般封堵螺螄殼口的厴,將螺肉挑出并去掉不適宜食用的部分,既考驗(yàn)細(xì)心,也考驗(yàn)?zāi)托摹蛘撸€要考驗(yàn)狠心。田螺是卵胎生動(dòng)物,雌螺體內(nèi)往往揣著數(shù)以百計(jì)的幼體。很多田螺在螺肉被挑出的過程中,都能從螺殼底部帶出一大簇的小田螺,其中很多已經(jīng)完全成形,是縮微版田螺的樣子。
我記得有一回?fù)斓奶锫萦悬c(diǎn)多又有點(diǎn)小,我蹲在家門口的柚子樹下挑田螺肉,大半個(gè)小時(shí)過去了,依舊沒能完工。暮色深處,田螺的腥味吸引了成群的蚊子嗡嗡飛舞,叮得我渾身疼癢,偏偏兩手都是黏糊糊的臟污,既打不得蚊子,又撓不得癢。
但田螺肉炒紅辣椒,是無比鮮美可口的菜肴,既下飯,又滋補(bǔ)。
也有不用于制作佐餐的菜肴而是側(cè)重休閑口味的時(shí)候。這時(shí)的田螺就不用去殼挑肉了,直接剪去田螺殼的尖尾,連殼帶肉加入大量的調(diào)料放鍋里烹炒。這樣炒制出來香辣無比的田螺被我們稱為嗦螺。撮一粒在嘴里吮吸,濃郁的調(diào)料味與田螺的本味雜糅,讓人越吃越想吃,欲罷而不能。
辣椒炒田螺肉是母親的拿手菜。嗦螺卻不是她所擅長(zhǎng)的菜式。炒嗦螺的高手集中在本縣另外一個(gè)鎮(zhèn)子里。
這是一個(gè)名叫桐木的鎮(zhèn)子,江西與湖南兩省在這個(gè)鎮(zhèn)子里有著犬牙交錯(cuò)般的邊界。當(dāng)?shù)匾粋€(gè)老人很認(rèn)真地告訴我:鎮(zhèn)子里有人家的房子廳堂在上栗,臥室在宜春,廚房在瀏陽。我將老人的話當(dāng)成夸張與玩笑,不太相信邊界插花地帶會(huì)有宅基地選得這么巧合。但這個(gè)10萬人口的鄉(xiāng)鎮(zhèn)地處贛湘兩省三市的邊界,倒真實(shí)不虛。
桐木鎮(zhèn)炒嗦螺的高手也不是遍布全鎮(zhèn),而是主要集中在一個(gè)村子里。
這是一個(gè)名叫楚山的村子。楚是楚國(guó)的楚,山是山嶺的山。村子里有楚王臺(tái),有供奉楚昭王的祠廟,也有信奉屈原的民間信仰。楚山之上,石壁上依舊有種種牽強(qiáng)附會(huì)但又隱有聯(lián)系的傳說,還有韓愈詩《楚王臺(tái)》“真跡”。楚王臺(tái)全國(guó)各地有不少,韓愈寫了《楚王臺(tái)》也確鑿,他曾到過贛西上栗也是史實(shí)。但石壁上的簡(jiǎn)化字毛筆筆跡透出村民們某種可愛的天真。
既然已經(jīng)說了與楚國(gu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那么楚國(guó)那溝渠密布、濕地沼澤隨處點(diǎn)綴的地理特性,自然也適用于桐木,適用于楚山。
可以想見,在農(nóng)耕時(shí)代,桐木或者楚山的溝渠稻田、河流水塘、濕地沼澤,到處都是螺螄活躍的空間。
那時(shí)的田螺,因?yàn)槭澄镓S富又少有打擾,生得年深日久者(實(shí)際田螺只在前幾年生長(zhǎng)體型),想來偶爾會(huì)有突破常規(guī),長(zhǎng)得拳頭大小一個(gè)的吧。個(gè)頭大了,年歲久了,自然田螺姑娘的故事也就有了基礎(chǔ),更多與田螺有關(guān)的神話傳奇也就有了基礎(chǔ)。幼年時(shí),讀過一本缺頁的《仙佛全傳演義》,隱約記得里面有田螺成道,后來因緣際會(huì)諸多仙佛人物在螺殼里匯聚做法事的情節(jié)。我一直將此視為俗語“螺螄殼里做道場(chǎng)”的源頭。但近來查看網(wǎng)絡(luò)資料,卻大都說這一俗語的來源是另外的民間傳說。
不管來源如何,螺螄殼里做道場(chǎng),形象又貼切。尤其是對(duì)于經(jīng)常撿田螺、吃田螺、熟悉螺螄殼的人來說,這樣一句俗語的豐富且復(fù)雜的況味,細(xì)細(xì)一咂摸,就會(huì)不禁沉默。
楚山村的楚是楚昭王的楚,楚王臺(tái)的王是昭王的王。《孔子家語》說楚昭王在萍鄉(xiāng)渡江撿到一個(gè)漂浮的紅色果實(shí)卻不知名,最后孔子辨識(shí)出來說是“萍實(shí)”。后來黃庭堅(jiān)也專門寫詩說起這個(gè)典故,說萍鄉(xiāng)就是因?yàn)槠紝?shí)之鄉(xiāng)而得名。楚山村屬于桐木鎮(zhèn),桐木鎮(zhèn)屬于上栗縣,上栗縣屬于萍鄉(xiāng)市。楚山人相信,當(dāng)年楚昭王撿到萍實(shí)的地方,就是在上栗的大河里,楚昭王曾在桐木留下大量的活動(dòng)痕跡。
我跟村里的老人開玩笑,那當(dāng)時(shí)楚山人有沒有給楚昭王炒上幾碗嗦螺呢?
大家都笑。我們都沒有專業(yè)的歷史知識(shí),不清楚楚昭王時(shí)代的食物烹煮水平和調(diào)料普及程度是個(gè)什么情況。那時(shí)的人們,學(xué)會(huì)了將田螺作為食物來源嗎?又學(xué)會(huì)了以什么樣的方式來烹制螺螄呢?
如果從楚山人現(xiàn)在烹炒嗦螺的幾種主要調(diào)料在歷史上被普遍使用的時(shí)間來看,至少當(dāng)時(shí)楚昭王是沒有口福嘗到今天這種口味的嗦螺。
今天這種口味的嗦螺匯集了贛西地區(qū)最常見的辣、鮮、咸、香等諸多口味,甚至也匯集了大眾美食所需要的各種視覺和嗅覺效果。村子里的人實(shí)誠(chéng),老老實(shí)實(shí)將自己村子里常用配方和烹炒方法制作出來的嗦螺冠以村名,稱為楚山田螺。沒有哪一家哪一戶將此作為私有的品牌,也沒有哪一家哪一戶對(duì)烹炒工藝諱莫如深。
這種開放的態(tài)度,催生了大批的夜宵店鋪以楚山田螺為招牌,也催生了近十家的食品工廠專門生產(chǎn)楚山田螺。
每到夏天的夜晚,贛西地區(qū)的夜宵攤點(diǎn)上,總是少不了一份嗦螺。夜宵攤點(diǎn)是個(gè)神奇的地方,夜宵相聚的人應(yīng)該都是親密的人。
我不常見陌生的人相約一起吃夜宵、吃嗦螺,他們只宜到酒店包廂里正襟危坐進(jìn)行交流。而一起吃嗦螺,總是有幾分親近和隨意,不講究排場(chǎng)而側(cè)重個(gè)體的放松體驗(yàn)。
嗦螺的吃法似乎有幾分粗獷,幾個(gè)大老爺們配上幾瓶啤酒,邊嗦邊大聲說話,那嗦螺的香味,很快就彌漫整個(gè)就餐空間。
但是,不要忘了,嗦螺的菜碗前,女性似乎也不少。想象一下,餐桌前的纖纖玉手,伸出兩根手指,撮起一粒螺,放嘴邊輕嘬。轉(zhuǎn)眼間身前就堆滿了螺螄殼,轉(zhuǎn)眼間兩手就滿是湯汁。對(duì)于講究的人來說,這樣的場(chǎng)景只宜在親密者面前呈現(xiàn)。
實(shí)際上一起嗦螺的人都沒有這種顧忌。既然是嗦螺,要的就是這種酣暢淋漓,要的就是這種味蕾爆炸。所以,我一直認(rèn)為,能夠一起吃嗦螺的人,定然都是隨和隨性的人。
就像嗦螺本身,用各種調(diào)料隨性地翻炒烹煮。也像田螺本身,在各種場(chǎng)所隨性活,隨性吃,隨性長(zhǎng)。超強(qiáng)的適應(yīng)性,讓田螺成了自然生態(tài)水體里治污的好物種。超強(qiáng)的繁殖力,讓田螺在一些養(yǎng)殖場(chǎng)成了螃蟹、青魚的好食物。
同樣隨性的夜宵攤,漸漸也衍生出了夜市經(jīng)濟(jì)的概念,衍生出了吃嗦螺和炒嗦螺的人的煙火人間,衍生出了一個(gè)嗦螺生產(chǎn)產(chǎn)業(yè)。
在吃過嗦螺很多年,也早已不到水里撿田螺很多年后,我偶然來到了楚山村。那一次之后,我到楚山村,不為訪古,也不為考據(jù),只為了嗦螺而來。在這個(gè)村子里的田螺繁育基地,各種各樣的螺螄扎著堆。但田螺食品廠的采購(gòu)經(jīng)理告訴我,這樣的畫面根本算不了什么。在一些大湖大河里,在螺螄的主產(chǎn)區(qū),工人們都是用挖掘機(jī)采挖螺螄的,經(jīng)常是數(shù)十噸一次地出貨。在這個(gè)村子里的田螺加工廠,各種口味各種包裝的田螺堆成山。但附近臨時(shí)攤點(diǎn)排成兩公里長(zhǎng)的夜宵街上的廚師告訴我,這樣的產(chǎn)量根本算不了什么,嗦螺幾乎是有多少就能消耗多少。
我看著一個(gè)小小村莊里的田螺清洗池,看著一張窄窄出貨單上各色口味的嗦螺貨品,看著每天數(shù)字驚人的交易量,仿佛看到了餐桌前撮起嗦螺的纖纖玉手,仿佛看到了河湖間舉起挖掘斗的捕撈船。
突然地,就想起了幼時(shí)鄉(xiāng)間赤腳下水撿田螺的樸素與天然,想起田螺姑娘的故事和紅辣椒炒田螺的鮮香。那種佐餐的鄉(xiāng)間菜肴,與嗦螺有著完全不同的滋味。突然地,就想起來要感謝田螺強(qiáng)大的適應(yīng)性和繁殖力,要感謝養(yǎng)殖田螺、繁育田螺的人,讓天然水域的一部分田螺,還能夠繞過嗦螺產(chǎn)業(yè)的碾壓,繼續(xù)野生野長(zhǎng),讓古老的田螺繼續(xù)綿延自己的傳奇,讓更多喜歡嗦螺的人在很多年之后還可以繼續(xù)有螺可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