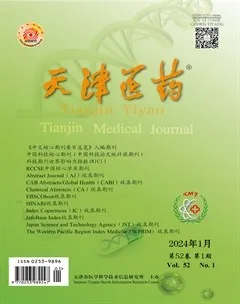氣道類器官顯微注射及極性反轉模型的構建
宋立成,張宇涵,余忠闊,解立新△
研究表明,體外生長的3D類器官能夠再現體內對應器官的基本屬性,成為研究損傷和修復再生的有力工具[1]。肺成體干細胞(adult stem cells,ASCs)衍生的類器官完全由上皮細胞組成,較普通2D培養平面可動態展示細胞增殖分化過程,這更有利于呼吸道病毒感染后肺損傷的體外研究[2-3]。ASCs 分化成各類上皮細胞后,形成正常的頂端連接復合體,并具有上皮極性,但頂端或管腔表面包裹在類器官球體內,而面向球體外部的基底外側表面與細胞外基質(ECM)相互作用[4]。氣道上皮許多功能需要接觸球體的頂面或腔面,包括微生物相互作用,吸收藥物或毒素。類器官極性內向(apical in,AI)的特點有可能限制其在感染模型中的廣泛應用[5]。然而通過機械破碎氣道類器官使頂端表面暴露于培養基中的方法不能精確復制感染過程,甚至可能引起非特異性反應[6]。本研究旨在開發一種類器官顯微注射模型,將病毒注射入類器官,使微生物與上皮極性表面直接接觸造成感染。為了更好地模擬呼吸道病毒感染,筆者優化實驗條件,成功構建極性外向(apical out,AO)肺類器官,增加呼吸道病毒對上皮的可及性,為呼吸道感染研究提供新平臺。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材料 8 周齡雄性SPF 級C57BL/6 小鼠60 只,體質量18~20 g,購自斯貝福(北京)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動物生產許可證號:SCXK(京)2019-0010。小鼠均用于肺組織獲取及類器官培養。小鼠飼養于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SPF級動物房內。分選磁珠為去死細胞磁珠、CD45 磁珠及CD326(EpCAM)磁珠均購自Miltenyi Biotec 公司。DMEM/F12、B27 補充劑、GlutaMAX、青霉素-鏈霉素雙抗溶液購自Invitrogen 公司。Rspondin1、Noggin 購自MedChemExpress 公司。 N-acetylcysteine、Nicotinamide、SB431542、SB202190、CHIR99021 購自Sigma 公司。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GF)-7、FGF-10 購自Peprotech 公司。ROCK 抑制劑Y-27632 購自STEMCELL 公司。兔抗鼠α-微管蛋白(α-tubulin)抗體購自Proteintech 公司,大鼠抗小鼠緊密連接蛋白(ZO-1)購自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公司,驢抗兔二抗IgG H&L(Alexa Fluor?568)及羊抗大鼠IgG H&L(Alexa Fluor?647)抗體購自Abcam 公司。無生長因子基質膠、transwell 小室及配套的24 孔板購自Corning 公司。顯微鏡為徠卡公司的DMI3000 B型,顯微操作系統為艾本德公司的TransferMan?4r 型,微量自動注射儀為艾本德公司的FemtoJet?4x 型,微量移液器拉拔器為Sutter 公司的P-97 Flaming/Brown 型。綠色熒光蛋白(GFP)標記的流感病毒PR8(GFP-PR8)為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方敏實驗室贈送。PCR 試劑盒、TRIzolTM試劑和反轉錄試劑盒購自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
1.2 實驗方法
1.2.1 呼吸道原代上皮細胞的獲取 參照Li等[7]的方法,1%苯巴比妥5μL/g 麻醉小鼠,切開腹膜后剪斷腹主動脈,沿胸骨柄剪開胸廓,結扎氣管,將1.5 mL 注射器吸取少量混合分散酶和膠原酶D的酶液注入肺內,將肺鼓起。將結扎后的肺取下,置于磷酸鹽緩沖液(PBS)中漂洗,在3 mL 的Hanks'平衡鹽溶液中室溫消化30 min。將肺組織在DNase+DMEM 的培養基中將肺葉解離并切碎,置于搖床上按照300 r/min震蕩15 min。使用70μm及40μm篩網過濾組織懸液,1 200 r/min離心5 min后,懸液加入紅細胞裂解液1 mL置于37 ℃培養箱90 s。再次離心、重懸、計數,將細胞移至6 孔板中培養。按照說明書要求,分別采用去死細胞磁珠、CD45磁珠及CD326磁珠對獲取的單細胞懸液進行抗體特異性陽性選擇和陰性選擇,以獲取上皮細胞進行肺類器官構建。
1.2.2 培養基的配制 參考多項研究對氣道類器官培養基進行整合優化[8-10]。根據生長及分化需要,培養基分為擴增及分化兩種類型。在培養的第1周,采用擴增培養基誘導干細胞增殖并形成類器官,從第2周起改為分化培養基,促進干細胞向終末細胞分化。干細胞擴增培養基的主要成分包括Advanced DMEM/F12、雙抗(1%)、Rspondin1(500 μg/L)、Noggin(100 μg/L)、B27 添加物(2%)、Y-27632(5 μmol/L)、SB431542(10μmol/L)、SB202190(1μmol/L)、FGF-7(5μg/L)、FGF-10(20μg/L)、CHIR99021(3μmol/L)。干細胞分化培養基在擴增培養基基礎上添加10%胎牛血清(FBS),并去除SB431542和CHIR99021。
1.2.3 類器官模型的構建 參考Li等[11-12]的方法,獲得的上皮細胞在干細胞擴增培養基中稀釋,調整細胞含量為2×106/mL,放置無菌冰上。將4 ℃解凍的無生長因子基質膠在冰上用預冷低溫低吸附槍頭與細胞懸液等體積混合。在37 ℃細胞培養箱中放置transwell 小室及配套的24 孔板,30 min 后拿出。迅速將100μL 細胞懸液加入小室底部,所有小室添加完畢后,將24孔板再次放入細胞培養箱中,每隔10 min將24孔板上下翻轉放置。30 min 后拿出24 孔板,在小室外每孔加入410μL 干細胞基礎培養基,覆蓋小室底層膜。此后每隔2 d更換下層培養基。1周后更換為類器官分化培養基。2周后進行傳代。采用傳3代的類器官進行后續實驗。
1.2.4 類器官顯微注射 使用拉拔器將1 mm的細絲毛細管拉至一個細點,注射針經酒精燈加熱形成90°彎曲,最大限度地減少注射過程中基質膠中斷和針斷裂。在針頭直徑漸變至20μm處用細鑷子鉗斷注射針。在微量注射前的7 d,將類器官進行傳代培養。選取橫斷面半徑為60~80μm 的類器官作為注射對象。通過使用0.4 nL 0.8%的70 ku FITC-dextran 靶向類器官進行微注射來評估該平臺的效率。設置注射儀參數:注射壓力200 hPa,注射時間0.1 s,補償壓力2 hPa。觀察注射前后類器官直徑的變化。
1.2.5 類器官極性反轉 將transwell小室從24孔板取出,放置于超低吸附的6孔板中,每孔中加入3個transwell 小室,并加入5 mL EDTA 溶液,在4 ℃搖床上100 r/min 震蕩60 min。用1 mL低吸附槍頭輕柔沖洗transwell小室底膜,直至基質膠全部回收。將6孔板內的EDTA溶液及消化后的基質膠全部放入15 mL 離心管中,4 ℃,200×g,離心3 min,去除上清液,加入干細胞擴增培養基3 mL,然后轉移至超低吸附6孔板中繼續懸浮培養。每隔2 d,小心吸取上層1/3的培養基進行換液,并輕柔混勻整個培養基。通過光學顯微鏡每日統計各transwell內反轉的類器官的比例(5個transwell為一組進行合并統計)。培養1 周后,將類器官4 ℃,200×g,離心3 min,重新鋪到基質膠中,通過HE染色鑒定是否反轉成功。
1.2.6 流感病毒感染類器官實驗 將普通類器官培養體系的下層營養液更換為同體積病毒維持液,分別加入0.1、0.01、0.001 感染復數(MOI)的GFP-PR8 病毒,在37 ℃下孵育2 h。將病毒維持液吸凈,用PBS清洗小室外層及孔板內部3次,再添加等體積干細胞擴增培養基,24 h后觀察類器官形態及熒光產生情況。在類器官注射實驗中,計算類器官體積后,按照60μL/mm3分別將PBS、GFP-PR8、PR8注射入類器官球中,在接種期間和接種后分別在下層培養基中加入絲氨酸蛋白酶抑制劑0.125 mmol/L。24 h 后,收集小室底部的基質膠并進行HE 染色及熒光染色。在類器官反轉模型中,將反轉后的類器官的培養基更換為病毒維持液,加入0.01 MOI 的GFPPR8病毒,在37 ℃下孵育2 h后進行洗滌,隨后將接種的類器官重新包埋在基質膠中,然后在擴增培養基中培養。在PR8感染中,將4塊6孔板中懸浮培養的類器官分成4組,分別為對照組、感染0.001 MOI 組、感染0.01 MOI 組、感染0.1 MOI組,在37 ℃下孵育2 h。在接種期間和接種后分別用絲氨酸蛋白酶抑制劑(0.125 mmol/L)處理PR8 接種的類器官。24 h后,對照組及各濃度感染組收集類器官進行后續免疫熒光及PCR分析,重復6次。對類器官進行PCR分析時,將Trypsin-EDTA 200 μL 加入上層小室中,對應24 孔板中加入500 μL Trypsin-EDTA,在37 ℃細胞培養箱中放置30 min,每隔10 min 用1 mL 槍頭機械破碎基質膠。30 min 后將基質膠吸出,放置于15 mL 的預裝等體積Trypsin-EDTA 離心管中,10 min 后加入等體積培養基,4 ℃,500×g離心5 min,去除上清液及云霧狀基質膠,細胞沉淀用于后續實驗。
1.2.7 免疫熒光染色 將transwell 底膜及黏附的基質膠用刀片小心割下,在4%多聚甲醛中剝離基質膠,并固定20 min,在70%乙醇中滲透,在含有0.1%Triton X-100 和3%牛血清白蛋白的PBS 中封閉60 min。將基質膠與兔抗鼠αtubulin,大鼠抗小鼠ZO-1 抗體在4 ℃封閉緩沖液中孵育過夜,用PBS洗滌2次,分別與二抗驢抗兔IgG H&L抗體及羊抗鼠IgG H&L抗體孵育,置于阻斷緩沖液中在室溫下放置2 h,用PBS洗滌2次,與DAPI孵育,用PBS洗滌2次。
1.2.8 RT-PCR TRIzol 試劑盒提取基質膠消化后的類器官的總RNA,Nanodrop 分光光度儀檢測RNA 純度和濃度。以RNA 為模板,使用逆轉錄試劑盒逆轉錄獲得cDNA,以cDNA為模板進行擴增,反應條件:95 ℃30 s;95 ℃10 s,60 ℃30 s,共40個循環。以GAPDH為內參基因,采用2-ΔΔCt法計算基因的相對表達水平。引物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合成,序列見表1。

Tab.1 Primer sequences for qPCR表1 qPCR引物序列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GraphPad Prism 8.1.1 進行數據分析和繪圖,數據分布采用Shapiro-Wilk 檢驗。正態分布的數據采用表示,行t檢驗。非正態分布的數據采用M(P25,P75)表示,行Mann-WhitneyU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顯微注射對類器官形態的影響 將FITC-dextran 注射入類器官后,類器官的體積發生明顯增大,且直徑越小的類器官形態改變越明顯,見圖1。熒光顯微鏡下觀察發現,FITC-dextran 可均勻分布于整個類器官內部,使球體充分充盈,熒光素未出現外溢,見圖2。

Fig.1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microinjection of FITC-dextran in organoid圖1 類器官顯微注射FITC-dextran后的形態學特點

Fig.2 Observation of organoid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under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after microinjection圖2 熒光顯微鏡下觀察顯微注射后的類器官顯像特點
2.2 顯微注射GFP-PR8 病毒感染類器官特點 見圖3、4。在培養基中添加GFP-PR8 病毒,類器官上皮細胞感染效率很低,當顯微注射GFP-PR8病毒到類器官腔內,細胞感染率顯著增加,表現為極性向內的纖毛區域GFP熒光更明顯,而α-tubulin的表達明顯減弱;HE 染色提示顯微注射后的類器官結構松散,細胞間連接明顯破壞,細胞內較多空泡形成。注射GFP-PR8 后,類器官內的細胞表達的ZO-1 較注射PBS 的表達量顯著減少,提示細胞間連接遭到的明顯破壞是由GFP-PR8感染,而非顯微注射引起。

Fig.3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fic proteins in organoids after microinjection of GFP-PR8(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圖3 顯微注射GFP-PR8后類器官特定蛋白表達特點(免疫熒光染色)

Fig.4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fic proteins in organoids after microinjection of GFP-PR8(HE staining,×400)圖4 顯微注射GFP-PR8后類器官特定蛋白表達特點(HE染色,×400)
2.3 類器官極性反轉后的形態學特點 類器官內部細胞核向中央腔偏移、纖毛反轉向外的類器官逐步增多,且類器官間的黏附程度增加。反轉后的類器官大小穩定,未出現新的增殖、分化。纖毛細胞極性隨時間逐漸反轉向外,于第6 天起反轉比例趨于穩定。見圖5—7。

Fig.5 Morphological comparition of AI and AO organoids(HE staining)圖5 AI及AO類器官形態學特點比較(HE染色)

Fig.6 The proportion of organoids with polarity reversal in the upper chamber of transwell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organoids圖6 Transwell上層小室中極性反轉的類器官占總體類器官的比例

Fig.7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oids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conditions(×100)圖7 類器官在不同培養條件下的形態特點(×100)
2.4 極性反轉增加GFP-PR8 病毒感染類器官效率 GFP-PR8感染兩種類器官后,通過熒光顯微鏡觀察AO 類器官GFP 的熒光明顯強于AI 類器官,提示AO 類器官PR8 感染效率更高,見圖8。通過HE染色可觀察到AO類器官內部有較多壞死物質堆積,外層纖毛排列紊亂,細胞連接松散,細胞質疏松,有空泡形成,見圖9。

Fig.8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oidafter infection with GFP-PR8(×100)圖8 類器官感染GFP-PR8后的特點(×100)

Fig.9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O organoids infected by PR8(HE staining)圖9 PR8感染AO類器官后的形態學特點(HE染色)
2.5 極性反轉增強類器官對病毒感染的致傷效應 見圖10。在低濃度時(MOI=0.001),兩種方式類器官內IL-1β、CCL2、SCGB1A1、SCGB3A2、MUC5B 的mRNA 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中濃度時(MOI=0.01),類器官的上述基因表達水平AO均顯著高于同濃度刺激下的AI 類器官。而高濃度時(MOI=0.1),上述因子的表達水平AO較AI均有降低趨勢,而AI在濃度升高后mRNA水平還有繼續升高的趨勢。FOXJ1的表達水平在AO和AI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Fig.10 Gen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in AI and AO organoids after stimulation with different virus concentrations圖10 不同濃度病毒感染AI及AO類器官后的基因表達特點
3 討論
構建真實模擬呼吸道病毒感染體外模型對肺部感染性疾病防治具有重要科學意義和臨床價值[13-14]。本研究中,筆者描述了兩種新的氣道類器官研究方法,目的是加強干預因素與類器官極性表面的直接接觸。兩種方法利用了內源性干細胞的強大增殖能力,以及它們聚集并生成類器官的能力。這些類器官的組成細胞具有顯著的緊密連接,并由club細胞以及分化的纖毛細胞組成。纖毛細胞顯示出類似于體內觀察到的形態特性,即纖毛處于極化段,細胞核位于尾端。由于小鼠及人類支氣管上皮對流感病毒均敏感,所以類器官是研究急性肺損傷的良好體外模型。
3.1 類器官極性反轉對模擬病毒感染意義重大 細胞極性在人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IAV)感染中起重要作用。人氣道上皮細胞,包括纖毛細胞和杯狀細胞,是IAV的易感細胞,與非極化的細胞相比,極化的上皮細胞特征獨特,位于這些細胞的頂端和基底層的IAV特異性受體的差異表達和細胞蛋白的極化運輸,這些在體內系統中對塑造病毒的感染性起著重要作用[15]。使用類器官來研究微生物與宿主相互作用的一個挑戰是,上皮的頂端表面被封閉在球體內,而外層基底膜封閉性較強,病原體難以進入內部[16]。筆者設計了一種方法來扭轉類器官的上皮極性,使頂端表面向外。通過去除培養系統中的ECM 蛋白,使類器官懸浮生長,并保持了3D結構。上皮極性逆轉可能是蛋白質和細胞器從一極遷移到另一極的結果,也有可能存在其他機制,如對機械力的響應,有助于調節腸樣外翻和極性,本研究描述的方法提供了一個平臺,以進一步研究協調上皮形態發生。Co等[17]的研究也發現,反轉后類器官Ki67 的表達有降低趨勢,提示反轉過程對增殖和分化有影響。
3.2 類器官極性反轉后黏附性增加 在懸浮培養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類器官聚集黏附的現象。一方面是由于類器官極性反轉后,極性向外的區域具有分泌黏液蛋白成分的特性,導致相互接觸后產生粘連;另一方面,類器官外部的基質膠若未完全消化,殘留的成分也會導致相互粘連[18]。因此,后續的改良實驗需要盡量減少類器官之間的黏附,避免聚集成團后影響病原體與所有上皮的有效接觸。
3.3 顯微注射的應用范圍可進一步拓展 類器官顯微注射模型的顯著特征包括保持類器官形態的完整性,可防止頂端分泌的產物擴散到培養基中,并能夠選擇性地感染極化上皮的頂端。因此,該模型允許對微生物、上皮細胞及其分泌產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廣泛研究[19]。目前,已有多項研究證實了顯微注射技術在腸道及呼吸道類器官中關于病原體-宿主相互作用、急性損傷等方面的可行性及價值[19-21]。未來更有前景的研究方法是將類器官與免疫細胞及基質細胞共培養,從而更加貼近實景下實現各種病理條件下的細胞相互作用,這對于深入探索復雜生態位的分子病理機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