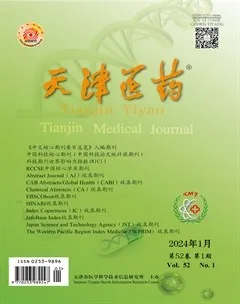類器官在癌癥基礎研究和臨床轉化中的應用
司吳雪蓉,蔣明
癌癥是疾病相關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發病率正在不斷上升。在傳統的癌癥治療方法中,患有特定類型癌癥的大部分人都會接受類似“一刀切”的標準治療,然而這些治療方法對于不同患者表現有不同的治療效果[1]。癌癥精準治療是指根據癌癥和個體的遺傳特征,為每位患者匹配最準確、最有效的治療方式[2]。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體外構建出個性化腫瘤模型,該模型需要具備與原發腫瘤相似的遺傳特征,能夠反映患者的疾病進展和治療靶點,以更準確地預測患者對藥物的反應。與傳統的二維(2D)細胞系和患者源性異種移植(patient derived xenotransplantation,PDX)模型相比,腫瘤類器官與原始腫瘤的生物學特征更為相似,因此更有可能準確地預測患者對藥物的反應。現就類器官技術在腫瘤基礎研究和臨床轉化中的應用價值進行闡述。
1 類器官概述
類器官被定義為具有自我更新和自我組織能力的體外三維(3D)細胞簇,具有類似于體內器官的結構和功能,一般從組織駐留干細胞、祖細胞、胚胎干細胞或誘導多能干細胞發育而來,其培養過程會受到培養環境的物理特征、內外源信號、起始細胞類型以及系統條件的影響[3]。目前類器官可用于模擬器官發育和疾病建模,在基礎研究、藥物發現和再生醫學中具有廣泛的應用。
1.1 腫瘤類器官的構建 腫瘤類器官是3D原代腫瘤細胞培養物,保留了原始腫瘤的組織學和突變特征。患者源性腫瘤類器官(patient-derived tumor organoids,PDOs)一般可以通過穿刺活檢和手術切除腫瘤來構建,腫瘤細胞被包裹在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ECM)中,并需要在生長培養基中添加特定的生長因子進行培養[1]。PDOs 的培養方法因腫瘤類型不同而存在差異,目前大多數腫瘤類器官使用Matrigel水凝膠進行培養,該基質膠是由小鼠肉瘤細胞分泌產生的膠體蛋白混合物[4]。培養基成分取決于類器官模型的種類,主要包括各種生長因子(R-spondin、Wnt3A,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表皮生長因子,Noggin 等)、HEPES、GlutaMAX、煙酰胺、B27、小分子抑制劑,以及促進類器官生長的各種激素[5]。類器官構建成功與否需要通過HE染色、免疫熒光和基因測序等多個維度進行驗證和評估;確定類器官與原始腫瘤的一致性是展開后續研究的先決條件[6]。
1.2 腫瘤類器官的優勢 在癌癥研究中,傳統的2D細胞培養和動物模型在基礎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兩種模型均存在一定的缺陷。2D細胞培養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來建立腫瘤細胞的連續傳代,因此不利于維持各種細胞亞型和親本腫瘤的關鍵驅動基因表達。細胞系作為體外選擇的產物,在選擇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腫瘤分子特征的丟失,包括拷貝數變異、突變和內部異質性。并且細胞的單層培養無法模擬體內細胞與細胞間的相互作用,而這種相互作用對于信號通路和基因表達的調節至關重要,是細胞發揮生物學功能的基礎[7-8]。
常用的動物模型包括轉基因模型和PDX。通過基因工程生成的動物模型無法真正模擬人類的致病過程,且該模型的生成也非常耗時[9]。相比之下,通過將部分新切除的患者腫瘤直接移植到動物模型中構建而成的PDX 模型可更好地保留腫瘤的重要特征。然而,PDX模型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來構建,才能使其具備較高的移植效率和表現出腫瘤細胞的宿主浸潤特征[10]。細胞系和PDX的衍生效率較低,不能為大規模的個體化治療做出貢獻。此外,這兩種模型通常來自晚期腫瘤,因此其不能完全捕獲癌癥發展全過程的生理特征[11]。PDOs 是在手術切除后最初幾周內由腫瘤構建產生的,其最大的優勢是可以有效地保留患者的遺傳和表型異質性。與使用含血清培養基的2D培養細胞系相比,原發性腫瘤類器官細胞在多次傳代中積累的遺傳變異較少[12]。3種模型在腫瘤建模和藥物篩選中的特點見表1。

Tab.1 Characterization of 2D cell lines,PDX and PDOs in tumor modeling and drug sreening表1 2D細胞系、PDX和PDOs在腫瘤建模和藥物篩選中的特點
2 類器官在腫瘤基礎研究和臨床轉化中的應用
類器官不僅保留了與體內器官高度相似的組織學和遺傳學特征,而且在預測抗癌藥物方面具有極高的臨床相關性,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腫瘤基礎研究和臨床轉化等方面,包括腫瘤類器官樣本庫、腫瘤微環境的構建,腫瘤發生發展機制的研究及個性化藥物篩選,見圖1。

Fig.1 Application of organoids in bas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anslation of cancers圖1 類器官在癌癥基礎研究及臨床轉化中的應用
2.1 構建腫瘤類器官樣本庫 類器官生物庫作為一種“活體庫”,可以為基礎和轉化醫學研究持續提供患者來源的樣本,同時保留腫瘤組織的生物學特性。與傳統的生物樣本庫相比,類器官生物庫應用范圍更廣泛,尤其是在腫瘤生物標志物篩選、藥物靶點發現、耐藥機制研究和藥物療效評價等方面[6]。Petersen等[13]發現ECM凝膠可用于培養正常人乳腺上皮細胞和人乳腺癌細胞后,隨著3D培養技術的革新和培養基成分的優化,越來越多患者來源的腫瘤被用于構建類器官生物庫。目前,研究人員已成功培養了多種腫瘤類器官,包括結腸癌、胃癌、胰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腎癌、卵巢癌、子宮內膜癌等[4]。腫瘤具有一定的異質性,包括腫瘤間異質性和腫瘤內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會隨著病程的發展而加劇,從而導致患者對治療的敏感性及預后情況不同。因此,全面了解腫瘤的異質性對于制定有效的治療策略至關重要。目前,已成功構建的乳腺癌[11]、胃癌[14]、腎癌[15]、肺癌[16],膠質母細胞瘤[17]以及結直腸癌肝轉移[18]等類器官生物庫均被證明很好地維持了患者內和患者間的腫瘤異質性,同時還保留了原始腫瘤的組織病理學和遺傳學特征。部分腫瘤如胸腺瘤、間皮瘤、橫紋肌肉瘤、胃腸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的發病較為罕見,缺乏可以有效進行藥物篩選的臨床前模型,阻礙了新型療法的開發[19-20]。因此,這類腫瘤類器官庫的成功構建將能夠加速抗癌藥物的研發。綜上所述,類器官生物樣本庫可以作為臨床前細胞培養模型,為基礎癌癥研究、藥物篩選和個性化醫療提供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特征的模型。
2.2 重建腫瘤微環境 腫瘤微環境指的是腫瘤中存在的非癌細胞及它們產生釋放的因子,其主要通過循環和淋巴系統與腫瘤細胞相互作用,進而影響癌癥的發生和進展[21]。癌癥免疫療法正迅速成為許多癌癥的標準治療方式,但患者的應答反應主要取決于癌癥的類型和腫瘤靶分子的表達,這正是由于微環境的作用導致某些腫瘤細胞對免疫療法產生了一定的抗性[22]。許多研究都構建了癌細胞與非癌細胞的共培養模型,通過在體外模擬腫瘤微環境來探究細胞間的交互作用,這對于癌癥治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氣液界面交互技術植入天然免疫細胞后得到的PDOs 不僅準確保留了原始腫瘤的T 細胞受體譜,還能模擬免疫檢查點阻斷過程[23]。除免疫細胞外,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作為活化的成纖維細胞,能夠產生和重塑細胞外基質,是腫瘤基質中最重要的細胞類型之一[24]。許多研究者將腫瘤類器官與相應患者來源的CAFs 共培養,以探究CAFs 在腫瘤發生與發展中的作用。Tsai 等[25]在人胰腺癌類器官和CAFs 共培養模型中觀察到了肌成纖維細胞樣CAFs 的活化與淋巴細胞的浸潤。Luo等[26]發現在未添加生長因子的情況下,CAFs 能夠維持水凝膠中結直腸癌PDOs的增殖。Schuth等[27]同樣發現CAFs促進了原代胰腺導管腺癌類器官的增殖,且類器官中上皮間充質轉化相關基因的表達增加。在有些腫瘤的發生過程中,內皮細胞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Lim 等[28]利用水凝膠系統建立了共培養模型以模擬和表征體外肝細胞和內皮細胞之間的血管分泌信號,從而探究內皮細胞在肝細胞癌發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這些共培養系統有望促進腫瘤-微環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但這些模型仍在發展中,腫瘤微環境的構建是否對傳統和新型研發藥物具有耐藥性,是否可以用于優化體外治療反應,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證明。
2.3 研究腫瘤的發生及發展機制 基因組DNA 序列的異常改變是正常細胞轉化為癌細胞的重要原因。近年來,CRISPR-Cas9 介導的基因編輯技術引起廣泛關注,許多研究人員將其與類器官培養相結合,從而探究特定基因在癌癥發生發展中的作用。Lo 等[29]對人胃類器官進行了ARID1A的敲除,Dekkers 等[30]在乳腺祖細胞中敲除了4 個乳腺癌相關的腫瘤抑制基因。Liu 等[31]從患者活檢組織中生成了組成型Wnt 激活的人巴雷特食管類器官模型,這些類器官在經過基因編輯后均表現出與腫瘤發生密切相關的現象,如更高的增殖復制能力、更少的細胞凋亡及黏液分化等。Takeda等[32]同樣通過對類器官進行基因編輯評估了單個基因(Apc和Kras)突變在結直腸癌中的致瘤能力,最終發現Acvr1b,Acvr2a和Arid2可以作為結直腸癌的腫瘤抑制基因,并揭示了Trp53在腫瘤轉移中的作用。此外,利用癌基因轉化類器官模擬人體治療過程,可以為耐藥治療提供更有效的信息,這樣不僅可以建立腫瘤模型,還可以研究特定基因突變對藥物的治療反應。Verissimo等[33]發現引入致癌Kras突變的正常結腸類器官對EGFR-RAS-ERK 通路靶向抑制劑的藥物反應譜與RAS突變的結直腸癌類器官一致。這可能有助于證明相關突變基因對藥物反應的影響,并排除如細胞狀態、其他癌癥突變的存在等復雜因素的干擾。
2.4 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及藥物篩選 個性化腫瘤模型的制定是開發個性化治療方案的前提,研究人員發現類器官可以很好地保留患者體內腫瘤的特征,且微環境中殘留的免疫細胞如腫瘤浸潤性淋巴細胞,可以用來評估相應腫瘤類器官的殺傷效率。利用微流體技術從患者腫瘤組織中快速生成的微器官球能保留大部分原始腫瘤駐留免疫細胞,且PD-1阻斷和雙特異性抗體等免疫療法可以激活TILs以攻擊MOS 內的腫瘤細胞[34]。Dijkstra 等[35]則證明自體腫瘤類器官和外周血淋巴細胞的共培養可以用來富集錯配修復缺陷的結直腸癌和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外周血來源的TILs。實現構建個性化模型后的關鍵問題在于類器官能否準確預測出藥物在患者體內的反應。大量研究表明抗腫瘤藥物在類器官中的反應與患者體內反應一致,且經類器官篩選得到的藥物在患者體內也具有一定的療效,這些在乳腺癌[36]、胰腺癌[37]、結直腸癌[38]和胃食管癌[39]中均已得到證實。利用類器官進行藥物篩選具有篩選周期短、準確性高的特點,對指導患者用藥和臨床試驗,以及加快抗癌藥物的研發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已經建立了一些相對成熟的類器官高通量藥物篩選平臺,利用PDOs可以在1 周內完成藥物篩選,具有較高的轉化應用價值[40]。但類器官中腫瘤微環境的不完全保留會限制其篩選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和抗血管生成類藥物,且在基于癌癥類器官藥物篩選更廣泛地應用于個性化治療之前,還需要進一步評估其對不同癌癥類型的穩定性、可重復性和適用性[41]。
3 研究困境與挑戰
雖然多項研究證明,類器官在腫瘤基礎研究和臨床轉化中具有廣泛的應用,具備高度的臨床相關性,能夠有效地對患者進行藥敏試驗,使個體化的精準腫瘤治療成為可能。但類器官技術仍處于發展的早期階段,許多因素限制了該技術的應用。首先,腫瘤微環境的ECM 組成成分比僅富含層黏連蛋白或透明質酸的ECM 凝膠復雜,目前所構建的PDOs 中腫瘤細胞-ECM 間的相互作用還過于簡單,且存在于原代PDOs 中的基質細胞在長期培養過程中會逐漸丟失[42]。盡管已經開發了許多共培養體系,但仍然無法非常準確地復制出患者體內的微環境。因此,用體外構建的PDOs進行藥物篩選與體內療效的一致性仍需進一步探究。除微環境成分的缺乏,類器官還缺乏血管結構,由于氧氣和營養物質在細胞間的擴散距離有限,類器官體積的增加易導致中心細胞的死亡。其次,由于生長因子和基質膠的成本較高,類器官的培養成本遠高于2D 培養細胞系,且培養過程更耗時,培養技術難度大[43]。目前,雖然已顯示出將類器官技術用于非上皮癌的可行性,但該技術主要用于生成起源于上皮的惡性腫瘤[20]。再者,類器官培養過程中,生長因子條件培養基中需要有小鼠來源的基質膠、胎牛血清等動物來源產品,因此無法直接實現臨床上的轉化,且這些提取物的組成存在批次間的差異,可能會影響實驗的重現性[6,41]。最后,類器官的培養純度也十分關鍵,正常類器官的過度生長易造成腫瘤類器官的污染,有時僅添加與腫瘤類器官相關的生長因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正常類器官的生長[44-45]。
4 小結與展望
類器官在近十幾年間迅速發展,已在發育生物學、癌癥前臨床研究等領域取得了許多突破,如發現基因序列與抗癌藥物敏感性間的關系,體外模擬腫瘤及其微環境以實現藥物篩選,新型藥物的研發和免疫療法的評估等。腫瘤類器官在具備一定優勢的同時又有一些限制,但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類器官將能夠更好地模擬人類腫瘤的特征并預測藥物反應,從而避免臨床過度治療及不良反應,有利于提升精準治療的水平,在腫瘤的基礎研究和臨床轉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