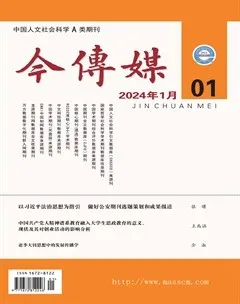淺析民國縣級報刊的內容面向與保存現狀
何雨蔓
摘 要:民國時期新聞業是我國新聞史發展的源頭與火種,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政治、經濟、文化情況不一,因此,民國時期新聞業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態勢。遂寧地處四川盆地中部,民國時期它的新聞事業受當時區縣政府的限制,廣播、報紙等行業發展較為緩慢,但是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因此,其新聞事業發展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本文以1948年2月5日《涪聲日報》第八四六期為研究對象,對其內容進行文本細讀并作簡要分析,且對民國文獻的保存和利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旨在為民國報刊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涪聲日報》;縣級新聞事業;民國報刊
中圖分類號:G21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4)01-0075-04
一、引 言
近代來,我國新聞事業隨著社會的變動而呈現出此起彼伏、革故鼎新的發展態勢。民國時期新聞業是我國新聞史發展的源頭與火種,是學術研究的重點。目前,大部分民國新聞史的研究主要圍繞《大公報》等大報,并將目光聚焦在報業發達的大中城市,而對于區縣報刊的研究較少。朱志剛、李淼等認為,報刊在基層的普遍出現標志著近代化在我國的廣泛延伸[1],而從遂寧———四川腹地的民國報刊出發,可以窺探民國時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縮影。
二、民國時期遂寧地區新聞事業概述
遂寧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涪江中游,東漢建縣,東晉穆帝永和三年設遂寧郡,民國時期為四川省第十二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所在地,1985年經國務院批準,撤遂寧縣,建為省轄地級市。
據《遂寧市志》記載,遂寧最早的廣播出現在民國22年,即1933年;最早的報刊出現在民國27年,即1938年[2]。在1936年許晚成主編的《全國報館刊社調查錄》中,只查詢到遂寧周邊射洪縣的《縣政旬刊》、鹽亭縣的《新鹽亭》等,未查詢到遂寧縣的報刊,佐證了這一事實[3]。
(一)廣播事業
民國22年(1933年),遂寧縣政府在所轄保衛團設有收音室,配有收音機1部,收音員1人。民國27年,收音室遷至民眾教育館,工作人員增至2人,每天印發《遂寧廣播通訊》60-70份供縣政府有關部門參閱。
根據《四川省志·廣播電視志》,民國時期四川省內的廣播電臺主要分布于重慶、成都兩地,重慶廣播電臺最早于1932年12月建立,1936年9月成都廣播電臺建成并開始播音[4]。而省內除重慶、成都之外,只有西康、自貢兩個地區分別于1943、1947年成功建設廣播電臺,其他地區均配備收音設備接收信息。
(二)報刊事業
民國時期,登載遂寧縣政治、經濟、教育等相關內容的報紙寥寥無幾,在《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第一~十一輯)》中對“遂寧”這一詞條進行搜索,僅獲得461條相關內容,時間主要集中在1930-1949年,登載報刊主要為《四川月報》及各省級部門公報。
據《遂寧市志》記載,民國27年(1938年)春,民眾教育館編輯出版4開版土紙小報《遂寧日報》,辟有副刊《戰號》,后更名為《野火》,民國28年初,又更名為《后方文藝》。副刊先后由楊仲明、朱竹隱、曾似鴻任編輯,以詩歌、散文、小品、雜文等文學樣式宣傳抗日救國,共刊出20多期。
民國28年(1939年)冬,遂寧專署(即四川省第十二行政區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黃綬命令所屬接管《遂寧日報》后改組為4開版的《涪江日報》。報社由民眾教育館遷往專署內,為專區地方報紙,在專區所轄9縣發行,日發行量萬份以上。民國30年,黃綬調離時停辦。
民國32年(1943年),遂寧專署創辦了4開版的《涪聲日報》,社址位于縣城小西街帝主宮。民國34年底至民國35年約半年時間內,因報紙銷路不暢,曾一度改名《涪聲三日刊》,后復名《涪聲日報》,直至民國38年接近解放時停辦。
三、《涪聲日報》縣報實錄
《涪聲日報》共4版,雙面印刷,從左至右打開,豎排版,通篇采用白話文寫作。本文以1948年2月5日的《涪聲日報》第八四六期作為文本研究對象,通過對報刊內容的詳細解讀回溯當時的社會民情。
《涪聲日報》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民生、國際局勢等多個方面,也穿插了當時時髦商品的廣告及政府部門的公告。報頭居中,標題“涪聲日報”采用行書書寫,報眉標有新聞紙類別、期數、登記刊號、發行人、報紙零售價及廣告刊登費用等。《涪聲日報》每期刊發50余篇文章,分為國內新聞、國際新聞、本縣及周邊信息、社論及特寫、商業廣告和登報啟事等6個部分,其中國際、國內新聞均來自中央社。
(一)國內新聞
國內新聞主要分布在報紙頭版,內容涉及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民生等各個方面,共計13篇。與軍事相關的報道有《白崇禧將飛京》《魯李兩將軍殉職蔣主席飭撫恤金》《嚴防偷渡長江江陰岳陽沙市等地加派船艦常州駐守》《軍校招考新生二月截止報名》《鄂中國軍完成縝密部署宣城當陽恢復常態劉匪受創徘徊塘港》等,其中,《鄂中國軍完成縝密部署宣城當陽恢復常態劉匪受創徘徊塘港》一文標題加粗,字號最大,為本刊頭版頭條。與經濟相關的報道有《搶運開灤存煤沈熙瑞抵平洽商并視察平津工業》《西藏代表團晉京洽商與內地貿易》《南京將配售食米每人每月配一斗》,其中《南京將配售食米每人每月配一斗》一文采用“中央社南京四日電”,報道了南京市全面配售食米定于三月一日開始,“受配人數按照一百一十萬人計算,每人每月配食一斗”,“價格較市價為低”。與法律相關的報道有《孫副主席講———憲法與憲政》,報道了時任國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長孫科向人民群眾普及憲法與憲政知識的消息。與政治相關的報道有《北方代表請愿團在京滬結果圓滿》《同濟學潮已告解決》。與民生相關的報道有《東北人民生活不易》《臺北長壽橋下月可竣工》等。
(二)國際新聞
《涪聲日報》在1948年2月5日當天登載了印度、英國、日本、美國4個國家的新聞,尤其對印度和平使者甘地的意外死亡進行了大篇幅報道。《甘地噩耗傳出印度舉國哀慟舉行追悼絕食祈禱兇手為馬拉泰會員》一文采用“中央社新德里四日合眾電”,講述了圣雄甘地在晚禱現場被槍殺案件始末,報道側重于印度政府及其國民對于甘地去世的悲痛和惋惜。此外,還有報道日本暴徒毒殺銀行員工并搶奪巨款的《日本殺毒案》,以及美國鑒于燃料石油缺乏而減少石油輸出的新聞。
(三)本縣及周邊信息
《涪聲日報》本縣及周邊信息共計16篇報道,內容包括政府公告、商情、娛樂等,主要分布在第三版。其中,《本區保安司令部分駐各縣保警隊如有違法舞弊情事準各縣監督與檢舉》為特訊,本區保安司令部面向社會宣告6種保警隊違法舞弊行為,即“好賭”“販運煙毒”“紀律欠佳”“清匪不力”“勒索或欺壓人民”“其他違法舞弊”,分令各縣縣長嚴密監督管理,并許任人檢舉,如查屬實,決予嚴懲。標有“本報訊”的文章有《辦理契稅認真稽征》《呈報征實數額不得虛浮不實》《省府明令提示鄉鎮注意事項》《省縣中等學校征費標準決定》《遂寧立委選舉業已順利完成》5篇,內容涉及契稅稽征、田賦征收、學校征費標準等民生話題,以及鄉鎮公所幕僚長制、縣立法委員會選舉結果等政治話題,說明當時區縣的報人擁有獨自進行新聞采編并撰稿的能力,但是報刊的總體篇幅還是以摘錄其他來源的新聞為主。
本縣商情和娛樂信息與人民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遂寧商情》羅列了遂寧縣當日商品的價格,大米、棉紗等生活資料的價格以“萬”為計價單位,通貨膨脹程度可見一斑。娛樂新聞有《遂寧集賢劇社籌募冬令賬濟平劇公演節目》,羅列了《武家坡》《五花洞》等劇目,并標注了主要角色。這部分的報刊內容幫助當地居民了解了本地新近發生的新聞,發揮了報刊傳遞社會信息的重要作用;同時,這部分內容的呈現也是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發展變遷的縮影,為后來人們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四)社論及特寫
《涪聲日報》在1948年2月5日當天刊發了一篇名為《怎樣使青年軍有力量》的社論,作者沈健,標題后寫有“續”,即表示該篇社論為連載文章。該文章提出:“我們要確立鮮明而光明正大的目標。就對外而言,第一是嚴懲出賣國家民族的反動集團,完成國家統一,保障建國成功;第二是打倒新的帝國主義;第三是懲戒反時代、反潮流、反民主、反私有的惡勢力,實行民權主義;第四是清算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就對內而言,第一是人人有衣穿,第二是人人有屋住,第三是人人有工做,第四是人人有書讀,第五是人人有車坐”。此外,該文章還配有山水樹木的插圖,這也是全報唯一的一張圖片。第二版面的《迎春特寫》的作者為本報記者單火,描繪了遂寧縣年關將近的市井生活,現場感極強。
(五)商業廣告
《涪聲日報》第八四六期共刊登了《遂寧久太綢布號》《火車牌、白家牌電池》兩則廣告,占據報紙第二版下方近三分之一的版面。廣告標明了店鋪名稱、經營范圍、產品特點以及店鋪地址,運用不同的字體和字號進行了區分,版面內容豐富,極具特色。
(六)登報啟事
由個人或組織在報紙上刊登《啟事》是《涪聲日報》的重要內容。1948年2月5日,《涪聲日報》共刊登了12篇《啟事》,既有在報紙中縫刊登的有關報價調整事項《本報調整報價啟事》《本報營業部緊要啟事》,也有宣傳各類組織內部相關事宜的《遂寧縣私立慈幼教養工廠為感謝天成亨捐款啟事》《川中師管區司令部啟事》《省遂師蓬溪同學會啟事》;既有刊登個人重要事項的《雷驚重要啟事》《蔡紹明遺失啟事》《蓬溪康家鄉蕭清廷緊要啟事》《遺失啟事》《從婚啟事》《鐘慎齊為三子書德脫離家庭關系緊要啟事》等,也有為他人獻上祝福的《蕭純夫先生杜天貞女士訂婚紀念》等。
四、從《涪聲日報》看當時縣級新聞業的發展狀況
《涪聲日報》作為有記載的、民國后期遂寧縣唯一公開發行的報紙,體現了鮮明的時代性和地域性,其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地區民國后期新聞事業的發展狀況。
(一)從民營轉向官辦
《涪聲日報》最初名為《遂寧日報》,由民眾教育館編輯出版,后被遂寧專署接管,轉為國民政府專區地方報紙,并在專區所轄縣發行。經查閱《四川省志·報業志》,四川省內多個縣市的數家報紙都是從民營轉為官辦,類似于《涪聲日報》成為全縣僅剩的報紙也大有所在[5]。
《涪聲日報》在報頭清晰標明“中華郵政局第二類新聞紙”。所謂第二類新聞紙,又稱立券新聞紙,指凡發行周期在10天之內,每次發寄數不少于500份的新聞紙,在郵局辦理登記立券手續后,可按立券新聞紙交寄,資費按月交付,并享受折扣[6]。由此可見,當時《涪聲日報》的發行量較為可觀。
(二)新聞來源較為單一
《涪聲日報》的國際、國內信息大多來自當時的中央社。中央社現為臺灣中央通訊社,1924年4月創立于廣州,歷史上總社社址先后設于廣州、南京、漢口、重慶、南京、廣州、臺北。從報紙登載時間來看,其新聞基本是前一日的電訊,由此可見,《涪聲日報》的時效性較強。此外,《涪聲日報》擁有專門的記者,可以自行采編,報紙中也有文章標明“本報記者單火”,但是“本報訊”的內容大多是省政府的會議結果、決議決策等,較少涉及非政府渠道的信息。從新聞來源可以看出,縣級報刊在內容選擇上范圍較窄,能夠為當地人民提供的新聞內容有限,新聞業發展較為緩慢。
(三)內容多反映時局變化
《涪聲日報》共四版,第一版、第四版為國際、國內新聞,第二、第三版與本縣發展和當地人民的生活關系密切。總體來說,不同類型的新聞在排版上趨于均衡。然而,從報紙的編排結構和新聞內容上,讀者依然可以較為清晰地了解到當時的時局變化。
首先,《涪聲日報》作為區域性、權威性的新聞報紙,在特殊歷史時期對戰爭時局進行了報道,為當時的百姓提供了較為可靠的消息來源,也為后來的研究者從不同角度了解時局提供了史料幫助;同時,報刊還傳遞了一些進步聲音,一些有志之士發表社論文章,對社會現狀針砭時弊,以期喚醒人民,為人民解放鑄牢思想基礎。
其次,從報紙內容來看,反映了時局的不穩定。一方面國民政府想要管理違法舞弊行為,不允許各縣自行提高契稅,對保警隊在各縣的違法舞弊行為也提供檢舉途徑,加強對鄉鎮公所人員的管理等。然而,彼時解放戰爭已經進行到戰略反攻階段,并且社會通貨膨脹嚴重,各地物價狂漲,(“大米法幣六萬元一斤,高粱米五萬元”“潘陽街,到處是倒閉的商店、關門的飯店”),致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四)人民群眾公開表達的渠道
《涪聲日報》第八四六期的50篇文章中,有12篇為私人啟事,或是慶賀婚禮,或是失物招領,又或是表達感謝等。報紙作為一種公開發行的刊物,將群眾私人領域的社交內容刊登于報紙上,增強了社會互動性。何秋紅、劉潔等人認為,彼時報紙在我國還屬于新生事物,這種在公開場域發布私人社交信息的行為,滿足了群眾的社會互動需求,契合當時的社會現實[7]。
五、對民國時期報刊保存與保護的反思
民國時期的報刊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它是一個區域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民風民俗等方面的歷史記錄,然而,目前的保護與利用工作不是很到位。就本次史料收集過程來看,遂寧檔案館館藏紙質檔案13.7萬余卷、62萬余件,民國檔案34259卷,但多為圖書和口述資料,現存民國報刊只有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十七日《遂寧日報》第一版,規格為57.5cm×40.5cm,是保存的遂寧市最早的報紙。與之對應,民間收藏家即使有保存完好的報刊原本,此類報刊藏品數量也非常稀少,很難形成完整的研究體系,對于個別案例的研究也無法推演出當時的新聞業態和社會實情。因此,政府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應加強對民國報刊的保護與研究,充實民國史料,還原當地歷史,避免文獻歷史出現“民國斷層”危險。
(一)征集民國報刊進館
報刊的保存受紙張原材料和保存環境的雙重制約,普通方式無法長期保存報刊原刊。早在2005年,《人民日報》就刊登過《如果不及時搶救,民國文獻將在50至100年間消失殆盡———文獻歷史會出現“民國斷層”》一文,并提到“在歷代文獻的保存中,民國時期文獻的壽命最短,加之民國時期裝幀工藝落后,造成民國期刊在使用過程中容易造成破損”[7]。因此,對民國報刊的保護不能僅寄希望于個人收藏家,而應交由博物館、檔案館等具備專業設備和專業人員的機構進行保存,這需要我們明確報刊收集的主體責任,與當地檔案館、圖書館等文獻資料保管部門相互配合,使史料保存和管理工作制度化、秩序化,方便讀者利用文獻搜索讀取較為完整的地方民國史。
(二)錄入電子數據庫,豐富虛擬館藏
目前,全國多數地區都實現了民國文獻的數據庫錄入。數據庫錄入,即對圖書、報刊等文獻通過電子掃描、復印、制作微縮膠片等手段建立專題電子檔案庫,既方便保存,也方便讀者和研究人員調取內容進行閱讀,避免文獻原本再遭破損,這是目前保存民國文獻生命續存的最好方法之一。
六、結 語
《涪聲日報》反映了當時該地政府治理、商業發展、娛樂生態、社會民情的變化,將社會宏大敘事與市井生活同時呈現,既為我們研究近代社會發展提供了寶貴的信息來源,也為民國報刊及其他文獻進行更好保存、避免地區文化斷層提供了借鑒。
參考文獻:
[1] 朱至剛,李淼.被嵌入的主角:報刊基層化中的國民黨縣級黨報[J].國際新聞界,2017,39(8):156-171.
[2] 謝志成,李劍華.遂寧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3] 許晚成.全國報館刊社調查錄[M].上海:龍文書店,1936.
[4] 陳杰,陸原,李放,陳立源.四川省志·廣播電視志[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
[5] 湯霞.從“新知”到“新媒介”:晚清時期的譯報實踐與媒介新知[J].編輯之友,2022(5):94-103.
[6] 何秋紅,劉潔.透過大眾媒介的私人交往———以《通海新報》私人啟事為例[J].華中傳播研究,2016(2):70-87.
[責任編輯: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