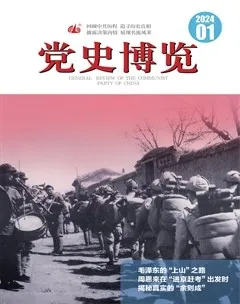揭秘真實的“余則成”
秦正

? 電視劇《潛伏》劇照。右起:吳敬中、余則成、李涯
諜戰劇《潛伏》一經播出便轟動一時,主人公余則成打入軍統天津站與敵人斗智斗勇、屢建奇功的潛伏故事,成為人們獵奇的熱門話題。余則成這個人物是否有原型?余則成、陳翠平假扮夫妻的情節是否憑空虛構?保密局天津站是否真實存在?值此平津戰役勝利75周年之際,讓我們重溫那段隱秘而光輝的歲月,走進余則成身后鮮為人知的一段段密戰往事。
劇中的余則成只身潛伏,真實的“余則成”是個英雄群體,他們不叫余則成,卻共同塑造了余則成。余則成似乎并不存在,“余則成”實則無處不在。
軍統天津站史上確有。國民黨派駐天津的特務機關,最早可以追溯到黨務調查科時期。
1929年12月,徐恩曾由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一職調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負責人,受命拓展、強化這個特務機構。徐恩曾將此前打入無線電管理局擔任秘書的共產黨員錢壯飛帶入黨務調查科擔任其機要秘書,委托錢壯飛擴充人員,在南京組建特務首腦機關,進而在全國重點地區布局設點。中央特委周恩來指示:“你們把它拿過來!”于是,李克農、胡底趁此機會打進黨務調查科,與錢壯飛一起“協助”徐恩曾籌建特務總部和基層特務組織。1930年間,他們3人進一步籌劃在南京、上海、天津建立了4個情報機構——長江通訊社、民智通訊社、長城通訊社和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廣播新聞編輯部。
1930年下半年, 胡底被派往天津籌建長城通訊社并出任社長。天津長城通訊社實際上就是黨務調查科天津站,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最早設在天津的分支機構。1935年黨務調查科升格為處,1938年3月黨務調查處擴充為中統,1947年4月中統改組為黨通局,其間均在天津繼續派駐常設機構。幾乎與此同步,從1932年起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開始在天津設點派駐,1935年復興社特務處擴充為軍統后專門設立了天津區,該區后于1939年被日軍破獲。抗戰期間,軍統又先后兩次在天津秘密設站,均遭瓦解。日本投降后,軍統天津特別站復建,1946年6月軍統改組后改稱國防部保密局天津站。
溯源中共隱蔽戰線斗爭史,情報員胡底成了國民黨特務機關派駐天津的第一位負責人,可以說是首任站長。他是第一位打入天津特務機關的中共情報員,從這個意義講,是最早的“余則成”。
經實地考察,胡底決定把長城通訊社設在日租界,但日本駐天津領事館始終不準。后經錢壯飛動用關系,“請出”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幫助疏通,才獲日租界批準,天津長城通訊社遂在日租界秋山街5 號一幢四層樓開始運營。
錢壯飛把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妻弟張家垅派到胡底手下當記者,配合胡底工作。張家垅晚年回憶說,胡底幾乎每天都帶著他上街“采訪”,他們并不像文學和影視作品里的特工那般神神秘秘,而是談笑風生,以“采訪”為名出入各種場所了解情況。胡底經常打麻將,以此作為拉關系、搞情報的主要手段之一。胡底還讓張家垅每天把天津主要報刊的新聞摘抄下來,寄往南京長江通訊社總部。胡底保密意識很強,他所從事的秘密工作對黨外人士張家垅守口如瓶。
張家垅還回憶,胡底告訴他,自己曾在上海影片公司工作,還拍過幾部電影,而當時恰巧日租界一家電影院正在放他拍的一部電影,于是胡底就請張家垅一起去看。由于年代久遠,張家垅不記得電影的名字了,但胡底的多才多藝讓他這個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非常佩服。

中共情報戰線上的“龍潭三杰”。左起:胡底、錢壯飛、李克農
1931年4月26日深夜,胡底收到李克農發來的電報:“胡底,克潮病篤。”“這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克’是說李克農,‘潮’指錢壯飛的別名錢潮,‘病篤’意即事情嚴重。”胡底接到電報后需要馬上轉移,卻拿不出足夠的錢買船票,張家垅當即變賣了愛人的手鐲,為胡底湊齊路費。
胡底乘坐外國輪船離開天津第二天,張家垅被日本租界抓捕,并被移交給國民黨當局。由于他并非中共黨員,且對胡底的秘密工作一無所知,又沒有暴露與錢壯飛的親戚關系,敵人只得將他釋放。他離開天津回到老家,隱姓埋名當了一名教師,與胡底再也沒能重逢。
《潛伏》劇中的站長吳敬中,其原型是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景中少將。1948年12月解放軍分割天津、解放唐山、切斷平津鐵路之后,吳景中召集在津公開與秘密兩條線各機構負責人舉行緊急會議,部署了6條應變措施:1.實時跟蹤戰況,密切注意警備司令部和戰防部隊轉移動向,準備隨部隊突圍。2.各公開秘密機構人員一律配發槍支并隨時準備輕裝集體行動。3.命令保密局三有企業公司華北辦事處準備充足路途給養。4.盡快安排家眷乘船南下,以免突圍時拖累。5.派專人事先雇妥大批漁船,必要時先乘小船去塘沽,再從海上去青島。6.成立突圍撤離指揮部。
吳景中還秘密布置組建了4個潛伏組,并為他們配備槍支和電臺,妄圖在天津解放后繼續從事各種破壞活動。
然而,此次會議后僅僅5天,看似要與解放軍頑抗到底的吳景中卻突然不辭而別,丟下天津站所有部屬,于18日秘密乘飛機逃往南京。毛人鳳事后給天津站發電稱:“吳景中棄職逃走,罪該萬死,現已拘押,定予嚴懲。”
《潛伏》劇中的行動隊隊長李涯,其主要原型之一是天津站最后一任代理站長李俊才。與《潛伏》劇情一樣,現實中的李俊才與吳景中確實有過一段師生關系。1938年吳景中在軍統湖南臨澧訓練班第二中隊任政治指導員時,李俊才是第一中隊的學員。吳景中棄職逃走后,毛人鳳電令李俊才即日接任代理站長,命他從速恢復站部工作,接手吳景中組建的4個潛伏組,并隨電發來4組潛伏人員名單及其住址,要求李俊才化裝后與各潛伏小組分別秘密取得聯系,強化潛伏部署,督飭各組臺與保密局本部開始通報。
遵照毛人鳳電示,李俊才于1948年12月末至1949年1月初先后單線聯系、秘密召見各潛伏組組長和電臺報務員,向各組組長發放5兩黃金作為半年活動經費,傳達毛人鳳來電規定的各潛伏小組與南京保密局本部直接聯系的化名以及此后保密局派到天津與各組接頭聯絡人的化名、特征、衣著、暗語等等。他向各組報務員發放2萬元金圓券作為半年活動經費,明確與南京保密局本部聯絡的稱號、波長、時間、雙方化名、密碼更換辦法,配發特工電臺及所用電池等配套器材,責令站部電臺臺長親自指導各組報務員秘密架設、調試電臺,從速與南京保密局本部通報聯絡。1949年1月上旬的一天,李俊才接到報告,“南京總臺來電,4個潛伏臺已與總臺試通成功,通報情況良好”。僅僅數日后的1月15日,天津解放,李俊才被解放軍俘虜,根據他的交代,4個潛伏組和秘臺被悉數破獲。
《潛伏》劇中余則成與陳翠平假扮夫妻的故事,主要原型之一是中共晉察冀分局華北社會部潛伏在北平的秘臺工作人員王文、王鳳岐夫婦。
王文14歲參加紅軍,在鄂豫皖根據地反“圍剿”斗爭中表現突出,由普通一兵成長為連指導員。1935年5月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后參加西路軍,隨部隊突圍至新疆,于1938年初被派往蘇聯學習無線電通信和情報業務。
王文是參加紅軍后才學識字的,文化水平有限,學習無線電通信、電學、物理學、數學等課程的難度可想而知。他憑借頑強毅力和刻苦精神,僅用一年多時間就熟練掌握了無線電通信技術和情報專業知識,于1940年學成回國,進入華北社會部領導下的平西情報站負責電臺工作。

王文、王鳳岐夫婦與陳老太太(中) 的合影
王鳳岐年僅20多歲時就參加抗戰,因作戰英勇、槍法奇準,被任命為區婦聯游擊隊隊長。她像劇中的陳翠平一樣英姿颯爽,頭剪短發,腰別一支20響盒子炮,率領隊伍在白洋淀一帶與日軍進行游擊戰。
一次,日軍突襲游擊隊所在村莊,王鳳岐不幸被捕。日軍將她五花大綁押回縣城。途經白洋淀岸邊時,押解她的兩個日軍興奮地“觀賞”水中魚兒,王鳳岐乘機猛然發力,生生把兩個日軍都頂落到了水里。她反捆著雙手飛奔遠去,兩個日軍狂追不舍,密集槍擊,子彈不時把王鳳岐身邊的莊稼稈打斷。她沉著機警地躲過子彈,一口氣狂奔5公里多,終將日軍甩掉。王鳳岐卻不敢停下來,又跑了很遠才停下。她渾身像散了架似的一頭撞開一戶老鄉的屋門,隨后一口鮮血噴了出來。后來,王鳳岐在回憶起這段驚險逃亡的經歷時說:“我把自己的肺都跑炸了!”
1942年,王文、王鳳岐分別被選入華北社會部接受秘工培訓,除情報技能外,還要熟悉掌握北平各方面情況,尤其是城市環境、生活方式等。
一天,華北社會部領導找到王文談話,“組織上決定派你和王鳳岐同志一起到北平建立秘密電臺。為了合理掩護,由你們倆和一位陳老太太組成一個革命家庭。如果你們雙方同意,組織上可以批準你們結婚。假若不同意,為了革命工作也要裝成名義夫妻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隨后,社會部領導又與王鳳岐進行了同樣內容的談話。她的任務是以家庭主婦的身份掩護、配合王文的秘臺工作,并負責傳遞情報。
1942年冬在組織安排下,王文、王鳳岐與一位陳姓老太太(假扮王文母親)“一家三口”進入北平,輾轉落戶至德勝門新開路大石橋胡同7號一處獨門獨院。房東是日軍憲兵隊的翻譯官,對門是偽警察所的警長,這樣的居住環境為王文一家提供了一道天然保護屏障。
按照情報工作慣例,王文、王鳳岐潛伏北平的前3個月,上級沒有給他們下達任何任務,讓他們集中精力盡快熟悉工作環境,適應城市生活,落實社會身份,對接必要關系。
3個月假扮夫妻的朝夕相處,王文、王鳳岐彼此互生好感,于是他們決定服從組織安排,正式結為夫妻,從此攜手到老,度過恩愛一生。
3個月后,組織上確定他們已站穩腳跟,委托一位法國朋友將王文在平西情報站使用過的電臺運進北平。經測試,這部電臺輸出功率太小,北平城里交流電線多、干擾大,天線又不能架得太高,與后方無法通聯。為盡快開展工作,王文決定自己組裝一部發報機,但日偽時期北平無線電行業受到特務嚴密監控,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王文避開街面上的無線電商行,到隆福寺、護國寺、白塔寺廟會上,在售賣老舊無線電零配件的地攤上一件一件地購買。地攤上實在買不到的,他就時而東城,時而西城,時而南城零散采購,兩個多月后終于湊齊了所需配件,組裝出一臺30瓦輸出功率的發報機。其間,他還搞到了一部美國海軍用的長短波兩用收音機,將其改裝為收報機。他找來一根粗鐵絲,拴在兩根竹竿上搭到房頂,平時晾衣服避人眼目,需要時搭上電臺線就變成了天線。為避開日偽偵測時段,王文選擇凌晨2時到5時開機工作。他還專門模仿日偽電臺報務員的手法,迷惑敵監聽人員。
王文對外身份是銀行職員,每天油頭粉面、西裝革履地上下班。王鳳岐則是一副職員太太的打扮,女游擊隊隊長干練的短發留成了披肩長發,燙成流行的大波浪卷,身著質地上乘的旗袍。在鄰居的眼中,王家是一戶闊綽人家。沒有人會知道,他們每人每天只有一毛五分錢的生活費,有時連飯都吃不飽。白天光鮮靚麗的王鳳岐,到了晚上換上舊衣服,偷偷跑到菜市場撿爛菜葉,一家人煮著充饑。
為了改善生活,農村出身的王鳳岐壘起一個雞窩養雞,既可以吃到雞蛋,又可以作為王文的隱秘“工作室”。夜間,王文鉆進雞窩工作,王鳳岐則站在雞窩上面望風,遇有風吹草動,就用腳跺幾下雞窩報警。一開始,雞窩里的雞對王文的“造訪”十分反感,有的躁動不安,有的咯咯亂叫,有的撲上來叨他,“半夜雞叫”的故事頻頻發生。久而久之,王文和雞相互適應了,彼此相安無事。他每次出來都滿身雞毛,后來雞看見他都不叫了。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王文、王鳳岐夫婦在北平幾進幾出,屢立戰功,經他們發出的重要情報不計其數。清風店戰役期間,駐石家莊敵精銳部隊新3軍第7師北移保定的動向情報,就是王文發出的。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據此調動部隊奔襲100多公里,于清風店地區全殲新3軍軍部、第7師主力和軍直特務營8000余人,活捉國民黨中將軍長羅歷戎。
平津戰役期間,傅作義一度考慮率主力經天津、塘沽從海上撤往青島,北平地下黨偵獲此情報后,即經王文電臺報告上級,解放軍遂切斷了平津鐵路公路。傅作義一招不成又出一招,下令在東單至南跑馬場一帶修建機場,企圖將主力空運至青島,地下黨得此情報后,又一次經王文電臺報告上級,解放軍圍城部隊炮兵迅速封控了東單機場。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際,王文與長期分離的王鳳岐在天津團聚,后來雙雙進入公安系統。王文曾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長,王鳳岐曾任行政處副科長。
《潛伏》劇中余則成的重要功勛之一,就是在平津戰役中獲取到敵天津守軍的防御作戰計劃。英雄從不孤行,天津戰役前夕地下黨的“余則成”們,通過各種渠道先后獲取了8份敵城防計劃,使攻城部隊對敵情有了十分詳盡準確的掌握,得以僅用29小時就攻克了“固若金湯”的天津城。
1948年6月,華北局城工部天津市政工委書記王文源接到上級指示,要求獲取敵天津城防圖。王文源遂把任務交給了國民黨天津工務局職員、地下黨員麥璇琨。麥璇琨當時只是天津城防工程10個工段中第8工段的總監工,并不掌握城防整體情況。為摸清其他9個工段的情況,他以向同行學習為名,四處參觀,伺機搜集各工段圖紙,最終繪制出一份完整的城防圖,包括城防外圍線、護城河寬度深度坡度、人行道、交通壕以及碉堡的位置、形狀、出入口、厚度、高度、槍眼位置與尺寸等詳細數據。
王文源收到城防圖后,馬上交給國民黨天津市地政局測量隊繪圖員、地下黨員劉鐵淳對圖紙作隱匿處理。劉鐵淳當即找到由他單線領導的地下黨員、大眾照相館經理康俊山連夜拍照。康俊山將城防圖分為4塊,縮拍成8寸照片,經化學處理隱去圖像,裱糊在一對老年夫婦2張12寸大照片背面,轉給交通員趙巖送往解放區。
趙巖晚年回憶:“我一看是兩張老年夫婦的單人照片,就有把握了。我說這個好送,好應付。”“我就說我是在天津做買賣的,照片上的兩個老人已經故去了,我是到城市里放大這兩張相片,帶回老家祭拜用的。”
1977年初,在一次老地下黨員座談會上,王文源對大家說“老趙可是立過大功的”,趙巖這才知道他當年送的那兩張照片就是天津城防圖。
麥璇琨一直不知道他繪制的城防圖的下落,直到1991年5位老人聚會時,他才第一次得知,他繪制的那份城防圖在解放天津的時候“管用了”。
當時天津外圍的城防工事建筑工程,由國民黨天津市政府工程局建筑科負責驗收。該科技術員、畢業于北大工學院土木系的張克誠是地下黨員,負責驗收城防工事圍子里專門運送彈藥和給養的城防公路。張克誠辦公桌對面是一位姓常的工程師,負責驗收整個城防工事。此人行蹤詭秘,直接受局長調遣外出查看工事,手中圖紙每天看后都會鎖起來。
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一天下班前,常工程師正看圖紙,局長忽然派人找他,他來不及把圖紙鎖起來,就隨手放在書架上匆忙離去了。張克誠等到辦公室的人都下班走了,把圖紙放進公務包拿回家中復制。
“這是一張天津市城防工事布置圖。圖上把整個城防碉堡包括明堡、暗堡、地堡、外堡、內堡,描繪得很清楚。”
由于這份圖紙很大,張克誠當晚未能完成全圖復制。他的內心很矛盾,不送回地圖,極可能被敵人發現;送回去,估計再也沒有機會得到這份完整圖紙了。考慮再三,張克誠決定冒險把圖紙留在家中。他第二天從容上班,見常工程師正在辦公室到處翻找,就問找什么,常支吾不答,可見并未懷疑到自己。第二天晚上張克誠又描繪了一夜,才完成了整圖繪制,第三天上班將原圖“完璧歸趙”。

張克誠
為防止圖紙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張克誠以檢查城防公路為名,到現場核查,掌握到更詳盡、具體的情況。他在復制圖紙基礎上,自制了一份城防工事圖。“將各種碉堡用不同符號標出,各種碉堡的大小、高度、層次、射孔位置繪制成示意圖,并按照原圖的有關說明,將每座碉堡的設計兵員人數、火力配備、輜重存放位置等注明——這是1948年下半年陳長捷剛剛增建的城防工事,是最新、最完整的城防圖”。
張克誠繪制城防工事圖的同時,還安排由他單線領導的地下黨員、表弟李天祥繪制了一幅天津城區機關、工廠、學校、醫院、車站、碼頭、倉庫分布圖,用不同顏色的筆在圖上標注,并可到實地一一核對。
直到20世紀80年代,李天祥閱讀了時任天津工委企業黨委書記王文化的回憶文章,才知道表哥張克誠當時是天津工委下屬的天津市政銀行委員會委員。
此外,打入到敵天津最高軍事指揮官、警備司令陳長捷身邊擔任警衛連連長的地下黨員王亞川,也利用“保護”陳長捷的職務之便,獲取到敵軍事部署防守圖。
打入國民黨天津市市長杜建時身邊任新聞秘書的地下黨員方紀文,在出席杜建時召集的全市處以上干部會議時,乘亂獲取一張天津城防圖平面圖,縫入座椅墊交給了上級。
天津戰役期間,天津市民常說,解放軍炮彈有“眼睛”,只打國民黨,不打老百姓。
陳長捷被俘后哀嘆:“共產黨調查研究工作的細致達到神化莫察的地步。”
1959年1月,劉亞樓在天津解放1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應該說,天津是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打下來的。在天津戰役開始前,我們拿到一張詳細的敵人城防圖,對各條街道在什么位置,敵人在哪兒,碉堡在哪兒,天津周圍的情況等,了如指掌。這樣,仗就好打了,地下黨對天津戰役的貢獻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