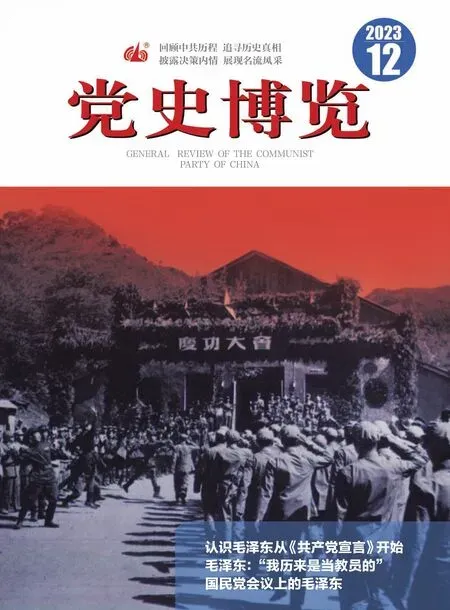博覽之窗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何孜孜不倦研讀《二十四史》
毛澤東愛讀歷史書。從青少年時代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歲月,他都手不釋卷。中南海毛澤東故居藏書中有一套清乾隆武英殿版的 《二十四史》。這部《二十四史》,是工作人員根據毛澤東對中國古籍的廣泛需要于1952年添置的。毛澤東對之愛不釋手,從1952年到1976年,24年朝夕相伴。這套《二十四史》,成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讀得最多、批注圈畫最多的歷史書。
毛澤東之所以24年孜孜不倦、下苦功夫研讀《二十四史》,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 了解中國歷史的客觀需要。當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出國求學,他的同學也都懇勸他出國磨礪,但毛澤東最終還是選擇留在了國內。他說:“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不分晝夜地讀《二十四史》 等中國史籍,就是為了更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就是為了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知道得更多一些、更深入一些、更全面一些。(二) 科學對待我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題中之義。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對待歷史文化遺產,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養。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孜孜不倦研讀《二十四史》 并寫下大量批注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三) 堅持古為今用,讓歷史更好為現實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必然要求。學習研究中國歷史,包括學習研讀《二十四史》,最重要的目的是從歷史中汲取有益的東西,以古人之智慧,開今人之生面。這是毛澤東酷愛讀史的一條主線。
(秋實摘自《黨的文獻》 2023年第3期,徐中遠文)
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的確立和含義
1934年1月,毛澤東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文中指出:“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這實際上明確了群眾路線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群眾成為黨和軍隊的銅墻鐵壁,軍民一心,建立統一戰線,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解放戰爭時期,人民群眾為解放軍運送物資,為取得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重大戰役的勝利提供支持。1943年6月,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 一文中,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共產黨人在理論和實踐中繼續踐行群眾路線。1956年,黨的八大首次將“群眾路線” 寫入黨章,并提出必須不斷發揚群眾路線的傳統。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中,對群眾路線的內涵作出進一步闡明:一方面,人民群眾必須自己解放自己,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工作能否保持正確,要看它是否能夠采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的工作方法。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堅持群眾路線是實現新時期社會發展的根本保證。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對“群眾路線” 的含義作出簡明概括,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晝錦摘自《同舟同進》 2023年第6期,劉思敏文)
周恩來與碧螺春茶葉
碧螺春是中國傳統名茶,產地主要集中在蘇州吳中區太湖洞庭東、西山一帶。1954年4月,日內瓦會議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會議。這是新中國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為參加好這次會議,外交部和有關方面提早做了很多準備。1954年3月中旬,蘇州吳縣(今吳中區)東山西塢村、西山梅益村等地接到采制“分前” 碧螺春的緊急任務。當地村民立即行動,上山采茶,精心炒制,將二斤多的“分前” 碧螺春按期送往北京。周恩來將這包碧螺春帶到日內瓦會場,向各國朋友宣傳介紹中國的茶文化。
1954年6月的一天,周恩來在日內瓦駐地萬花嶺別墅會見澳大利亞外長凱西。主客雙方落座后,工作人員沏茶倒水,用的茶葉就是從蘇州帶來的碧螺春。打開杯蓋,茶湯碧綠清澈,清香襲人,凱西外長連連稱贊。在友好的氛圍下,雙方圍繞日內瓦會議的進程和相關議題交換看法。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會談期間,周恩來請隨行的基辛格品嘗碧螺春。臨行前,周恩來特意把碧螺春作為國禮贈予基辛格,客人倍感中國總理的細心和溫暖,這段佳話在中美交往關系史上廣為流傳。
(洹漳摘自《人民政協報》 2023年4月13日第11版,蘇哲文)
李達兩部“大綱”對構建馬克思哲學體系的貢獻
1937年,李達出版了《社會學大綱》。這部系統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觀點的著作,以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為基本線索,以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三者的同一為基本原則,建構了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
在體系安排上,《社會學大綱》仍然實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二分結構”。《社會學大綱》已經自覺地意識到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基礎,自覺地意識到實踐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存在著內在聯系。《社會學大綱》 的出版,標志著具有“中國元素” 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基本形成。
1961年,毛澤東委托李達再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1965年,李達完成了 《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內部討論稿)》 的唯物辯證法部分,并送毛澤東審閱。同年,毛澤東在閱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 時作了批注。他明確提出,在辯證法的闡述上“不必抄斯大林”。在此之前,毛澤東還提出,“解釋和發揮” 列寧的辯證法思想,“研究中國歷史和中國哲學史”,“改造哲學體系”,這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對建構具有“中國作風”“中國特點” 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期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委托李達編寫 《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實際上重啟了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新探索。
(春華摘自《中國社會科學》 2023年第4期,楊耕文)
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的紅色音樂
20世紀以來,一批海外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初步掌握了現代音樂知識。他們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在音樂創作中將西方音樂與中華優秀傳統音樂文化相結合,突出愛國主義主題,在借鑒傳統曲調客家山歌的基礎上,創作了《十送紅軍》 《革命道路要認清》 等大量紅色歌曲。
抗戰時期,廣大音樂工作者更是借助民歌曲調創作了大量紅色歌曲。如賀綠汀《墾春泥》 借鑒了湖南花鼓戲音調;冼星海更是善于將傳統民族風格與西方作曲技巧融合,創作出《黃河大合唱》 《生產運動大合唱》等合唱作品。
音樂家們另一擅長使用的創作手法是依曲填詞,當時很多紅色歌曲都是在借鑒中國民歌曲調基礎上汲取民間音樂的營養和精華,通過革命話語改編創作而成,“它的形式是舊的,它的內容卻是革命的”。如《東方紅》歌詞就是由農民李有源演唱并改編,再由公木修改而成。后來,賀綠汀創作出四部合唱《東方紅》,作曲家李煥之改編成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使之成為響徹祖國大地經久不衰的經典。
(筱蕾摘自《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2023年第4期,郭路遙文)
張寒暉與歌曲《松花江上》的誕生
在有關東北的抗戰歌曲中,創作于1936年的《松花江上》 無疑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歌曲之一。
《松花江上》 的創作者張寒暉一生都未踏足東北。1936年夏,張寒暉赴西安,任西安省立二中國文教員。張寒暉回憶,該校學生中有一批東北學子,“多數是當官的孩子,公子哥兒氣十足,整天花天酒地,你用心教他們,他們卻不用心學,真把我氣壞了”。學生們不知“亡國恨” 令張寒暉感到十分憂心。同年秋,老友孫志遠探望張寒暉時表示,“東北軍中抗日的情緒正在高漲”,希望張寒暉創作一首“直接反映東北軍思想感情的歌曲”。他還為張寒暉帶來了一本東北軍第67軍出版的《東望》 雜志,雜志封面印著該軍軍長王以哲的親筆題字:“我們何時能返回那美麗的田園?何時能安慰我們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時能救我親愛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 這些話給張寒暉以極大的啟發:“你們不是不想家鄉嗎?我偏偏就講你們的家。我于是寫了個歌詞,就從我的家寫起。” 《松花江上》 就這樣誕生了。
《松花江上》 的歌詞具有很明顯的地域指向,但它的傳唱范圍并沒有局限在東北流亡者中,而是流傳到了全國各地。
(邶風摘自《抗日戰爭研究》 2023年第2期,劉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