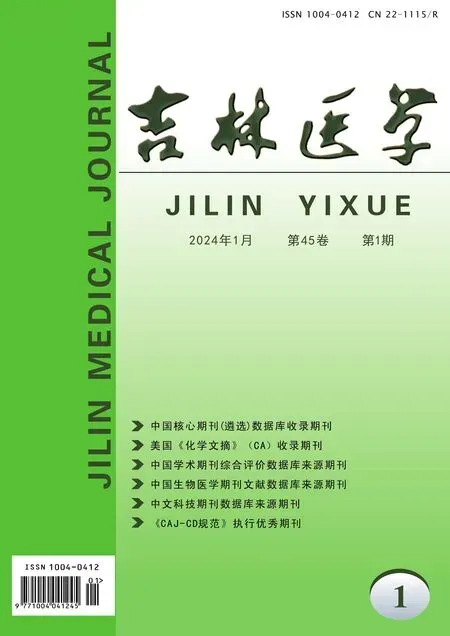可溶性CD146與膿毒癥嚴重程度的關系及對急性腎損傷的預測價值
孫文波
[常熟市中醫院(新區醫院)重癥醫學科,江蘇 常熟 215500]
膿毒癥是一種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性反應綜合征,一直是重癥醫學面臨的棘手難題,亦是重癥監護病房患者病死的主要原因之一[1]。隨著膿毒癥病情的發展,可演變為嚴重膿毒癥膿毒性休克,患者的病死率較高,若能準確地評估病情,及時予以有效治療,是挽救患者生命的關鍵所在。與此同時,急性腎損傷是膿毒癥最常見的嚴重并發癥之一,亦是導致患者病死的重要原因[2]。對此,當前臨床急需尋找與膿毒癥嚴重程度密切相關的實驗室指標,用于準確預測急性腎損傷發生,為膿毒癥的診治提供依據。一直以來,臨床主要采用肌酐、尿素氮等指標用于評估膿毒癥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的風險,然而上述指標存在一定滯后性,判斷膿毒癥嚴重程度的準確性相對有限。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表明,在膿毒癥發生、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腎功能損傷,其中CD146是一種位于內皮細胞且能調控其黏附、增殖等的跨膜糖蛋白,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升高與內皮細胞損傷和腎功能障礙密切相關[3]。由此推測,可溶性CD146與膿毒癥的關系密切,有助于預測急性腎損傷發生,然而相關研究鮮有報道。本研究分析可溶性CD146與膿毒癥嚴重程度的關系及對急性腎損傷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2019年1月~2022年1月常熟市中醫院(新區醫院)接診的145例膿毒癥患者為研究對象,根據嚴重程度,分為膿毒癥組(n=50)、嚴重膿毒癥組(n=57)和感染性休克組(n=38)。其中膿毒癥組男27例,女23例;年齡19~75歲,平均(49.86±6.72)歲;導致膿毒癥的基礎性疾病:肺部感染22例、胰腺炎13例、彌漫性腹膜炎7例、其他8例;嚴重膿毒癥組男29例,女28例;年齡20~74歲,平均(51.23±5.89)歲;導致膿毒癥的基礎性疾病:肺部感染25例、胰腺炎12例、彌漫性腹膜炎9例、其他11例;感染性休克組男19例,女19例;年齡21~76歲,平均(50.23±5.88)歲;導致膿毒癥的基礎性疾病:肺部感染17例、胰腺炎10例、彌漫性腹膜炎5例、其他6例。三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納入標準:①年齡18~80歲;②符合中國膿毒癥/膿毒性休克急診治療指南(2018)關于膿毒癥的診斷標準;③在本院確診并收入診治;④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通過,患者及(或)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配合治療和隨訪。排除標準:①合并晚期惡性腫瘤、嚴重凝血障礙、免疫功能紊亂及膿毒性休克者;②心、肝、腎等重要臟器移植術后者;③近3個月內接受糖皮質激素治療或有輸血史者;④基礎性疾病預后惡劣且短期內可能導致患者死亡。
1.2檢測方法:所有患者在入組24 h內,收集空腹靜脈血10 ml,其中5 ml用于檢測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使用日本HITACHI 76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血肌酐、血尿素氮;另外5 ml靜脈血,使用枸櫞酸鈉抗凝處理,2 000 r/min離心5 min,分離血清,使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檢測試劑盒來源于上海臻科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嚴格按照操作說明書進行檢測操作,采用美國MD SpectraMax 190全波長酶標儀檢測結果。
1.3觀察指標:比較三組血清可溶性CD146、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急性生理與慢性健康狀況評分系統Ⅱ(APACHE Ⅱ評分)、膿毒性相關器官功能衰竭評分(SOFA評分),使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可溶性CD146水平與APACHE Ⅱ評分、SOFA評分;隨訪28 d,觀察急性腎損傷發生情況,以患者在48 h內血肌酐絕對值增加≥26.4 μmol/L或增加≥50%,作為判斷急性腎損傷的依據[4];通過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下面積(AUC)評價可溶性CD146對急性腎損傷的預測效能。
1.4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2.0統計學軟件進行t及χ2檢驗,三組間比較使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組間AUC比較,使用DeLong檢驗。
2 結果
2.1三組可溶性CD146、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比較:膿毒癥組、嚴重膿毒癥組和感染性休克組血清可溶性CD146、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依次升高,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三組可溶性CD146、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比較
2.2三組APACHE Ⅱ評分、SOFA評分比較:膿毒癥組、嚴重膿毒癥組和感染性休克組APACHE Ⅱ評分、SOFA評分依次升高,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三組APACHE Ⅱ評分、SOFA評分比較分)
2.3可溶性CD146與APACHE Ⅱ評分、SOFA評分的相關性分析:經Pearson相關性分析,膿毒癥患者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與APACHE Ⅱ評分、SOFA評分均呈正相關(r=0.345、0.298,P=0.000)。見圖1。

圖1 可溶性CD146與APACHE Ⅱ評分、SOFA評分的關系散點圖
2.4急性腎損傷組與非急性腎損傷組可溶性CD146、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比較:145例膿毒癥患者均獲得隨訪28 d,發生急性腎損傷44例,占30.34%;急性腎損傷組血清可溶性CD146、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均高于非急性腎損傷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急性腎損傷組與非急性腎損傷組可溶性CD146、血肌酐、血尿素氮水平比較
2.5可溶性CD146預測急性腎損傷的ROC曲線分析:經ROC曲線分析,血清可溶性CD146預測膿毒癥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的AUC為0.914(95%CI:0.000~1.000),大于血肌酐的0.690(95%CI:0.421~0.960)和血尿素氮的0.767(95%CI:0.539~0.994),經DeLong檢驗,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Z=2.712、2.248,P=0.000)。ROC曲線見圖2。

圖2 可溶性CD146預測急性腎損傷的ROC曲線
3 討論
膿毒癥是一種因機體對感染反應失調引起的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也是導致急性腎損傷的重要因素[5]。在臨床上,高達50%的急性腎損傷的發生與膿毒癥密切相關,隨著膿毒癥病情的加劇,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的風險隨之增大。對此,尋找與急性腎損傷密切相關的血液學指標,用于評估膿毒癥嚴重程度,有助于指導疾病的診治。近年來,國內外研究表明,在膿毒癥發生、發展過程中,患者機體血流動力學異常,存在明顯氧化應激,導致腎血管收縮,引起腎小管損傷,加上內毒素對腎功能的影響,造成腎臟缺血[6-7]。CD146是內皮細胞活化與損傷的標志物之一,腎小球內皮細胞的損傷可能是膿毒癥病情惡化的重要始動因素[8]。可見,膿毒癥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不斷升高,預示著氧化應激、炎性反應損傷、毒素蓄積等引起的腎小球內皮細胞損傷隨之加重。本研究提示可溶性CD146可能與膿毒癥的病情進展有關;對于膿毒癥患者,若血清可溶性CD146較高,應警惕急性腎損傷發生,及時予以有效干預,以延長病情進展。與Savarin等[9]的研究結果相似。
以往研究報道了血肌酐、血尿素氮等腎功能指標與膿毒癥嚴重程度的關系,然而這些指標出現較晚,對判斷膿毒癥嚴重程度的效能較低,尤其在評估急性腎損傷發生風險上的準確性較低[10-11]。CD146能在腎小管上皮細胞中表達,能夠有效反映內毒素對腎小管和腎小球的損傷程度,推測可溶性CD146水平與膿毒癥嚴重程度有關[12]。本研究結果表明可溶性CD146與膿毒癥嚴重程度呈相關,分析原因為膿毒癥病情惡化,導致腎功能障礙,經腎小球內皮細胞連接部位的CD146釋放量明顯增多。也有文獻報道,感染性休克患者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明顯升高[13],亦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基于本研究的臨床實踐,認為膿毒癥患者機體的炎性反應和氧化應激可增強腎小管上皮細胞合成CD146的能力,加上毒素蓄積、酸堿失衡等病理機制,可加劇內皮細胞連接處受損程度,促進CD146釋放,進而提高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14-15],這可能是可溶性CD146與膿毒癥嚴重程度關系密切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強化對膿毒癥患者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的監測,可能有助于判斷患者的病情演變,指導治療方案的制定,增加臨床獲益。在本研究中,145例膿毒癥患者均隨訪28 d,發生急性腎損傷44例,占30.34%,與既往研究報道結果相符[16]。Abed等[17]研究表明,膿毒癥患者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升高,不僅反映患者病情處于進展狀態,還預示著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的可能性隨之增大。也有研究認為,CD146可調控膿毒癥患者的微血管性炎性反應,介導白細胞增殖,進而導致腎小球內皮細胞損傷[18]。在臨床實踐中,在膿毒癥患者病情好轉的同時,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呈明顯下降趨勢,發生急性腎損傷的風險較小。對此,本研究認為,可溶性CD146水平有助于評估膿毒癥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的風險。表明可溶性CD146預測膿毒癥患者發生急性腎損傷的效能較好,提示在膿毒癥患者診治期間,應注意監測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的波動情況,以衡量急性腎損傷發生的風險。基于本研究結果可知,CD146拮抗劑有望用于治療膿毒癥,期望降低血清可溶性CD146水平,以增加患者的臨床獲益。
綜上所述,可溶性CD146與膿毒癥嚴重程度呈正相關,預測急性腎損傷發生的效能較好,值得臨床予以重視應用。但本研究樣本量不多,未分析可溶性CD146與患者遠期預后的關系,有待日后擴大研究規模,動態監測患者治療期間可溶性CD146的波動情況,深入分析CD146在膿毒癥病理機制中的具體作用,將有助于明確可溶性CD146與膿毒癥的關系,為此疾病的診治提供高級別證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