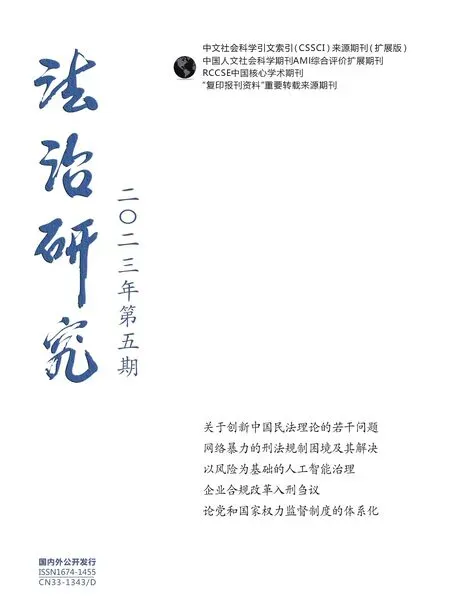《民法典》中近親屬醫療同意的規范構造
周雅婷
《民法典》對醫療知情同意規則的規定基本沿襲《侵權責任法》,置于《民法典》第1219 條第1 款第2句,其中第2 句前段是患者知情同意規則,后段是近親屬醫療同意規則。較之《侵權責任法》第55 條改動處有三:(1)第1 款第2 句前段中的“書面同意”改成“明確同意”;(2)第1 款第2 句后段中的“書面同意”改成“明確同意”;(3)第1 款第2 句后段中的“不宜向患者說明”前增加“不能”的情形。①《民法典》第1219 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具體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并取得其明確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并取得其明確同意。醫務人員未盡到前款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從法條表述來看,前后段間使用分號,意指前后段在法律上作同等評價,即近親屬同意等同于患者的同意。因此,近親屬同意規則應屬于醫療知情同意規則的組成部分,其立法目的和規范意旨應與患者的知情同意規則相一致。但近親屬同意本質上并非患者本人的同意,何時近親屬得為同意,近親屬的范圍如何界定,當近親屬意見和患者意見或者患者可推測的意見不一致時如何處理,近親屬同意在法律上性質如何,醫生是否可根據自身專業和經驗判斷而不采納近親屬意見,以及近親屬濫用同意權的法律后果等,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事實上,日常醫療活動中由近親屬進行同意的情況極其常見,疫苗接種、孕婦生產、外科手術等都需要近親屬簽署知情同意書。同時,也產生許多問題,典型如“肖志軍拒簽事件”“榆林產婦跳樓事件”,其他如手術中更改麻醉方式未取得近親屬同意②參見江西省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贛08 民終2829 號民事判決書。、拔牙后腦出血近親屬補簽知情同意書③參見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9)貴民申5252 號民事裁定書。等情況亦屬常見。當然,醫療活動中還存在大量同時向患者和近親屬告知并取得同意,分別簽署知情同意書或者在同一知情同意書上均簽名的情況,此時的近親屬同意應為患者自身同意的加強或者患者同意的證明人,與本文所討論的近親屬醫療同意不屬于同一范疇,也非法條所規定的近親屬同意。因此,本文所討論的近親屬醫療同意是指只要取得近親屬同意,醫生便可實施醫療行為的情形。
《民法典》第1219 條的規定豐富了近親屬醫療同意的類型,更重要的是,置于《民法典》中有了體系解釋的條件和必要,目的解釋也有更為豐富的資源。本文嘗試從解釋論角度對近親屬醫療同意規則進行闡述,就教于方家。
一、近親屬醫療同意的規范功能
(一)醫療行為的界定
我國現行法律沒有對醫療行為作出明確規定。通常認為《醫師法》第22 條中的“醫師的執業活動”和《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88 條中的“診療活動”是相類似的概念。④參見王岳主編:《醫事法》(第3 版),人民衛生出版社2019 年版,第15 頁;艾爾肯:《論醫療行為的判斷標準》,載《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4 期。《醫師法》第22 條第1 項規定“在注冊的執業范圍內,進行醫學診查、疾病調查、醫學處置、出具相應的醫學證明文件,選擇合理的醫療、預防、保健方案”。《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88 條規定“診療活動:是指通過各種檢查,使用藥物、器械及手術等方法,對疾病作出判斷和消除疾病、緩解病情、減輕痛苦、改善功能、延長生命、幫助患者恢復健康的活動”。學界使用較多的還有我國臺灣地區和日本對于醫療行為的界定,其中我國臺灣地區認為:“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接目的,所為的處方或用藥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之總稱,謂為醫療行為。”⑤轉引自陳聰富:《醫療責任的形成與展開》,臺大出版中心2019 年版,第2 頁。日本學者認為:“醫療行為是指疾病的預防、患者身體狀況的把握和疾病原因以及障害的發現、疾病和障害治療以及因疾病引起的痛苦的減輕,患者身體及精神狀況改善等為目的對身心所作的診察治療行為。”⑥轉引自艾爾肯:《論醫療行為的判斷標準》,載《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4 期。應該說,各國各地區對于醫療行為的界定大致相同,是指針對人體疾病的治療、預防及保健行為。
(二)醫療行為傷害說與非傷害說立場
醫療行為是針對人的身體的行為,難免造成人體傷害。但就一般社會觀念,人們很難將醫療行為與傷害聯系在一起。因此,對于醫療行為存在傷害說和非傷害說。醫療行為傷害說肇始于德國法院“骨癌截肢案”判決,該案認為醫療行為具有傷害性,阻卻違法必須征得患者同意。⑦參見錢葉六:《醫療行為的正當化根據與緊急治療、專斷治療的刑法評價》,載《政法論壇》2019 年第1 期。此后,醫療行為傷害說為德、日等主要大陸法系國家普遍接受,尤其在刑法領域,基于醫療行為傷害說立場討論醫療行為正當化的成果頗豐。⑧參見曹菲:《治療行為正當化根據研究——德日的經驗與我國的借鑒》,載《刑事法評論》第29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240 頁以下。而醫療行為非傷害說則認為醫療行為的本旨在于恢復患者身體健康、保全患者生命,行善原則被認為是醫生必須履行的積極義務,⑨Marc Stauch &Kay Wheat,Text,Cases and Materials on Medical Law and Ethics,Routledge Press,2015,p.17.只要醫療行為是出于維護患者身體健康的目的,就符合患者的最佳利益,不能認為是傷害。⑩同前注⑦。在父權主義醫療時代,醫療行為非傷害說為主導,強調醫者仁術。即便在醫療行為傷害說早期,也以“業務權說”進行正當化解釋,認為醫療行為是為國家、個人的利益并為法律所承認,只要從醫學知識上足以達成醫學目的,且法律未明文禁止就是被允許的,即使可能對病人身體造成傷害。?同前注⑦。但隨著病人權利運動的推進,患者自己決定權獲得重視,醫療行為正當化根據也從“業務權說”轉向“患者同意說”,患者最佳利益成為醫療行為追求的最高目標,且須重視患者的主觀意思。患者的知情同意逐漸成為醫療行為正當化的核心根據。?參見滿洪杰:《醫療損害責任法的體系反思與解釋論構建》,法律出版社2022 年版,第146 頁。普遍認為,醫療知情同意規則成為醫療活動中的基本規則,奠定醫療行為的合法基礎。?參見王岳主編:《醫事法》(第3 版),人民衛生出版社2019 年版,第49 頁。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司法實務對醫療行為傷害說出現動搖。不少實務見解認為,如果醫療行為未造成患者健康上的傷害,即便醫生在醫療行為前未進行充分告知,醫生也無責任,患者也無任何請求權可主張,?BGHZ 176,342.并認為該種情形如果允許患者以人格權受侵害而請求損害賠償,有過于擴張醫生義務之虞。?同上注。此種實務見解實際上緩和了醫生在醫療行為傷害說下的責任,被不少法院采納,亦獲得學界支持。在德國實務中,還有極少數人認為,即使患者基于醫生的不完全告知而同意治療,如果患者在同意時已經知道嗣后可能發生的醫療風險,醫生對于該風險也不承擔賠償責任。?BGHZ 168,103(111).該種案型的說理實際上是否認醫療行為傷害說,在德國屬少數見解,遭到學界批評。由此可見,即便在德國,醫療行為傷害說也時常被動搖。只有在醫生未取得患者同意實施醫療行為,并造成患者健康損害時,穩健地采醫療行為傷害說,而在未造成患者損害時,多采上述第一種案型的見解。
實際上,醫療行為傷害說與非傷害說出現模糊化趨勢。?參見吳志正:《解讀醫病關系IV 醫療訴訟篇(下)》,元照出版公司2022 年版,第65 頁。對于醫療行為客觀上屬于增進或維持患者健康必要且相當、具有社會正當性而符合診療規范及當時醫療水平之要件者,無論采醫療行為傷害說還是非傷害說,其結果并無實質差異。其中,采醫療行為傷害說,是不預先對醫療行為進行違法性與否的評價,而是假設其符合傷害行為構成要件,再在違法性階層進行審查。而采醫療行為非傷害說,則將醫療行為違法性與否的評價提前至構成要件符合性階層,先判斷該醫療行為是否屬于正當的醫療行為。換言之,從法規范評價層面來看,醫療行為傷害說實為一種階層式犯罪構成或侵權構成分析的前提假設,其目的乃基于法律分析邏輯上的考慮,為讓醫療行為正當化事由得以在違法性階層上進行系統探討或體系建構。從判斷結果來看,二者的界限漸趨模糊,區分意義已不明顯。德國學說上也認為,醫療行為正當化需要主觀上出于醫療目的,客觀上遵守一般醫療準則,具有醫學適應性,而患者之所以同意接受醫療行為,也是建立在知悉及確信醫生的行為是根據醫學知識,符合一般醫療準則,以及遵守一切醫療常規下所為。?Tr?ndle/Fischer,StGB,54.Aufl.,2007,§223,Rn.13.即便如此,本文認為,不能讓此種法律邏輯上的醫療行為傷害的預設進入到現實醫療實踐的價值判斷中,換言之,醫療行為傷害說應當僅停留在法律的邏輯推演中,不可進入一般民眾對醫療行為的評價,否則,不但不助益于醫患關系的和諧,反而加深醫患鴻溝。
(三)患者自主決定人格價值
醫療知情同意規則的核心在于保障患者自主決定權,即患者自己的身體與健康由自己決定。其核心要素在于意思決定自由,即患者在決定自己身體與健康時,不受他人欺詐、脅迫或不法干涉。如果患者受醫生欺詐、脅迫而同意接受治療,通常認為醫生侵害患者自主決定權。但在患者因醫生非欺詐而為之勸告、通知、說明、介紹時,即便信息有錯誤或者不充分,進而作出決定,也不能認為患者的自主決定權受到侵害。醫療實務上,醫生未善盡告知義務,致使患者在不充分的醫療信息下同意接受治療,就屬于這種情形。對此,如果認為此時患者意思決定自由未受欺詐、脅迫或不法干涉,則患者不能因自主決定權受到侵害請求損害賠償,尤其是精神損害賠償。
但實際上,對人身完整性的自主決定,雖然具有意思決定的權利外觀,但與物權上的自主處分和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在性質上并不相同。對身體健康與人身完整性的自主決定,除有意思自由成分外,更有人的尊嚴不因疾病而有減損的意義,彰顯其獨特人格價值,屬于人格尊嚴延伸,或者具有“知的利益”和“做決定的自由”?參見楊秀儀:《論病人自主權——我國法上“告知后同意”之請求權基礎探討》,載《臺灣大學法學論叢》2007 年第2 期。
(四)規范功能重構
基于上述討論,醫療知情同意規則在民法上應具有雙重功能:一是醫療行為法律上正當化事由。此種正當化事由并非認為醫療行為本身具有傷害性,而是指當醫療行為固有風險現實化時責任的分擔,或稱之為醫療固有風險分擔功能。二是患者的一項重要權利及人格價值。稱之為患者自主決定人格價值。就近親屬醫療同意而言,因其屬于知情同意規則的一部分,理應具有上述兩種規范功能。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近親屬同意等同于特定情形下患者自己同意,暗含一種法定授權。從權利保障角度,屬于患者自主決定權的延伸,也是特定情況下對患者權利的保障。從責任分擔角度,醫療固有風險非屬純粹患者個人風險,其中身體損害當然只能由患者自身承受,但因身體損害帶來的照顧責任和經濟負擔有不少會由家庭成員承擔,因此,近親屬同意不能簡單認為是代理患者同意,毋寧說,近親屬同意意味著家庭和家庭成員對醫療固有風險的分擔。
二、近親屬醫療同意的適用類型
《民法典》第1219 條第1 款第2 句后段將近親屬醫療同意規則區分為“不能向患者說明型”和“不宜向患者說明型”兩種類型。
(一)不能向患者說明型
此種類型指患者欠缺同意能力時,例如嬰兒、幼童、精神不濟或神志虛弱的人,或者昏迷無法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此時可以由近親屬同意。這里需要討論的問題是患者同意能力的判斷基準。
只是一些簡單的色素附著或者是一些牙石、色素導致的,可以進行洗牙這樣的治療,去除這些黑色的東西,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色素。還有,建議患者可以多吃一些含粗纖維的食物。
民法上與同意能力最接近的當屬法律行為制度。民法采定型化行為能力制度,即主要以年齡劃分行為能力的有無和范圍,輔之以辨認能力標準。實際上,行為能力的有無是事實問題,應當結合行為人年齡、智力及精神狀態就具體法律行為進行具體判斷,不應設立統一標準。?參見梁慧星:《民法總則講義》(修訂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51 頁。考慮到實踐中難以貫徹,故采定型化行為能力制度,而法律行為能力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維護交易安全。同意則屬于行為人對自己權益的處分,非屬交易場合,只需要在同意時認識到可能發生的損害,并不需要具有法效意思。?參見王澤鑒:《侵權行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227 頁。因此,通說認為,患者的同意能力應基于患者個別的識別能力而非行為能力來判斷,不能完全適用民法關于行為能力的規定。
但行為能力制度對于患者同意能力而言,仍具有適用空間。首先,8 歲以下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同意能力應類推適用《民法典》第20 條規定,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實施醫療同意。其次,8 歲至18 歲智力和精神狀態正常的未成年人,是否認為欠缺同意能力,不能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9 條,應當引入個別的識別能力標準,也就是在個案中就患者個別的識別能力進行具體判斷。?參見孫也龍:《醫療決定代理的法律規制》,載《法商研究》2018 年第6 期。只要具有識別能力,仍可以進行有效的同意,而不是必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認。但對于重大醫療行為,通常認為須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此重大醫療行為和患者個別識別能力的判斷應交由醫生。關于未成年人的代為醫療同意,荷蘭《民法典》規定具有參考價值。荷蘭《民法典》第7 編第450 條第2 項規定:“患者為12 歲至16 周歲的未成年人時,亦應取得有監護權的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但為避免患者遭受嚴重傷害,雖未取得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仍可以進行醫療處置。于父母或監護人拒絕同意時,如經病人謹慎考慮后,仍愿進行醫療行為的,亦同。”第447 條第1 項規定:“16 歲以上未成年人,因其已具備醫療契約之行為能力,自己成為得為同意之人,得單獨同意醫療處置行為。”?法條英文版見網站:http://www.dutchcivillaw.com/civilcodebook077.htm,譯文轉引自陳聰富《:醫療責任的形成與展開》,臺大出版中心2019 年版,第146 頁。最后,對于成年人則完全適用個別的識別能力標準。換言之,即使是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成人患者,在具體情況下欠缺識別能力,則無同意能力,應由其近親屬同意。反之,應由患者自己同意。
比較法上,英國《心智能力法》(Mental Capacity Act,2005)就同意能力認定一般標準包括“診斷標準”和“功能標準”。診斷標準指的是有大腦損傷或者大腦功能障礙。功能標準指的是因大腦損傷導致個體不能自主決定。?參見[英]喬納森·赫林:《醫事法與倫理》,石雷、曹志建譯,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22 年版,第208 頁。后者強調的是,如果一個沒有大腦損傷的患者拒絕所有治療,仍然認定其具有心智能力。
(二)不宜向患者說明型
此種類型主要基于保護性醫療理念。為避免和減少對患者的影響,醫務人員常須就患者個人隱私、病情、治療過程等采取一定程度的保密等保護性措施。如針對癌癥晚期患者,出于保護患者情緒和精神狀態的考慮,不向其說明真實病情和治療措施,而僅向家屬說明。在我國醫療衛生領域立法上早有此概念,如2008 年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62 條第2 句規定“因實施保護性醫療措施不宜向患者說明情況的,應當將有關情況通知患者家屬”。保護性醫療的倫理基礎是醫生行善原則,在我國,主要是家庭主義醫療傳統的體現。但實際上保護性醫療是在特殊情況下將患者本人的醫療決定權經由醫生斟酌裁量而移交于患者近親屬。?參見李欣慧、李明:《我國保護性醫療制度及其存在的法律問題》,載《醫學與哲學》2021 年第2 期。這與強調患者自主權的醫療知情同意規則相悖。原《侵權責任法》第55 條只規定“不宜向患者說明”類型,與患者本人知情同意相并列,說明在“不宜”場合,患者近親屬的同意視為患者本人的同意。但“不宜”二字非屬規范用語,其適用的具體范圍、手段、方式、程序等不明確,雖醫療實踐中多適用于末期患者和絕癥患者,但實際上判斷標準難以界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主觀性較強。如果說“不能向患者說明型”還有基于患者具體識別能力的考量,那么“不宜”型則主要基于醫方從專業角度的主觀判斷。因此,要嚴格該類型的適用情形,并且在出現合適的可以告知患者本人真實情況的時候,要及時告知患者本人,回歸到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
需要說明的是,保護性醫療理念是否屬于醫療實踐中的慣例。日本最高裁判所1995 年在一起醫療糾紛案件中認為,對于某癌癥患者醫院未告知其病情真相不屬于未盡告知義務,實際上是認可醫療慣例,限制患者知情同意的適用。?參見[日]能見善久:《日本法中的醫療責任》,趙廉慧譯,載《判解研究》2007 年第1 輯(總第33 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 頁。我國將“不宜向患者說明型”規定在條文中,可以說是將醫療慣例法律化。就其適用效果,如上文所述,不宜擴大其適用范圍,否則患者自身知情同意將空洞化,但是否認定為立法上的不足,還需審慎考慮。其一,保護性醫療理念不僅是醫療慣例,也是醫療領域的立法慣例,同時是傳統東方社會人情交往善意原則的體現,不能因為其確定性不足而主張刪除。其二,法條中并非說不宜向患者說明就減輕或免除醫生告知義務,而是必須向患者近親屬告知,并非剝奪患者的知情權,應該是患者的直接知情權變成了間接知情權,而同意權改由近親屬行使。此為醫療慣例上升為法律規范后的改良,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其三,隨著我國患者權利意識的不斷提升,醫學知識的不斷普及,醫療技術和水平的不斷進步,不宜情形在醫療實踐中的適用會自行減少。試想十年前聽到的癌癥多為不治之癥,如今一些常見癌癥已有有效的治療手段,患者自身的可接受度也在提升。如果一味認為保護性醫療是陋習,應當摒棄,看似有利于患者自身權利保障,實則某種程度上加重患者負擔,也不符合我國社會生活實際。
(三)近親屬的范圍
對于近親屬同意的主體范圍,醫療衛生領域立法曾經有過“家屬或關系人”的表述。?比如《醫療機構管理條例》(2016 年)第33 條規定“: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征得患者同意,并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并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時,應當取得家屬或者關系人同意并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無家屬或者關系人在場,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準后實施。”《執業醫師法》(1999 年)第26 條規定:“醫師應當如實向患者或者其家屬介紹病情,但應注意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后果。醫師進行實驗性臨床醫療,應當經醫院批準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屬同意。”從實務操作來看,因欠缺規范性和確定性,近幾年相關立法都陸續修改為“近親屬”的表述。對于近親屬的范圍,《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一般規定中的第1045 條第2 款作出了界定,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值得說明的是,位于侵權責任編的第1219 條是否一定要適用第1045 條第2 款關于近親屬的規定。有學者認為,第1045 條第2 款的規定本質上屬于婚姻家庭法的范疇,并非所有關于近親屬的規定都要作統一適用,應根據相關制度的立法目的進行具體解釋。?參見陸青、章曉英《:民法典時代近親屬同意規則的解釋論重構》,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6 期。本文贊同該觀點。從目的解釋的角度,“法概念的相對性”能夠修正“法秩序的統一”這一原則,且此種修正不僅表現在不同法律中,甚至在同一部法律中,概念也可能需要作不同的解釋。?參見[德]托馬斯·M.J.默勒斯《:法學方法論》(第4 版),杜志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6 月版,第329 頁。“近親屬”概念在《婚姻家庭法》和《侵權責任法》中功能不盡相同,或者說重要性不能等同,因此并非要完全進行一致解釋,但第1045 條第2 款對近親屬范圍的界定對于此處的適用仍具有規范意義。
具體而言,可區分三種情形。第一,如果8 歲以下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同意能力類推適用《民法典》第20 條規定,就會出現法定代理人范圍比近親屬范圍窄的情況,法定代理人指的是監護人,通常就是父母。因此,針對8 歲以下未成年人,可為醫療同意的近親屬范圍應限定為法定代理人,此種解釋既符合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則,也符合保護低齡未成年人的目的。但有疑問的是,當父母沒有同意能力或不在場時,能否類推適用《民法典》第27 條第2 款關于監護人順位的規定。應區分不同情況來看,在父母沒有同意能力且喪失監護能力的情形,直接適用第27 條第2 款,此時不存在類推適用;在父母沒有同意能力但未喪失監護能力的情形,比如父母酒醉未醒或父母重病意識不清時,應類推適用第27 條第2 款;父母不在場且無法聯系上的場合,應類推適用第27 條第2 款,由祖父母、外祖父母行使同意權,祖父母、外祖父母無同意能力時,由有同意能力的兄、姐行使同意權,若后期聯系上父母,應告知父母并取得其同意;父母不在場但可以聯系上的場合,理應取得父母的明確同意,但可由在場的其他近親屬代為簽字。第二,8 歲至18歲具備識別能力的患者,對于重大醫療行為,可代為同意的主體范圍應與8 歲以下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情況一致。第三,8 歲至18 歲不具備識別能力的患者和成年不具備識別能力的患者,可代為同意的主體范圍應與第1045 條第2 款的近親屬范圍相一致。
需要說明的是,在極端情況下,若患者無一近親屬,僅有長期同住照顧的“關系人”,如保姆或未婚伴侶,該“關系人”能否實施醫療同意。我國立法上基于保護患者利益和防止同意權濫用考慮,對于可代為醫療同意的主體范圍進行限縮,從實施效果來看,有助于規范知情同意規則的適用,但確實存在不便之處。針對上述極端情形,可區分三種具體情況對待。第一,與成年監護制度銜接。當該成年患者已是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時,根據《民法典》第33、35 條規定,可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由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代理進行醫療同意,但應當最大程度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愿。第二,當該成年患者非屬無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為能力人,卻無識別能力時,實踐中醫院往往會在對患者進行醫療行為前,要求患者出具授權委托書,明確由特定主體代為作出醫療同意?參見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21)浙02 民終6046 號民事判決書。,此時應當尊重患者的意思自治。若患者選擇“關系人”代為醫療同意,醫院應當尊重。第三,如患者在入院時已陷入無意識狀態,無法取得書面授權委托書,此時應適用《民法典》第1220 條關于緊急情況下知情同意的特殊規定。
三、近親屬醫療同意的法律性質
(一)推定的同意
有學者認為近親屬的同意屬于推定的患者同意。?參見魏超《:論推定同意的正當化依據及范圍——以“無知之幕”為切入點》,載《清華法學》2019 年第2 期。所謂推定的同意是指現實中沒有當事人的同意,但如果當事人知道事實真相后當然會同意,在這種情況下,基于對當事人一致的推定所實施的行為,屬于基于推定的同意行為。?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上)》(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8 月版,第301 頁。這種同意被認為是法益主體的一種“擬制意志”,是一種規范的結構,而非真實的意志。?參見車浩《:論推定的被害人同意》,載《法學評論》2010 年第1 期。推定的同意阻卻違法的前提是,無法取得或者無法及時取得患者的承諾。構成推定的同意須符合以下要件:(1)法益的可支配性;(2)承諾人的處分權限;(3)承諾人的認識能力和判斷能力;(4)患者未作出承諾;(5)干預符合患者的假定意愿;(6)主觀的違法阻卻要素。?參見[德]埃里克·希爾根多夫:《醫療刑法導論》,王芳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43 頁。
(二)推定的同意的參考資料
有學者認為近親屬的同意應屬于患者推定的同意的重要參考資料。?參見王皇玉:《強制治療與緊急避難——評基隆地方法院九十五年易字第二二三號判決》,載《月旦法學雜志》第151 期。認為在推定的同意概念下,已經隱藏替代不理性當事人做了一個理性的決定,而所謂理性的決定則取決于利益衡量的思考。因此,家屬的意思應屬于患者的理性決定與利益衡量的一項參考資料。?參見黃榮堅《:基礎刑法學》(上),元照出版社2006 年版,第359-360 頁;車浩:《論推定的被害人同意》,載《法學評論》2010年第1 期。基于該觀點,當法定代理人與配偶間或同順位近親屬之間對患者是否進行治療發生不同意見,比如該醫治而不醫治,醫生可基于患者可推測的同意,違反某些近親屬意愿而為治療行為。就理性患者而言,近親屬對其作出的不利的醫療意見,患者不應受約束。也就是說,近親屬無權作出與理性病人意見相違背的意見。正如學者所言,當一種侵犯如此密切地觸及人格的核心,這種允許是一種不能代表的決定。?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 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16 年12 月版,第375 頁。
(三)理性患者的判斷基準
通常認為,近親屬的同意意見應基于理性患者的考量,或者應最大限度尊重患者的真實意愿。所謂理性患者指的是該患者在作出是否進行某項醫療行為決定時,已經對該項醫療行為具有實質重要性的危險有充分了解,是在掌握了重要的醫療信息基礎上衡諸自身情況所作出的決定。?參見楊秀儀:《美國“告知后同意”法則之考察分析》,載《月旦法學雜志》2005 年第6 期。也就是醫生在告知時基于客觀上患者對于醫療信息的需要,并考量醫生的適當裁量余地,形成的客觀標準。
(四)我國應堅持推定的同意說
我國目前理論和實務界通說采推定的同意,從《民法典》第1219 條表述來看,也是認可近親屬的同意與患者本人同意具有相同的效果,即認可推定的同意。?同前注?。但我國臺灣地區有改采推定的同意的參考資料的趨勢,其目的在于規避近親屬對同意權的濫用,主要情形是當近親屬意見重大且明顯損害患者利益時,醫院可不采納。
本文認為,我國目前應堅持推定的同意說。基于以下三點考慮。其一,從法條文義及條文變遷來看,我國始終堅持患者的同意與近親屬的同意具有同一性,早期立法甚至將患者同意與家屬同意并列,并須同時具備。這主要基于自古以來根植于中華文化中的家族文化,在這種文化中認為,家族中個人的生老病死、興衰榮辱是屬于家族事務,而非單純的個人事務。?參見陳傳勇:《醫療知情同意權的合理配置》,載《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1 期。實際上,即便是患者本人同意,通常情況下,意見的形成也是基于家庭成員的共同討論和決定,而近親屬同意,在非緊急情況下,也多數是此前已經家庭成員討論。因此,近親屬同意應當與患者本人同意具有相同效果,性質上就屬于推定的同意。
其二,從與患者本人同意的關系來看,立法和實踐逐漸糾正了過去家屬同意代替患者同意,患者和家屬同時同意,以及患者或家屬任選其一同意的不明確狀態。增加了“不能向患者說明型”,更強調患者本人的同意,使得我國醫療知情同意規則更接近保護患者自主權的本旨。但是,是不是說明我國形成了近親屬同意為補充的“補充同意模式”,?同上注。值得討論。本文認為并未形成該模式,原因有二:一是適用近親屬同意的情況并非少數。“不能”和“不宜”情形的判斷多數是醫生基于具體情形的經驗判斷,法律規范在此僅具有指導意義,無強制性,亦無檢驗功能。因此,從適用比例上來看,不能認為近親屬同意是例外。二是醫療實務中,醫院往往會要求患者簽訂委托授權書,將自己的同意權分配給特定近親屬或者直接由特定人行使,此時的近親屬同意因具備了委托授權,產生了代理的效果,實際上變成了患者本人同意。換言之,近親屬同意在具有授權的情形,并非患者本人同意的補充。既然不是補充,那么第1219 條中的近親屬同意,性質上就應屬于推定的患者的意思。
其三,基于反面解釋,若近親屬的同意屬于可推測同意的參考資料,亦即醫生可以基于專業判斷或醫生推測的患者本人的同意,而不聽取近親屬意見,這其實是讓醫生陷入風險和不確定狀態。若治療之后患者恢復一定健康,但產生高昂費用,患者術后表示若是知道這樣讓家庭背上沉重負擔,自己會選擇不治療,那么費用承擔問題如何解決?若治療后患者恢復意識,但有后遺癥,該損失是由患者自行承擔還是醫生承擔?因此,宜認定近親屬同意等同于患者本人同意,通常情況下,醫生不得推翻。
但是,采推定的同意說存在當近親屬意見明顯違背理性患者意見時的處理問題。此時涉及近親屬濫用同意權的判斷和法律適用,下文詳細論述。
四、近親屬濫用同意權的法律適用
近親屬濫用同意權通常指近親屬意見重大且明顯損害患者利益。一般來說,指的是該醫治而近親屬不同意醫治情形。對于近親屬執意要醫治情形,難謂濫用同意權,因為不能做醫療行為惡意的假設。因此,對于近親屬濫用同意權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緊急情況下近親屬拒絕治療,二是非緊急情況下近親屬拒絕治療。
(一)緊急情況下近親屬拒絕治療
在緊急情況下,患者本身無法做同意與否的表示,而患者近親屬表示不同意繼續治療時,醫生是否應依據近親屬意見而停止醫療行為。此時,患者病情緊急,無法表達意見,如果不予以治療,可能立即死亡,而患者近親屬拒絕治療,但并非患者本人表示拒絕治療。醫生將陷入理性病人意見與家屬意見二者不一致的抉擇難題。此時,是否可適用《民法典》第1220 條進行緊急診療,關鍵在于近親屬拒絕治療是否屬于該條規定的“不能取得近親屬意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0〕17 號)(以下簡稱《醫療損害責任糾紛解釋》)第18 條規定了不能取得近親屬意見的情形“(一)近親屬不明的(;二)不能及時聯系到近親屬的;(三)近親屬拒絕發表意見的;(四)近親屬達不成一致意見的;(五)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其中第一、二種情形屬于客觀不能,顯然不能適用,能否適用第三、四種情形,從文義解釋上,此二種情形屬于主觀不能中的近親屬意見不明確,而非近親屬明確拒絕,實難進行涵攝。對于此問題,學理和實務多有分歧。學理上有觀點認為,此處的“不能”僅指客觀不能,不包含主觀不能。?參見程嘯《:侵權責任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643 頁。在立法機關釋義書中可以看到,民法典編纂過程中有建議在“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親屬意見”后增加“或者近親屬意見明顯不利于患者”,但最后沒有被采納。對此,立法機關的解釋是,在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下,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情況多種多樣,比較復雜,如果一概規定醫療機構可以實施強行治療,不但違反了意思自治原則,同時對患者及其家庭也不一定有益。?參見黃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釋義》,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54 頁。
司法實踐中,有些法院認為,應當對“不能取得患者或者近親屬意見的”情形進行擴張解釋。例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頒布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審理指引》第36 條規定,當近親屬拒絕發表意見,近親屬的意見不一致且形不成多數意見的,以及近親屬的意見明顯不利于患者利益時,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準,為挽救患者生命,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審理指引》(2015 年)第36 條規定“:下列情形,患者生命垂危且不能表達意見,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準,為挽救患者生命,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一)近親屬不明或者無聯系方式的;(二)有聯系方式但聯系不到近親屬的(;三)近親屬拒絕發表意見的;(四)近親屬的意見不一致且形不成多數意見的(;五)近親屬的意見明顯不利于患者利益的;(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前款情形下,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怠于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造成患者損害,患者請求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有觀點認為,醫療機構在是否采取緊急救治措施上,患者近親屬的意見重大且明顯地損害患者利益時,醫療機構應當拒絕接受患者近親屬的意見。?參見最高人民法院侵權責任法研究小組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年版,第404 頁。
本文認為,對于搶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緊急情況,醫生應就患者的身份、年齡、病史、當時的病情,參酌患者曾經表示的意思等,基于患者最大利益原則,作出醫療決定,實施緊急診療行為。如果醫生認為,依據理性病人的決定與患者近親屬意見相同的,比如,患者年事已高,病情嚴重,患病時間長久,生不如死,曾經表示不愿再給子女增加負擔,可依據患者家屬的意思,不為醫療行為。但如果患者家屬的意見重大且明顯損害患者利益時,醫生應基于患者本身可推知的意思,為患者進行醫療行為,而此時近親屬的拒絕治療應認定為同意權的濫用。《民法典》第132 條規定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其效果以承認權利存在、否認其行使為原則,具體而言,權利行使為民事法律行為應認定無效,為事實行為應禁止或停止該事實行為。?同前注?,第220 頁。對于近親屬同意權,基于前述論證,其為推定的患者的同意,也就是在患者不能或不宜作出醫療決定之時,近親屬的同意視為患者同意,可認為屬于近親屬擁有的一項合法權利,理應受到禁止權利濫用原則的約束。通常來說,認定權利濫用應由司法機關來判斷,不能交由權利人或相對人自行判斷。但本文認為,在近親屬意見對患者有重大不利益時,應賦予醫生根據其專業知識和經驗判斷近親屬構成權利濫用而不采納近親屬意見的權利。此時,醫生雖面臨評估患者意見的難題,但這既屬于醫生的緊急救治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醫師法》第27 條第1 款:“對需要緊急救治的患者,醫師應當采取緊急措施進行診治,不得拒絕急救處置。”,也屬于對于患者溫暖的關照,為醫療倫理中行善原則的表現。?參見陳聰富:《醫療責任的形成與展開》,臺大出版中心2019 年版,第192 頁。因此,在“肖志軍拒簽事件”中,患者關系人肖志軍拒絕簽字以及衛生行政主管人員的指示,使得醫生發生錯誤認識,誤認為自己并無行剖宮產進行緊急救治的義務,或者誤認為自己不進行救治有違法阻卻事由,但實際上,這種錯誤認識在民法上無法作為違法阻卻事由。但拒絕治療行為對于患者的死亡具有原因力,可依據過失相抵原則,減輕醫生的賠償責任。《德國民法典》在2013 年增訂醫療契約條文時,在第630 條之4 第1 項第4 句規定:“急迫措施之同意無法適時取得時,得依可得推知之病人意愿,于無同意情形實施。”51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臺大法學基金會編譯《:德國民法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第589 頁。
(二)非緊急情況下近親屬拒絕治療
在非緊急情況下,醫生履行告知義務后,近親屬表示不同意繼續診療。此時因為情況非緊急,不為繼續治療不至于造成患者重大損害或生命危險,不宜認為是權利濫用。比如腎結石患者疼痛難忍,但不至于威脅生命,近親屬不同意手術治療,此時醫生應尊重近親屬意見。醫生依據近親屬拒絕治療的意見而不予治療,就屬于患者推定的同意,具有阻卻違法的效力,即使產生損害,也無須負賠償責任。不治療雖不至于發生生命危險,但對患者有重大不利益,是否可認為患者近親屬意見屬于同意權的濫用,值得討論。
醫療實務上,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醫生為避免陷入患者和近親屬意見相左的兩難境地,不告知或不充分告知,而進行手術或特殊治療手段。如果事后患者治療效果良好,一般不會產生分歧,如果事后患者治療效果不好,在多數醫療糾紛案件當中,52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蘇民申7965 號民事裁定書。因無法證明不告知或不充分告知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而適用2021 年生效的《醫療損害責任糾紛解釋》第17 條5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 條規定:“醫務人員違反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義務,但未造成患者人身損害,患者請求醫療機構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不予支持。”。這里涉及醫生違反知情同意的告知義務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問題。對此,學說上存在主觀說、客觀說、修正的主觀說。主觀說認為此時因果關系的判斷應依據患者的個人情況。54Buchan v.Ortho Pharmaceutical(Canada)Ltd.,(1986)25D.L.R.(4th)685.客觀說認為應以理性患者作為判斷標準,但同時也須考量患者的特殊情境。55See JONES,supra note17,at556-557.修正的主觀說認為應采主觀說,但必須考量客觀上的評價。56See JONES,supra note17,at562.我國司法實務中,有判決認為“醫方雖然術前對腦梗塞的發生、術式的選擇上溝通不充分,但是根據患者周某某雙膝關節病變情況,市一院選擇雙膝關節置換術有手術指征”,57參見江蘇省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07 民終1536 號民事判決書。“周某某術后腦梗塞并非市一院未盡說明義務所致”58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蘇民申7965 號民事裁定書。。從該判決來看,所采立場為客觀說,也就是以理性患者為判斷標準。但也有判決認為“違反告知、說明義務的過失應承擔的責任比例與其他診療行為的過失不同,其通常不會造成人身的損害,而是表現為在醫師充分告知的情況下患者若作出不同選擇可能產生的后果與實際發生的后果之間的差額。若兩種后果之間不存在差額,或實際后果比作出不同選擇可能產生的后果要好,則可認為不存在損害后果,醫方不必承擔賠償責任”。59參見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浙02 民終129 號民事判決書。應該說,該判決所采立場為修正的主觀說。
醫療實務的現狀和司法實務的立場,實際上會變相成為醫生不履行或不充分履行告知義務的理由,長此以往,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會加劇。對此,學說上出現二行為理論,即醫生在實施治療前的告知說明行為與后續醫療行為屬于二行為,各有其行為標的、義務與責任。60同前注?,第42 頁。根據該理論,告知說明義務履行責任的基礎在于保障患者自主決定權,而后續醫療行為責任基礎在于保障患者接受符合診療規范的診療行為,二者分屬于不同的責任,不能等同。亦即,如果醫生違反告知說明義務,但后續醫療行為符合醫療常規,不得以違反知情同意規則推定醫療行為可歸責。本文贊同該觀點,應該說從我國立法和司法解釋結合來看,有采此意的傾向,理由如下。其一,《民法典》第1219 條第2 款規定醫生違反知情同意規則的請求權基礎,但何為“造成患者損害”需要進一步明確,《醫療損害責任糾紛解釋》第17 條明確規定須造成患者“人身損害”始得請求賠償責任,對“損害”進行了具體化。但是司法實務上對于二者間的因果關系仍有不同理解。如果僵化地認為需要未履行知情同意義務直接造成人身損害,則該條將無法適用,因為所有的損害只能是由醫療行為產生。如果認為不同手術方案的選擇將產生不同后果的差額屬于損害,雖然更具合理性,但是證明和說理難度較大。但如果只要醫生存在知情同意的履行瑕疵就認定損害,則又過于擴大醫生責任。因此,將知情同意義務與后續醫療行為進行二行為的分隔討論,具有精確劃分責任的優勢,值得肯定。其二,從客觀醫療實務上看,患者并非聽取醫生告知說明后就一定會接受后續醫療行為,期間會因為各種各樣的情況而使得二行為并非一定前后相繼發生,因此二行為理論是符合醫療客觀實際的。其三,從造成患者法益侵害結果的因果關系進程來看,違反知情同意規則的行為只是制造了患者法益侵害的可能性,需要患者或近親屬作出同意而實施后續醫療行為才可能發生人身損害的結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在非緊急情況下,如果近親屬拒絕治療的意見對患者有重大不利益,同樣應認定近親屬同意權濫用。當然,為避免某一個醫生的專斷,應有一定的程序保障,比如經科室綜合診斷形成意見等。此時應可類推適用《民法典》第1220 條,認定此情形屬于“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緊急情形,醫生可以基于患者的推定的同意,違反近親屬表示的意愿而為治療行為,無需承擔因知情同意規則而產生的賠償責任。當然,如果后續醫療行為存在過錯造成患者損害,則應當承擔相應損害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