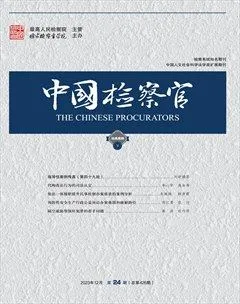代購毒品行為的司法認定
李心華 高永秀
摘 要:對于代購毒品行為的司法認定,首先要對代購毒品中的“代購”作出準確界定,即對受托人的地位作出形式判定,受托人自行尋找毒源并完成毒品交付,是獨立的毒品犯罪交易主體,成立販賣毒品罪正犯。其次將牟利與否作為代購毒品行為準確定性的關鍵要素,代購者收取、私自截留部分購毒款、毒品或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認定為加價或變相加價牟利情形,以販賣毒品罪論處;代購者從托購者事先聯系的販毒者處,為托購者購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的或者蹭吸、共吸的,一般不認定為販賣毒品罪;對于非牟利型代購毒品行為,則從主觀方面和代購毒品數量進一步認定。
關鍵詞:毒品交易 代購 牟利 販賣毒品罪
“代購”顧名思義就是代人跑腿、購人所需,在民事上屬于代理行為。[1]代購毒品指的是代購者根據托購者的委托購買毒品的行為。司法實踐中代購毒品行為復雜多樣,在行為的界定和牟利的認定上,存在較多難點,進而在法律適用上產生分歧。
一、代購毒品行為的法律適用分歧
[案例一]被告人劉某某與楊某某租住在一起,二人均吸食毒品。2012年9月中旬和10月10日前后,劉某某應楊某某要求,兩次分別以人民幣300元和350元的價格從他人處購買0.3克、0.5克甲基苯丙胺給楊某某用于吸食。法院認為劉某某兩次為楊某某代購用以吸食的毒品的行為,因無證據證實其從中牟利,故不應認定構成販賣毒品罪。[2]
[案例二]2019年6月至8月期間,被告人山某先后4次為宋某某代購毒品共計1g,每次均以每克人民幣200元價格從曹某處購得毒品,購買毒品后山某與宋某某共同吸食毒品。2019年8月4日22時許,張某某通過微信與山某聯系購買冰毒并向山某微信轉賬支付人民幣530元,山某通過微信與曹某聯系購買冰毒約0.2克,并通過微信支付毒資400元;后山某將該冰毒交給張某某并從中獲利人民幣130元。法院認為被告人山某販賣毒品0.2克,其行為已構成販賣毒品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1個月,罰金人民幣2000元。[3]
[案例三]2015年5月初,被告人齊某某與信某甲一起吸食毒品后,提及自己可買到低價甲基苯丙胺,信某甲與其哥哥信某乙即欲購買。同月9日,齊某某乘火車到廣東省陸豐市,與毒品上家商定取貨價格為每克人民幣40元,送貨價格為每克人民幣80元。齊某某遂電話告知信某甲每克人民幣80元,信某甲與信某乙商議后,決定購買甲基苯丙胺4000克,先向齊某某匯購毒款人民幣22萬元,尾款收貨時付清。同月14日,齊某某從上家購買甲基苯丙胺7包,并駕車運往遼寧省。16日15時許,齊某某在京沈高速公路塔山服務區被抓獲,現場查獲甲基苯丙胺7包,共計6974.8克。齊某某辯稱自己是代購毒品,法院判決認為被告人齊某某為獨立毒品上線,齊某某販賣、運輸毒品數量巨大,罪行極其嚴重,又系累犯,判處死刑。 [4]
上述案例代表了司法實務中典型的代購毒品或者辯稱為代購毒品的行為。關于上述行為的定性,因對代購者地位界定不明、牟利認識不清等原因,導致實務中案件處理標準不一,爭議焦點主要在于對相關毒品違法犯罪行為是否評判為販賣毒品罪。厘清毒品代購行為,從類型化角度提出法律適用意見,對于認定獨立成罪、共犯或出罪具有重要意義。
二、代購毒品中“代購”的界定
(一)“代購”的概念厘定
代購毒品這一表述是在最高法審判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中逐漸細化明確的。代購毒品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代購毒品中的“代購”,是指行為人受吸毒者委托無償為吸毒者代為購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案例一中劉某某為楊某某代購用于吸食的毒品,劉某某沒有從中加價,就是狹義的代購毒品。
廣義的代購毒品中的“代購”,還包括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代購毒品以及介紹毒品買賣等情形。如明知他人購買毒品的目的是販賣而幫助其聯系購買毒品的,行為人主觀上有為他人販賣毒品提供幫助的共同犯罪故意,客觀上有非法買賣毒品的行為,因此無論其是否從中獲利,都應當按照販賣毒品罪的共犯處理。案例二有代購后“蹭吸分食”情形,如山某為宋某某代購毒品,購買毒品后山某與宋某某共同吸食毒品。該類型的代購行為表現為代購者代購毒品后與托購者當場分食,或收取部分毒品以供日后吸食。[5]案例二還包含了加價代購毒品行為,該類型的代購行為表現為行為人為他人代購用于吸食的毒品,代購者加價牟利銷售毒品,山某為張某代購毒品,從中獲利人民幣130元,就是加價代購毒品。
(二)“代購”的行為界定
販賣毒品罪是以公眾健康為保護法益的抽象危險犯,代購的毒品交付后可能存在將毒品擴散給他人的行為,具有侵害公眾健康的抽象危險。[6]毒品犯罪危害性極大,代購毒品行為加速了毒品擴散危險。在打擊毒品犯罪時,要準確區分認定代購毒品行為和辯稱為代購毒品但實際上是獨立的販賣毒品的行為。因此在實務上,首先要對受托人的地位作出形式判定,再考慮其行為實質作進一步評價。
形式上先判定受托人是獨立的交易主體還是居間的代購者。在當前持續高壓嚴打的禁毒環境下,對于購毒者來說,毒品交易的最大難度在于找到隱蔽的購毒渠道,購毒者對毒品價格和質量等都有較高的容忍度。2023年6月印發的《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昆明會議紀要》)指出,購毒者無明確的托購意思表示,又沒有其他證據證明存在代購行為的,一般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案例一和案例二中代購者均是應托購者的要求,在托購者明確的意思表示之下購買毒品的,可以認定為代購毒品行為。反之,若購毒者沒有明確的購毒渠道,行為人自行尋找販毒者并買回毒品,明顯超越了“為他人代購”毒品的基本范疇,不能再被認定為代購毒品。[7]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確立一個基本的判斷原則,即為購毒者尋得販毒者,聯系到毒品來源,并完成毒品交付,就算仍由購毒者出資,行為人不應當確認為代購者,其在交易地位上應列為獨立的交易主體,不能認定為是代購毒品行為,應以販賣毒品罪論處。
本文案例三即不能認定齊某某為代購毒品的行為。信某甲、信某乙與齊某某事先對齊某某是否獲利、獲利多少、獲利方式等均無約定。但在實際交易時,齊某某先以每克40元的價格與販毒者完成交易,而后對信某甲、信某乙隱瞞該重要價格信息,再以每克80元的價格賣與信某甲、信某乙。此時,齊某某向購毒者隱瞞重要價格信息從中牟利,實質上是加價販賣,齊某某實際上已經成為購毒者信某甲、信某乙的實際上家,不再是居間介紹人。齊某某主觀上與販毒者及購毒者信某甲、信某乙均無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觀上也不是為販毒者與信某甲、信某乙提供交易機會,以促成販毒者與信某甲、信某乙達成毒品交易,而是其本人實際參與交易,即先作為下家與販毒者達成交易,再作為上家與購毒者信某甲、信某乙達成交易,其與前后環節的交易對象都是上下家關系,顯然不屬于代購行為,而是獨立毒品上線,應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
三、代購毒品行為的定性
(一)代購毒品“牟利”的認定
界定代購毒品行為后,牟利與否是對代購毒品行為準確定性的關鍵,代購者加價或者變相加價從中牟利的,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昆明會議紀要》指出,代購毒品加價或變相加價牟利有兩種情形:一是在交通、食宿等必要開銷之外收取“介紹費”“勞務費”;二是收取、私自截留部分購毒款、毒品。第一種情形是金錢性質(包括貨幣、有價證券或其他容易變現的財物等)的牟利,爭議性不大。如案例二山某在代購過程中獲利130元,認定代購牟利,構成販賣毒品罪,其他無獲利的4次毒品代購行為均不認定為販賣毒品罪。第二種情形通過毒品回饋方式體現的非金錢性質的“牟利”,在理解和適用上存在困惑。但《昆明會議紀要》明確用毒品支付勞務報酬、償還債務或者換取其他財產性利益的,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是對“毒品事實上是一種財產性利益”的進一步確認。從毒品交易的現實狀況分析,在吸毒者群體中,毒品與貨幣等一般等價物之間有較穩定的兌換關系,二者價值容易通過交易互轉,因此代購者只要從代購行為中獲取部分毒品作為好處,亦即獲得了能以貨幣衡量的有價財物。換言之,對于托購者來說,其收到的毒品數量減少,毒品的單價實際上提高了,代購者的行為實質上相當于變相加價出售毒品,認定該行為實質就是牟利并無不妥。
(二)代購毒品并收取、私自截留毒品、蹭吸共吸行為的區別定性
如前所述,收取、私自截留毒品是變相加價牟利,對代購者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但《昆明會議紀要》指出,代購者從托購者事先聯系的販毒者處,為托購者購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并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的,一般不以販賣毒品罪論處。司法實踐中,對收取毒品、截留毒品、蹭吸或共同吸食等行為是否認定為販賣毒品罪需要謹慎處理。
一是收取毒品。收取毒品隱含之意是征得購毒者同意,不管是受脅迫還是主動提出,一般分為作為酬勞的收取毒品和接受贈予的收取毒品。收取毒品有的是基于雙方約定,有的是托購方默許,有的是托購方事后贈予。若將無約定的事后贈予行為定性為販賣毒品罪,將會出現因犯罪既遂后的行為對既遂前的行為進行刑法評價,造成罪刑責錯位的矛盾。其間亦要防止遺漏、逃避處罰的兩種情形:一種是購毒者事后將毒品用來支付代購行為持續期間而發生的差旅費等成本支出,此時雙方已形成債權債務關系,購毒者以毒品償還債務,應當以販賣毒品罪定罪處罰。另一種是代購者屬于“以買養吸”的職業型代購,此類代購者長期頻繁為不同購毒者服務,購毒者心照不宣,雖無約定和承諾,亦可推定代購者受托時主觀上有形成默契的牟利,而非單純的事后被動受贈。
二是私自截留毒品。私自截留毒品是《昆明會議紀要》新增的內容,包含兩層意思:其一表明代購行為尚未完成交付;其二未征得購毒者同意,是代購者擅自處分。私自截留毒品比收取毒品更能體現代購者的牟利沖動,但《昆明會議紀要》將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作出特別規定,當代購者從托購者事先聯系的販毒者處,為托購者購買僅用于吸食的毒品,考慮到該行為實質上相當于吸毒行為和幫助吸毒行為,一般不認定為販賣毒品罪。如何判斷何為“少量”毒品,從常理上判斷,此處的“少量”既指絕對的數量少,也指相對比例小。若代購者只單人吸食了一次或者當場吸食完交付的,基本可以推定是屬于“少量”毒品。
三是蹭吸或共吸毒品。蹭吸是代購者通過與托購方共同吸食毒品而獲得的一項“福利”,可以分為代購者交付毒品前有約定的“蹭吸”和購毒者事先未承諾或默許,而是在收到毒品后為表示感謝主動邀請代購者共同吸食。如案例二中山某先后4次為宋某某代購毒品后均共吸毒品,無證據表明蹭吸行為是購買前約定,判決中沒有認定為販賣毒品。若系有約定的蹭吸,表明代購者是有牟利故意的,其實施代購行為時已明知自己可以獲得好處,事后也獲得了分食的利益,是否以販賣毒品罪論處仍有爭議。但可以作類比分析,舉重以明輕。相對于收取、截留毒品,蹭吸型牟利是主觀惡性和危害性最輕的獲利行為。代購者一般當場參與吸食,不擁有毒品所有權和處分權,吸食的毒品也不可能像收取、截留的毒品有再次參與市場流通和擴散的風險,再者單次吸食的數量也有限,認定為“少量”毒品并無不妥。綜上,約定蹭吸行為輕于收取、私自截留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就算仍屬于代購“牟利”中的一種情形,在情節顯著輕微情況下,一般不以販賣毒品罪論處。其間要顧慮的是防止職業型的代購逃避處罰,實踐中可通過審查代購者和購毒者的關系親疏,是否系偶爾性的代購行為,綜合判斷其行為性質是否已發生根本改變。
(三)未牟利型代購毒品行為的定性
未牟利的代購毒品行為如何認定,要先從主觀方面考慮。對于代購毒品行為,認定其未從中牟利的,若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代購毒品的,以相關毒品犯罪的共犯論處;若沒有證據證明代購者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代購毒品,代購者代購的毒品數量未達到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標準的,不以犯罪論處。如案例一中劉某某應楊某某要求為其購買毒品,劉某某購買毒品的目的在于滿足托購者楊某某的吸食需要且沒有牟利,購買毒品的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促成了毒品交易,但其在主觀上沒有販賣毒品的共同犯罪故意,故對其不能以販賣毒品罪論處。代購者代購的毒品數量未達到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標準的,最終不以犯罪論處。若毒品數量達到定罪標準的,對托購者、代購者均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若代購毒品在運輸途中被查獲,且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