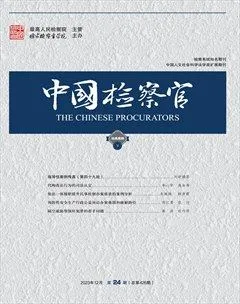人身檢查措施的違法性認定與適用原則
李繼華 王興周 杜同舟
摘 要:人身檢查是刑事偵查的一種重要手段。刑事案件證人是否可以作為人身檢查的適格對象,以及男工作人員能否作為檢查婦女身體的適格主體,是偵查監督實踐中遇到的疑難問題。證人可以成為人身檢查的適格對象,從保護婦女權利和人格尊嚴的立法目的出發,應將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第3款規定的“婦女的身體”限縮解釋為婦女身體的隱私部位,因而男工作人員對婦女的非隱私部位進行人身檢查不具有違法性,但應遵循關聯性原則、有限同意原則與身份區分原則。
關鍵詞:人身檢查 目的性限縮解釋 主體對象 適用原則
人身檢查對查清案件的性質、犯罪的手段和方法,作案所用的工具及犯罪的情節,從而準確認定犯罪事實、查明犯罪人具有重要意義。刑事訴訟法要求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身體應當由女工作人員或者醫師進行檢查,即貫徹同性別保護原則。然而實務中由男偵查人員對婦女進行人身檢查的情況并不鮮見,從而產生其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的違法性認定問題。
一、人身檢查措施的違法性認定爭議
[基本案情]2023年3月某日凌晨,犯罪嫌疑人王某與情人陳某乙(女)的哥哥陳某甲因瑣事發生糾紛,持菜刀將陳某甲砍傷致死,陳某乙系現場目擊證人。兩名民警在案發現場樓道處用棉簽提取陳某乙面部他人濺射血跡一處,在陳某乙手指甲提取拭子一枚,用采血卡在陳某乙手指提取血跡一份。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人員發現對陳某乙進行人身檢查的兩名民警均為男性。
刑事訴訟法第132條規定,“為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可以對人身進行檢查,可以提取指紋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樣本”“檢查婦女的身體,應當由女工作人員或者醫師進行”。本案中,兩名男性民警在陳某乙的面部、手部提取生物樣本的行為是否違法存在爭議。爭議焦點可概況為兩點:其一,證人是否可以作為人身檢查的適格對象;其二,男工作人員能否在特定情形下成為婦女人身檢查的適格主體。
二、證人可以成為人身檢查的適格對象
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外,證人能否作為人身檢查措施的適格對象,是本案中偵查行為是否違法的爭議問題之一。有觀點認為人身檢查的適用對象應限于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不得對其他人采取[1];亦有觀點贊同人身檢查的對象包括證人[2]。筆者認為,證人亦應屬人身檢查的適格對象。
(一)符合條文目的
就刑事訴訟法第132條作字面理解,“為了確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傷害情況或者生理狀態”系不包括對象限定語的目的性表述。換言之,即凡利于該目的實現,證人亦不為法律所排除適用。本案中因陳某乙的體表留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生物樣本而對其進行身體檢查即為適例。
(二)符合條文邏輯
刑事訴訟法第128條為“勘驗、檢查的范圍”,該條規定了檢查的范圍涵蓋“與犯罪有關的……人身”,并未限定人身的主體范圍。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與第132條屬于“總-分”邏輯關系,前條文效力及于后條文,將證人作為人身檢查的對象,符合刑事訴訟法條文邏輯。
(三)符合客觀需求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在實務中,偵查機關對目擊證人進行身體檢查的現象并不鮮見,其目的在于通過人身檢查全面收集證據,迅速偵破案件。立法者在懲罰犯罪與保護人權的價值選擇中持動態平衡的觀點。證人對于偵查機關發現客觀真實意義重大,同樣負有接受人身檢查等偵查措施在內的容忍義務,只是對其可采取的人身檢查種類與強制程度均明顯低于犯罪嫌疑人。在本案中,從陳某乙體表提取的生物樣本能夠幫助確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傷情、生理特征及狀態,故對其采取人身檢查措施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第1款之規定,陳某乙系人身檢查措施的適格對象。
三、男工作人員特定情形下可作為婦女人身檢查的適格主體
從立法目的和司法實際出發,男工作人員在一定條件下應當被允許作為婦女人身檢查的適格主體,但應限縮解釋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第3款中“身體”概念的外延,補充隱私部位的界定,從而準確貫徹刑事訴訟人身檢查過程中的同性別保護原則。
(一)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第3款作目的性限縮解釋的合理性
法律實施離不開法律解釋。面對豐富多彩的司法實踐,對法律條文作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釋,作處理結果符合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解釋,是司法機關保障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的應然選擇。目的性限縮解釋作為一種法律漏洞補充方法,指依法條之文義已涵蓋某一事實類型,但依立法目的,該類型本不應包括在內,于是將該類型排除在法律適用范圍之外,積極地將不合規范意旨部分予以剔除。[3]換言之,目的性限縮的適用前提是法律條文可預測的理解范圍過廣、涵攝面過大而形成法律漏洞,導致對個案判斷違背常理。在前述案例中,立足司法實際和常理常情,將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第3款中“婦女的身體”限縮解釋為婦女身體的隱私部位,并進一步將概念外延界定為陰部、胸部、臀部、腰部、大腿等人們通常認為的隱私部位符合本法條保護婦女人身權利和人格尊嚴的立法目的。
在法律適用技術層面,司法機關在個案中作目的性限縮解釋具有實務可行性,且有其先例可循。在2020年王某非法交易費氏牡丹鸚鵡一案中,交易標的雖為禁止交易的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但涉案30只鸚鵡系由人工繁育,總價不過幾百元,若對法律進行字面的文義解釋,預期刑罰將高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明顯悖于立法目的。經審慎調研論證,徐州鐵路運輸檢察院認為王某等的行為未實際侵害瀕危野生動物資源或造成瀕危野生動物被侵害的風險,決定對王某等人作不起訴處理。[4]檢察機關在該案中對犯罪嫌疑人的出罪處理,正是運用了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即在瀕危野生動物的認定過程中排除了已被廣泛人工繁育的費氏鸚鵡。案件處理結果順應了民眾對法律的樸素認知與期待,真正實現了“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
在實質價值層面,通過目的性限縮解釋對男工作人員檢查婦女身體非隱私部位的行為作出合法認定符合比例原則。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第3款體現了對婦女人身權利、人格尊嚴等法益的特殊保護,其實現路徑是以降低偵查效率為代價,對男工作人員實施人身檢查的職權范圍作出額外限制。依據通說,比例原則包括適當性、必要性與相稱性[5],而刑事訴訟法作為公法,亦不外于比例原則之調整范疇。筆者認為,在人身檢查制度現有規范基礎上作“身體”表述的目的性限縮解釋,可以兼顧婦女人身權益與偵查效率:其一,從實然法角度考察,現有人身檢查制度中已有相當數量的程序性規范,制約機制較為完善。譬如人身檢查由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偵查部門負責,檢查人員必須持有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強制檢查應當經辦案部門負責人批準;檢查的情況應當制作筆錄,由參加檢查的偵查人員、檢查人員、被檢查人員和見證人簽名,被檢查人員拒絕簽名的,偵查人員應當在筆錄中注明等等。其二,依照社會通常觀念,在履行充分告知、說明并取得婦女同意后,依照流程檢查其日常裸露的非隱私身體部位,即使由男工作人員實施,也不存在婦女性自主權等權益受損的風險,因而不具有違法性。其三,以觸碰、目視婦女身體隱私部位為手段的人身檢查措施,不論是否系強制檢查,其實施主體一律排除男工作人員,能夠最大限度避免男工作人員介入引發的婦女人身權利風險。本案中,兩名男工作人員從女性面部和手指采集標本的行為,如果機械地認定為違法,則有違立法目的,也難以被社會公眾所接受。
(二)男工作人員特定情形下作為適格主體系客觀需要
在偵查實務中,男工作人員對婦女身體進行人身檢查多系客觀條件限制下的變通措施。公安機關作為采取人身檢查的首要主體,女性工作人員比例長期偏低。截至2021年初,全國200萬公安民警中,女性人數不足29萬,僅占隊伍總數的14.3%。[6]加上女性更易被分配于行政或內勤類崗位上的現實情況,可資調配于實施人身檢查的女工作人員更是寥寥無幾。譬如在深夜時段、地點偏遠的時空環境下,若現場情形具有立即檢查婦女身體的緊急必要性,安排女工作人員可能存在現實困難。因此,有必要重新劃分人身檢查中男工作人員的職權邊界。
應當注意的是,人身檢查主體的職權邊界劃分應當始終以同性別保護為原則,男工作人員介入應被視為緊急必要性情形下的例外做法。即凡具備女工作人員或醫師能夠參與的客觀條件,則應由其實施,從而最大限度尊重婦女意愿、爭取積極配合。從刑事訴訟法第132條釋義看,“必要性”可與該條第2款強制檢查“必要的時候”做類似理解,即若不進行人身檢查,偵查活動無法正常進行。“緊急性”則應主要指兩種情況,其一是涉及可能對被檢查人或其他人造成傷害的危險物品,如體腔內部的爆炸物、毒物等;其二是人身檢查所涉及的證據可能由于時間推移、被檢查人行為等情況而存在滅失風險。綜上,緊急必要原則能夠在同性別保護女性權利的基礎上兼顧偵查便利需求,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四、準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32條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為確保刑事訴訟法第132條關于人身檢查措施的法律正確實施,保障刑事訴訟順利進行,保障公民合法權利,偵查機關采取人身檢查措施應當確立并遵循以下原則:
(一)關聯性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證據的關聯性應當理解為與案件事實的關系。證據具備關聯性是其具有證據能力的必要條件,人身檢查措施同樣應當秉持關聯性原則。《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402條規定,證據是否相關,取決于以下兩個標準:“(a)該證據具有與沒有該證據相比,使得某事實更可能存在或者更不可能存在的任何趨向;并且(b)該事實對于確定訴訟具有重要意義。”[7]該規定對于我國人身檢查制度貫徹關聯性原則、明確具體適用標準而言具有較強的參考價值。遵循關聯性原則,人身檢查措施的檢查主體、受檢對象、檢查目的及必要手段等問題,均可得到妥善回應。
(二)有限同意原則
從刑事訴訟法第132條第2款規定來看,“犯罪嫌疑人拒絕檢查”以及“偵查人員認為有必要”為采取強制檢查的條件,而依照相關釋義,偵查人員在此之前必須首先問明原因,向其講明檢查的目的、意義,讓其接受檢查,如果犯罪嫌疑人經教育仍拒絕檢查的,偵查人員才可適用強制手段。此外,本款規定的“必要的時候”是指不進行強制檢查,人身檢查的任務無法完成,偵查活動無法正常進行,而經教育,犯罪嫌疑人仍拒不接受檢查等。[8]因此,不論作為人身檢查對象的婦女在案件中居于何種身份地位,偵查人員均應當事先向其告知檢查目的、部位與手段。不論是否采取強制手段,人身檢查均應當以取得婦女同意為原則,這是婦女權利特別保護在立法層面的直接體現。
但是,有限同意原則也應當在人身檢查中得到遵循,即婦女接受人身檢查的容忍授權必須具有客觀限度。一方面,偵查人員認為必要時可以進行強制檢查;另一方面,即使婦女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也不得作為男工作人員檢查其隱私部位的正當性理由。原因有二:其一,偵查活動不得有傷風化、違背公序良俗。由于醫師普遍在長期醫學教育中建立起了“去性化”的人體抽象認知,其自身性別不為職業所考量,因此我國并未在人身檢查措施中限制醫師性別。然而,無醫學專業背景的普通男性偵查人員檢查婦女隱私部位,不論是否得到婦女本人授權,均有悖于社會基本倫理之嫌,其行為本身足以在客觀上構成《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99條所禁止的“貶低其名譽、人格的方法”或第200條同樣禁止的“有傷風化的行為”,遑論其間存在個別不法分子通過誘騙、恐嚇取得婦女同意,假借職權行為二次侵犯人身權利的潛在風險。其二,男工作人員檢查婦女身體隱私部位有損社會公眾對公權力行為的合理信賴。若允許男性工作人員對婦女采取直接涉及身體隱私部位的職權行為,一旦面臨相關控告、申訴將難以自證清白,公權力機關將同樣面臨輿論壓力,由此得出的檢查結論亦難免面臨“毒樹之果”之質疑。綜上,在人身檢查過程中遵循有限同意原則,不僅是對婦女自身權益的保護,也是對偵查機關公信力的保護,更是對在案證據合法性的保護。
(三)身份區分原則
依據被檢查人在案件中的身份地位不同,以全面性、層次性的梯度化規范分別明確各自的容忍義務,以及所對應的可采取手段類型與強制程度,是檢察機關準確認定人身檢查措施是否具有違法性的必要前提。考察現行法律法規文義,犯罪嫌疑人為明確可以強制檢查的對象;被害人的容忍義務僅見于部分實務界觀點;證人的容忍義務則歸于空白。域外立法多較為詳備,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81c條第2款規定,“對被指控人以外的其他人員,如果對健康無不利之虞且措施為查清真相不可避免,準許不經受檢查者同意,進行確定血統的檢查和抽取血樣”[9]。可見,德國不僅嚴格區分被檢查人的身份,還對被指控人以外的其他人員設定了明確具體的人身檢查容忍義務。因此,我們可立足本土國情,參照域外立法,在制定法層面增加被檢查人身份的區分性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