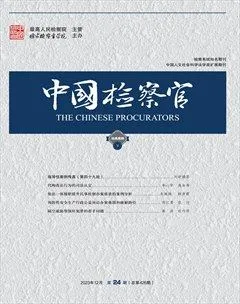死亡賠償金納入刑附民賠償范圍的正當性分析
隴雅寒 張帝 馮安祥
摘 要:死亡賠償金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能否得到支持,司法實踐中并不統一。將死亡賠償金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已具有正當性,主要理由是死亡賠償金為物質損失已成為共識,立法層面也為死亡賠償金判賠預留空間,民事責任優先和死刑慎用理念的普及、審執分離司法機制的施行為其提供了實踐基礎。社會公眾法律意識普遍增強、經濟社會發展下社會道德觀的進步、死亡賠償金納入賠償范圍的司法實踐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為其提供了社會基礎。
關鍵詞: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賠償范圍 死亡賠償金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中死亡賠償金是否判賠的實踐爭議
[案例一]2014年,被告人王某甲(1973年3月出生)因瑣事與被害人王某乙發生口角并抓打,王某甲持木棒將王某乙頭部打傷,王某乙經搶救無效死亡。刑事訴訟過程中,王某乙近親屬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經濟損失人民幣765898.86元(包含死亡賠償金人民幣413341.4元)。一審法院以死亡賠償金不屬于刑附民賠償范圍為由未予支持,判決王某甲有期徒刑13年。王某乙近親屬因法院判決未支持死亡賠償金不服一審判決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后王某乙近親屬另行提起民事訴訟,一審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上訴后二審法院維持裁定。此后,王某乙近親屬輾轉各地進行申訴、上訪。
[案例二]被告人忻某某綁架兒童楊某某后將其殺害,一審判決忻某某犯綁架罪,判處死刑,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死亡賠償金317640元。忻某某對一審量刑不服提起上訴,二審法院改變一審刑事判決中的量刑,維持附帶民事訴訟判決。后檢察機關以量刑錯誤為由抗訴,再審后法院仍支持附帶民事訴訟原告的死亡賠償金請求。
以上兩個案例體現了死亡賠償金在刑附民案件(交通事故案件除外)中能否得到支持的兩種對立觀點。實踐中,刑附民案件中對死亡賠償金判決的主要法律依據為民法典(民法典實施以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最高法《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刑訴法司法解釋》)、《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司法解釋》)。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釋關于死亡賠償金的規定較為模糊,《刑訴法司法解釋》第175、192、201條既未將死亡賠償金明確為刑附民案件禁賠項目,如當事人自愿調解等可予以支持,也未明確為應賠項目。立法模糊導致實踐中法律適用不統一,有的認為死亡賠償金不應為刑附民案件的賠償范圍,主要理由有:一是死亡賠償金是屬于物質損失還是精神損失尚未明確,刑附民的賠償范圍僅限于物質損失,故死亡賠償金不應在判賠范圍;二是被告人接受刑事處罰,已然是對受害人進行撫慰和救濟的重要手段,如果再承擔大額民事賠償,則構成“雙重處罰”,尤其是在判決死刑的案件中,讓其承擔死亡賠償金顯失公平;三是顧慮執行難,害怕空判引發上訪等社會問題。
筆者并不贊同上述觀點和理由,案例一中,被害人近親屬因死亡賠償金訴請未得到支持,多年來持續上訪,同樣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案例一和案例二同類案件不同判也引發公眾對公平正義的質疑,這倒逼我們思考將死亡賠償金納入刑附民賠償范圍是否具有正當性。對此,需要在考察立法現狀、司法實踐和社會發展程度的基礎上予以回答。筆者認為,刑附民案件不支持死亡賠償金的做法背離了立法初衷,將死亡賠償金納入刑附民賠償范圍已具有司法實踐基礎和社會基礎。
二、將死亡賠償金納入刑附民賠償范圍的司法實踐基礎
(一)將死亡賠償金定性為物質損害賠償已成為共識
“死亡賠償金并非對生命權的救濟或者對生命價值的賠償,而是對侵害生命權的行為所引起的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的各種現實利益損失的賠償”[1],即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不死亡的預期收入進行賠償,與人的生命期限有關,與死者親屬遭受的痛苦無關,而精神損害賠償與所遭受的精神打擊、損害程度有關,因此,“死亡賠償金是對逸失利益的賠償”[2],應當屬于物質損害賠償。案例二在一審判決書中將死亡賠償金表述為“原告應得的”,暗含死亡賠償金用于彌補損失之意,此后該案歷經了二審、抗訴后再審,但歷次審判均未改變一審法院判決認定的死亡賠償金,說明審判機關并未將死亡賠償金視為精神損害而絕對禁賠。
2003年《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31條明確將死亡賠償金確定為物質損害賠償;民法典將死亡賠償金和精神損害賠償列為并列的賠償項目;從最高法在2020年底修改《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將原第9條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撫慰金的規定徹底刪除來看,最高法傾向于將死亡賠償金界定為物質損害賠償,學界也基本認同此觀點,只是對死亡賠償金是屬于直接損失還是間接損失存在爭議。但無論是界定為直接損失還是間接損失,“不予賠償死亡賠償金都是對被害人權利的漠視,不僅未能填補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的損害,還通過對被害人救濟權利的否認,使其受到二次傷害”[3]。
(二)法律規定層面為死亡賠償金判賠預留空間
案例一一審和二審刑附民判決均適用2012年《刑訴法司法解釋》155條規定,以死亡賠償金未在列舉范圍內不予判賠。2021年《刑訴法司法解釋》192條關于刑附民賠償范圍的規定與2012年《刑訴法司法解釋》第155條相比雖然沒有變化,但2020年以來,新修改的法律、司法解釋等對刑附民案件中精神損失費、死亡賠償金禁賠的態度出現明顯松動跡象,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司法解釋對之前刑附民案件中絕對禁賠的精神損失費預留了空間。2021《刑訴法司法解釋》第175條第2款將2012年《刑訴法司法解釋》第138條第2款對精神損失費“不予受理”的規定修改為“一般不予受理”,“一般”二字,為精神損害賠償預留了空間。“舉重以明輕”,絕對禁賠的精神損害賠償已打開“半扇窗”,那么將死亡賠償金納入賠償范圍則也可行。二是法律條文表述為支持死亡賠償金提供支撐。如前所述,一方面《精神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刪除關于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撫慰金的規定,否定了死亡賠償金屬于精神損失的說法。另一方面,2021年《刑訴法司法解釋》192條“……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在末尾用了一個“等”字,從語法角度,可以將該條理解為不完全列舉,將死亡賠償金作為等外理解。綜上,現今將死亡賠償金納入刑附民賠償范圍并不違反立法規定。
(三)民事責任優先和死刑慎用理念普及的需要
“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傳統思想將民事責任、刑事責任混同,違背了民事責任優先原則。受害方的民事權利救濟理應高于罰款、罰金等政府罰沒收入。案例二中,一審法院在判決被告人死刑的同時仍然判決其承擔死亡賠償金,且被告人忻某某未對判決其承擔死亡賠償金的民事責任表示不滿,其在二審上訴中也僅是對刑事責任部分進行上訴,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被告人對自己需要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有較高的接受度和履行意愿。實踐中,在被告人經濟能力一般的情況下判決大額罰金或沒收被告人全部財產,卻以“被告人無履行能力”為由不予支持被害人近親屬死亡賠償金的訴求明顯違背了民事責任優先理念。同時,隨著死刑慎用理念的普及,以“以命抵命”為由拒絕判賠死亡賠償金的現實基礎已不復存在。
(四)審執分離司法機制的施行
審判程序的性質是“審”,執行程序的性質是“執”,不能以執行難為由拒絕支持死亡賠償金。實踐中,在一些法院執行部門看來,“空判”浪費司法資源,還不如不判。[4]這種觀點本末倒置,判決僅僅是執行的前提,因害怕無法執行而不判決支持死亡賠償金,以此促使雙方達成妥協,本質上是一種“懶政”行為,因“執行難”“空判”等原因而限制刑附民賠償范圍是“因噎廢食”之舉。同時,被告人現階段暫無履行能力不代表未來也無履行能力,若法院直接判決不支持則將被害方的預期利益也全部剝奪。如案例一中,被告人的刑期為13年,就算沒有獲得減刑、假釋等提前出獄機會,被告人出獄后僅54歲,仍具有勞動能力,出獄后仍可通過就業償還部分或全部死亡賠償金。
三、將死亡賠償金納入刑附民賠償范圍的社會基礎
(一)社會公眾法律意識普遍增強
全面依法治國以來,法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社會公眾法律意識明顯增強,司法途徑逐步成為民眾解決矛盾糾紛的重要方式。隨著公民法律意識普遍提升,大部分當事人都可稱之為“理性的守法公民”,對于法院判決勝訴并不等于執行到位已有較理性的認識,都能基于樸素的正義價值觀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作出符合社會預期的維權行為,并在維權時優先選擇司法途徑等合法途徑。如案例一中,被害人近親屬不服法院不支持死亡賠償金的判決,沒有立即上訪,而是在上訴未得到支持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被法院裁定駁回后對裁定再次上訴,上訴被駁回后又向檢察機關申請監督,仍未能得到支持才開始上訪維權。對此,司法從業者需避免用舊思維給被害人近親屬貼上“獅子大開口”“坐地起價”等標簽,并據此阻斷被害人近親屬的死亡賠償金之路。
(二)經濟快速發展下考慮大眾道德觀的需要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國民物質生活水平大幅上升,被告人的經濟條件“水漲船高”。加上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呈現年輕化傾向,出獄后仍然年富力強的被告人逐漸增多,很多被告人在經過監獄勞動改造出獄后仍可能有較好的發展,如案例一被告人出獄后仍具有勞動能力,可以通過再就業改善經濟條件。即使被告人被判處死刑,其名下也有可能存在可供執行的財產,如存款、房車等,在此背景下,用被告人個人財產彌補被害人近親屬痛失親人遭受的利益損失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是遵循社會樸素道德觀的體現。如果在被告人尚有可供執行財產的前提下,否定被害人近親屬的死亡賠償金訴請,反而判處被告人罰金、沒收財產等,超出了社會大眾通過樸素正義價值觀對法律的理解。案例二中,刑事判決部分在判決忻某某死刑的同時,還判處沒收被告人忻某某全部個人財產,此種情形下,如果否定被害人楊某某父母的死亡賠償金訴求,反而將被告人個人全部財產沒收國庫,不僅讓已經痛失孩子的楊某某父母難以接受,也導致社會大眾從情感和倫理道德上較難理解。
(三)支持死亡賠償金的司法實踐取得良好社會效果
近年來,判決支持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或精神撫慰金的案件受到社會好評,如尹某軍訴顏某奎健康權、身體權糾紛案,安徽省淮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在裁判文書中將殘疾賠償金的性質認定為物質損失,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尹某軍在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后請求賠償殘疾賠償金的訴訟請求進行了支持,取得良好社會效果,入選《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5]2021年7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牛某性侵未成年人案的二審判決,維持支持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一審判決,是2021年《刑訴法司法解釋》實施后,上海首個在刑附民案件中支持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案例,被作為典型案例入選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6]最高法、最高檢將支持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的案例進行推廣,是對刑附民案件中的精神損害賠償作出了較好司法探索,精神損害賠償在刑附民判決中予以支持也能得到大眾的普遍認可。此外,一些地方已出臺相關規定明確支持刑附民案件中的死亡賠償金,如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日出臺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的意見》第3條明確規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7]。上述司法探索,為死亡賠償金納入刑附民訴訟賠償范圍作出了有益嘗試,不僅意味著將死亡賠償金納入賠償范圍,逐漸被理論界和實務界所接受,同時對于矛盾糾紛化解、維護司法權威也起到促進作用,受到社會民眾好評,取得良好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