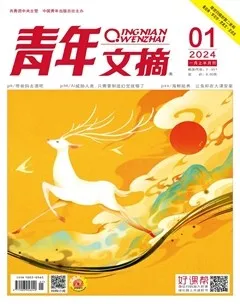古人為什么要搗衣
孟暉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這詩句平易得像說話,卻氣象闊大,意境幽美。同時,也讓人不由得感到好奇:古人為什么搗衣?
唐人王建有一首《搗衣曲》,講得比較明白:“月明中庭搗衣石,掩帷下堂來搗帛。……回編易裂看生熟,鴛鴦紋成水波曲。
重燒熨斗帖兩頭,與郎裁作迎寒裘。”
其中“回編易裂看生熟”一句點出了“搗帛”的目的:讓衣料由“生”變“熟”。
關于絲帛,一向就有“生”“熟”之分,在唐代,新織出來的各種紡織品,要經過初步的加工工序,去除織物中的絲膠等天然雜質和污物。經過如此處理的織物稱為“生”
織物、“生”料子——去除了雜質所以分量會大大變輕,同時織物的經緯會變得稀疏,輕薄透氣,是為“生”。
唐人生活中,夏季服裝一定用生料子制作,稱為“生衣”。白居易就有《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一詩:“淺色衫輕似霧,紡花紗薄于云。莫嫌輕薄但知著,猶恐通州熱殺君。”
可見他特意給元稹寄去輕衫薄褲,免得好友被“熱殺”。
但是,一入秋天,薄、輕的“生衣”就不適合穿了。為應對季節轉換而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用“熟衣”代替“生衣”,白居易《感秋詠意》里寫:“炎涼遷次速如飛,又脫生衣著熟衣。”
搗練的目的,就是把“生練”制成“熟練”,以便制作“熟衣”。
唐代名家張萱所作的《搗練圖》,畫上優美的女性,正是在加工秋冬的御寒衣料。
其步驟是先給“生練”上漿,用米粉、面粉等糧食粉加冷水調成稀糊,把“生練”在其中浸泡一陣,然后還得用雙手在“生練”的兩面仔細涂抹粉糊,直至涂勻。接下來,將上了漿的“生練”折疊成幾疊,置于砧石上,進入真正的搗練環節,反復用長杵擊打。
這樣,粉糊能被砸進經緯之間的空隙,讓練帛變得密不透風,而且持續的搗打還能把織物的經緯線砸扁,讓經緯線彼此聚攏,變得密集,從而使整幅料子成為厚而不透、結實韌牢、不易脫絲的質地。這樣不僅耐用耐穿,而且保暖,同時衣料表面均勻柔和,穿著舒適。
搗練總是發生在秋夜。女人們白天為了家里家外的事情忙個不停,入夜之后,孩子睡了,雞鴨入籠,牛羊入圈,萬物都安歇了,她們才有了完整的“空閑”時間。搗練是非常耗費體力的活計,于是,或者婆婆、兒媳一起,或鄰近女伴一起,采用合作互助的形式來提高效率,正如劉禹錫的《搗衣曲》寫的“戶庭凝露清,伴侶明月中”那樣。借著月光,為一家人搗練,預備寒衣。
從南北朝文學起,與搗練相關的情形被提煉出來,成了很多詩文的主題:男人戍邊,女性在與丈夫久別的情況下,為他制作寒衣,托人送往邊塞。她們在失去兒子或丈夫的陪伴下,一邊承擔著生活辛勞,一邊牽掛著遠方的親人。
文學家們敏感地意識到了這其中所蘊含的巨大矛盾,感受到那些卑微的生命所面臨的問題,并把這些感受與人類的大問題聯系起來加以思索。他們在心懷天下的時候,是把“國”與“民”,也就是整體與個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因此有了李白的《子夜吳歌·秋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率先由文學家們開發出的主題,很快傳導到繪畫領域,從唐代開始,搗練便成為歷代畫家反復表現的主題,理解古人的豐富情感,才能更好地感受那些優美作品的魅力。
(摘自《環球人物》2023年第17期,佟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