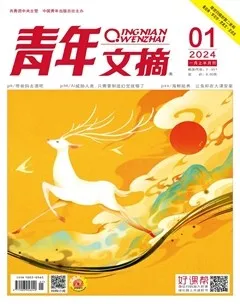成“圣”前的孔子有點難
劉志斌

多年以后,當孔子筆削《春秋》,修訂到魯襄公十年(前563年)的陽之戰時,準會想起自己將父母合葬的那天。
孔子生父名叫孔紇,字叔梁,在史書中被稱為“叔梁紇”。叔梁紇勇武過人,身長十尺——無論按哪種度量衡,都是妥妥的巨人——曾在陽之戰中以一己之力托舉住城門處放下的懸門,挽救了一整支攻入城中的部隊。魯國大夫孟獻子形容他“有力如虎”,任命他為曲阜東南的陬邑宰——魯國下屬一個鄉鎮的管理者。作為回報,他要在自己60多歲時依然披甲上陣,冒死沖鋒。
68歲時,叔梁紇的第二個兒子呱呱墜地,這孩子名丘,字仲尼。“仲”,就是家中排行老二的意思,老大名叫孟皮,字伯尼。
伯尼不幸是個跛子,這對勇武過人的叔梁紇來說,是個殘酷的打擊——一個跛子顯然無法繼承家業。因此叔梁紇四處物色合適的女子,最后找到了庶民出身的孔子生母、不滿20歲的顏氏。由于老夫少妻、男尊女卑,因此《史記》中用“野合”一詞形容兩人的結合,暗示他們可能并沒有舉行正式的婚禮。而更不幸的是,孔丘出生3年后,叔梁紇便去世了,顏氏被排斥在葬禮之外,她只能帶著年幼的孔丘,回到娘家。那是一段清貧的生活,日后孔丘曾這樣總結自己的少年時代:“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不過即便這樣的生活,也在孔丘15歲后戛然而止了。
長期操勞摧毀了顏氏的身體,她沒來得及看到孔丘加冠便撒手人寰。而孔丘不得不開始獨自面對這個禮崩樂壞的世道,將父母合葬,成了他需要獨立解決的第一件大事。
此事最大的難點,在于孔丘并不知道父親的墳墓在什么地方。為此,他頗費了一番周折,先是將母親的棺柩停放在大路旁,然后不斷向過往的行人打聽消息:我的父親是叔梁紇,您可知道他的墳墓在哪里嗎?
不知過了多久,終于有人給這個孩子指明了叔梁紇的墓地所在。那是孔子第一次見到親生父親的墳墓,史書中并沒有記載此刻他的心情。然而在多年以后,已經名滿天下、以恪復周禮著稱的孔子卻堅持要違反禮制,在父母的墓上堆起一個四尺高的土丘。那天大雨滂沱,門人們擔心墳墓崩塌,留下來冒雨加固墳墓,早已年過不惑的孔子聞訊泫然而泣,在情感與信念的沖突之中,他顫抖著說出一句話:“吾聞之,古不修墓。”
然而不修墓,又要如何安葬自己對父母的思念呢?
那一刻,孔子不再是一個周游列國的智者,他再次成了那個守著母親的棺槨,向路人打聽父親消息的少年。
后來他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對現代人而言,15歲才開始學習未免晚了一點,不過對孔子來講,卻是剛剛好。
那時,學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春秋戰國,書在簡牘,人們說孔子筆削《春秋》,這個“削”
字可不是個形容詞,而是因為當時想要在簡牘上進行刪改,必須要手持小刀,將原本的字跡削去才行。
這代表想要大規模記錄信息、儲藏知識,只有王室官府才能做到。因此歷代典籍,均由官府收藏,職官專守,民間只聞其名,而不知其書。
而且,有些東西不是你想學就能學的。以樂器為例,周公“制禮作樂”,以使尊卑有序。你若是貴族中最低一級的“士”,跑去說自己要學編鐘,那顯然是頭腦發昏。因為編鐘乃是頂級的樂器,只有天子和諸侯國王才能使用。
所以周代教育的顯著特點,就是“學在王官”。
什么人能學什么東西,早有定數。
同時,為確保孩子們贏在起跑線上,不同等級的貴族入學時間也不盡相同。比如,諸侯之子8歲就可以入學,公卿太子10歲才能入學,其余的孩子要等到15歲才能入學——此時跟孔子同歲的諸侯之子,已經都學完最初級的課程了。
然而就算是15歲入學,也不是人人都有資格的。孔子生母顏氏,乃是庶人,庶人之子想要入學,是件頗有難度的事。所以對孔子來說,合葬父母除寄托哀思外,更重要的是他終于有了一個說得過去的出身,可以去上學了。
一個身份,這便是叔梁紇為孔丘留下的全部遺產。孔子明白,如果不能借助這個身份,盡快拿到一張貴族圈子的入場券,那么等待著自己的,便只會是庶民那種單調而清貧的一生。
巨大的危機感驅使著孔子,讓他像干燥的海綿一樣,盡情吸收著一切知識。很快,他勤學好禮的美名便為人所知。只可惜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一次意外的羞辱,讓他看清了自己在其他人心中的真實處境。
那是一次由季孫氏舉辦的盛宴——當時禮崩樂亂,魯國也不例外,季孫氏、孟孫氏和叔孫氏三家貴族已經架空了國君,而其中又以季孫氏的權勢最大。孔子以為,既然季孫氏要宴請魯國之士,自己作為叔梁紇之子,又已進學,理應有資格出席宴會。
不料滿心歡喜的他卻遭到了莫大的羞辱。季孫氏的家臣陽貨見到孔子竟然怒斥道:“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季氏宴請的乃是“士”,而您不是!
陽貨向孔子展現了這個世界最赤裸的真相:在叔梁紇去世十幾年后,他所遺留下的一切都已不復存在。被陽貨狠狠關上的不僅僅是季孫氏宴會的大門,更是孔子曾經幻想過的晉身之階。
這件事對孔子的打擊之大難以想象,據說此后孔子見到陽貨時甚至“卻行流汗”。又或許那流下的并不是汗液,而是一個少年曾經的全部尊嚴。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陽貨的羞辱并沒有殺死年輕的孔子,反而激發了他的斗志——在明白已經失去退路之后,孔子將全部的熱忱都投入學習中。只有知識,會平等地對待每個追求它的人。
18歲這年,孔子迎娶了來自宋國的丌()官氏。第二年,丌官氏誕下一個男孩,這個孩子的到來讓孔子欣喜若狂,以至于孔子為他取了個很有意思的名字,叫作“鯉”,字伯魚。
有鯉又有魚,孔子怎么會給長子起這樣一個名字呢?答案非常簡單:這條鯉魚,是魯國國君魯昭公聽說孔子喜得貴子,專門賞賜給他的。
毫無疑問,數載勤學苦讀,此刻終于開花結果。在孔子眼中,這條鯉魚并不僅僅是一條魚,而是國君對自己的認可。短短三兩年間,昔日被陽貨拒之門外的孔子,終于卷土重來。
這或許是孔子一生中最為暢快的日子,短短一年之間,他完成了結婚、生子與加冠這三件人生大事,還得到國君的認可,回到魯國的貴族圈中。而更多讓他喜上眉梢的事情接踵而至:季孫氏為他提供了一個不錯的職位,有了職位的孔子,終于可以理直氣壯地稱自己為“士”了。
孔子非常重視這個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他明白,國君的鯉魚能榮耀一時,卻不能供養一世。
對于除了能力之外一無所有的他而言,如果不能抓住眼前的機會,那昔日被拒之門外的場景隨時可能重演。因此他施展渾身解數,只為在工作中證明自己。按《史記》所載,他先管倉庫,賬目清楚;再管牲口,牛馬肥壯。只不過這些低級職位能提供的俸祿終究有限,若要供孔子繼續求學問道,那便捉襟見肘了。
二十出頭的孔子,開啟了副業之旅——去教學生。
稍有門路的貴族子弟,都進入官學之中,愿意來跟孔子學習的,大多是平民百姓。而且,當時魯國的私學競爭也十分激烈。在種種壓力之下,孔子很快便提出一個劃時代的教學主張:有教無類,就是不論你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愿意跟我學習,那我就收你為徒——當然,拜師不是沒有條件的,所謂“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有一種解釋便是需要奉上十條干肉。
用今天的話說,此舉無疑擊穿了行業壁壘,十分大膽。只不過在降低招生門檻的同時,也難免會有一些奇怪的人跑來騷擾孔子,比如,某日竟然有一位“野人”身著奇裝異服,頭戴插滿雄雞羽毛的帽子,手持利刃,跑來要“陵暴”孔子!
當然,春秋時的野人可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野人。周代內外尊卑等級儼然,居住在國中的士農工商,稱為國人;而生活在邦國之外的則被稱為野人,也叫庶人。而打上門來的這位野人性格粗鄙,孔武有力。孔子為降伏他展現了自己深邃的文化造詣,最終讓他主動換上了儒服,投到孔子門下。之后,他由一介野人,成長為孔門十哲之一,精通政事,后出任衛國蒲邑之宰,實現了春秋時代堪稱奇跡的階級跨越。他叫作季由,字子路。
顯然,教導這些出身各異的學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來《論語·雍也》中記載的“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多半就是孔老夫子晚年回顧自己早期教學生涯時發出的無奈吐槽:有些學生的素質就是中人以下的水平,你根本就沒法跟他談那些高大上的東西!
只是為了那十條干肉,孔子卻也不得不打起精神來,絞盡腦汁地去尋找合適的教育方式。不要小瞧那些干肉,當時算是公認的“硬通貨”。有一次,郯國國君郯子朝魯,在席間魯昭公向郯子詢問以“鳥”命名的官職,郯子對答如流。孔子聞訊后急忙登門拜訪以學之,而他登門時所獻的禮物,八成就是弟子們拜師時送上的干肉。
這次向郯子求學后,孔子感慨自己聽說天子官學失傳,而學在四夷,如今果不其然。然后他便加大了四處求學的力度,甚至在兩年后跑去晉國,向善琴的師襄學琴,其間師襄數次催促孔子繼續往下學習,而孔子卻堅持反復練習同一首曲子,稱自己尚未領略曲中隱藏的旨趣。終于某日孔子若有所思,表示自己已經完全融會貫通了:這首曲子所贊頌的人志向高遠、目光遼闊、涵蓋四方,除了文王以外,還有誰配得上這首曲子呢?師襄大驚,盛贊孔子為“圣人也”,因為這首曲子就是《文王操》。
在存世文獻記載中,這是第一次有人稱孔丘為“圣人”。這是魯昭公十九年發生的事,過了這年,孔子即將30歲。
他說:“吾三十而立。”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2023年第20期,本刊有刪節,佟毅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