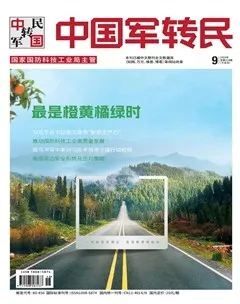俄烏沖突對南海局勢的影響與中國應對
張旭東 簡安琪
【摘要】迄今,俄烏沖突已持續一年有余,戰火不僅給俄烏兩國和周邊地區造成破壞,其影響也在不斷外溢,引起南海局勢的變化。針對俄烏沖突,南海各聲索國的立場不一。俄烏沖突對南海局勢的影響體現在外交政策、雙邊貿易和能源開發等方面。為應對南海局勢變化帶來的沖擊,我國有必要在多方面采取應對措施,維護海洋利益。
【關鍵詞】俄烏沖突∣南海爭端∣聲索國∣輿論戰
俄烏沖突爆發至今,已持續一年有余,不僅給交戰兩國和周邊地區造成巨大影響,其影響也在不斷外溢,引起南海局勢的變化。在南海爭端日益復雜化、政治化和國際化的背景下,有必要全面掌握南海聲索國對俄烏沖突的立場,研判其政策走向,分析沖突對南海局勢的具體影響,并采取有效應對措施,促進我國的南海維權。
一、南海聲索國對俄烏沖突的立場
俄烏沖突爆發后,南海聲索國迅速表明立場,多采取中立的態度,顯示出各國在對于大國博弈中的審慎態度。
(一)越南
越南官方對俄烏沖突的態度很明確,即:面上頂住美國的壓力,實際上變相支持俄羅斯。原因在于:第一,雙邊關系上,俄羅斯一直是越南最重要的防務伙伴。越南軍隊裝備中,俄系占約80%。第二,越南與俄羅斯油氣公司簽訂了在南海的勘探協議,以保障越南推進南海主張。第三,俄烏沖突并不損及越南實際利益,盡管有美國的唆使(如美國國務卿顧問串訪東南亞),但越南不會選擇得罪俄羅斯。
越南開始反思其外交政策,其國內精英普遍認為,越南與烏克蘭處境相似,其精英與民眾都認識到不能過度依賴美國而激怒中國 [1]。
此外,越南擔心中國會效仿俄羅斯,使用“爭議性”借口(俄羅斯的“反納粹”,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南海采取類似的軍事行動或“灰色地帶行動”。美國也抓住這種心理,大肆渲染,拉攏南海聲索國“抱團”對抗中國。
(二)菲律賓
菲律賓的官方表態仍保持中立的態度,主要集中在關切在烏菲律賓人的安全,同時呼吁和談,譴責戰爭。
菲律賓作為美國的正式盟友,其表態中規中矩。菲律賓駐美大使羅穆亞爾德斯作出的“若美國參與,那么菲律賓將開放基地等設施”表態,可以看作是一種安撫。從聯合國會議投票看,菲律賓并未實際對俄制裁。
近年來,菲律賓與俄羅斯的雙邊關系較好,比如:俄羅斯捐贈新冠疫苗,簽訂在南海的油氣勘探協議等。兩國的防務關系密切,但經濟聯系不足,俄烏沖突難以影響菲俄雙邊關系[2]。
總體上,菲律賓認為應該吸取烏克蘭的教訓,避免成為大國競爭的犧牲品[3]。這一認知與越南趨同,也反映了其他聲索國的心理變化。
(三)馬來西亞
針對俄烏沖突,馬來西亞總理伊斯梅爾·薩布里表示,他對烏克蘭遭遇感到“難過”,馬來西亞關注在烏國人的安全,呼吁兩國盡快達成和平共識。馬來西亞外交部發布的兩次聲明,表示馬來西亞對烏克蘭沖突升級“嚴重關切”,并強烈敦促“有關各方”立即采取措施。
馬來西亞的表態也很中立,但馬來西亞國內有聲音呼吁減少俄羅斯武器采購,甚至直接抵制俄公司參加武器展覽。此外,馬來西亞也有對中國打破東南亞平衡局面的擔憂。
(四)印尼
2022年2月24日,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在推特上發表推文,表明其中立態度。印尼政府和外交部發表的官方聲明稱,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宗旨與原則。拒絕對烏克蘭的軍事攻擊。
印尼的官方表態深刻體現了其一貫的平衡外交作風,既在道義上迎合國際主流觀念(如贊成聯大決議),又不直接得罪俄羅斯(如聲明沒有明確點名俄羅斯)。
印尼于2022年主辦了G20峰會,烏克蘭此前曾敦促其在G20峰會期間討論俄烏沖突,美西方國家也要求將俄羅斯排除在本屆G20峰會之外,但印尼仍按慣例向俄羅斯發出了邀請,并堅持將峰會主題聚焦在經濟和氣候等議題上。
近年來,印尼有意加強了與俄羅斯的經貿聯系。2021年6月,印尼貿易部長訪問俄羅斯,并與歐亞經濟聯盟負責人舉行了會晤,促進印尼與俄羅斯及中亞國家的貿易。在國防方面,印尼在武器進口上較為依賴俄制武器,去年印尼參加了首屆東盟-俄羅斯海上演習,表明印尼不會站在俄羅斯對立面。
二、俄烏沖突對南海局勢的影響
俄烏沖突持續時間已不短,不僅重塑了歐洲地緣政治格局,其影響也在不斷外溢[4],引起了南海局勢的變化,具體將表現在外交政策、雙邊貿易和能源開發等方面。
(一)外交政策上
在外交政策上,南海聲索國普遍進行了反思,認識到應該吸取烏克蘭的教訓,避免成為大國競爭的犧牲品,美國趁勢大肆渲染中國將會在南海采取軍事行動。預計各聲索國將采取更加中立務實的外交政策,不在中美間“選邊站隊”。但預計美國將加大在南海的介入力度,拉攏南海聲索國“抱團”對抗中國,如組建南海聲索國聯盟、多國海上巡邏執法等;慫恿其采取激進措施,如提起又一樁南海仲裁案。
(二)雙邊貿易上
在雙邊貿易上,美西方的對俄制裁直接影響到俄羅斯與南海聲索國的雙邊貿易,特別是在軍事裝備方面。盡管俄羅斯可能試圖與南海聲索國產生更多的聯結以擴展自己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但美國可能援引其《制裁美國對手法》對南海聲索國進行制裁,逼迫其與俄羅斯劃清界限。此外,南海聲索國也在考慮軍事裝備的多樣性,尋求其他備選方案。
(三)能源開發上
在能源開發上,俄烏沖突對世界能源的供給和需求都產生較強的持續性沖擊,已經影響到全球能源格局,世界各國油氣價格攀升,且化石能源價格將持續較長時間處于高位震蕩。隨著近年來清潔能源技術水平以及可普適性的提升,南海聲索國認識到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并開始布局海上風電等可再生能源。俄烏沖突爆發后,越南吸引到了美國Gen X Energy公司和全球風能理事會對其海上風電項目的投資,菲律賓也發布了海上風電路線圖。海上風電在宣示海域主權、推進海洋主張等方面也發揮重大作用。越菲兩國發展海上風電,不僅能產生實際的能源效益,對其南海主張也是一項潛在的支持。
三、俄烏沖突背景下的中國應對
南海問題本就復雜,俄烏沖突的外溢影響將導致其進一步政治化、多元化和國際化[5],對我國的南海維權不利。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妥善應對俄烏沖突對南海局勢的影響,維護我國海洋權益。
(一)總體策略
在俄烏沖突日漸白熱化之際,我國應繼續占據道德高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思想,加強與南海聲索國的交流溝通。在資源開發、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上與南海聲索國深化合作,爭取其宏觀上在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微觀上謹慎處理與我國在南海可能的潛在沖突。在俄烏沖突這一敏感時期,對南海聲索國釋放善意信號,進行安撫,避免對其產生刺激,引發南海局勢進一步動蕩。
此外,還需堅持底線思維,警惕南海聲索國與域外國家串聯,通過發展海上風電實際推進島礁建設。密切關注南海聲索國的海上風電項目,特別注意其項目選址,以及存在南海域外國家企業與南海聲索國開展海上風電合作的可能性,需要總結現有的各國海上風電海外投資項目的詳細情況,積累情報,以備未來反制之需。
(二)宣傳場域
第一,利用各種渠道,努力強化南海聲索國對外交政策的反思。在官方、智庫、媒體、學術等不同場域,強調中國不允許“烏克蘭悲劇在身邊重演”等觀點,對各聲索國敲打警告。
第二,針對南海話題,充分利用宣傳資源,引導國內媒體和公眾保持理性,避免情緒化言論的蔓延和發酵,以避免國內輿情引起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
第三,在俄烏沖突的輿論戰場域,烏克蘭通過互聯網采取了新策略和新戰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這一新范式有可能被南海聲索國學習和借鑒,并運用到與我國的南海話語權爭奪中。鑒于此,我國需要特別注意網絡安全問題,特別是涉及南海的網絡輿情。一方面,有必要加強網絡安全建設,防范境外對我國的網絡攻擊和滲透,積極防范信息戰,加強信息安全保護體系,提高網絡監測和反制能力,減少信息泄露風險;另一方面,也應加強對網絡自媒體用戶(特別是具有較大影響力的頭部賬號、大V等)和社交平臺的引導和監管,打擊不良信息和謠言,維護網絡空間健康發展。
(三)法律路徑
以法律作為維權武器,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協商與談判。密切關注俄羅斯與越南、菲律賓兩國南海油氣勘探協議的執行情況,適時以俄烏沖突后俄羅斯亟需我國的戰略支持為契機,要求俄羅斯退出或減少南海油氣勘探業務。
(四)情報方面
俄烏沖突對南海的影響是廣泛的,需要全面掌握南海域內和域外利益相關方的立場和傾向,并研判其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行動和戰略等。因此,相關情報的獲取和積累便是關鍵。有必要完善情報收集網絡,探索情報獲取新渠道,加大對開源情報的重視力度,以期及時跟進相關事態發展,并制定有效預案。
四、結語
隨著戰事升級,俄烏沖突的影響不斷外溢,蔓延到南海地區,對南海局勢造成不小的震動。南海聲索國的立場以中立為主,清醒地意識到不能卷入大國競爭中。俄烏沖突已經在外交政策、雙邊貿易和能源開發等方面引起南海局勢的變化,南海聲索國在思考下一步的出路和解決方法。對于我國來說,俄烏沖突帶來的南海局勢變化,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俄烏沖突導致美西方政治經濟影響力和國際軟實力持續下降的背景下,有必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擴展我國在南海地區的戰略空間,獲取實利。
參考文獻
[1] Hoang Thi Ha.The Russia-Ukraine War: Parallels and lessons for vietnam, fulcrum[EB/OL]. [2022-12-15]. https:// fulcrum.sg/the-russia-ukraine-war-parallels-and-lessonsfor-vietnam/.
[2] Joshua Bernard Espe?a.How the Russia-Ukraine War will impact Philippines-Russia relations, the diplomat[EB/ OL].[2022-12-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3/howthe-russia-ukraine-war-will-impact-philippines-russiarelations/.
(作者單位: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