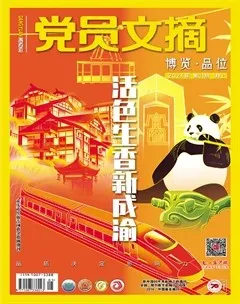望江樓上望江流 江流千古匯長江
杜江茜 楊濤 柴楓桔
相傳,大禹在治理完岷江水患后,順江東下抵達三峽。那時,三峽不通,長江之水都堵在成都平原。
巫山神女瑤姬暗中相助,相贈黃陵寶卷。大禹手持利斧,鑿開巫山、瞿塘峽、西陵峽,引滾滾江水東注大海。
歷史學家告訴我們,上古時代,四川盆地由于地勢低,雪山之水匯聚于此,這里被稱為“古蜀巨湖”。直到長江之水沖破巫山,驚濤滾滾奪峽而去,岷江、金沙江、嘉陵江、沱江四條支流浩蕩而下,這才成就了天府之國的天下糧倉,也匯聚出渝州碼頭的交錯航運。
——同時擁有長江上游這一流域,這僅僅是地質歷史上,成渝兩地千絲萬縷的聯系之一。
這一流域串聯起了雙子星——成都和重慶,四川盆地的盆地和盆周,地勢不同造就了彼此相通又各自璀璨的古代文明——巴與蜀。千河匯江,如同一雙巨手,一手拉起巴文明,另一只手拉起蜀文明,它讓兩個文明在相遇相融中,開啟了巴蜀大地四千年命運與共的偉大成就。
對于整個華夏文明而言,長江在上游沖破巫山阻攔,奔入湖廣丘陵,收容湘資沅澧,一路奔騰東流,遂與海通。它打通巴、蜀、楚、吳、越,將幾個孤獨的區域匯聚成整個中華文明中的長江流域特色。
望江樓上望江流,沒有這江水千萬年的沖刷,巴國之地不會有豐富的巖鹽資源,使人民在先天低下的農耕水平中維持富足生活;沒有江水的順暢奔騰,四川盆地不會有天府之國的沃野千里,更不會有農業時代的城市崛起;沒有這同一江流域,奇崛瑰麗的巴蜀文明更是封閉的,畢竟“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
江流千古匯長江,流淌的是兩座城市彼此成就的通道,孕育的是兩種文明奇崛瑰麗的交融,這里是華夏文明的上游,也是成渝雙子星從遠古到現在,一直流淌著的未來。
從唐古拉山蜿蜒而下的涓涓細流,在進入四川后,變得奔騰浩蕩。它在西南深谷襲奪金沙江,再接納沱江、岷江、嘉陵江,浩浩湯湯,始成洪流。
“可以說,金沙江、岷江、嘉陵江、沱江,這四條支流匯合壯大了長江上游,成都和重慶共享這一流域,自古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巴蜀文化研究資深專家祁和暉先生看來,千百年來,巴蜀人民沿著江河生存,順著江河歌唱,江河的上游有山水靈氣,江河的下游有激流浩蕩。一只腳邁出寧靜盆地,另一只腳就踏上了綠色山嶺。如果要相互抵達,就勢必經過一段巫峽云遮霧繞、奔騰雄壯的旅途。
在這里,長江奇雄的力量初現,它讓驚濤滾滾東去,那些從山地中裹挾的沙石、粘土、有機物沉淀,被低洼地勢的成都平原容納。此后在這些巨厚的河流沖積物上,聚集建造起富庶一方的繁華城市,巍峨連片的百姓角樓,而那些肥沃的土壤,自然成為農業時代城市崛起的財富。
江水繼續奔騰而下,巨浪裹挾而過,漫過沿途的嶺谷山脈,形成天然水道,下至巴地,在川東出口堆積起層層礦物質,這讓居住于此的巴國人擁有豐富的巖鹽資源,他們將鹽賣給附近的蜀國和楚國,過上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生活。
大自然毫不吝嗇地將所有瑰麗的色彩都賦予了這一流域,大江大河大山大谷大盆地,曾煙濤微茫信難求,但對內,兩地之間早已往來頻繁。
“巴蜀之間的內部交通,從古邊開始發達。”對此,祁和暉先生表示,古時,從江州(現重慶)到成都,多條水路可通,而在陸路上,現在的成渝鐵路所經過的,基本上就是古代成渝兩地的驛站。
如今,長江的黃金水道依然將兩座城市連在一起。川東和川北的重要城市,可以經嘉陵江、涪江、渠江直接溝通重慶;川西、川南的所有城市,則可以沿岷江、沱江經瀘州和宜賓兩城中轉,走長江進入重慶,“可以說,重慶天然就是四川盆地物資的匯聚點”。
在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看來,長江水系,支流復雜,多姿多彩,更近似文化長河的變化景象。在復旦大學歷史學家葛劍雄看來,世界上壯麗的峽谷有很多,但三峽和所有的都不同,因為別的峽谷多是荒蕪而遠離人煙,而三峽卻是一個人來人往的黃金水道,是一條文化傳播的走廊。
對千百年來的巴蜀人民而言,那千河匯江的奔騰江水,讓他們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創造于斯。歷史已經證明,這一江流域奇詭神秘的巴蜀文明是一體的,巴山蜀水,僅僅只有蜀的悠然和緩是不夠的,僅僅只有巴的湍急張揚也是不夠的,只有當兩種氣質相互交融,彼此聯系,我們才能看到浩蕩奔放、大江傾瀉的大才大氣。
三峽險峻,歷史記載中,巴人憧憬“歌舞戰神”。《華陽國志》中提到,周武王伐紂時,得到巴師幫助。巴師勇銳,歌舞凌敵。邊歌邊舞邊打仗,這就是巴人的氣質。

蜀地多水患,古蜀人治水的智慧甚至影響著當時王權的更迭。蜀王杜宇治水,收效甚微,后來鱉靈開鑿泄洪道,減輕了成都平原的洪澇災害。也因此,望帝杜宇禪讓王位于鱉靈(蜀王開明氏)。
流水鍛造著兩地的些微不同。巴蜀之間,巴人出將,蜀人出相,大江大河高山深谷,自然也孕育出詩人、作家、書法家……行走在這一江流域的,是司馬相如、楊雄、陳子昂、李白、蘇軾、杜甫、楊升庵、郭沫若、巴金……江水亙古東流,他們在此留下浪漫到極致的文化力量。
這些力量是多元的、華麗細膩的、沉郁頓挫的、天馬行空的……似乎,從沒有一個地方,如同巴蜀之間的這一流域,匯聚如此多的星光。流水是詩人的靈感,高山是詩人的靈感,峽谷也是詩人的靈感,峭壁、落葉、猿猴、輕舟,都能引發巨大共情,詩人們的才情在此碰撞,閃耀出智慧的火花。
自然鍛造了這一流域,文化成就了這一流域。古往今來的數十萬首詩歌,鋪陳于這山水之間,一山一詩,一水一歌。
在三峽,這個中國詩歌的長廊,沿江數百里,在溶洞、古剎、高山、浪濤尖、懸崖峭壁中,三峽石刻被鐫刻下了那些瞬間,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石刻,靜默在江邊數千年,江水一次次拍打,那些古人們定格的瞬間,那些穿越了時空的禮物,仍在原封不動的傳承和展示著。
這是巴蜀人民的鄉愁,是長江文明的上游,是人類的起源地之一。江河萬古、巴蜀千年,一江而下,腳下的歷史陳跡正在悄悄延展至未來。
(摘編自《四川日報》、封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