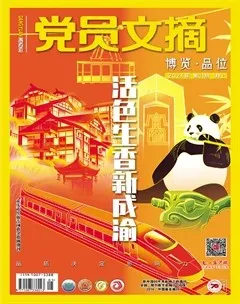人與美食的江湖本色
吳冰清 戴竺芯
要領略成渝兩地的江湖味道,便要從這里的一日三餐開始。
在重慶,無論街頭巷尾,總能看到小面的影子。
“隨手一抓,一把水面,幾根青菜,三兩分鐘煮熟,五六分鐘下肚”,許多重慶人的早晨是被一碗簡單的小面喚醒的。
忙碌的小店,匆匆的行人,吆喝聲不絕于耳,小面的香氣縈繞鼻尖,任誰不想來上一碗?

“南方喜米食,北方喜面食”,自古以來便是人們的傳統認知。重慶雖處南方,卻對面食情有獨鐘,少不了歷史上幾次移民的影響。
重慶人將移民過程中帶來的面食與當地嗜辣的特點相結合,使小面漸漸走進每個重慶人的日常生活。
重慶小面的作料是其精華之處,小面雖小,但從其作料來看,可一點也不小。
小面里的作料種類有十幾甚至二十多種,每種調料的比例不同,最終小面的味道也不同,各家面館通常還會分別持有自家的獨門秘方,也就有了“一家一味,百家百味”的特色風味。
小面雖言“小”,但能量一點也不小,是暖心的撫慰,滿心的惦念。
都說“川渝一家親”,重慶人如此愛吃小面,那成都人對面條又有多喜愛?吃面又有哪些方式?
在成都,家里的陳菜要拿來下面;肉末臊子除了普通的,還可以再細分;去面館,別人都是直接要三兩牛肉面,成都人喜歡這么點,一兩雞雜面,一兩素椒雜醬面,一兩甜水面。
三個碗,擺一桌子,吃面也像吃席。
無論形式和口味如何變化,對成渝兩地的人們來說,兩地地緣相近、人緣相親,本就一脈相承、情誼深厚,早餐吃面就是他們日常的一部分。
什么是江湖?江湖似是酒入豪腸的三分性情七分真摯,再加一群同氣相求的英雄。而成渝兩地的江湖,就藏在一道道重慶“江湖菜”或川菜里,更在一段段江湖故事里。
曾有外國人豪言,誓要三個月內吃遍中國美食。結果僅僅在四川,他就流連了整整一年,迷失在這“百菜百味,一菜一格”的天府之國。
川菜在發展過程中分為三大流派,即上河幫菜(蓉派川菜)、下河幫菜(渝派川菜)、小河幫菜(自內幫/鹽幫菜)。
江湖菜,則是集合了渝派川菜、鹽幫菜兩派所長,且在近30年才紅遍全國的“新派川菜”。
很多人最愛的川菜——酸菜魚,據考證就是發源于客商匯集的重慶江津。
江津是渝西地區的交通要道,沿水路可南抵貴州,陸路又有成渝鐵路相鄰,各路客商貨運十分集中。商旅往來,貿易繁榮,一派火爆。
長江穿城而過,江畔濕寒之氣逼人,跋涉往來的客商正需要辛辣逼出其寒濕,也需營養滋補其身體。于是,川渝地區傳統的辣子、酸泡菜和江中肥美的草魚就在這里相遇了。
味道,或有雅俗之別,但并無高下之分,但能讓更多的人吃得酣暢淋漓,又不失川味之筋骨,江湖菜足稱人間珍味。
在一天忙碌之后,成渝兩地夜晚的夜生活美食屬于火鍋。
麻辣火鍋,早已成為川渝地區的一張名片。外地游客無論是到重慶,還是成都,吃火鍋都是一道“必修課”。
火鍋,這道發源于重慶江邊的美食,已然成為川渝之間不分彼此的文化符號,并且在“一切皆可燙”的理念下衍生出形形色色的種類和形態,形成龐大的“表兄弟”群體,比如冒菜、麻辣燙、串串、缽缽雞、毛血旺……
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這些形似且神似的美食中,川渝兩地人民卻吃出了各自的風格。
“重慶人做火鍋,是關東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的豪邁與火爆;成都人做火鍋,則是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殘風曉月’的溫婉與細膩。”《重慶味道》作者盧郎曾這樣形容川渝兩地火鍋的差別,同是一鍋紅湯,卻燙出了川渝兩地不同的氣質和味道,或精致而多變,或傳統而豪放。
四川人將火鍋鍋底的制作玩出了花樣,比如海底撈火鍋,光是鍋底就有8種口味。而在重慶,不管潮流如何變化,人們最看重的還是傳統牛油火鍋。

除了傳統的牛油麻辣火鍋,在川渝兩地,還有一種美食被稱為“一個人的火鍋”。
在四川,它的名字叫“冒菜”;在重慶,它被稱為“毛血旺”。它們和火鍋的區別是由店家將各類菜品煮熟后端上桌,不用食客自己動手。
如果說冒菜和毛血旺是“一個人的火鍋”,那么“串串”就可以被稱為“穿著竹簽燙的火鍋”。
重慶的串串,通常是指“火鍋串串”,它和火鍋的最大區別在于將食材穿在竹簽上煮。在盧郎看來,重慶的火鍋串串和火鍋的區別并不大,更多是借助了竹簽的形式。這樣一來,不僅可以吃更多樣的菜品,還避免了浪費。
四川的串串,除了火鍋串串,還有更多的含義。比如成都冒椒火辣店的“冷鍋串串”,按照老板李菲比的說法,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成都“手提串串”的延續。那時候,商販騎著二八式自行車,車后座架著一口小鍋和蜂窩煤爐子,走街串巷賣串串。為了方便食客拿取,就為食物穿上了竹簽。
盡管一鍋紅湯吃出了各自的風格,但這些不同并不能斷開成渝兩地飲食文化存在的“血緣”關系,自古川渝是一家。在未來,兩地也將攜手在更廣闊的天地闖蕩。
(摘編自《四川日報》、《重慶日報》、封面新聞等)